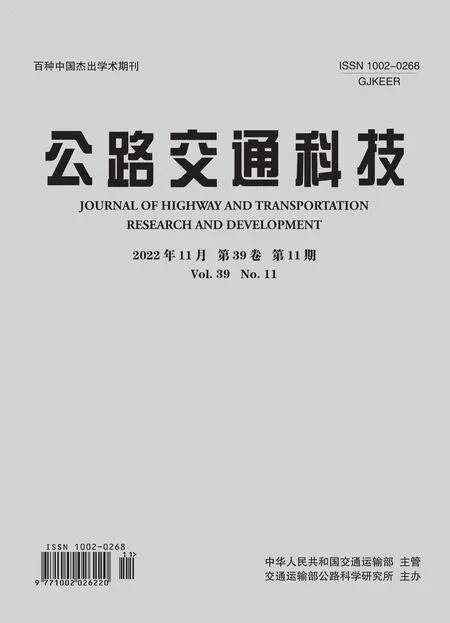剛構橋梁墩梁結合部的拓撲優化及拉壓桿模型
余茂峰,楊 屾,李 闖,戴少東,賀志啟
(1.浙江數智交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杭州 310030; 2.東南大學 土木工程學院,江蘇 南京 211189)
0 引言
整體長聯剛構體系橋梁通過墩梁固結傳遞荷載(見圖1),具有整體剛度好、行車舒適、后期維護少等諸多優點[1]。目前世界上最長的整體長聯高架橋是2017年建成的比利時A11高速公路K032高架橋[2],該650 m長聯由23孔構成,橋墩和主梁之間采用完全剛性連接。在國內,廣州地鐵12號線、鄭州市四環線、浙江杭紹甬高速公路上虞1號高架橋等橋梁采用跨度為30~46 m的多跨長聯連續剛構體系,以達到減少支座維護、降低運維成本的預期。

圖1 整體長聯剛構體系橋梁的基本布置Fig.1 General layout of integral long rigid-frame system bridge
在整體長聯剛構體系橋梁中,墩梁結合部是關鍵的連接構造和受力部位。墩梁結合部可視為T形節點,承受以彎矩為主的彎、剪耦合作用,是典型的應力擾動區[3]。我國2018版《公路鋼筋混凝土及預應力混凝土橋涵設計規范》(JTG 3362—2018)[4](下稱公路橋規)中推薦采用拉壓桿模型等方法進行應力擾動區的設計。拉壓桿模型是從混凝土結構連續體內抽象出的一種簡化力流分析模型,由壓桿、拉桿和節點組成,用以反映結構內部的傳力路徑[5]。針對拉壓桿模型合理構形的問題,常用的方法有荷載路徑法、應力跡線法、拓撲優化法等[6-7],但迄今仍沒有普適性的簡明方法。國內外學者針對建筑框架結構的L形和十字形梁柱節點,開展了基于軟化拉壓桿模型的節點抗剪承載力計算方法研究[8-11],以及基于拓撲優化的節點區域拉壓桿模型構形研究[12]。美國加州大學Sritharan[13]針對蓋梁與橋墩的連接節點,開展了基于拉壓桿模型的節點抗震性能評估研究。由于剛構體系墩梁結合部T形節點的受力工況和傳力機理復雜,目前尚缺少合適的拉壓桿模型構形方法。
本研究基于拓撲優化分析方法,研究了典型工況下墩梁結合部T形節點的彎矩和剪力傳遞路徑,并構建了相應的拉壓桿模型,可直接用于結合部的配筋設計。
1 墩梁結合部的內力分析
多跨長聯剛構體系橋梁結構承受的主要荷載作用可以分為兩類[14]:一是溫度、制動力等引起的水平力作用;二是恒載、汽車活載等引起的豎向力作用。為掌握墩梁結合部的內力情況,將多跨長聯橋梁結構簡化為圖2所示的框架結構進行分析。在梁端水平力和跨中豎向力工況下,剛構體系的彎矩分布可以利用力法進行求解。節點區域的彎矩分配取決于主梁與橋墩的線剛度比β:

圖2 典型工況下剛構體系的彎矩分布Fig.2 Distribution of bending moments in rigid-frame system under typical working conditions
(1)
式中,ib,ic分別為一跨主梁及橋墩的線剛度;Ib,Ic分別為主梁截面慣性矩及橋墩截面順橋向慣性矩;L,H分別為主梁跨徑及橋墩高度;Ec為混凝土彈性模量。
在梁端水平力Fh作用下,墩梁結合部兩側作用的梁端彎矩大小相等、方向相同(這里定義彎矩以逆時針為正),柱端彎矩值是梁端彎矩值的2倍,可以表達為:
(2)
Mc=-2Mb,L,
(3)
式中,Mb,L,Mb,R分別為節點左側和右側梁體的彎矩;Mc為節點的柱端彎矩;彎矩以逆時針為正。
在跨中豎向力Fv作用下,墩梁結合部兩側作用的梁體彎矩方向相反(彎矩以逆時針為正),可以表達為:
(4)
(5)
(6)
根據式(4)~式(6),可以定義節點梁體右端與左端所承受彎矩大小的比值α為:
(7)
由此可見:跨中豎向力工況下,墩梁結合部右端梁體彎矩是左端的2倍以上。以浙江杭紹甬高速公路上虞1號高架橋為例,該橋采用7×30 m整體長聯剛構體系,主梁為14片30 m標準跨徑T梁,橋墩高度為20 m左右,采用雙肢薄壁墩。經計算,主梁與橋墩線剛度比β取值約為5,則式(7)中的α取值約為2.3。
墩梁結合部的剪力和軸力等內力情況,亦可通過結構力學方法確定,在此不再贅述。
2 墩梁結合部的拓撲優化分析
2.1 拓撲優化的原理及二次開發
拉壓桿模型的自動生成問題可轉化為連續體的拓撲優化問題。結構漸進拓撲優化(ESO)的原理[15-16]為:不斷地從連續體中剔除應變能密度低的單元,實現結構總體剛度的極大化,即結構應變能的最小化,優化的目標函數為:
Minimize:∑CjWj,
(8)
式中,Cj為結構中單元j的應變能;Wj為單元j的重量。
通過定義結構性能指標PI,則優化目標是使PI取得極大值,即:
(9)
式中,C0,W0分別為初始狀態結構的應變能和重量;Ci,Wi分別為經過i次優化后結構的應變能和質量;下標中的“0”表示初始狀態;“i”表示經過第i次優化后的狀態。
本研究通過對通用有限元程序ANSYS進行二次開發,實現了結構漸進拓撲優化功能,可實現拉壓桿模型的自動生成[17-18]。該程序的基本流程為(見圖3):不斷地剔除低應變能密度的單元,直至有限元模型的連續性遭到破壞而不能運算為止,性能指標PI取得最大值時對應的拓撲構形即為最優構形。

圖3 拓撲優化分析的流程Fig.3 Flowchart of topology optimization analysis
2.2 結合部彎矩傳遞的拓撲優化分析
在水平力工況下,墩梁結合部兩側作用的梁端彎矩大小相等、方向相同,柱端彎矩值是梁端彎矩值的2倍。這里利用本研究編制的程序進行墩梁結合部的拓撲優化分析。圖4顯示了結合部在此邊界力情形下的漸進演化過程。當演進至第60步時,性能指標PI達到最大值1.79,此時對應的最優拓撲構形為X形。在豎向力工況下,墩梁結合部兩側作用的梁端彎矩方向相反,且右端彎矩值是左端的α倍(前述上虞1號高架橋,α取值為2.3)。圖5顯示了結合部在此邊界力情形下的漸進演化過程。當演進至第55步時,性能指標PI達到最大值2.0,此時對應的最優拓撲構形為“△”形。

圖4 水平力工況下墩梁結合部彎矩傳遞的拓撲優化分析Fig.4 Topology optimization analysis of pier-girder joint bending moment transfer under horizontal force working condition

圖5 豎向力工況下墩梁結合部彎矩傳遞的拓撲優化分析Fig.5 Topology optimization analysis of pier-girder joint bending moment transfer under vertical force working condition
2.3 結合部剪力傳遞的拓撲優化分析
在梁端水平力Fh作用下,結合部左側梁體的軸力為Fh、右側梁體的軸力為0.5Fh,則傳遞至橋墩的水平剪力為0.5Fh。圖6給出了結合部在此邊界力情形下的漸進演化過程。當演進至第45步時,性能指標PI達到最大值2.1,此時對應的最優拓撲構形為“X”形。

圖6 水平力工況下墩梁結合部水平剪力傳遞的拓撲優化分析Fig.6 Topology optimization analysis of pier-girder joint horizontal shear transfer under horizontal force working condition
在跨中豎向力Fv作用下,結合部右端的豎向剪力為Vb,R= 0.5Fv,左端的豎向剪力vb,L為:
(10)
式中λ為剪力比例系數。
以浙江杭紹甬高速公路上虞1號高架橋為例,主梁與橋墩的線剛度比β約為5,則Vb,L= 0.085Fv。圖7給出了結合部在此邊界力情形下的漸進演化過程。當演進至第42步時,性能指標PI達到最大值1.33,此時對應的最優拓撲構形為魚腹形。

圖7 豎向力工況下墩梁結合部豎向剪力傳遞的拓撲優化分析Fig.7 Topology optimization analysis of pier-girder joint vertical shear transfer under vertical force working condition
3 墩梁結合部的拉壓桿模型
3.1 4種典型工況下的拉壓桿模型
拓撲優化分析的結果可以作為拉壓桿模型構形的直接依據[15]。表1給出了4種典型工況下墩梁結合部的拉壓桿模型及拉桿內力計算公式,再結合公路橋規中對拉桿承載力的計算規定[4],可直接用于結合部的配筋設計。參考公路橋規的規定,拉壓桿模型的內力臂z可取為0.9h0(h0為梁體或墩柱截面的有效高度)。

表1 典型工況下墩梁結合部的拉壓桿模型及拉桿內力計算公式Tab.1 Strut-and-tie models for pier-girder joints and calculation formula of internal force of tie under typical working conditions
根據表1中的拉壓桿模型,可以清晰地得出墩梁結合部的傳力路徑及關鍵受力效應:
(1)在水平力工況下,結合部通過“X”形交叉的斜拉桿和斜壓桿傳遞兩側梁部的同向彎矩,一側梁頂至另一側梁底的連續配筋是傳力的關鍵構造。
(2)在豎向力工況下,結合部通過“△”形交叉的斜拉桿和斜壓桿傳遞兩側梁部的反向彎矩,將橋墩受拉側鋼筋內彎伸入結合部頂部是傳力的關鍵構造。
(3)在水平力工況下,水平剪力通過交叉桁架傳遞至橋墩,將橋墩受拉側鋼筋豎直伸入結合部是傳力的關鍵構造。
(4)在豎向力工況下,豎向剪力通過斜壓桿進行傳遞,將梁頂的鋼筋下彎,對控制斜向受剪裂縫的開展有利。
我國新版《公路鋼筋混凝土及預應力混凝土橋涵設計規范》(JTG 3362—2018)[4]中給出了拉壓桿模型構形的基本準則和方法,包括拓撲優化法、應力跡線法、力流線法等。但是,針對墩頂結合部這一具體構造和受力情形,規范中并沒有給出具體的拉壓桿模型構形。本研究遵循了規范中建議的拓撲優化分析方法,給出了墩梁結合部的拉壓桿模型,是對規范的有益補充。
利用表1計算得到拉桿內力后,可根據公路橋規按下式進行相應的配筋計算:
fsdAst+fpdAps≥γ0Td,
(11)
式中,γ0為橋梁結構重要性系數;Td為拉桿內力設計值;fsd為普通鋼筋抗拉強度設計值;Ast為充當拉桿的普通鋼筋面積;fpd為預應力鋼筋抗拉強度設計值;Aps為充當拉桿的預應力鋼筋面積。
3.2 復合受力下的拉壓桿模型
墩梁結合部往往受到彎矩、剪力和軸力的復合作用,受力十分復雜。基于前述的單工況分析結果,圖8給出了復合受力情形下的拉壓桿模型構形示意圖,可供設計參考。根據Schlaich等[5]的建議,也可偏于簡化和保守考慮,按各單個工況分別進行配筋設計并疊加。

圖8 彎矩剪力軸力共同作用情形下的拉壓桿模型Fig.8 Strut-and-tie model under combined action of bending moment, shear force and axial force
4 結論
本研究基于拓撲優化方法和拉壓桿模型方法,研究了典型工況下墩梁結合部T形節點的彎矩和剪力傳遞路徑,主要結論有:
(1)基于結構漸進拓撲優化分析,可以清晰地得到墩梁結合部T形節點在典型工況下的最優拓撲構形和傳力路徑。
(2)在水平力工況下,結合部通過X形交叉的拉桿和壓桿傳遞梁部兩側的同向彎矩,通過交叉桁架傳遞水平剪力;在豎向力工況下,結合部通過Δ形交叉的拉桿和壓桿傳遞梁部兩側的反向彎矩,通過斜壓桿傳遞豎向剪力。
(3)構建了4種典型受力情形下墩梁結合部的拉壓桿模型,并給出了拉桿內力計算公式,可供配筋設計參考。
(4)本研究將墩梁結合部看作平面問題進行分析,有一定的近似性。實際上,上部結構往往由多片梁構成,上部結構荷載通過墩梁結合部傳遞至蓋梁再傳遞至橋墩,具有一定的空間傳力特征,值得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