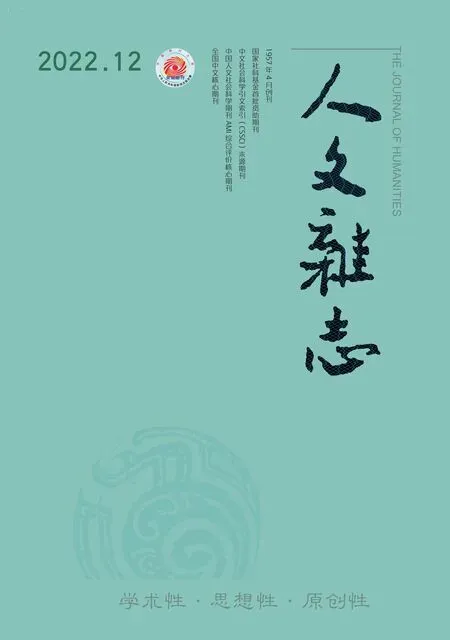從“圣王”到“素王”:公羊學視域下的德性政治*
王文軍
內容提要 “素王”問題導源于孔子有德無位的生存處境和儒家“德位合一”思想信仰之間的理論張力。在公羊學中,它內嵌于“素王改制”的義理結構,以獨特的政治思考傳達出強烈的道德意識;在德性政治脈絡下,它則凸顯出儒家關于“德位合一”這一理想政教的思想路徑與價值訴求。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素王”可以成為我們理解春秋公羊學乃至整個儒家政治哲學的關鍵樞紐。
儒家政治傳統包含非常豐富的內容。然而,如果我們可以簡約化地將其概括為一種德性政治,(1)作為一個融攝性概念,德性政治一詞包含非常豐富的內容,但其核心旨趣主要還是指向政治生活中的道德優先性。而就本文論述的重點來看,這一優先性不僅體現在對理想政治的詮釋與建構,也同樣體現在對現實政治的批判與反省。那么,從思想旨趣出發,這一傳統或許還可以被稱為“圣王政治”。實際上,在儒家學說中,“圣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簡單來看,所謂“圣”與“王”,實際上就是“德”與“位”,而理想的政治狀態當然就是“圣王合一”(德位合一)。然而,問題的復雜性就在于:一方面,“圣王合一”是儒家根本性的思想信仰;另一方面,這一信仰卻在儒家學說建立的開端處即遭遇困境,那就是作為圣人的孔子有德卻無位。由此,對孔子身位的安頓實際上就成為儒家“圣王合一”論所要解決的首要難題。而就“素王”來看,這一理論主要出現于春秋公羊學,在公羊學的傳統中,它由于和“改制”理論嵌套在一起,因此有著結構性的內涵和義理。但是,如果我們從儒家德性政治的大脈絡來看,“素王”之說實際上仍導源于孔子的有德無位,仍是對孔子身位的一種安頓,因而也就同樣寄托著儒家對“圣王合一”這一思想信仰的訴求,就此而言,“素王”實際上與“圣王”分享著共同的理論前提。正是在這一前提下,本文嘗試結合二者,希望可以在厘清公羊學“素王”理論的同時,對其在儒家德性政治上的價值形成更加深入的理解。
就當前學界來看,對“素王”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向:其一,從思想史層面考察“素王”觀念的形成、流變及其現實意義,如王光松《漢初“孔子素王”論考》(《廣東教育學院學報》2008年第2期),孫鳴晨《“素王”內涵流變考》(《文藝評論》2017年第2期)。其二,在公羊學“素王改制”框架內探究“素王”之說的基本內涵及其蘊含的思想意圖,如曾亦《〈春秋〉“素王”考論》[《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4期],朱雷《“孔子為王”與今文學的王者批判》(《哲學動態》2019年第6期)。其三,對經學家(尤其晚清)有關“素王”的經說作義理層面的梳理和解讀,如黃開國《宋翔鳳的孔子素王說》(《衡水學院學報》2016年第3期),李長春《“素王”與“受命”——廖平對今文經學“受命”說的改造與發展》(《求是學刊》2011年第2期),郜喆《“素王改制”與〈五經異義〉——廖平“平分今古”的兩個基礎及其關系》(《人文雜志》2020年第12期)等。總的來看,現有的研究涵蓋了“素王”問題的基本面向,也較為充分地打開了這一問題的豐富性。然而,如前文所言,“素王”理論在根源處關聯于由孔子身位所折射出的“圣王”問題,特別是這一問題不僅在公羊學的義理中呈現出一種道德意味,而且頗為根本地凸顯出儒家德性政治的核心主題和價值訴求。
一、儒學史中的“圣王”問題
縱觀整個儒學史,孔子的身位問題一直在歷代儒者的視域中處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從子思言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到孟子以孔子《春秋》為“天子之事”,從董仲舒尊孔子為受命素王到二程、朱熹置孔子于道統譜系,這是一場關于孔子“圣”與“王”的持久爭論。從表面上看,這場爭論體現的或許僅僅是孔子生命際遇的尷尬以及后世儒者對其不同的理解。但實際上,它在某種程度上頗能凸顯儒家政治哲學的內在理路。從儒家的視野來看上古文明史,(2)之所以言儒家的視野,是因為對于上古文明史的真實狀況我們已經很難得知,可以獲取其信息的核心資料是被后世稱為六經的文本。因此,所謂上古史,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乃是來自儒家的詮釋或建構,而其主要目的則是傳達自身的思想義理與價值訴求。在孔子之前的三代甚至更早,“圣”與“王”在文明史的演進中一直是合一的,從上古堯舜禹的“禪讓”,到夏商周三代的“革命”,王者得位的方式雖然不同,但它背后的邏輯卻是統一的,那就是“大德必得其位”(《中庸》),這可以用“圣必王”來概括。然而,到了孔子這里,其作為至德圣人卻無王者之位,這樣一種局面使得“圣必王”的邏輯鏈條第一次出現斷裂,由此“圣”與“王”之間的理論張力開始形成。
接受“圣王不一”這樣的觀點看上去影響似乎不大,但將其在事實層面接受和在思想層面接受卻存在著很大差別。如果僅僅在事實層面接受,那么它只表明了一種個人際遇的尷尬或無奈,在理論設想或價值訴求上仍然有可能為“圣王合一”保留可欲的空間。但如果在思想層面接受這樣的觀點,則會產生非常大的危險:在儒家的信仰中,“位”是與“天”聯系在一起的,王者之位乃是天所授予(“天命”),而此聯系的中間環節就是“德”——只有具有了德,天才會賦予其位。但如果“德”與“位”不再具有必然關系,那么“位”與“天”就會發生斷裂,從而“位”也就失去其神圣性而成為某種隨機事件。如此,非但政治的正當性難以得到解釋,其形而上的基礎“天”也會隨之坍塌,而后者正是儒家學說的理論根基。因此,對孔子有德無位及其引發的“圣王不一”問題的解釋實際上是儒家政治哲學的根脈性內容,它不僅關乎孔子個人的身份定位,而且關乎儒家對理想政教的闡發與建構。
“圣王合一”的觀念雖然來自儒家的理論建構,但其根源卻是夏商周乃至更早的政治文化傳統,尤其是周人滅商的政治實踐,使得“德”作為一個重要的概念被引入天人關系之中。周人在總結自己獲得天下的原因時將其歸結為“德”,這樣,自周朝伊始就形成了一種“敬德”的觀念,特別是經過周公的政治陶鑄,這一觀念成為周朝平治天下的核心價值:一方面,周公在攝政、平亂、制禮作樂的過程中所呈現出的“圣德”,使其成為德位合一的人格典范,并被不斷稱頌;(3)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周公德業盛大,后世儒學史還形成了周公是否“攝政稱王”的問題。劉豐在考察了戰國至漢的諸多文獻后認為,從戰國到漢代的儒家普遍肯定周公攝政稱王之事,并強調“周公攝政稱王并不是一個歷史問題,而是一個哲學問題。……因為這是儒家素王說或王魯說的理論前提。”(劉豐:《周公“攝政稱王”及其與儒家政治哲學的幾個問題》,《人文雜志》2008年第4期)這一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本文的論述。實際上,先秦至漢的儒家之所以肯定周公攝政稱王,正是由于對周公圣德的肯定,而其背后所秉承的恰恰是對周人開創的“德位”觀念的繼承,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周公成為公羊學家孔子素王說的“理論模板”。另一方面,周公在施政過程中通過對“德”的不斷強調,還形成了一種德性天命觀,其最精煉的表達就是《尚書·蔡仲之命》所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4)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十三經注疏》卷1,臺灣藝文印書館,2013年,第254頁。經過周代禮樂制度的陶冶積淀,這種天命觀逐漸發展成為一種根本性的政治信念,并最終以集大成的方式呈現于孔子。作為周代禮樂的傳承者,孔子對“德”無疑具有某種天命式的自覺與自期,這在他充滿自信的話語中有所體現,如“天生德與予,桓魋其奈我何?”(《論語·述而》)“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論語·子罕》)等。此后,正是基于這種思想信仰的維度,儒家對上古政教進行了一種道德本位的建構與擴充,從而形成了精深的政治哲理。從整個儒學史來看,儒學在發展過程中雖然經歷了許多變化,產生了不同的流派,形成了不同的理論旨趣,但從廣義上來說,“圣王合一”或“德位合一”始終是儒家的終極追求。針對這一追求,歷代儒者通過不斷回溯源頭,從孔子乃至上古三代的文明遺產中汲取精神養分,進而形成了以“王道”“仁政”“教化”等價值為核心的德性政治理論。而從傳統政教的演變來看,儒家的德性政治雖然不是傳統政教的全部,但作為政治價值的核心內容,無論是朝廷的施行還是民間的普及,都構成了歷代政治實踐的主流,并不斷塑造其精神氣質,最終形成了獨具中華特色的德性政治文明。
由此可見,孔子身位問題及其寄托的“德位合一”思想信仰實為理解儒家政治哲學的一條關鍵線索。在儒學史中,針對這一問題,不同時代的儒者都作出過不同的解讀,并形成了豐富而深刻的思想。如孟子從“天—命”的角度為孔子的“無位”辯護:“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孟子·萬章上》)進而通過“天爵”與“人爵”的劃分凸顯出“德”對于“位”的優先性:“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孟子·告子上》)又比如荀子通過對“國”與“天下”進行層級劃分來化解圣人無位的尷尬,從而強調圣人之治與普通君王之治在境界上的區別:“國,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國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王也;天下者,至大也,非圣人莫之能有也。”(《荀子·正論》)當然,還有宋儒建構獨立于政統的道統譜系,并主張以后者影響前者,如朱子云:“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5)朱杰人等編:《朱子語類》卷108,《朱子全書》卷17,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511頁。就是希望通過圣人相傳的道統心法“致君堯舜”,從而達成“圣王合一”的政教理想。而就本文所要論述的內容——“素王”來看,未始不可置于這一脈絡之下審視。
二、公羊學“素王”說的形成
“素王”是春秋公羊學對孔子的一種稱謂,成說于漢代。所謂素者,空也,意謂孔子有王者之德,卻無王者之位,故尊其為素王。不過,就“素王”一詞來看,其或許有更早的來源。《莊子·天道》云:“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圣素王之道也。”(6)王叔岷:《莊子校詮》,中華書局,2007年,第469~470頁。這應該是傳世文獻中“素王”的最早出處,盡管這里描述的“素王”更加接近道家清靜無為的旨趣。另一較早提及“素王”的是《史記·殷本紀》:“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7)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2014年,第122頁。1973年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老子》甲本似乎佐證了司馬遷的這一記錄,在該本卷后所載的古軼書中,有一篇關于商湯與伊尹的對話(編者名其為《九主》):“后曰:‘□□九主之圖,所胃(謂)守備搗具、外內無寇者,此之胃(謂)也。’后環擇吾見素,乃□三公以為葆守,藏之重屋。臣主始不相吾(忤)也。”(8)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編:《馬王堆漢墓帛書》卷1,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31頁。葛志毅認為這里的“素”字后當缺一“王”字,并認為“素王”之本意“似乃草昧初開,質樸無文時代的上古帝王,其性質應與氏族部落時代的酋長相當。”(9)葛志毅:《玄圣素王考》,《求是學刊》1992年第1期。這一觀點正確與否暫且不論,從《史記》和《九主》的對勘來看,司馬遷所言其來有自,“素王”一詞應當有更早的來源。此外,《鹖冠子·王鈇》云:“此素皇內帝之法。”(10)黃懷信:《鹖冠子校注》,中華書局,2014年,第205頁。這里提到的“素皇”,學人也多與《莊子·天道》聯系起來理解。關于伊尹的思想,從留存的材料來看,多合于道、法二家;《莊子·天道》篇雖有偽作之爭議,但其要多合于黃老;(11)對于《天道》篇,后世學者多以其為偽作,如王夫之就認為“此篇之說,有與莊子之旨迥不相同侔者,特因老子守靜之言而演之,亦未盡合于老子;蓋秦漢間學黃老之術以干人主者之所作也。”參見王夫之:《莊子解》,《船山全書》卷13,岳麓書社,2011年,第236頁。至于《鹖冠子》,學界也一般認定其為戰國黃老一派的作品。由此可見,“素王”一詞來源甚早,或可上溯至殷商,其后戰國黃老道家多用之,內涵亦多合于斯旨。司馬貞《索隱》云:“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質素,故稱素王。”(12)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2014年,第123頁。此解近是。
到了漢代,“素王”一詞開始進入儒家的視域。漢代最早言及“素王”的應該是賈誼,在《過秦論》中,賈誼說道:“諸侯起于匹夫,以利會,非有素王之行也。”(13)閻振益、鐘夏:《新書校注》,中華書局,2000年,第16頁。雖然很難說這里的素王就是指孔子,但從“利”的角度來區分諸侯與素王,這和《莊子·天道》中的道家旨趣已經有明顯的不同。明確將素王與孔子對應起來的是《淮南子》和董仲舒的《舉賢良對策》。《淮南子·主術訓》云:“孔子之通,智過于萇弘,勇服于孟賁,足躡郊兔,力招城關,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弒君三十六,采善鋤丑,以成王道,論亦博矣。”(14)劉文典:《淮南鴻烈集釋》,中華書局,2013年,第375頁。這里明確將素王指向孔子,并且和《春秋》聯系到了一起。《舉賢良對策》亦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萬事,見素王之文焉。……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15)王先謙:《漢書補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035~4036頁。這已經是典型公羊學式的“素王”之說了。王光松通過對《過秦論》《主術訓》和《舉賢良對策》的比較,認為“在賈誼同時或之前的漢初《春秋》學研習中,‘素王’一詞在儒道兼習的時風中實現了由道入儒的過渡,但該詞彼時既未專指孔子,也未被寄予深意。《主術訓》作者受孟子的影響與啟發,將其‘《春秋》,天子之事’的論述與賈誼式‘素王’論相結合,‘素王’遂由泛指而專指孔子,到董仲舒在改制更化的問題意識下用受命論貫通此種素王說,后世通論意義上的孔子素王論始得以成型。”(16)王光松:《在“德”、“位”之間》,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66頁。大體而言,這一勾勒是準確的,不過,董仲舒“孔子素王”之說是否來自《淮南子》或許值得商榷。蓋孟子以“天子之事”言《春秋》自不待言,然公羊學“孔子素王”之說雖成型于董仲舒,但這種觀念卻不一定沒有更早的來源。實際上,《公羊傳》雖然在漢代才成書,但在此之前已有口說傳承,《淮南子》雜采諸家之說,其中亦不乏公羊學的理論,故在“素王”在這一點上,很難說《淮南子》沒有受董仲舒之前的公羊學影響。至于賈誼,其學多受《榖梁》影響(賈誼《新書》四引《榖梁》之說),而后者與公羊學都屬于《春秋》的釋經傳統,這在一定程度上或許也能佐證董仲舒的“孔子素王”之說有其自身的脈絡。
事實上,促成董仲舒“孔子素王”之說的關鍵正是《春秋》中的“西狩獲麟”這一事件,更準確地說,是《春秋公羊傳》對這一事件的描述:“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 ,孔子曰:‘吾道窮矣。’”(17)何休注,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十三經注疏》卷7,臺灣藝文印書館,2013年,第355~357頁。誠然,麟為仁獸,其出現是一種嘉瑞,意味著時有圣王,但從《公羊傳》中孔子的悲嘆來看,“西狩獲麟”這一事件并沒有被視為嘉瑞——麟在亂世被狩似乎影射著孔子將歿,其道將窮。(18)皮錫瑞《春秋通論》云:“絕筆獲麟,《公羊》以為受命制作。有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之事,則是災異,并非祥瑞。”皮錫瑞:《經學通論》,中華書局,1954年,第29頁。然而,董仲舒的解讀使這一事件的基調發生了根本的反轉:“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至者,西狩獲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后托乎《春秋》正不正之間,而明改制之義。”(19)蘇輿:《春秋繁露義證》,中華書局,1992年,第157頁。在董仲舒看來,“西狩獲麟”乃是孔子的受命之符,正是通過這一事件,孔子被受命為素王,進而作《春秋》,明“改制”之義。這樣,經過董仲舒的解釋,作為《公羊傳》中不祥征兆的“西狩獲麟”就變成了孔子受命的符瑞。這實際上是董仲舒對《公羊傳》的一種創造性發揮,經過這一發揮,“西狩獲麟”這一本來具有悲情意味的事件就變成了某種神圣符號——“西狩獲麟”并非孔子“道窮”之證,反而是其受命之徵,正是有了“西狩獲麟”,孔子才得以成為素王;麟的死亡或許預示著孔子將歿,但因“獲麟”而受命的孔子卻也因此以素王身位作《春秋》,為后世立下一王大法。董仲舒這一反轉不可謂不大。
當然,董仲舒的解讀也并非無中生有,而是有其自身的合理性與深刻性。其一,就《公羊傳》對“西狩獲麟”這一事件的解釋來看,麟雖然“非其時而來”,但麟作為“有王者則至”的仁獸,確實又是一種圣王符瑞,此實為董仲舒以“西狩獲麟”為孔子“受命之符”的理論依據。(20)華喆通過對比《論語·子罕》中孔子“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的哀嘆和《公羊傳》中孔子的悲泣,認為“如果按照《論語·子罕》中孔子感嘆的情形,那就是孔子出而無瑞應,所以孔子到底有沒有‘素王’的身份仍需證明。《公羊傳》顯然更進了一層,在孔子進入暮年之時終于有麒麟出現,這就更加能印證孔子是有其德而無其位,所以孔子的悲泣就變成了晚年自知其命而志不得伸的愁苦憤懣。” 參見華喆:《禮是鄭學——漢唐間經典詮釋變遷史論稿》,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第156頁。從這個角度來看,董仲舒對“西狩獲麟”的獨特解釋可以說推進了《公羊傳》的“未盡之意”。其二,孔子通過《春秋》褒貶諸侯,行“天子之事”(《孟子》),但其畢竟無王者之位,這其中確實存在僭越之嫌。因此,“通過賦予孔子以受命之王的身份,這就解決了《春秋》學中自孟子開始的一個老大難問題,即孔子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之行為的正當性問題。”(21)王光松:《在“德”、“位”之間》,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71頁。其三,當孔子以一種符瑞的方式受命為素王,則其王者身位在某種程度上就得到了天的認可或賦予,由此,孔子有德無位的遭遇實際上就變成了上天為成就其素王功業所作的一種安排,從而被視為某種缺憾的“無位”也反過來成為孔子神圣偉大的最佳注腳。更為重要的是,在這一維度下,非但孔子的身位得到了較好的安頓,儒家“圣王合一”的理論裂痕也得以彌合。因此,以“西狩獲麟”為孔子“受命之符”雖為董仲舒之創造,但它確實把握到了“西狩獲麟”這一事件中的某種微妙意蘊,在理論上也頗契合《公羊傳》中的孔子形象,因而能被后世公羊學家接受,成為公羊學中的“素王受命”學說。(22)當然,不可否認的是,“素王受命”學說在推動《公羊》學義理發展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讖緯之學神化孔子之風,并由此產生了許多荒誕不羈的理論,也使儒學沾染上神秘主義的色彩。
三、“素王”理論的德性意蘊
通過上文辨析可以看到,董仲舒將孔子塑造為受命素王實際上有著微妙而深刻的思想意義。不過,從義理角度來看,此說雖成于漢代,但卻有著更早的源頭,如孟子言孔子《春秋》為“天子之事”就可以視為一個重要的來源。然而,此說既然來自公羊學,那么其自身的義理源頭自然不可忽視。從《公羊傳》來看,隱公十四年的《傳》文對“西狩獲麟”事件中孔子的哀嘆做出了詳細描述,孔子哀嘆的真正意圖我們難以得知,或者如其所言是“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論語·衛靈公》)。然而,在《傳》文的末尾提到這樣一句:“制《春秋》之義以俟后圣,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23)何休注,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十三經注疏》卷7,臺灣藝文印書館,2013年,第359、26頁。我們知道,漢儒多言孔子“為漢制法”,漢代統治者之所以接受孔子素王的理論,與漢儒的這一說法應當不無關系——素王制法為漢代政權尋求到了某種正當性支持。不過,就其理論自身來看,《公羊傳》“制《春秋》之義以俟后圣”或許才是這一說法的真正來源。而這也就意味著,對于“素王”一說,我們真正需要重視的應該是其自身的義理空間,尤其是要考慮這種義理空間中所承載的德性意蘊。
從公羊學來看。孔子素王實際上和公羊學的另一個理論“以《春秋》當新王”緊密相關,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二者是彼此成立的,可以說是同一義理的不同表達:“如果《春秋》被公羊家視為‘新王’,那么,作《春秋》的孔子自然具有‘王’的地位”;(24)曾亦:《〈春秋〉“素王”考論》,《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4期。反過來,只有孔子為素王,他才能寓王法于《春秋》,“以《春秋》當新王”也才能成立。因此,要理解孔子素王,首先應該將其與“以《春秋》當新王”這一說法聯系起來看。更進一步,“以《春秋》當新王”背后的完整主題其實是“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這一主題在董仲舒的公羊學說中已經有所體現,如“《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絀夏、親周、故宋”,(25)蘇輿:《春秋繁露義證》,中華書局,1992年,第187~189、185頁。而在東漢公羊學家何休那里,它則以“通三統”的言說方式被系統地呈現出來。所謂通三統,簡單來說,就是新王之統建立后,保存前二代王者之統,于自身之統相通為三,具體措施表現為:“王者存二王之后,使統其正朔,使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圣,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于是可得而觀之。”(26)何休注,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十三經注疏》卷7,臺灣藝文印書館,2013年,第359、26頁。作為公羊學最重要的義理之一,“通三統”不僅僅意味著王朝政統之間的替代或循環,而是有著更加豐富的思想內涵。其一,它表示新王之統與舊二王之統的相通,從而既意味著政治統緒的承接與延續,也體現出一種師法和禮讓的政治品德,更可引申出“天下非一家所有”的政治觀,這些思想無疑讓緊張性的政統更替傳達出強烈的道德意識。(27)《白虎通·三正》云:“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后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謹敬謙讓之至也。” 陳立:《白虎通疏證》,中華書局,1994年,第366頁。以“謹敬謙讓”言“通三統”,其中的道德意識不言而喻。其二,也是更為重要的,“通三統”實際上是為了張大新王之統(此亦“大一統”之原初意味),確立后者的正當性,而其表現在具體的政治中就是“新王必改制”:“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28)蘇輿:《春秋繁露義證》,中華書局,1992年,第187~189、185頁。通過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之類的改制之舉,不但能昭示新統與舊統的區別,而且也彰顯出新王的天命所歸。由此可見,在公羊學中,“素王”一說實際上蘊含著非常豐富的義理,它不僅承載著公羊學家對孔子以及《春秋》的理解與定位,而且內嵌于一套系統的義理結構,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公羊學家關于政治非常獨特的思考。正因為如此,“素王”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成為理解春秋公羊學的一把鑰匙。
從德性政治來看。如前文所述,“德位合一”一直是儒家政治哲學的核心旨趣,而“素王”理論之所以能被漢儒提出和接受,除了現實層面的原因,其根本原因恐怕也是因為這一理論契合了儒家政治的德性底色。“素王”說的形成固然體現出公羊學自身的理論架構,但從本質上來看,它仍然是對孔子有德無位的一種安頓,而其背后的思想深意則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其一,就現實政治而言,經歷了周秦政治的演變,“先秦儒家的德位統一觀念已然讓位于君與臣格局下的主導者和輔助者之間的關系”。(29)干春松:《制度儒學》,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第12頁。不過,雖然儒者作為君主的輔助者存在,但由于承擔政治制度及其價值原則的制定與解釋,儒者在某種程度上仍具有一定的獨立性,而這種獨立性的抽象體現就是對孔子素王身位的確認。素王雖然是空王,但孔子的身份卻不僅僅是一個至德圣人,而且是現實政治的立法者;政治制度雖然由君王主導,但其原則的確立和闡釋卻來自作為立法者的素王,這無疑保證了儒家對現實政治的建構性。更為關鍵的是,這種建構性建立在一種道德本位的基礎之上,它規定政治生活的展開始終要以符合道德準則和禮樂精神為基本方向,而這也就意味著,“素王”學說會因其道德高度對現實政治展開持續的考量,進而為良好政治秩序的建立提供更多可能。其二,就思想訴求而言,儒家理想的政教狀態當然是“德位合一”或“圣王合一”,但這一訴求呈現在“素王”學說中,實際上還隱含著另外一個重要的問題意識,那就是所謂政治統治的正當性問題。一方面,在儒家看來,王者得位的正當性在于修德,其統治的正當性亦在于修德,《大學》云:“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所謂修身,即是修德。而從“素王”的理論邏輯來看,孔子之所以能稱為素王,根本原因也在于孔子之圣德。就此而言,“素王”之說的提出實際上進一步凸顯了儒家政治對于道德優先性的根本考量,它“將修身并滿足為王條件的必要性,逼迫至現實中每一個君主的身上,使任何王者都面臨自己是否有為王的資格、自己的統治是否合法等問題的挑戰”,(30)朱雷:《“孔子為王”與今文學的王者批判》,《哲學動態》2019年第6期。從而也昭示出道德作為良善政治秩序準繩這一古典政治的基本原則。另一方面,孔子以布衣修德行道,上達天命而成素王,故而作《春秋》一經、立百世大法,這其實在一定程度上還隱含一種“權威二元化”的觀念,即“不僅天子……可以承受天命,樹立政治與社會的權威中心,而且任何人憑著人格的道德轉化,也可以直接‘知天’、‘事天’,樹立一個獨立于天子和社會秩序的內在權威。”(31)張灝:《幽暗意識與時代探索》,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9頁。從這個角度來看,“素王”理論不僅對現實政治提出了強有力的質問與反思,而且在一定意義上開啟了儒家政治實踐的一種新模式,即所謂“圣人立法”,這一模式和三代以上的“圣王一體”以及唐宋時期的“圣人道統”互為呼應,共同構成了儒家關于理想政教的路徑化表達。
由此可見,“素王”理論有著廣闊的義理空間,其中蘊含著濃厚的德性意蘊,此說雖然來自公羊學家的理論建構,但無論是從公羊學義理還是從儒家德性政治旨趣來看,它都有相當程度的理論自洽性。“素王”承載著公羊學高標的政治智慧,呈現出強力的建構性與批判性;傳達著儒家政治哲學的價值訴求,因而也反映出儒家德性政治的思想底色。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素王”可以成為理解春秋公羊學乃至整個儒家政治哲學的關鍵樞紐。
四、結語
的確,無論從公羊學還是儒家德性政治來看,“素王”之說都含納了豐富的思想義理。不過,作為言說主體,由于它和公羊學“改制”理論嵌套在一起而有很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因此很容易被經學家用來表達個人的政治主張,從而變得面目皆非。在這一點上,晚清以降的“經學突圍”無疑提供了充分的例證。
晚清是公羊學復興的時代,面對傳統政教乃至整個華夏文明的危機,許多今文經學家倡言“素王”,試圖從這一理論中找尋醫治危機之方。如廖平以《王制》為管鑰,重新判攝經學,將整個六經都解釋為“素王之制”,從而將孔子塑造為真正意義上的文明立法者。(32)王文軍:《從〈春秋〉到六經:廖平的“素王”新說——以前二變為中心》,《哲學門》第39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91~110頁。又如康有為借助“素王”話語,吸收西方理論資源,將孔子改造為不但是改制的“制法之王”,而且是創教的“大地教主”。(33)康有為:《孔子改制考》,中華書局,2012年,第200頁。雖然我們可以理解這些學人借助“素王”之說表達思想主張、安置傳統政教的良苦用心,但客觀地講,這些新的詮釋也使“素王”的原初意義被拉伸、放大,甚至產生了某種扭曲,由此不但“素王”的本來面貌變得模糊不清,而且也對孔子的形象乃至傳統經學造成了一定傷害。而且,晚清今文經學家對“素王”的理論闡發雖然極大地擴展了公羊學“素王改制”這一思想議題,但“素王”的另外一個面向卻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那就是其蘊含的對理想政教的深層訴求。從儒家政治哲學的內在旨趣來看,“德位合一”始終是歷代儒者對完美政治狀態的一種表達,而“素王”理論的提出實際上也蘊含著這一旨趣,孔子雖然沒有現實的王位,但依其圣德當居王者之位,故被稱為素王。在歷代儒家的政治實踐中,“素王”一說雖然因為與時王政治潛在的矛盾而難以彰顯,但“德位合一”這一內在的價值訴求卻并未因此中斷,無論是漢儒如董仲舒所言“見素王之文”,還是宋儒如程頤所言“格君心之非”,所表達的其實都是這一訴求。就此而言,對“素王”的論說或許還是不應脫離儒家德性政治這一根本主題。
晚清以降,由于反傳統的時代語境,孔子乃至儒家一直被看作封建專制的伴生物,由此“素王”所傳達的深層意義就被完全遮蔽,但就這一理論所表達的價值訴求來看,與其說它是封建專制的伴生物,毋寧說其站在了封建專制的對立面。在這個意義上,本文所作的工作更像是一種“澄清”,然而,這種“澄清”并不意味著要重新追認孔子的素王身位或者給孔子貼上王者的標簽。“素王”是為解決孔子有德無位問題形成的理論,此說或許并非孔子本意,也非歷史真實,但它的哲學意義卻大于歷史意義,因為這一理論的真正重要之處并不在于解釋“素王受命”事件本身的真假,也不在于是否還原了真實的孔子,而在于透過“素王”這樣一個命題去重新思考儒家德性政治所能呈現的現實價值,特別是在經歷了“現代性”的洗禮,當代世界普遍反思西方政治弊端時,“素王”維度下的孔子及其融攝的儒家政治哲學或許能帶給我們一些新的啟發:第一,借助“素王”理論,我們可以重新理解儒學中作為立法者的孔子形象,從而為孔子的現代安頓提供更為豐富的可能。“在儒家看來,精神的領袖始終只能是孔子,即便君王、朝代發生了改變和更迭,……但是精神的領袖就只能是孔子。所以,孔子擁有一個特殊的地位。在某種程度上,他有超越于某一個王朝皇帝的地位。”(34)干春松:《制度儒學》,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第439頁。而在君主制度已然成為陳跡的時代,“王”不必再追尋,但“孔子的尺度”或許不應該就此消失。第二,通過對“素王”的重新理解,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幫助我們回到傳統經學,尤其是公羊學的內在理路,通過進一步挖掘“素王”話語中所蘊含的如“王者改制”“通三統”等理論,從而在一定意義上為當今政治哲學研究提供來自華夏文明的思想資源。當然,“在現代社會,任何經學大義都必須在現代歷史學研究面向說明自己的合理性。”(35)傅正:《古今之變:蜀學今文學與近代革命》,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12頁。因此,“素王”理論的當代詮釋恐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第三,在公羊學“改制”的面向之外,還要看到“素王”理論所蘊含的道德價值對當代政治實踐在權力監督、人事導向、行為審核等更寬泛層面可能具有的意義,從而幫助我們建構更加健康合理的政治生活。而在一個神圣性已然消失的世俗時代,還需要考慮的或許是,我們在多大程度上還能尋回古典政治對高貴德性的敬仰與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