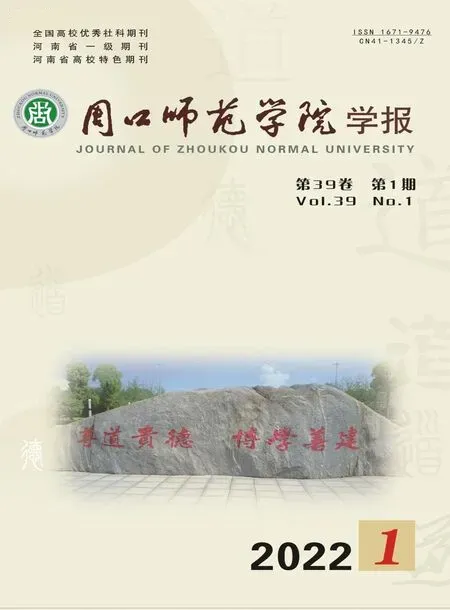張伯駒《八聲甘州·三十自壽》藝術解析
張春梅
(周口師范學院 設計學院,河南 周口 466001)
八聲甘州·三十自壽
幾興亡,無恙舊河山,殘棋一枰收。負陌頭柳色,秦關百二,悔覓封侯。前事都隨逝水,明月怯登樓。甚五陵年少,駿馬貂裘。
玉管珠弦歡罷,春來人自瘦,未減風流。問當年張緒,綠鬢可長留?更江南、落花腸斷,望連天、烽火遍中州。休惆悵、有華筵在,仗酒銷愁。
張伯駒的女婿樓宇棟在《張伯駒詞集》后記中說:“先岳丈自三十歲學為詞(一九二七年),至甲午(一九五四年)間所作,集有《叢碧詞》。”[1]381周汝昌也在該書序言中敘及:“《叢碧詞》先有木刻本,后來增訂排印。”[1]1《叢碧詞》前后出版多次,每次都是張伯駒親手敲定,開篇第一首都是《八聲甘州·三十自壽》。為什么張伯駒把它作為第一首呢?固然與該詞創作的時間較早有關,更關鍵的是這首詞奠定了整個《叢碧詞》乃至于張伯駒一生詞作的基調。《八聲甘州·三十自壽》創作于1927年,正值張伯駒30歲的生日。此時,正是張伯駒一生中最得意的時刻。他身處名士圈,有錢有勢力,可謂“春風得意馬蹄疾”。此詞創作5個月后,因張作霖去世,張學良退出了名士圈,“隨著國事日艱,以他們為中心的中國最后一個名士圈也失去了凝聚力,如風吹浮萍,在時代的大潮下,每個人按自己的人生軌跡開始新的滑行”[2]34-35。
張伯駒的人格有兩面性:一面是愛國志士,關心國家前途,心系民族蒼生;一面是怡情山水,耽于享樂的名士,優哉游哉地享受著自己優越的生活。前者為公,后者為私。這首《三十自壽》代表著張伯駒的人生價值取向。其中,強勢的是歷史,是大勢,無法由個人憑一己心意所能改變;弱勢的是詞人,是萬千眾生中的一員,其命運由歷史、大勢決定。因為勢單力薄,因為力量微小,張伯駒決定做好自己。其心態與兩年后的《蛇尾集》(1)袁克定、郭則沄、方地山、張伯駒唱和的詞作編成合集《蛇尾集》,連載于《北洋畫報》1930年1月7日到1930年3月8日,共17首。基本一致。“《蛇尾集》反映出當時一部分貴族名士面對時局江河日下,自忖擔不起天下重擔,但也不愿隨波逐流;內心既不甘沉淪,但由于特殊社會身份的拘束卻又一無可為的矛盾心態。詩酒自放,逍遙度日是表象,內心實有不可言說的悲哀。”[3]6
由此,對《八聲甘州·三十自壽》一詞的解析,需要著眼于文學傳統對詞人抒情達意的制約,以及詞人對于傳統的突破與創新,明確敘述模式在文本中的結構特點和美學作用,更應該置該詞作于彼時的情景之下,并在創作的情景中去理解作者的心理和意蘊。同時,該詞也是當代文藝美學語境中的文本,應該著意于明確它在中國美學研究中的價值。
一、韻律格式
張伯駒于1927年開始學習作詞并創作《八聲甘州·三十自壽》,該詞質量之高,已頗顯其在創作詩詞方面的天賦。在韻律格式規范方面,《八聲甘州》作為詞牌,以柳永《八聲甘州·對瀟瀟暮雨灑江天》為正體,其后有6種變體。查張伯駒此作,雙調97字,前后段各9句,四平韻,前段46字,后段51字,符合正體。但第53字“春”為平韻,不合詞譜。張伯駒學《八聲甘州》的正體,但又不嚴格依循正體。他一定知道“春”字不合詞譜,為何仍用此字?這個不合詞譜的“春”字,說明張伯駒當時的思想與固定的詞譜尚未達到完美的融合。其思想好比一頭大象,固定的詞譜好比是籠子,大象進入籠子,但鼻子還留在外面。“春”必須要寫么?張伯駒的生日是正月二十二日,這個時節還屬于隆冬,但他想到的是春天。這個“春”字蘊含著他對未來的期待。另外,《八聲甘州》這種詞牌的特點就是上闋回顧,下闋展望,上下之間有突轉。而在這首詞作中,“春”字擔負起此種突轉的責任和功用。
從音韻和情感波動的關系來看,成語云“言為心聲”,韻律的變動不僅僅與語言學、修辭學有關,還與作者的心理狀態、情感波動密切相連,也與文藝心理學有關系。這首詞在音韻上多為仄起平收,全詞8句,其中6句是仄起,8句全為平收。與之相對應的是詞人在情感上的表現——由情緒高昂起始,漸漸歸于平順,終以陰郁收尾。全詞始終糾纏于兩種情緒——正面積極情緒是詞人看到中華大地多災多難,需要有志者為之奮斗獻身,如“幾興亡、無恙舊河山,殘棋一枰收”“秦關百二”等;負面消極情緒是面對紛繁復雜的時局,個人勢單力薄,所有曾經的雄心壯志都被現實消弭于無形,如“悔覓封侯。前事都隨逝水,明月怯登樓”。整首詞在積極與消極之間幾度轉換,在高昂與陰郁之間數次折返,展現出來的是有志青年志氣不得伸張,抱負無法實現,以至于忍受生不逢時的苦悶。對此,張恩嶺做出如是評價:“詞作上片有‘秦關百二,悔覓封侯’句,表示對自己側身官場、軍隊的悔恨;下片表達了對連年軍閥混戰的憂思,對政治的厭倦,同時表示有意追求風流恬淡的人生。”[4]100
二、精神意涵
詩詞是作者心理和情緒的文學表達,由外在的韻律和內在的精神構成。其中,韻律是美麗的外衣,既賦予詩詞美麗的形式,又規范和約束作者的自由創作;精神是作者內在的活生生的思想,或是作者內在的難以言表、難以外顯的境界,即所謂“以詩言志”之“志”。內在的精神如何與外在的韻律完美契合?張伯駒的《八聲甘州·三十自壽》把時間元素當作黏合劑,整個詞作都在時間的鏈條中延伸往復。《八聲甘州》分八韻,一韻代表一個層次,八韻即八個層次。八個層次之間,層層銜接,層層遞進。
在生日的時候,人們通常想到的是時間和生命,張伯駒亦不例外。在創作這首生日詞作時,他的思緒始終在時間的隧道中來回穿梭。詞作開篇便將華夏上下五千年盡收眼底,詞云:“幾興亡、無恙舊河山,殘棋一枰收。”張伯駒在文詞上化用清代詞人納蘭性德在《滿庭芳·堠雪翻鴉》中的所寫:“須知今古事,棋枰勝負,翻覆如斯。嘆紛紛蠻觸,回首成非。剩得幾行青史,斜陽下、斷碣殘碑。年華共,混同江水,流去幾時回。”[5]188張伯駒將這首詞所表達的意思濃縮成一個“舊”字,顯示著他是在中華文明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思考中國當下的局勢,預測今后的國家局勢;“棋枰”作為核心意象,牽連著“收”字,則表明他預測國家一定會統一,也是基于一個事實,即在中華文明五千年的歷史演變中,變動的是帝王將相,而中華始終是中華。
緊接著第二句,張伯駒化用唐代詩人王昌齡和抗清名將金聲(字正希)的聯語,將眼光聚焦于唐、明兩個時代,從歷史上穿梭到大唐盛世和明末清初——“負陌頭柳色,秦關百二,悔覓封侯”。在這一句中,作者化用王昌齡《閨怨》中“閨中少婦不曾愁,春日凝妝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6]168的句子和金聲“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關終屬楚;苦心人天不負,臥薪嘗膽,三千越甲可吞吳”[7]287一聯。其中,“秦關百二”所代表的是秦始皇滅亡六國,統一華夏的史實。既是回應上一句的“收”字,又是重申中國必將統一的預言。這兩句在氣勢上最恢宏,聲調亦高昂,展示著詞人較好的心情和較高的情緒。
在第三句中,張伯駒化用魏晉時代王粲的典故“前事都隨逝水,怯登樓”,所謂“前事”指的是中國悠久的歷史,指的是秦始皇的統一大業。這是銜接前文,目的是為了實現文脈上的通貫。“明月怯登樓”是化用宋代詩人真山民的《漁浦晚秋旅懷》,詩云:“西風吹夢越中游,剪剪輕寒入短裘。雁字不將鄉信寫,蛩聲空和旅吟愁。郵亭冷雨孤燈夜,漁市斜陽一笛秋。是處山川即吾土,仲宣何用怯登樓。”[8]454詩中的“仲宣”是王粲的字,為“建安七子”之一。王粲博學多識,文思敏捷,善詩賦,在荊州投靠劉表,郁郁不得志,因此創作《登樓賦》,借寫眼前景物,以抒郁憤之情,是為“王粲登樓”的典故,后代詞曲中常以“王粲登樓”比喻士不得志。在這里,張伯駒借用王粲的“怯登樓”,卻將“怯登樓”主角“仲宣”換成了“明月”。如李白《把酒問月·故人賈淳令予問之》中所說:“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當歌對酒時,月光長照金樽里。”[9]2459張伯駒的做法十分高超,令人嘆服!一方面,古往今來,滄海桑田,世事變遷,循環往復,月亮始終不變,照應前文“幾興亡,無恙舊河山”一句;另一方面,古往今來,不得志的人又豈只王粲一人,詞人也是不得志啊!相較于前一句的高昂情緒,此句則頗受挫折,情緒略顯低沉。
從詞意來看,詞的前三句已經實現詞人的意圖,然而詞人的情緒尚未完全得以抒發,故有了第四句——“甚五陵年少,駿馬貂裘”。這里“五陵年少”化用的是白居易《琵琶行》中“曲罷曾教善才服,妝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10]301句;而“駿馬貂裘”則化用蘇軾《江城子·密州出獵》中“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云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11]78。顯然,前者婉約,后者豪放。這第四句把時間的穿梭與兩種情緒的轉換融合在一起。人都是有情感的,詞人在縱橫游覽過歷史之后,在見證了興衰存亡之后,自會激起內心的諸多感慨。這種情感既是對歷史的慨嘆,也傳達出詞人對不能掌控自身命運的無奈。
到了下闋,詞人開始思考此生的選擇,寫下第五句:“玉管珠弦歡罷,春來人自瘦,未減風流。”一個“罷”字,不僅表明“玉管珠弦”中的“風流”生活要告一段落,還表示詞人情緒的微調,猶如一聲輕微的嘆息。“春來”點明時間節點。萬物復蘇、欣欣向榮之際,人卻消瘦了,實質上消瘦的不僅是詞人的身體,還是詞人的意志、詞人的理想抱負。“春來人自瘦”實際是化用李商隱《贈歌妓二首》中的“只知解道春來瘦,不道春來獨自多”[12]1996一句,詞人在這里反其意而用之,這五個字也是首次出現在中國詞作中。“未減風流”巧妙化用唐代李白的《泛沔州城南郎官湖》:“風流若未減,名與此山俱。”[9]2982既關涉“玉管珠弦歡罷”,又暗含經過深思熟慮,張伯駒決定追求萬世流芳的“名”“山”事業。
在上一句的鋪墊下,張伯駒在第六句中就順理成章地提出了自己人生的楷模。“問當年張緒,綠鬢可長留?”張緒的事跡記載在《南齊書·張緒傳》中,其特異處有二:一、張緒情操高潔,不計較功名利祿,不屑于阿諛奉承,“緒忘情榮祿,朝野皆貴其風。嘗與客閑言,一生不解作諾。時袁粲、褚淵秉政,有人以緒言告粲、淵者,即出緒為吳郡太守,緒初不知也”[13]600。二、張緒輕看榮華富貴,不計較金銀財寶。“緒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言端坐,或竟日無食。門生見緒饑,為之辨餐,然未嘗求也。”[13]602兩人有著較明顯的相似性,張緒的這兩個性格特點也恰是張伯駒的。同時,張緒的胡子也被稱為“綠鬢”,《南史》記載,武帝曾賞柳咨嗟,因綠柳風流,枝條甚長,狀若絲縷,貌如當年張緒鬢發,故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時。”[14]810對此,伽達默爾提出了一個深刻的觀點,認為“人類只有在藝術領域自己的塑性權能中才能認識自己”[15]148。張伯駒正是通過歷史上張緒的為人處世,在自己的詞作中向世人表明自己的立世原則。
雖然詞人已經確立了人生的楷模,明確了人生志向,但舉目四望,看到的是“更江南、落花腸斷,望連天、烽火遍中州”的場景。放眼江南,正值隆冬時節,萬物凋零,讓詞人十分傷感。遠望家鄉,卻是烽火連天,正是中原大戰熾烈之時。南方沒有戰火,卻是凜冽寒冬;北方雖是溫馨的家鄉,卻是烽火連天。中國這么大,詞人一心想要獨好其身,竟然找不到理想中的安樂凈土。這里有地域的對比,“江南”對“中州”,前者正值“落花腸斷”。此時,張伯駒在江南嗎?張伯駒在北京啊,他為何說江南是“落花腸斷”呢?張伯駒是否到過江南?“江南”包括上海、浙北、蘇南、皖南、贛北等。而張伯駒1920年在安徽擔任長江巡閱使署咨議,1921年擔任湖北、湖南、四川、江西四省經略使署咨議,他尚未到過江浙一帶。故作者所指之江南,也許是安徽南部。他在北京能夠看到中原大戰的硝煙嗎?當然也看不到,但能夠聽到現實生活中朋友們的議論。可見,張伯駒這里寫的是他想象中的情景而非寫實。
到了收尾的時候,一句“休惆悵、有華筵在,仗酒銷愁”概括了張伯駒彼時彼地的心情。所有的苦惱、所有的無奈都要在這一刻消融,但能夠幫助詞人消釋憂愁的只能是酒,再加上豪華宴會上的笙歌燕舞。在這里,詞人勸自己不要惆悵,其意有二:一、不要在意國家前途,因為自己無能為力;二、不要追逐世俗名利,因為自己志在“名山”,詞人只能暫且借助這奢華的酒宴來委蛇度日。這首詞作將國家大局與個人前程相互對照,國家處在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中原大戰正如火如荼。正值“而立”之年的張伯駒面對“于公無望”的情況,只能“于私有悔”,即不能奮發有為,只能麻醉自己,“仗酒銷愁”了。
整首詞中,意象較為稀少,只有柳樹、高樓、樂器、落花,且多為化用前人詞句得來,這是由這首詞的內容決定的。因為不同于寫景、題畫的詞,它是一首寫生日的詞,著意突出的是時間、歲月、人生價值等,所以該詩詞更多展現的是感慨、感想,多的是寫聯想到的事物。因此,這首詞充斥著詩意的想象,并借助想象,構筑了一種奇妙的社會圖景,國家的紛亂與民國公子張伯駒等紈绔子弟的笙歌燕舞形成強烈的反差,也使得詞意跌宕起伏、百轉回腸,蕩人心魄。
該詞的上闋引用典故多處,時間橫跨秦、魏晉、唐、明清等時代。若細加分析,又可以區分出兩種情形。一是詩詞專屬的典故,如“百二韶關”等,在發揮點石成金、化腐朽為神奇作用的同時,營造一種情感抒發的氛圍,以激發作者的創作興趣。二是歷史典故,如詞中所提張緒,張伯駒視之為人生楷模。此外,我們還要注意到,詞人同時化用婉約派和豪放派的典故,巧妙地將兩種迥然不同的風格融匯一爐,婉約中不失豪放,豪放中又內含著婉約,因而,這首詞奠定了張伯駒一生詞作的基本風格。
三、時局觀
在張伯駒眼中,彼時的中國是什么狀況呢?張伯駒的棋藝很好,而下棋講究整體布局,所以他從棋局的角度來看待國家大局,認為當時的中國就是一局“殘棋”,是瀕臨生死存亡關頭的“殘局”。在此后的很多詞作中,張伯駒都有使用“棋局”的意象。如《摸魚兒·同南田登萬壽山》下闋云:“空懷感,到處離宮荒館,消歇燕嬌鶯婉。舊時翠輦經行處,惟有碧苔蒼蘚。君不見,殘弈局,頻年幾度滄桑換。興亡滿眼,只山色余青,湖光剩綠,待付誰家管。”[16]161再如《前調·和正剛韻》云:“曾記白練聽歌,青衫涴淚,憔悴京華客。陵谷幾經朝市換,殘弈渾難收拾。”[16]193說明張伯駒用棋局來看待時事、看待歷史滄桑、看待人生變幻的習慣,既是他一直以來的思維,也是其以棋盤為媒介,謀局人生、追求境界的方式。
綜觀張伯駒一生詞作,其中難掩作者對舊秩序的反感和對新秩序的渴望。張伯駒這種“對立統一”觀念的形成,源自于歷史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信念,其中關鍵在于保持各方勢力的平衡,所以他用了“一枰收”來喻指國家統一的理想。這一觀念一生未改,張伯駒在其1977年創作的《金縷曲·和君坦詞兄預祝余八十壽詞》中寫道:“過眼云煙外。溯生平、多聞多見,司空不怪。紈绔儒冠皆誤我,披上袈裟衣壞。任幻化、紅桑碧海。世事百年如弈局,看興亡、幾換山河在。茲依樣,葫蘆賣。”[17]160這首詞與《八聲甘州·三十自壽》雖時隔五十載,但在詞意和志趣上保持著一脈相承、一以貫之的風格。
張伯駒的一生并非秉持一種避世厭世的消極態度,而是用一種積極的人生觀念來應對時局的變化。他時刻關注著國家大事和歷史大局,并以詩詞創作的特殊方式進行記載和反思。他在1978年交稿的《續洪憲紀事詩補注》中,就簡明扼要地記錄了約30年間中國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關于這一點,可以從張伯駒的家世背景和社會身份的角度進行解釋。無論張伯駒本人如何處世,他那顯赫的家世背景都會把他置于一個又一個歷史漩渦,避無可避。同時,他還有一個身份,決定著他不可能完全把自己關進紙醉金迷的自我世界,因為他與袁世凱家有很密切的關系,他與袁世凱的幾個兒子都是同班同學,終生都有聯系。當然,也正是因為張伯駒擁有這樣的身份和地位,才使得他能夠在歷史的關鍵時刻,發揮出別人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對此,張伯駒在《續洪憲紀事詩補注》第97首中有所記載。抗日戰爭期間,在日本人占據北京之際,張伯駒聽說袁克定(1878-1955)拒絕日本人的高官厚祿,為此極為欣慰。當日本人將目標轉向袁乃寬(1868-1946)時,張伯駒說:“余聞之,夜往與談,勸其勿出。次日乃寬遂托病不出面,終保令名。日寇投降,余歸自西安,河南旅京同鄉會開會,對乃寬皆以鄉長尊之。乃寬與克定稱兄弟,先后守氣節,嚴出處,亦袁氏之佳事也。”[16]130張伯駒雖然是文弱書生,但在民族大義方面始終秉持著正義凜然的高貴氣節。
四、結語
張伯駒懷揣著消弭戰火、國家統一的希望,但沒有為之奮斗的信心與勇氣,否定了自身有能力改變現實的可能性。因而這個詞作雖多言國事、少言私事,但豪放風格中帶有諸多壯志難伸的婉約。這說明,詞人在亂世中的取舍——心有不甘,卻又無奈。因此,這首詞是一個關于命運的故事,關于自身命運的述說,是張伯駒既往生活的自我映照。他在自己的文化意識中闡釋自己,為自己的行為找尋合理性,為自己明確了一種無可辯駁、無可置疑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