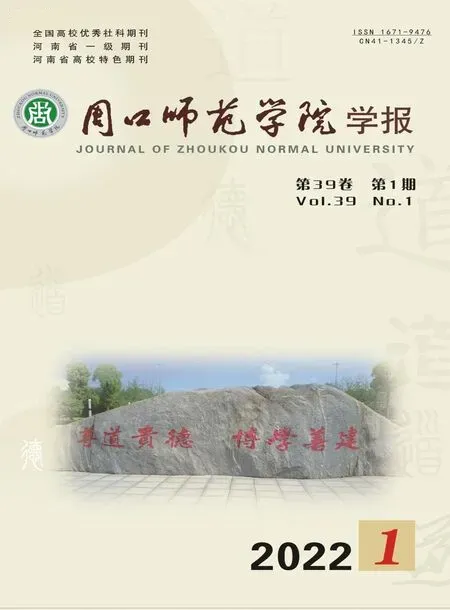當代都市女性的精神困境與追求
——賈平凹長篇小說《暫坐》6人談
楊劍龍,羅敏儀,徐國慶,冰 馬,錢思衡,徐振華
(上海師范大學 人文學院,上海 200234)
楊劍龍:2020年12月26日,中國小說學會2020年度小說排行榜評出,賈平凹的長篇小說《暫坐》為入選的5部長篇小說之一。《暫坐》發表于《當代》雜志2020年第3期,為《長篇小說選刊》2020年第4期選載,并被《長篇小說選刊》雜志社主辦的“第五屆長篇小說年度金榜”列為5部作品榜首,2020年9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單行本。賈平凹創作勤奮精力旺盛,《暫坐》是賈平凹第17部長篇小說,這在當代作家中也是少見的。賈平凹早期創作受到孫犁“荷花淀派”的影響,女性形象大多柔美,后來寫鄉村生活也有各種的女性形象出現。《暫坐》中出現這么龐大的女性族群,突破了其以往的書寫風格。這部作品的背景空間是都市西京城,是賈平凹繼《廢都》之后又一書寫城市生活的佳作。
一、“暫坐”:當代都市的生存圖景
楊劍龍:賈平凹的《暫坐》后記里有這么一段話:“在《暫坐》里,以一個生病住院直到離世的夏自花為線索,鋪設了十多個女子的關系,她們各自的關系,和他人的關系,相互間的關系,與社會的關系,在關系的脈絡里尋找著自己的身份和位置。”[1]5-6這部長篇小說以西京城當下生活為背景,以暫坐茶莊為主要空間,以茶莊女老板海若為核心,演繹十多位女子(陸以可、嚴念初、虞本溫、向其語、應麗后、司一楠、徐棲、希立水、夏自花、馮迎、辛起、伊娃)與一位男作家兼書法家羿光的故事。
賈平凹在展現這些人的物質追求和性格特征過程中,筆觸涉及商場與官場、紅道與黑道等充滿了算計、喧嘩與蒼涼的生活現實,給我們呈現一幅人世艱辛與命運叵測的真實市井風情圖景。
冰馬:《暫坐》頗有一些《紅樓夢》的味道,《暫坐》里的“西京十三玉”與“金陵十二釵”有異曲同工之妙。作品在呈現西京城這樣一個現代城市空間過程中,以海若為主塑造了十多位女性彼此之間類似一種女性互助合作社的關系,構建一個類似烏托邦式的商業群體。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女性群體在情節發展中存在著沖突與凝聚的悖反關系。此外,《暫坐》中出現的“員工守則十三條”,彰顯了一個傳統完美女性形象的標準。從表面來看,每個女性都有光鮮的職業(幾乎都是商人),都實現了經濟獨立,卻都處在離婚或未婚狀態。于是,我們不難看出,賈平凹重點去書寫整個女子互助社在經濟、精神與心理層面上的溝通交流,而在處理男女關系上劍走偏鋒。
羅敏儀:《暫坐》以伊娃來西京為始,回圣彼得堡為終,作家將敘事目光寄寓在伊娃身上,將半個月來發生的事盡收眼底,并將對西京城的現實認知不斷拼接起來完成故事,再現西京城的自然與人文景觀,大街小巷,店鋪林立,城市人日常生活。以上諸種情形,都可認為是賈平凹在秉承其一貫的寫作原則——“變得現實主義”[1]5-6,以一個親歷者與見證者的身份來書寫西京城。
小說共35章,每一章的標題設計為“人名+地名”,構思巧妙的背后是作者在每章節里對西京城面貌的敘述,從西京城中最具有現代化氣息的商場、公司、高檔小區,到混雜的城中村、拆遷區、棚戶區等,其中重點展現了西京城里具有傳統文化質感與鄉土氣息的大街小巷,如興隆街、筒子樓與故事的核心空間“暫坐茶莊”。小說里對茶莊的描述:“如果說延安是革命的圣地,茶莊就是我們走向新生活的圣地。”[2]25海若是茶莊的老板,作為整個故事的核心人物,她將眾多姐妹聚集起來,貢獻“解決生命中的疑團的想法和力量”[2]25。于是,暫坐茶莊自始至終就被賦予了這樣的象征:拯救不和諧與回歸正常生活秩序。更重要的是,暫坐茶莊有不同于其他都市空間的特殊性:有著濃郁的傳統文化歷史色彩,室內裝潢無處不彰顯海若的信佛之道,充滿著神秘與疏離感。此外,又摻入現代性的諸多異質因素:權力、資本與情感的匯聚。
徐國慶:在經歷了經濟的飛速發展后,城市也留下許多后遺癥。《暫坐》中最常出現的意象便是霧霾,霧霾貫穿故事的始終,伊娃在霧霾中尋求新的開始,又在霧霾中悻悻離去,故事似乎因霧霾起也因霧霾終。霧霾的城市中,人依然在相互奔走,生活還在繼續。小說中的眾女性在城市的霧霾中行走,為各自的生活奔波。城市的空氣在變糟的同時,人卻依然無法自拔于其中,因為“人是走蟲”[2]5,所以,從“廢都”到“霧霾城”,城市在變,人也隨之在變。海若等人也在變,但是就像小說中所寫的霧霾一樣,變化不定,海若和姐妹們的命運也在不斷變化,城市的變化歸根結底是人的變化。
錢思衡:小說中的人物關系呈現出復雜的網狀結構,海若是所有人物關系的交匯點,圍繞著她的種種人、物、事錯綜復雜,難能可貴的是作家在這種復雜關系中將故事有條不紊平穩地推進。事實上,從小說開頭俄羅斯姑娘伊娃的到來到小說最終伊娃離去,不過半個多月的時間,高密度的“事件”使這張復雜的關系網越發緊密,顯示了作家強大的故事編織與架構能力。在小說中,這張復雜網狀鏈接形成一條潛在利益線索,無論是求字、廣告牌,還是打探消息、賄賂官員等,都是因利益的驅動,即使是海若周圍的女性好友,也是因在茶館里能夠達到信息共享互相幫助。
徐振華:《暫坐》盡管是一部典型的都市題材小說,但卻融入了作者對城鄉文明關系的思考。小說中的辛起是陜西南部鄉下人,她到西京城打工。她不僅“洋氣”“時尚”,還“長著時髦,又學會了普通話,比城市人還要像城市人了”[2]29。然而,她雖然經濟并不富裕,“在穿戴上的花銷是吃喝上的十多倍”[2]29,也因此糟踐了身體患了胃病,帶來的是精神的掙扎與肉體的折磨雙重苦痛。在西京城打工的年輕姑娘,談論著股市、房租、跳槽等城市生活成本,商量著辭職后轉向電商還是網紅。然而,最終沒有任何結果,生活的車輪依舊按部就班地前行。鄉村生活的熟悉與對城市生活的隔膜,更呈現在精神觀念層面,以至于她們對年邁仍未退休的科學家心存敬畏之心的同時,卻感慨道:“世上凡是太好的東西都是不用的。”[2]58夏自花因病逝世出殯后,張嫂按照鄉下習俗將挽聯燒掉了。虞本溫指斥其為沒文化的鄉下人,燒掉了書法家羿光所寫的挽聯,燒掉了十幾萬。
楊劍龍:小說中海若有一段話:“什么老板不老板的,僅僅都有個小生意罷了,大家抱團兒相互幫扶著,就如羿光老師所說的是一窩蛇,彼此都不安分,跑出去尋些吃的。”[2]69蛇本身是冷血動物,抱在一起也無法暖和彼此。小說整體上還是把女性團體的人間溫暖寫出來了,大家互相幫襯:夏自花生白血病住院,大家彼此安排輪值照顧;辛起和老公離婚搬家具,海若派車派人幫忙。但在傳統中國,一個團體沒有強大的后盾是無法支撐下去的,海若開茶莊本身也依靠背后的政府力量,文人羿光也需要和政府捆綁,商業行為與文化行為密不可分。賈平凹在談到小說《暫坐》時說:“人生就是一場暫坐,每個人來到世上都是暫坐。”[3]小說題目“暫坐”蘊含著一切都是短暫的,人生就是一場暫坐,最后都會曲終人散,小說繪出了一幅當代都市的生存圖景。
二、“自我”:女性群體的精神困境
羅敏儀:小說以夏自花身患白血病住院治療至死亡為線索,穿插著諸多女性的身世與精神困境。夏自花愛上有婦之夫,生了男孩也沒有得到名分,最后年僅40就不幸去世,留下孤苦伶仃的兒子與母親;應麗后為了討回自己的資金,求助討債人章懷卻被訛了幾十萬;辛起出身農村身份低微,幻想著過上上層社會的生活,于是婚內出軌一個有錢的老男人,最終也沒有過上她想要的生活;海若看似是作品中最為灑脫與通達之人,但卻被不學無術、玩世不恭,只會伸手要錢的兒子羈絆等。正如古語“墻東一隙地,可二畝許,誅茅夷險,繚以土垣,垣外雜種榆柳,夾桃花其中”[1],生活在都市里的每個女性都有著自己的困境,這種困境不僅是物質的,更是精神的。小說中悲劇的色調與結尾的處理,說明了作家試圖去找尋答案卻無能為力。作家的使命就在于,“風雨冰雪,陰晴寒暑,吃喝拉撒,柴米油鹽,生死離別,喜怒哀樂,這眾生之相即是文學”[1]。小說通過對各種人際關系的描寫,在眾生之相描寫中呈現日常生活。
徐國慶:如海若一般,作家描寫的雖然有多位女強人,但她們在“強”的外衣下卻有“弱”的內在。如陸以可對父親的執著想念,司一楠和徐棲的同性戀關系,夏自花與已婚老板同居生子,辛起婚內與香港富豪同居并希望通過試管嬰兒的方式奪財。種種看似“不透明”的行為,構成了最真實的社會生活。每個人都渴望改變生活,渴望變得更加獨立,成為能主宰命運的人,但現實卻不盡然。小說中體現了這種不確定性:陸以可不斷看見父親的影子,夏自花生病去世,馮迎似乎意外死亡,辛起放棄去香港的計劃,海若被牽扯到貪腐,伊娃期望而來失望而去,暫坐茶莊意外爆炸,眾姐妹分崩離析。小說中的生活是潑煩瑣碎的,但體現的是現實,充滿生活的合理性。
徐振華:小說在情感上女性們同樣追求自由獨立,她們或未婚或離婚或婚內出軌,婚姻已不再是束縛她們的枷鎖。然而,她們又陷入另一種泥淖:或因情感的傾訴與表達,或因虛榮心的滿足,而與男性名流保持不正當關系。羿光柜子中的小陶瓶里保存著多位女性的頭發,是對女性們與羿光交往的注腳。已單身抑或獨立行事的女性們,依然消解不了情感上的孤寂。自由仍是表象,美好只是虛妄!小說中頻繁出現的象征自由的“飛天”,終究飛不上“天”;預示救贖的“活佛”,最終也未出現。這是女性們的宿命,體現了作家對于性別文化、傳統文化等本源性問題的思考。
錢思衡:小說中的女性,事業成功、長相美麗、年齡不一,但大多數是中年精英女性,全部沒有婚嫁,有的是還沒結婚,有的是離婚后孑然一身,有的是女同性戀。作家敏銳捕捉到現代中產階層的某種情感指向,傳統道德大廈的傾倒與“現代”意識的生長,使得古老的框架中無法安放現代情感與需求。小說中的女性大多為單身,這是作家有意設置的,情感上的孤獨與虛無是必然的,于是,一種結構性矛盾貫穿始終。
冰馬:小說反映了當代都市語境中復雜的日常生活狀態,作家試圖努力在復雜和混沌中建構某種出路,最終卻是烏托邦式的毀滅。為什么賈平凹構建這樣一種悲劇性結局?體現了作家對現實的無法把握。正如賈平凹的寫作意圖:小說并不是為了解決問題,而是在提出問題、發現問題與追問問題的過程中,無論是等待戈多還是活佛,實際上我們內心在等待的都是自己。
楊劍龍:賈平凹在小說后記中寫道:“她們充滿活力,享受時尚,不愿羈絆,永遠自我。”[1]5-6小說中的這些女性,雖然充滿活力永遠自我,卻始終難以擺脫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小說開頭以俄羅斯女孩伊娃眼光走進茶莊,但整體上伊娃還是個旁觀者。從標題看,賈平凹以人物與空間的轉換來構成小說的結構,整體上寫出現代人在都市空間中呈現出精神無所寄托的混沌狀態。“西京十三玉”本身聚集起來成為一個團體,目的在茶莊聚會互相抱團取暖,但在經濟高速發展的過程中,這些女性都充滿孤獨、惆悵與郁悶等情緒,靈魂無所安放,最終每個人都沒有在這個團體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園。小說中貫穿始終的一條線索是等待活佛,但我們也知道,活佛是不會到來的,就像等待戈多一樣。因此,我們可以看到,賈平凹竭力想寫出現代人在都市中的孤獨與失落感,而且想從傳統文化那里找到解決方案,卻最終也沒能實現。
三、“撐竿跳”:從《廢都》《山本》到《暫坐》
徐國慶:《暫坐》是一部以女性為主體的小說,也是一部以城市為背景的現實主義小說。與賈平凹之前創作的《山本》相比較,《暫坐》顯得嬌小玲瓏,這不僅體現在小說的體量上,更體現在風格的差異中。《山本》充滿了磅礴的氣勢和命運的血色,勾勒了一幅秦嶺的山水鄉土畫;《暫坐》則聚光于城市,聚集于暫坐茶莊,頗有氤氳之風、小巧之氣,在相對封閉的空間內勾畫出了一幅都市紅樓之景。同樣是描寫女性,《山本》以聚焦的姿態,描寫女主人公陸菊人通過對井宗秀的期望與寄托來實現自己的理想;《暫坐》則敘述了多位城市中的“成功”女性,但這些女性有著多樣而豐富的人生經歷,其中有對金錢的渴望、對愛情的追求、對欲望的執念,也有對信仰的憧憬(等待活佛的到來)。種種因素凝合而成一種復雜性,這種復雜性成了當代女性生存現狀的形象呈現。
羅敏儀:賈平凹擅長寫“秦嶺”的鄉村風物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學界將其視為鄉土作家的代言人。20世紀90年代《廢都》的出現,賈平凹被淹沒在“驚濤駭浪”中,被視為與其創作“前二十年”格格不入,甚至具有某種顛覆性與對抗性的狂傲姿態。這部作品在賈平凹的創作軌跡中具有某種標志性意義,賈平凹一改往日的以鄉村為書寫背景,選擇都市西京城里的景觀與莊之蝶“文化名片”式的身份而展開敘事。27年后,《暫坐》的問世,延續了《廢都》的文本空間——西京城,故事依舊圍繞著一個莊之蝶式的文化人“羿光”與纏繞在其身邊的“西京十三玉”生成。在這樣的前提下,賈平凹新作《暫坐》中對于書寫經驗的延續與突圍顯得尤為重要,這也是我們理解賈平凹這一部小說的意義之所在。
冰馬:從大的空間來說,《山本》描繪的是20世紀20年代末期30年代早期軍閥割據時代,渦鎮作為軍閥割據和國民革命混戰時期一個半封閉半開放的小社會,從自給自足邁向商業化,賈平凹塑造的陸菊人是一個遵守婦道、賢惠善良的傳統女性;《暫坐》書寫的是知識者、商人和官場腐敗分子共生的一個城市空間,著重塑造的是女性群體。這兩部作品有三個相似的安排:第一,兩部作品都寫了茶莊,《山本》中有6個茶莊連鎖店,陸菊人是其掌舵人,同時陸菊人通過茶莊的建設與營銷資助井宗秀的隊伍。《暫坐》的故事發生主要空間就在海若的茶莊。第二,井宗秀送給陸菊人銅鏡,在《暫坐》里羿光也曾送了海若一個銅鏡。銅鏡作為一個意象對文本女性形象的構建起到了重要的隱喻作用。第三,《山本》中的宗教場所“菩薩廟”,在革命戰爭時期讓勞苦百姓的精神得到慰藉;《暫坐》也營造了一個類宗教場所——海若將茶莊二樓改造了以迎接活佛,但活佛成了一個被期待卻永遠不會出現的象征物。賈平凹的兩部小說從場景到道具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系。
徐國慶:《暫坐》與《廢都》相比較,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廢都》中的城市以20世紀末中國社會的發展為背景,賈平凹以批判的姿態對城市進行解剖。小說講述了以莊之蝶為代表的西京知識分子的故事,同時看到了處于時代發展轉型期的城市的變化。在《廢都》中,人和城構成了一種相互關系,浮躁墮落的生活氣息充滿城市之間,因而成了作家眼中的“廢都”。《廢都》是以知識分子為中心的敘事,男性成為女性爭奪的“戰場”,女性在一定程度上是附屬品。到了《山本》中,男性中心的光環逐漸退去,女性依托男性成就理想,從而形成一種平衡關系。《暫坐》中,男性光環雖然存在,但早已不再是《廢都》中的核心。女性成為中心,男性變成了某種意義上的附屬品。敘述視角的變化,呈現出的是城市發展的變化,小說中的羿光也只是起到了姐妹關系網中的輔助作用。羿光褪去了莊之蝶的風采,呈現出某種平面化意味。
冰馬:如果從女性主義視角來理解《山本》與《暫坐》的話,從《山本》到《暫坐》恰恰暴露了賈平凹的一個弱點:進入城市書寫的時候,賈平凹還是沒有以秦嶺為空間進行創作時那么自如。為什么這么說呢?從男性與女性之間的這種關系建構來看,《山本》構建的一個核心事件:陸菊人以自身的能力與思想推動井宗秀走向成為英雄的道路,井宗秀被塑造成渦鎮中無人能匹敵的領袖;但在《暫坐》中,羿光形象的塑造稍弱一些,其與“西京十三玉”之間交往的生動性和豐富性明顯地被弱化了。
楊劍龍:《山本》中的女主人公陸菊人被塑造得有些不食人間煙火,呈現過于理想化狀態。《暫坐》中的女性與當下生活比較接近,顯得更為生活化。賈平凹在《暫坐》后記中說:“寫過那么多的小說,總要一部和一部不同。風格不是重復,支撐的只有風骨。《暫坐》就試著來做撐竿跳,能跳高一厘米就一厘米。它的突破每每以失敗為標志,俄國的那個巴捷耶娃似乎從沒有見好就收。”[1]5-6
我們從小說整體來看,賈平凹從《廢都》《山本》到《暫坐》的文學撐竿跳是成功的。一方面,《暫坐》寫城市,寫城市女性,寫城市女性團體互相抱團取暖的故事,在他的整個創作歷程中是很有新意的。雖然對于男主人公塑造上沒有太多創新,但對于女性描寫是有突破的,每個女性都有自身的獨特性,這是相當有難度的。另一方面,從場景來建構整個作品,刻畫女性群體的人物形象,場景置于當下的生活中書寫,寫女性爭取人的獨立與經濟的追逐,圍繞著商場、官場與黑社會等種種現實生活展開,努力寫出當代都市人的精神困境與追求。賈平凹的這一“撐竿跳”是成功的,因此他的這部新作《暫坐》進入了2020年中國小說學會排行榜中,成為其中5部上榜的長篇小說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