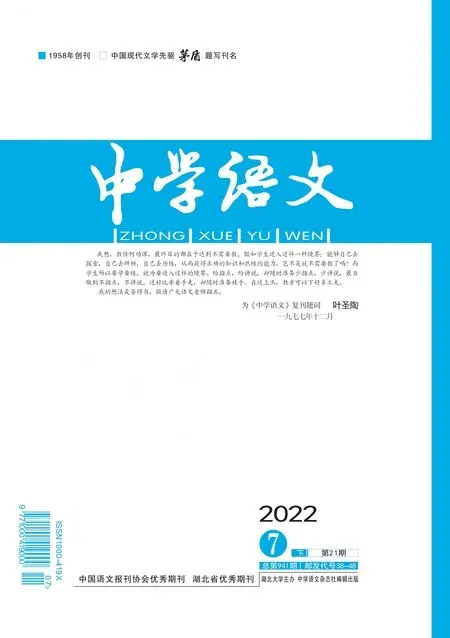青衫秋浦別
——深入解讀《琵琶行》
劉玉玲
紅袖夜船孤,蛤蟆陵邊,往事悲歡商婦淚;
青衫秋浦別,琵琶筵上,一時棖觸謫臣心。
江州司馬夜晚到湓浦口送別前來探望自己的友人,主客相離,此生恐難再見,設宴餞別,愁懷慘淡。恰在此時,忽然聽到琵琶聲隔水傳來。悠悠樂聲,令人著迷,主人忘記打道回府,客人忘記行船出發(fā)。不由感嘆多么高超的技藝,多么令人打動人心的曲調。
從繁華的京城來到偏僻江州,能夠聽到的不過是杜鵑“不如歸去,不如歸”令人思歸的聲聲哀啼;不過是日暮時分山野間猿猴使人分肝腸寸斷的悲鳴;當然也有所謂的山歌村笛,但嘔啞嘲哳如何聽得。今晚聽到錚錚然的琵琶聲,讓人神清氣爽,難道這樂聲來自天界嗎。見見彈奏者,見見彈奏者,在如此蠻荒偏僻之地,怎么會有如此優(yōu)美的曲調,如此嫻熟的技藝,這分明是京都最頂尖的高手在演奏。當然,必須要懇請她再次演奏,用善聽的耳朵,歆享可遇不可求得音樂。劃船近前,重整宴席,挑亮燈盞,延請樂者。態(tài)度懇切,神情肅穆,演奏者才肯出現(xiàn)。轉軸撥弦,輕攏慢捻,樂聲流淌,沒有歡呼,沒有喝彩,更沒有打賞,整個空間靜悄悄的,唯有一輪明月映在江心。演奏者明白,今天遇到了知音,在這個了無人跡的江邊,在人生落寞之際,遇到了一個真正能夠聽懂自己音樂的人,也算聊慰平生了。不由的要談談自己的遭際,說說往時今日的不同。江州司馬懇求演奏者再彈一曲,愿為其的音樂寫詩一首。這是怎樣的一支曲子,樂聲再起,令人動容,所有聽到的人,統(tǒng)統(tǒng)掩面哭泣,坐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
司馬青衫濕——江州司馬為何在一個素不相識的琵琶女面前淚濕青衫?
傷別,一個因所謂“越職言事”被貶謫到州郡,又遭無恥讕言中傷,貶到江西九江的偏遠地區(qū)的區(qū)區(qū)司馬,一個遠在江湖者,有職無權,有名無實的失意者,居然有老友前來探望,不辭千里路遙,更不避政治風雨。即使那個“垂死病中驚坐起”元稹,“每到驛亭先下馬,尋墻繞柱覓君詩”那個沿途留詩元稹,“君埋泉下泥銷骨,我寄人間雪滿頭”令人想念不已的元稹,也只能是遙寄心意。而客人卻真真切切的到達九江,到達自己的身邊,千里萬里,風雨無阻,來看望自己,其間包含的深情厚誼,哪里是能用語言能表達的。匆匆相聚,又要別離,自此之后,天各一方,人生間能不能再次相見,未可預料。本想擺酒起宴,也想瀟灑的說說當日與友人初識的歡愉,遙祝別后一切如意。可是,面對千里而來的人,這一切多么蒼白,多么無力,對面的友人懂得自己,懂得自己的一切,何必掩飾,來痛痛快快的飲一杯。如何這酒沒有了滋味,沒有了醇厚,沒有了辛辣。留不住友人,留不得友人,喝一杯,再喝一杯,無情無緒,酒沒有喝盡,人已然醉了。想想也許今日一別,便是永別呢,如何能不讓人黯然銷魂。
傷景,湓浦江邊,長江岔口,應該是水面浩蕩,月色無邊,水天相接無邊無際,若在平日,當有興趣放舟江面,做一個自由自在的神仙。可惜今夜只有滿目秋色,寒月冷照,秋風颯颯,處處楓葉深紅,荻花凄美,令人頓感秋涼襲身,心情不由得凄苦愁慘。遠看江流宛轉,友人今夜就要隨這江流離開,四面寂靜無聲,江面在月色下更顯水霧迷蒙,寬闊無垠,煙波浩渺,像極了自己的迷茫人生啊。
傷曲,音樂的本質在于抒發(fā)感情,高超的演奏者,正是借助演奏來表達哀愁、傷感、憂郁、歡樂……所謂聆聽,必是自曲調中領會蘊含的情思,進而受到音樂的感染。音樂在演奏者和傾聽者間架起了溝通的橋梁,形成同頻共振。正如韓愈所說,“穎乎誠能爾,無以冰炭置我腸”。穎師彈琴,起初琴聲細柔宛轉,繼而驟然軒昂,和聲中主調分明,輔音相和,恰似百鳥齊鳴,喧啾不已,在眾鳥舞蹈中,一只鳳凰翩然高舉,清高孤傲,不甘于凡鳥為伍,一心向上,飽經躋攀之苦,每一段向上的攀登卻是那樣的艱難,失勢跌落下來,一落多于千丈。難道不是作者的人生寫照嗎?穎師一曲不由分說的撥動了作者的心弦,使之“濕衣淚滂滂”。
江州司馬本就有高超的藝術修養(yǎng),在京城之際,自己的詩歌更是遠播朝鮮,成為當時朝鮮勛貴追捧的對象,更可以想見他的詩歌在大唐王朝——這個詩歌的國度里流行的程度。唐代詩歌是和樂可唱的藝術,一個常年流連于酒肆教坊的詩人,應該本來就屬于藝術家的行列。因此琵琶女轉軸撥弦間,他已經捕捉到弦聲飽含感情,演奏的過程更是被撥動心弦。多年的京城生活,早就造就了江州司馬善聽的耳朵,在他聽來琵琶女無限心事是隨著音樂自然流淌的。攏、捻、挑,多么熟悉的技法,當日里殿堂級的音樂《霓裳羽衣曲》《六幺》傾瀉而出。樂聲時而急促,如急雨打窗;時而細膩,如情人私語;時而清脆,如珠落玉盤;時而宛轉,是鶯語間關;時而低沉,似泉流冰下;時而休止,如幽愁暗恨;時而激昂,如鐵騎突出,刀槍齊鳴,殺聲震天……音樂的樂章,就是生命的樂章啊,初出茅廬,努力奮斗,達到藝術巔峰,享受似錦繁花,肩負責任,努力斗爭……可惜在生命中的那么一刻,這人生只有跌宕,沒有了起伏,發(fā)出吶喊,發(fā)出怒吼,向這個世界宣戰(zhàn),只不過是最后的抗爭而已。如同這四弦同聲,不是裂帛,是人生的決裂,難以分說是人生還是音樂。
傷人,琵琶女豆蔻年華,生命底色是干凈的,生命的音色是清脆的。以超人的天賦,少年成名,在各種藝術家聚集的京城里,她的名字被書寫在教坊的頭牌,一曲奏罷,就是頂尖高手,也要頷首稱服。然而無論藝術水平多么的高超,在這樣的時代,她的命運卻是早已被確定了的,她的人生只能流連于勾欄瓦肆之間,以取悅武陵年少為追求。迷醉于燈紅酒綠,貌似這是她的成功,然而這正是她的不幸。王孫公子不是在欣賞她的藝術,而是在玩弄她的青春。當藝術家年老色衰的時候,就立刻遭到拋棄。作為一個飄零憔悴、流落江湖的長江歌妓,多么渴望來自親人來自愛人的陪伴,但薄情的丈夫“重利輕離別”,讓她“去來江口守空船”。面對清冷的江水,抄起琵琶,彈奏一曲人生的落寞。當日有多么繁華,今日就有多么寂寞,這現(xiàn)實使她悔恨交加,痛不欲生,“銀瓶乍破”的激越,想必是她對世人重色輕才和丈夫重利寡情的憤怒控訴。收撥一劃,更是憤激的哀號,更是對不公平社會現(xiàn)實和命運的抗爭!如今滿腔憤激幽怨,又能如何,算了吧,放棄吧,就與這清冷的江水,孤獨的空船一起,了卻殘生罷了。
傷己,江州司馬從小刻苦學習,白天黑夜地讀書作文,顧不上休息,以至于口舌生瘡,手肘磨出老繭。苦學使他的文學才華成熟較早。據傳在長安時,曾攜帶所作詩文去謁見前輩詩人顧況。顧況望著詩卷上“居易”這個陌生的名字,開玩笑說:“長安米貴,居大不易!”說著打開看,頭一篇《賦得古原草送別》,讀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句子,大為贊嘆道:“有句如此,居天不亦太難。”在顧況的推獎下,年輕的詩人開始聞名。
德宗貞元十六年(799)江州司馬考中進士第四名。十八年應吏部拔萃科考試,入甲等,授秘書省校書郎。元和二年(807 年)十一月,授翰林學士。次年五月拜左拾遣。他的立身處世的指導思想是儒家的“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這時,他抱著“達則兼善天下”的政府態(tài)度,為民請命,勇敢戰(zhàn)斗。曾提出“尊賢能以清吏治,薄稅斂以安民生,罷兵革以蘇民困”等主張。為了反對宦官吐突承璀做掌握兵權的“招討宣慰使”,甚至當面指責唐憲宗的錯誤。以儒家思想為底色,作為新近躋身仕途的精英,他具有很高的政治熱情。這與而元和初年憲宗的整頓朝綱、追求振興的政治意愿是相契合的,這也給他帶來一種政治興奮。此時張籍、王建、元稹、李紳等先后步入仕途,他們之間意氣相投,他們彼此唱和,在當時形成熱烈呼應的局面,他們熱情地把政治主張的宣傳寫進自己詩歌里、更是以詩歌反映各種嚴峻的社會問題,詩歌成了有力的政治工具。元稹、江州司馬更是積極地響應李紳的創(chuàng)作,以江州司馬為主力,提出了“詩歌合為時而作,文章合為事而著”的創(chuàng)作理論,真正把新樂府的創(chuàng)作推向了高潮。他的《新樂府》五十首,就產生于這個時期。這是在元和四年(809)前后。
這個時間段正是他官居諫官的時段,面對民生困苦,官吏盤剝,權利分裂,統(tǒng)治黑暗,面對統(tǒng)治階級生活奢靡,他勇猛戰(zhàn)斗,他不能任由這個偉大的時代衰落下去,他要挽狂瀾于既倒,“救濟人病,裨補時闕”的諷諭詩就是這時寫的,其中《新樂府》五十首和秦中吟等詩,鋒芒尖銳,象連弩一樣射向黑暗勢力。使“權豪貴近者變色”“執(zhí)政者扼腕”“握軍要者切齒”(《與元九書》)。
元和八年改任左善贊大夫,這是一個專門陪太子伴讀的閑官,不能過問朝政,這不符合他的志愿,他在給李紳的詩中曾流露出不滿情緒。
元和十年平盧節(jié)度使李師道派人刺死宰相武元衡,并刺傷其副手裴度。面對如此大事,韋貫之、張弘等宰相保持沉默,文武大臣紛紛不置可否。這種奇怪的局面是他不能忍受的,他激于義憤首先上書“急請捕賊,以雪國恥”。這觸怒了權貴們,權貴立即以“越職言事”加罪于他,將他逐出京城,把他貶為州刺史。不,不夠,要流放他,要打擊他,王涯就乘勢造謠中傷他,說他母親是看花時墜井而死,他寫賞花的詩和關于井的詩,有傷孝道。多么荒謬的借口,實際上是他的諷喻詩使這些人害怕,是他的戰(zhàn)斗讓這些人恐懼。然而,這些人就說他不配治理州郡,將他貶為江州司馬。
詩人自身橫遭貶謫,遠離京都,遠離政治,困守江州,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失意者、一個被拋棄者,面對“黃蘆苦竹繞宅生”的現(xiàn)實,何以不傷感。
但這些遠不是淚濕青衫的緣由。
傷時,作為一個詩人,一個立于時代潮頭的文人,江州司馬具有不同尋常的時代敏感,政治敏感。當自己被饞遭貶謫時,他清醒的認識到自己的時代結束了。自己成為一個遠在江湖的貶官,一個閑職,自己的命運的改變,并沒有令自己特別的憤懣。但在潯陽江頭,琵琶聲里,遇到了另一個曾經頂尖級的人物——琵琶女,如今也淪落江湖。琵琶女的哀怨、激憤組成了一支凄苦的歌,唱出了她不幸,立刻引起了江州的共鳴——他們的漂泊是社會的不公造成的。他更加清醒的認識到,這個時代不需要精英,權貴們不想改變社會現(xiàn)狀,權貴們只是耽于享樂,無意于家國社稷的振興。
一個曾經昌盛的時代,在走向衰落的時候,有多少仁人志士力圖扶大廈之將傾,挽狂瀾于即倒,然而卻被統(tǒng)治者一一拒絕了。元稹、韓愈、柳宗元……敢于抗爭的人,紛紛遭到貶謫,這個時代徹底拒絕了進步力量。
他知道那個大唐盛世已經不可挽回的去了。
貶謫江州之后,他在政治上逐漸走向消極,開始揉合儒家的“樂天知命”、道家的“知足保和”和佛家的出世思想,作為自己的精神寄托和“明哲保身”的法寶。他抵九江不久,就在香爐峰與遺愛寺之間,建一草堂。(《舊唐書、江州司馬傳》)他準備“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于斯,以就平生之志”。(《九江史話》)至于被貶為司馬之心情,他說:“州民康、非司馬之功;郡政壞,非司馬之罪,無言責,無事憂”,“余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命而已”。(《江州司馬廳記》)
一個詩人眼有多冷,心就有多熱。
“一枝一葉總關情”傷物,傷曲,傷人,傷己,傷別,徹底引發(fā)了江州司馬的傷時之感,借《琵琶行》唱一曲時代的哀歌,不由得詩人悲愴滿懷,淚濕青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