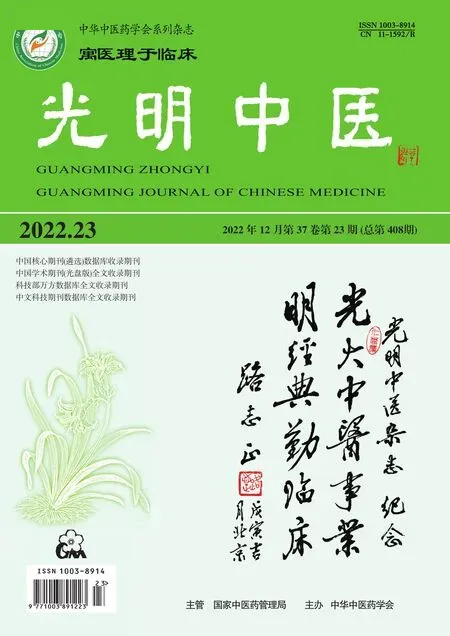李應(yīng)存教授敦煌療癭方治療癭病臨床經(jīng)驗(yàn)*
田云夢 李應(yīng)存△ 梁永瑞 劉馨遙 王梓丞
敦煌醫(yī)學(xué)是敦煌學(xué)的重要分支,是關(guān)于整理研究敦煌遺書、敦煌壁畫以及其他敦煌文物中醫(yī)藥史料的一門學(xué)科。敦煌醫(yī)學(xué)卷子主要來源于中國甘肅敦煌出土的古卷子醫(yī)書,另外還包括西域其他地區(qū)的個(gè)別醫(yī)學(xué)殘卷。敦煌醫(yī)學(xué)在豐富隋唐前后醫(yī)學(xué)典籍,提供古醫(yī)籍校勘和輯佚的依據(jù),補(bǔ)充漢代以前醫(yī)方、解決醫(yī)史爭議的問題及反映以隋唐時(shí)代為主醫(yī)藥學(xué)術(shù)的輝煌成就等方面有非常重要的學(xué)術(shù)價(jià)值[1]。李應(yīng)存教授現(xiàn)為甘肅省高校重點(diǎn)研究基地“敦煌醫(yī)學(xué)文獻(xiàn)整理與應(yīng)用研究中心”負(fù)責(zé)人,甘肅中醫(yī)藥大學(xué)基礎(chǔ)醫(yī)學(xué)院副院長,博士生導(dǎo)師,敦煌醫(yī)派代表人物,從事敦煌醫(yī)學(xué)文獻(xiàn)與臨床應(yīng)用研究30余年,致力于將古老的敦煌醫(yī)方重新應(yīng)用于臨床,讓敦煌醫(yī)學(xué)造福人類健康事業(yè),并逐漸形成個(gè)人的學(xué)術(shù)特點(diǎn)。用藥巧妙嚴(yán)謹(jǐn),廣受患者好評。
1 敦煌醫(yī)方療癭方的簡介
療癭方源自《雜證方書第八種》,此卷子法國編號P.3596,其首尾均缺,系正背兩面書寫。著名敦煌研究學(xué)者叢春雨叢老認(rèn)為此書與傳世古醫(yī)方無類同,因其內(nèi)容雜抄內(nèi)、外、婦、兒、五官等病醫(yī)方,據(jù)此稱為《雜證方書第八種》。《敦煌古醫(yī)籍考釋》稱其為《不知名醫(yī)方第九種》。療癭方原文:“昆布(八分) 參(四分) 枳殼(四分) 海藻(六分) 茯苓(四分) 桂心(四分) 芍藥(三分) 真珠(四分) 海蛤(三分) 松蘿(四分) 琥珀(三分) 羊靨(yè) 橘皮(四分) 通草(四分) 檳榔仁(五顆) 干姜(三分) 上件藥搗篩,蜜和丸,酒飲下,日服二十五丸,仍作彈丸如棗大,含細(xì)咽汁,朝含一丸,夜含一丸,忌菜、熱面、油膩、雞、豬、魚、肉、蒜”[2]。“癭”,病名,出自《爾雅》,俗稱是指頸前頜下結(jié)喉之處,有腫物如瘤,或大或小,可隨吞咽轉(zhuǎn)動(dòng),又名“癭瘤”或“頸癭”。相當(dāng)于如今甲狀腺腫大之類的疾病[3]。療癭方就是敦煌醫(yī)方里治療甲狀腺疾病的代表方劑。方用海藻、昆布、海蛤、檳榔仁、珍珠化痰消癭;人參、茯苓、干姜、桂心、橘皮、枳殼理氣健脾;琥珀、松蘿、通草利水通淋、祛痰;芍藥斂陰和營。諸藥搭配,琴奏合鳴,療癭之疾患。
2 療癭方臨床運(yùn)用
癭病多由情志不遂引起,為臨床常見病之一,中醫(yī)在治療上多從肝入手,有著顯著的療效。李應(yīng)存教授認(rèn)為癭病與肝脾關(guān)系密切,其發(fā)病以肝失疏泄為本,兼有氣滯、痰凝、血瘀為標(biāo)。在治療上,李應(yīng)存教授以理氣化痰、消癭散結(jié)為基本原則,辨證論治,隨癥加減。
本方海藻消痰軟堅(jiān),《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云:“主癭瘤氣,頸下核,破散結(jié)氣,癰腫癥瘕堅(jiān)氣,腹中上下鳴,下十二水腫”[4];昆布消痰軟堅(jiān),利水消腫,《名醫(yī)別錄》云:“主十二種水腫,癭瘤聚結(jié)氣,瘺瘡”,與海藻合用,加強(qiáng)軟堅(jiān)散結(jié)之功效[4];羊靨,為牛科動(dòng)物山羊或者綿羊的甲狀腺,有理氣散結(jié)之功效,《本草綱目》云:“甘淡,溫,無毒”,入肺經(jīng),治氣癭,符合中醫(yī)上所說的以形補(bǔ)形;松蘿,又名松上寄生、女蘿、天蓬草,苦甘,平,有清肝、化痰、止血、解毒之功效,可治療癭癰、瘰疬、瘧疾等;海蛤,化痰利水、軟堅(jiān)散結(jié),消癭瘤;枳殼、橘皮、檳榔寬胸理氣疏肝;桂心、干姜、茯苓溫陽化水,化其痰滯;通草、琥珀,養(yǎng)心通經(jīng)、活血利水、散瘀消癥,通其血滯;人參、芍藥補(bǔ)益氣血,祛邪而不傷正;珍珠鎮(zhèn)心安神,防邪郁而化火,擾及心神。縱觀全文,以化痰散結(jié)為主,兼顧行氣、活血、利水,又可扶助正氣,使祛邪不傷正,共消癭瘤。
李教授在臨床上注重辨病與辨證相結(jié)合,對于癭病的治療常規(guī)了解患者患病的病因,如遇女性患者,著重關(guān)注患者的家庭、情感以及子女等問題,以期尋找發(fā)病的根本原因。臨床上患者癭病多有心慌、乏力等心陰虛的表現(xiàn),李教授會(huì)在療癭方的基礎(chǔ)上加黨參、黃芪、柴胡、醋小茴香等,在散結(jié)消癰的基礎(chǔ)上滋陰益氣,增強(qiáng)調(diào)肝氣、補(bǔ)氣血的效果,鞏固療效,增強(qiáng)患者體質(zhì)。
3 典型醫(yī)案
某女,40歲。2021年4月21日初診。主訴:自覺頸前正中腫大1個(gè)月余,質(zhì)軟不痛。現(xiàn)癥見甲狀腺可觸及腫大,質(zhì)軟不痛1個(gè)月,未予重視,近來急躁易怒,胸悶氣短,喜太息,遂來就診,患者自訴病情與情緒波動(dòng)關(guān)系較大,生氣后病情加重,心情舒暢時(shí)可緩解,晨起咳嗽甚,痰量多易咳,自覺心慌,神疲乏力,汗出甚,食后胃脘脹滿,呃逆,納差,睡眠良好,大便秘結(jié),舌紅苔黃,脈弦數(shù)。月經(jīng)量少,周期時(shí)有延長,經(jīng)期小腹脹痛,既往體健,無傳染病史,無藥物過敏史,于當(dāng)日做頸部彩超示:2 mm×2 mm甲狀腺結(jié)節(jié)。
李應(yīng)存教授四診合參,中醫(yī)診斷為癭病(氣郁痰阻型),西醫(yī)為甲狀腺腫大。此患者病位主要在肝,與脾胃關(guān)系密切。治則:行氣化痰、軟堅(jiān)散結(jié),兼理脾胃,標(biāo)本兼治。處方如下:蜈蚣1條,浮小麥10 g,蒲公英20 g,苦參15 g,桑枝30 g,蜂房3 g,柴胡12 g,茯苓10 g,白術(shù)15 g,醋香附18 g,通草1袋(5g/袋),醋鱉甲15 g,鹿銜草15 g,陳皮12 g,路路通20 g,酒大黃3 g,浙貝母15 g,昆布15 g,海藻15 g,麩炒枳殼15 g,黃連10 g,當(dāng)歸25 g,木瓜15 g,連翹15 g。6劑,每日1劑,水煎服,早晚飯后1 h 服用。
2021年4月28日二診:藥后癥減,咳嗽痰多、心慌汗出、便秘癥狀基本消失,仍有食后胃脹、口渴多飲、多夢。去掉蜈蚣、浮小麥、桑枝、白術(shù)、鹿銜草、浙貝母、茯苓、木瓜,加玄參15 g,麥冬12 g,生地黃12 g,茯神10 g,山藥15 g。6劑,每日1劑,水煎服,早晚飯后1 h 服用。
5月12日三診:藥后癥減,觸診可明顯感覺甲狀腺結(jié)節(jié)漸小,口渴多飲癥狀緩解,胃脹緩解,情緒趨于穩(wěn)定。去掉醋鱉甲、蜂房、酒大黃,加黨參15 g,黃芪20 g。鞏固療效。6劑,每日1劑,水煎服,早晚飯后1 h服用。
按語:該患者初次就診,根據(jù)所述癥狀,李應(yīng)存教授對其進(jìn)行甲狀腺觸診,發(fā)現(xiàn)頸前腫大。高度懷疑為甲狀腺疾病,經(jīng)過與檢查結(jié)果結(jié)合,確診為甲狀腺結(jié)節(jié)。從中醫(yī)辨證來看,患者屬“癭病”的范疇,總體病機(jī)為氣、痰、瘀三者結(jié)合為患。患者平素急躁易怒,胸悶氣短,情志不暢為肝氣郁結(jié)的表現(xiàn);晨起咳嗽,胸脘滿悶皆為痰氣凝結(jié)于中上二焦所致;因其病程較短,故未出現(xiàn)明顯的血瘀癥狀。李應(yīng)存教授經(jīng)過辨證,選用敦煌療癭方行氣解郁,化痰散結(jié),根據(jù)該患者的具體癥狀進(jìn)行加減:加浮小麥固表止汗;加柴胡、香附、木瓜疏肝解郁,行氣通絡(luò);加蒲公英、連翹、鱉甲、蜈蚣增強(qiáng)消腫散結(jié)之效;加苦參、桑枝利水燥濕;加橘皮、浙貝母燥濕化痰;加黃連瀉火通便。二診患者癥狀有所好轉(zhuǎn),便秘癥狀消失,故在一診處方的基礎(chǔ)上去蜈蚣、浮小麥、桑枝、白術(shù)、鹿銜草、浙貝母、茯苓、木瓜等藥,加入玄參、麥冬、生地黃等藥滋陰潤燥,加茯神、山藥改善患者睡眠質(zhì)量。三診時(shí),患者癥狀基本好轉(zhuǎn),結(jié)節(jié)減小,痰氣互結(jié)有所改善,故減少軟堅(jiān)散結(jié)、燥濕化痰之藥,加入黨參、黃芪益氣生津,鞏固療效。在此次診療中,李應(yīng)存教授從痰氣出發(fā),調(diào)肝理脾,使肝氣暢達(dá)、脾氣健運(yùn),才能達(dá)到滿意的治療目的。
4 結(jié)語
癭病基本病機(jī)是氣滯、痰凝、血瘀壅結(jié)頸前。初期肝失于疏瀉,氣滯痰凝。壅結(jié)頸前成癭;中期氣滯血瘀,癭腫漸硬;或氣郁化火,心肝火旺;后期郁火傷陰耗氣,甚或陰損及陽,陰陽兩虛[5]。基于此病,李應(yīng)存教授在治療上注重泄肝理氣兼調(diào)理脾胃。李教授指出:該病主要發(fā)病機(jī)制是痰氣郁結(jié)于頸前,多為實(shí)證,但也會(huì)出現(xiàn)肝郁乘脾的表現(xiàn),會(huì)有脾胃虛弱的癥狀,所以在臨床診治一定要仔細(xì)分析辨證,重視患者的病因,從根本上祛除,才能達(dá)到滿意的療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