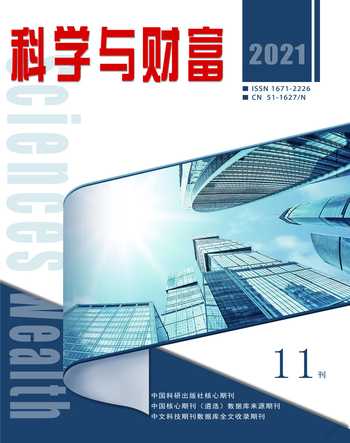新時代國有企業紀檢監察工作體制創新方向
李道君
摘 ? ?要:新時代我國國有企業的發展逐漸多元化,目前,國有企業紀檢監察工作已經變得制度化與常態化。但隨著新時代國有企業的性質、職能以及經濟地位的變化,國有企業及經濟上工作也應該對此做出一些調整。發現和解決目前國有企業紀檢監察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并據此確定好新時代國有企業紀檢監察工作體制的創新方向,唯有創新才能更好的發揮國企紀檢監察工作的作用。本文就當前國有企業紀檢監察工作的存在價值以及現狀展開分析,并據此提出國企紀檢監察工作體制的創新策略。
關鍵詞:新時代;國有企業;紀檢監察;工作體制創新
新時代紀檢監察、反腐倡廉工作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進。國有企業紀檢監察工作能夠有效的發現國企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并且如實上報,有利于國企中存在問題的解決。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肅清國有企業內部的不良風氣。國有企業紀檢監察工作是保證國有企業穩步發展的重要保障。但是目前大部分的國有企業紀檢監察工作都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并不能夠真正的發揮其作用,所以制定出創新的工作體制是非常有必要的。
1.新時代國有企業紀檢監察工作的重要性
現在新時代國有企業的發展過程中,對現代企業的制度進行不斷改善是重要的任務,使紀檢監察為目標更好發展,從而不斷組織落實實際工作,這對國有企業紀檢監察開展工作有有顯著的成效,國有企業的時效發展,讓企業完成良好的循環,提供好的就業環境機會從而有利于形成安逸和穩的環境,其次,違法亂紀的不良情況發生,會讓企業內各基層員工的心理出現不安,并且會造成內部關系矛盾激化從而發生沖突,所以國有企業紀檢監察工作這時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這對國有企業的核心發展以及穩定的工作環境的形成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存在性,通過紀檢監察工作的開展,使企業各部分工作有效的進行,員工之間具有良好和諧的合作關系,從而利于國有企業的整體先優秀的方向發展,對未來的企業工作安排具有不可或缺的決定性作用。
2.新時代國企紀檢監察工作的現狀
國有企業運營發展過程中,忽視紀檢監察工作,從而使紀檢監察部門的設置沒有特別的完美,從而影響國有企業在具體的工作形式中的可持續發展,企業紀檢監察機構目前面對的工作情況也更加的復雜多樣,它所涉及的企業生產活動和內容都比較的繁雜,這時候就需要紀檢監察人員要有一定的知識潛力,去有效的開展活動,從而起到監察、排污的重要作用。其次,國有企業紀檢監察工作形式單一,沒有足夠的實踐執行力,缺乏足夠的權威性和執行力,紀檢監察干部沒有絕對的話語權,從而沒有足夠的震懾能力。所以正是由于紀檢監察工作缺乏專一方向性,并且缺乏理論知識基礎,從而使國有企業的發展造成了很大的缺陷。
3.新時代國有企業紀檢監察工作體制創新策略
3.1創新思想
針對于解決目前國有企業紀檢監察工作存在的問題,其中最主要最關鍵的策略就是改變當前工作人員的思想意識,目前存在最嚴重的問題是紀檢監察工作人員對于國際工作監察的重視不足。這就會導致國企的經營和發展方向不受嚴格監控,容易出現問題。整頓創新目前國企紀檢工作,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創新紀檢監察工作人員的思想。要整頓整個紀檢部人員的思想,首先要做的就是領導人員創新自己的思想,發揮領導帶頭作用,要對紀檢工作人員進行不定期的思想培訓思想教育并做好個人思想報告,學習成果的匯報。關于思想培訓的內容,首先是做到思想上重視對國有企業的紀檢檢查工作,其次要進行職業道德思想的教育,讓工作人員嚴格遵守各項規章制度,依法辦事,誠實守信,公正無私。工作人員要做的就是恪盡職守,嚴格偵查,發現問題如實上報反饋[1]。
3.2創新國企監察的制度模式
當前國有企業的紀檢監察機構是由上級的監察機關和企業內部的行政機構。兩個部門的雙重領導。所以這就會導致目前國有企業的紀檢監察工作不充分不深入。這主要是由于監察機構中企業內部的行政機構的存在,這樣就使得對于企業內部高層領導的檢查力量較小,國有企業高層領導是這個企業的主心骨,其作風、思想、行為等又能夠深刻的影響國有企業的發展。這就需要紀檢監察部門應該是獨立于企業內部機構之外的部門,甚至應該脫離國有企業的組織架構。國企的紀檢監察工作完全由上級監察部門領導執行,這樣才能夠真正的保證監察工作的公正客觀,也能使國企上層領導得到充分的監督,使檢察工作也變得更加的全面深入。
3.3創新紀檢監察的方式方法
當前對于國有企業紀檢監察的方式,普遍是采取一種事后檢查,即當監察部門發現國有企業存在一種違反傾向以后,才開展對應的紀檢監察工作。這種工作模式存在很大的風險,稍有不慎可能就會有漏網之魚,而且也沒有能做到對于國有企業發展的嚴格把控,表面上貌似只是有傾向,但實際可能已經出現了嚴重的違法行為。新時代的國有企業紀檢監察工作應該保證一定的時效性,要改掉以前的滯后性。國有企業檢查部門可以通過增設舉報電話,網絡舉報入口等擴大對于國企信息的搜集和處理工作。除此之外,檢查部門也要定期不定時的去企業內部進行檢查工作,從根本上提高監察力度[2]。
3.4創新培養紀檢監察工作人員
為了使國有企業紀檢監察工作更能夠符合新時代的要求,領導人員要對紀檢工作人員進行創新培養,改變以往無用的開會,拿出時間來進行有關的教育培訓。提升檢察隊伍的整體水平和專業素養。紀檢監察工作人員的創新培養策略可以首先加強對于紀檢工作人員的專業知識,提高監察工作人員的專業水平。其次就是加強法律,紀檢監察等專業知識的培養,提高工作人員的知識儲備,并要不定期的組織會議進行工作經驗的交流。最后就是加強紀檢監察領導的帶頭作用,嚴格監控監察隊伍的作風[3-4]。
4.結語
時代背景下加強國有企業進行檢查工作是非常必要的,紀檢監察部門要做的就是根據當前紀檢監察工作中的問題制定相應的解決策略。創新監察工作人員的思想,創新人才培養策略,創新監察制度以及監察工作方式,只有做到不斷的改進,并且與時代進步發展相協調,才能夠使我國國有企業紀檢檢查工作更加的規范高效。
參考文獻:
[1]游東威.新時代國有企業紀檢監察工作體制創新思考[J].中外企業文化,2020(04):78-79.
[2]戴雙萍.新時代國有企業紀檢監察工作體制創新研究[J].市場論壇,2019(04):26-29.
[3]張志宏. 新時期國有企業紀檢監察工作的創新思考[J]. 電子樂園, 2020(7):1.
[4]章明全. 淺談新時代國有企業紀檢監察工作存在的問題及對策[J]. ?2021(2018-4):64-65.
32605011865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