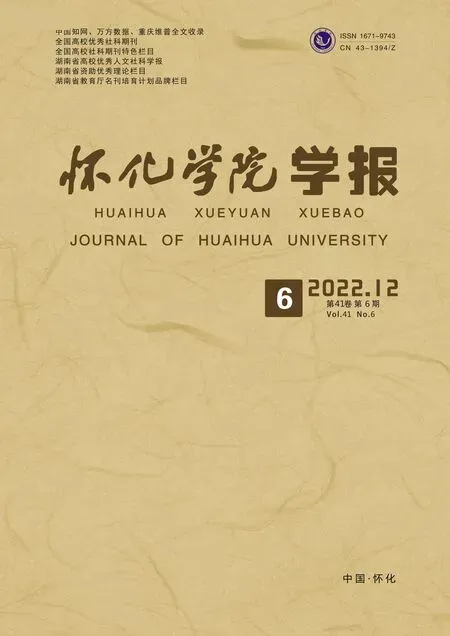論《哈姆萊特》中克勞狄斯的偽裝
曾 絳
(湖南科技大學(xué),湖南 湘潭 411201)
《哈姆萊特》(行文中簡(jiǎn)稱《哈》)為古今世人提供了以假面掩蓋心靈扭曲的一組群像:?jiǎn)烫佤數(shù)乱园苍斮t淑的外表掩蓋著她心靈的躁動(dòng)和情欲的膨脹;雷歐提斯則在血?dú)夥絼偟男愿窈万T士身份的掩蓋下實(shí)施劍上涂毒的卑鄙行為;羅森格蘭茲和吉爾登斯吞以帶有私欲的愚忠掩蓋他們見(jiàn)利忘義的丑惡;奧斯立克則以巧言令色掩蓋著他那心靈的空虛[1]230。從以上《哈》劇角色以假面掩蓋下的罪行中,我們所看到的是劇中主、次人物的靈魂都是被某種欲望所驅(qū)使、所支配,從而干著罪惡的勾當(dāng),或表現(xiàn)出趨炎附勢(shì)和厚顏無(wú)恥,或有意或無(wú)意地干出了為滿足一己私欲而損毀他人的惡行。然而,利用以上人物的惡行和私欲而導(dǎo)演這場(chǎng)群丑眾惡或狂歡或獨(dú)舞的是極擅偽裝且陰險(xiǎn)狠毒的克勞狄斯。
克勞狄斯是《哈》劇中一切丑行生發(fā)和一切禍端滋生的根源,是一個(gè)貪婪無(wú)恥陰險(xiǎn)狡詐的惡賊[2]477。他引誘王嫂并與之私通在先,弒兄奪位在后[3]125。為了奪取王位,他趕在哈姆萊特回國(guó)奔喪前與王嫂速婚,占據(jù)了合法繼承人哈姆萊特的王位,還以群臣擁戴的名義使自己的僭位合法化。《哈》劇從第一幕第二場(chǎng)始向世人呈上了一個(gè)“荒淫”“狠毒”“奸邪”“陰險(xiǎn)”的戲劇形象,一個(gè)馬基雅維利式人物的代表[4]178。
克勞狄斯以血腥手段和罪惡偽裝達(dá)到了他蓄謀已久的目的——坐上了夢(mèng)寐以求的寶座。然而,坐在萬(wàn)眾凝視和群臣仰望的寶座上,他如何能以假面掩蓋自己犯下的罪行?能否以偽裝的自我實(shí)行王權(quán)并治理多事之秋的國(guó)家?如何在靈魂的懺悔中繼續(xù)他的罪惡行徑?如何看待克勞狄斯的偽裝行徑及其政治后果?對(duì)克勞狄斯這一人物及其偽裝行徑和政治博弈進(jìn)行文本解讀,可增強(qiáng)對(duì)《哈》劇藝術(shù)性和政治性的認(rèn)知。
一、克勞狄斯的偽裝背景
《哈》劇一開(kāi)始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幕疑霧重重的背景:午夜時(shí)分的艾爾西諾城堡守望臺(tái)上萬(wàn)籟俱寂、寒氣逼人,如此時(shí)空使接近城堡的人不寒而栗。在如此肅殺靜穆的空氣里,老哈姆萊特的鬼魂連續(xù)三夜晃現(xiàn)在守望臺(tái)上,在陰森可怖的黑夜中徘徊輾轉(zhuǎn),增加了輪值守夜士兵的恐懼。霍拉旭(Horatio)據(jù)鬼魂的頻頻出現(xiàn)做出了自己的推測(cè):“這恐怕預(yù)兆著我們國(guó)內(nèi)將有一番非常的變故。”[5]185①霍拉旭的推測(cè)向觀眾或讀者暗示:老王之死存有蹊蹺,新王對(duì)此有著重大嫌疑;如果查證老王死因必然發(fā)生系列事件,此后的悲劇終會(huì)連續(xù)發(fā)生,國(guó)家的時(shí)局會(huì)產(chǎn)生變故。
(一)克勞狄斯面臨的動(dòng)蕩時(shí)局
當(dāng)值哨兵馬西勒斯(Marcellus)則由霍拉旭的推測(cè)聯(lián)系近期自己的所聞所見(jiàn),回應(yīng)霍拉旭:“國(guó)家正為備戰(zhàn)而忙亂騷動(dòng);軍民在夜以繼日地制造銅炮;民眾議論著政府要向國(guó)外購(gòu)買戰(zhàn)具;軍部正在征集大批造船工匠。”[5]185霍拉旭對(duì)馬西勒斯所道出的現(xiàn)象予以解釋:挪威王子小福丁布拉斯(Fortinbras,Jr.)趁丹麥老王新喪政局不穩(wěn),正在積極準(zhǔn)備用武力奪回曾經(jīng)失去的土地。克勞狄斯對(duì)此做出了備戰(zhàn)和外交的兩手準(zhǔn)備,一方面動(dòng)員全國(guó)軍民為可能發(fā)生的戰(zhàn)爭(zhēng)做著準(zhǔn)備,另一方面則采取綏靖的外交政策,派遣大臣出使挪威,向在位國(guó)王小福丁布拉斯的叔父面呈國(guó)書(shū),并要求挪威王遏制侄兒的野心。挪威王回應(yīng)來(lái)使:知情后對(duì)侄兒進(jìn)行了訓(xùn)斥,在侄兒誠(chéng)心答應(yīng)悔過(guò)下,現(xiàn)已委任他統(tǒng)帥他所征募的兵丁去征伐波蘭邊疆一小塊荒瘠的土地,并提出挪威軍隊(duì)借道丹麥的非分要求②。
挪威軍隊(duì)借道鄰國(guó)事關(guān)丹麥國(guó)家安全和丹麥與波蘭的睦鄰關(guān)系。然而,既是“謀殺者”又是“篡位者”的克勞狄斯驚魂未定底氣不足,應(yīng)允了挪威軍隊(duì)借道邊境的要求[6]43。這一退讓大大損害了丹麥國(guó)家主權(quán),民眾痛感喪失了國(guó)家的尊嚴(yán)。依此可說(shuō):莎士比亞塑造的克勞狄斯一角既是一個(gè)令人發(fā)指的謀殺者,又是運(yùn)用陰謀篡位的叛逆者,更是一個(gè)給國(guó)家和民眾帶來(lái)災(zāi)難和不幸的罪人,一個(gè)以偽裝為能事的陰謀家。因此,國(guó)家、人民以及他自己正面臨著嚴(yán)峻形勢(shì)。克勞狄斯面臨王兄的陰?kù)`不遠(yuǎn)、英名猶在和侄兒的王位歸屬、民心所向的挑戰(zhàn):一是,老哈姆萊特在位時(shí),國(guó)家強(qiáng)盛,稱霸一方,威名遠(yuǎn)播且具威懾力;二是,按“丹麥王位繼承法”,王子哈姆萊特是老哈姆萊特的血脈傳承者,是繼承大位的唯一人選[6]45。并且,王子哈姆萊特曾在威登堡大學(xué)讀書(shū),深受歐洲大陸人文思想浸潤(rùn),擁有民主意識(shí),心系民眾。克勞狄斯與其王兄兩相比照,顯然相形見(jiàn)絀、劣勢(shì)明顯。馬西勒斯“丹麥國(guó)體正在腐爛衰敗”的言論代表了大部分民眾的聲音[5]240。
(二)君臣間的緊張關(guān)系
此時(shí)的宮廷充滿了威脅、恐嚇、欺蒙和哄騙。而克勞狄斯則是威脅和欺騙產(chǎn)生的來(lái)源。克勞狄斯深知“王位世襲繼承”觀念在民眾心中根深蒂固[7]118,如非繼承,自己王位的穩(wěn)固需要多方勢(shì)力的支持和認(rèn)同。克勞狄斯深諳偽裝之道,將“眾臣視為舞臺(tái)下的觀眾”,自扮自演偽裝者的角色[8]80。在他的傾情演出下,眾臣為他哀悼老王“猝死”的表演所動(dòng)容,為他“不得不違情逆理”,讓“殯葬的挽歌和結(jié)婚的笙樂(lè)同時(shí)并奏,用盛大的喜樂(lè)抵消沉重的不幸”言辭所說(shuō)服,認(rèn)同他為國(guó)土統(tǒng)一而背負(fù)“娶嫂奪位”罵名的“擔(dān)當(dāng)”[5]195-196。克勞狄斯的偽裝不僅避免了一場(chǎng)內(nèi)部的“派系斗爭(zhēng)”,而且使得王位競(jìng)爭(zhēng)者哈姆萊特的“煽動(dòng)性言論”無(wú)法奏效[8]81。在贏得眾臣的認(rèn)同之后,克勞狄斯巧妙地運(yùn)用了“艷麗的”上衣和“寬松的”褲裝,塑造身份和烘托氣氛,來(lái)掩飾英明君主“猝死”和鄰國(guó)軍事騷擾共同作用下的混亂局勢(shì)[9]。但他還未意識(shí)到的是:欺蒙和哄騙是政體“腐敗”生發(fā)的土壤,是王國(guó)“迅速衰微”的苗頭[10]。
克勞狄斯將連環(huán)性的欲望變成現(xiàn)實(shí)后,連續(xù)地大宴群臣,并默許售賣他的畫(huà)像,由此助長(zhǎng)了奢靡的社會(huì)風(fēng)氣和阿諛?lè)畛械膶m廷惡習(xí)。對(duì)于克勞狄斯的做法,哈姆萊特評(píng)論道:“我的叔父是丹麥的國(guó)王,那些當(dāng)我父親在位的時(shí)候?qū)λ绻砟樀娜耍F(xiàn)在都愿意拿出二十、四十、五十、一百塊金洋來(lái)買他的一幅小照。哼,這里面有些不是常理可以理解的地方,要是哲學(xué)能夠把它推究出來(lái)的話。”[5]289-290哈姆萊特評(píng)論中暗帶嘲諷:老哈姆萊特的小像貴重?zé)o比,是“神圣信仰的標(biāo)志”。而克勞狄斯的小像低俗廉價(jià),是“真相被隱藏的符號(hào)”[8]80。一方面,這些惡習(xí)引發(fā)各級(jí)官吏對(duì)民眾的重利盤剝、橫征暴斂,貪污受賄之風(fēng)盛行,民亂大有一觸即發(fā)之勢(shì);另一方面,克勞狄斯默許小像四處兜售的行為帶有異教崇拜的嫌疑,比哈姆萊特視父親如同神明的做法更為教會(huì)所不容,會(huì)觸發(fā)國(guó)內(nèi)的政教沖突。
二、克勞狄斯的偽裝策略
克勞狄斯擁有很強(qiáng)的“以言行事”能力,且是一位行事果斷的“實(shí)干家”。他帶著陰險(xiǎn)的目的,披著偽善的外衣,運(yùn)用虛偽的語(yǔ)言,得到王兄的信任,博得王嫂的感情,取得群臣的認(rèn)可。在陰謀行徑達(dá)到目的后,他試圖繼續(xù)采用“言語(yǔ)偽裝”和“行徑偽裝”,以此應(yīng)對(duì)與他對(duì)立的任何人,尤其是哈姆萊特。然而,克勞狄斯終究是一陰謀家,而非思想家,且行的是惡,用的是偽,他行事的思考缺乏邏輯,他的言語(yǔ)本質(zhì)上是虛假的,他的行事留有漏洞。
(一)言語(yǔ)偽裝
克勞狄斯以“一石兩鳥(niǎo)”的伎倆既實(shí)現(xiàn)了“娶嫂為后”,又占據(jù)了本屬哈姆萊特的王位,然而再以自認(rèn)自說(shuō)的“群臣擁戴”使自己的篡權(quán)奪位的行為合法化合理化,進(jìn)而當(dāng)眾宣稱,這樣重大的事情事先“曾經(jīng)征求意見(jiàn),多蒙大家誠(chéng)意贊助”[5]196。克勞狄斯深諳“同類人群”的“語(yǔ)言游戲”及“語(yǔ)言規(guī)則”,反復(fù)使用空洞虛幻的言辭掩飾殘害王兄奸娶長(zhǎng)嫂篡奪王位的罪行[11]。更有甚者,他用表面上對(duì)哈姆萊特非常關(guān)心掩蓋其罪惡的心靈,要求哈姆萊特視己為父,許諾將像慈父一樣給予他關(guān)愛(ài),虛情假意地懇請(qǐng)他留在身邊伴隨左右,應(yīng)允他為王位的唯一繼承人。克勞狄斯“按強(qiáng)盜的邏輯,奪取了別人的東西,答應(yīng)自己不再使用時(shí)還給別人,還將自己美化成父親般的仁慈”[1]231,并惺惺作態(tài)地要求哈姆萊特“在朝廷上領(lǐng)袖群臣,做我們最親近的國(guó)親和王子”[5]204。然而,克勞狄斯在醞釀著殺機(jī),就在懷疑哈姆萊特裝瘋時(shí),內(nèi)心已經(jīng)形成鏟除他的方案——送往英國(guó),借英王之手將其處死。從克勞狄斯玩弄的兩面手法中,觀眾和讀者看到的是一幅偽裝的笑臉掩蓋下的兇殘、卑劣和狡詐且猙獰的面孔。
“君權(quán)神授”的觀念一經(jīng)打破,隨之而來(lái)的影響是任何民眾都可質(zhì)疑君主王位獲得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從而自擁稱王。克勞狄斯深知自己的王位既非“繼承”亦非“神授”,而是“竊取”,擔(dān)心雷歐提斯為父報(bào)仇的舉動(dòng)演變成顛覆其王位的民變,他立馬想到轉(zhuǎn)嫁矛盾,將雷歐提斯的怒火引向他處。面對(duì)雷歐提斯對(duì)父親死因的追問(wèn),王后為他開(kāi)脫的說(shuō)辭是,“但是并不是他殺死的”,減弱了雷歐提斯對(duì)克勞狄斯的憤怒,避免了一場(chǎng)由情緒沖動(dòng)可能發(fā)生的殺戮。依靠王后為其開(kāi)脫之詞,奸猾狡詐的克勞狄斯順勢(shì)引導(dǎo)他將憤怒的矛頭直指他的心頭大患——哈姆萊特。雷歐提斯報(bào)仇心切,正是克勞狄斯的所需,克勞狄斯終于為自己找到了消除心中隱患的工具,他接下來(lái)想要看到的是:這件“工具”能在比劍中刺中他的“心頭大患”。
因王后的指證和克勞狄斯的挑撥,雷歐提斯的復(fù)仇怒火開(kāi)始指向哈姆萊特。為自己全面開(kāi)脫,克勞狄斯揚(yáng)言以國(guó)土、王冠甚至生命為代價(jià)來(lái)證明自己的清白。他的言說(shuō)不僅是其為掩蓋心虛的狡詐之舉,而且反映出其本性中的愚蠢。接此,他趁勢(shì)以言語(yǔ)引導(dǎo)雷歐提斯將復(fù)仇目標(biāo)鎖定為真兇,真實(shí)目的則是:“可是他們假如認(rèn)為我是無(wú)罪的,那么你必須答應(yīng)助我一臂之力,讓我們倆開(kāi)誠(chéng)合作,定出一個(gè)懲兇的方案來(lái)。”[5]420身為大權(quán)獨(dú)攬的一國(guó)之君,他的言說(shuō)似乎不合常理,但仔細(xì)推敲,我們從此中可再識(shí)克勞狄斯的狡詐:在王位不穩(wěn)之際,他不能親自下令拘殺王后唯一的兒子,否則,這會(huì)使他失去到手的一切并暴露他的罪惡和陰謀。借他人之手除去哈姆萊特才是克勞狄斯玩弄陰謀的高明之處,同時(shí)也是他奸佞狡詐本性的體現(xiàn)。
(二)行徑偽裝
老哈姆萊特在位時(shí),克勞狄斯用盡心機(jī)偽裝忠于王兄,伺機(jī)對(duì)其施行謀害,終于得手。在由王親走上王位后的短暫時(shí)日里,克勞狄斯統(tǒng)治下的丹麥卻已充滿了人與人之間相互猜忌的風(fēng)氣:克勞狄斯對(duì)哈姆萊特充滿戒心,一直保持高度警惕,唯恐他知道了自己弒君篡位的底細(xì)而揭露真相并實(shí)施復(fù)仇;克勞狄斯對(duì)哈姆萊特以假恩虛惠收買不成,轉(zhuǎn)而動(dòng)了殺機(jī),將他派去英國(guó),名為“追索延宕未納的貢物”,實(shí)為一路被監(jiān)視下去受死,喬特魯?shù)聟s對(duì)克勞狄斯加害兒子的陰謀毫不知情;羅森格蘭茲和吉爾登斯吞對(duì)所傳國(guó)書(shū)的內(nèi)容全然不知,結(jié)果稀里糊涂地雙雙命喪英倫。此外克勞狄斯還為哈姆萊特與雷歐提斯的決斗設(shè)置了三道鬼門關(guān)(劍頭開(kāi)刃、劍刃蘸毒、備下毒酒),以取得一石二鳥(niǎo)的殺人效果。喬特魯?shù)聦?duì)克勞狄斯所設(shè)計(jì)的連環(huán)圈套全然無(wú)知,終而被害。
克勞狄斯施政伊始就在丹麥王宮大行窺探之風(fēng),哈姆萊特被他視為心頭大患。他投入最多時(shí)間和最大精力去探知哈姆萊特的行蹤言跡,使用各種手段探知哈姆萊特裝瘋中的言說(shuō)行止,從而猜中他的真正動(dòng)機(jī)以便做出及時(shí)應(yīng)對(duì):他應(yīng)允波洛涅斯安排女兒與哈姆萊特談話,以便掌握哈姆萊特的心理動(dòng)態(tài);接受波洛涅斯的建議由喬特魯特找兒子談話,以便獲得哈姆萊特在充滿母子親情的交談?wù)Z境下吐露的真實(shí)心境;羅森克蘭茲和吉爾登斯吞被特召回國(guó)充當(dāng)密探,按克勞狄斯的旨意窺探老同學(xué)的內(nèi)心世界。作為反制,哈姆萊特則以偽裝瘋癲作為防身之器,以使克勞狄斯放松對(duì)自己的警惕,給自己留下時(shí)空伺機(jī)復(fù)仇;他借此安排巡演戲班排演《貢扎古之死》,以戲中戲來(lái)從旁窺探克勞狄斯對(duì)劇中弒君情節(jié)的反應(yīng),從而確認(rèn)了鬼魂所說(shuō)為真實(shí)發(fā)生過(guò)的事件。
面對(duì)怒不可遏復(fù)仇心切的雷歐提斯,克勞狄斯心理空虛、底氣不足,只得自降身份,裝出一副“可憐”和“無(wú)辜”的嘴臉,親自告訴雷歐提斯殺父的真兇是誰(shuí),并告訴他哈姆萊特也在圖謀他的性命,并訴說(shuō)他不能以殺人罪對(duì)哈姆萊特施以懲咎的理由——他與王后喬特魯?shù)聜窝b的難分難舍的感情和哈姆萊特深受民眾的愛(ài)戴。
克勞狄斯一直畏懼的不僅僅是哈姆萊特本人,而是一旦失去王后的聯(lián)盟就會(huì)喪失王權(quán),導(dǎo)致民心不穩(wěn)、民情不安定而王位不保。雷歐提斯因復(fù)仇而振臂一呼,即喚起了民眾有力地證明了這一可能性的存在。終而,一場(chǎng)夾雜為父復(fù)仇和質(zhì)疑君權(quán)的大規(guī)模叛亂,就降格成了一次小型貴族私仇決斗。
哈姆萊特偶然看到克勞狄斯寫(xiě)給英國(guó)國(guó)王的信,從而成功跳脫出克勞狄斯為他預(yù)設(shè)的第一個(gè)死亡陷阱。哈姆萊特的突然返回使得使克勞狄斯驚愕了片刻。他一邊喃喃自語(yǔ):“要是果然這樣的話,可是怎么會(huì)這樣呢?然而,此外又如何解釋呢?”[5]428一邊思索著自己的縝密計(jì)劃何以被哈姆萊特破解的原因。狡詐的克勞狄斯對(duì)此迅速作出了反應(yīng),利用雷歐提斯的復(fù)仇心切,再一次為哈姆萊特設(shè)下陷阱,只需他對(duì)此陷阱稍加掩飾就可將哈姆萊特置于死地而自己還可脫離干系,達(dá)到既可蒙蔽王后又能避免引發(fā)民亂的目的。他為此慶幸:雷歐提斯的出現(xiàn)為自己找到了除掉哈姆萊特的工具,再一次為哈姆萊特設(shè)下了死亡陷阱。此外,克勞狄斯使用直接或間接的方式肯定雷歐提斯的高超劍術(shù),雷歐提斯準(zhǔn)備好了與哈姆萊特兵刃相見(jiàn)。
垂直運(yùn)輸采用懸臂式桅桿配以3 t卷?yè)P(yáng)機(jī)。將桅桿與煙囪里側(cè)的兩層操作平臺(tái)的橫桿固定到一塊,以增強(qiáng)其穩(wěn)定性。
在克勞狄斯提議劍斗之外,雷歐提斯內(nèi)心邪惡占據(jù)上風(fēng),準(zhǔn)備再在劍刃上涂上致命的毒藥以增加成功率。克勞狄斯還吸取此前借刀殺人未遂的教訓(xùn),設(shè)計(jì)了一條連環(huán)計(jì):“為了預(yù)防失敗起見(jiàn),我們應(yīng)該另外再想個(gè)萬(wàn)全之計(jì)。”他的萬(wàn)全之計(jì)是:“我就為他準(zhǔn)備好一杯毒酒,萬(wàn)一他逃過(guò)了你的毒劍,只要他讓酒沾唇,我們的目的也就同樣達(dá)到了。”[5]435-436克勞狄斯奸謀的深層目的是取得“一石二鳥(niǎo)”的結(jié)果——為哈姆萊特挖好了連環(huán)陷阱,也為犯下引導(dǎo)民眾暴動(dòng)的雷歐提斯準(zhǔn)備好了結(jié)局。
三、克勞狄斯偽裝的后果
戲班子的到來(lái)為哈姆萊特提供了證實(shí)復(fù)仇對(duì)象的契機(jī)。戲中戲激起了克勞狄斯的驚悸和恐懼,同時(shí)激活了他的靈魂深處的人性。在克勞狄斯的意識(shí)里,“花園謀殺”又一次浮現(xiàn)在眼前,他為自己的罪惡行徑懺悔,對(duì)自己的良心予以譴責(zé)。但是,克勞狄斯的本性是貪婪的、虛偽的和陰險(xiǎn)的,他不會(huì)以宗教信條和道德規(guī)范約束自己以及行為,他的欲望是永遠(yuǎn)擁有已有的利益,且心中的欲火既已燃起,就難以熄滅。
(一)政治影響
經(jīng)哈姆萊特改動(dòng)的《貢扎古之死》(更名《捕鼠器》)展現(xiàn)在艾爾西諾王庭,當(dāng)啞劇情節(jié)推進(jìn)到扮演琉西安納斯(Lucianus)的伶人將一種毒液佯裝滴進(jìn)正在酣睡中的國(guó)王(貢扎古)扮演者的耳朵中時(shí),哈姆萊特期望見(jiàn)到的戲外戲出現(xiàn)了:克勞斯斯驚恐萬(wàn)狀,臉色煞白,頓然站起身來(lái),大喊著“給我點(diǎn)起火把來(lái)”[5]346。此呼喊嚇壞了在旁的王后喬特魯?shù)拢团惆橛^劇的群臣,波洛涅斯喝令伶人:“不要再演下去了”[5]346。臺(tái)上的毒殺情景以及伶王伶后的肉麻對(duì)白打破臺(tái)下觀眾的平靜,徹底擊垮了克勞狄斯的心理防線,揭開(kāi)了克勞狄斯的偽裝臉孔,迫使他露出了驚恐萬(wàn)狀的真容。哈姆萊特以戲中戲驗(yàn)證了鬼魂申述事件的真實(shí)存在,明確了復(fù)仇的對(duì)象,堅(jiān)定了復(fù)仇的決心。而克勞狄斯在驚悸和憤怒之后,暗暗堅(jiān)定了除掉哈姆萊特的決心,決定加速實(shí)施殘害哈姆萊特的行動(dòng)。一場(chǎng)復(fù)仇和反復(fù)仇的斗爭(zhēng)拉開(kāi)了序幕。
中止觀劇后,克勞狄斯的心情無(wú)法平靜。他下令讓哈姆萊特立即離開(kāi)丹麥前往英國(guó),以中止來(lái)自他的公然威脅。此時(shí),當(dāng)年的謀殺場(chǎng)景浮現(xiàn)在他的眼前:王宮后花園的正午陽(yáng)光,大樹(shù)覆蓋下的陰涼處所,躺著在花坪上睡熟的王兄,他憋住呼吸,悄然地溜到王兄的身邊,輕聲呼喚數(shù)聲,見(jiàn)王兄未有反應(yīng)便從懷中掏出那瓶罪惡的毒液,給自己鼓上勁定好神,將毒液滴入王兄的右耳……。此時(shí),“滴毒入耳”的意象不斷在克勞狄斯腦海中浮現(xiàn),不斷提醒克勞狄斯所使用過(guò)的蒙蔽朝臣視聽(tīng)的伎倆。“滴毒入耳”具有具體和抽象雙重含義:一指毒藥滴入老哈姆萊特的耳朵,摧毀他的身體,致使他的凋亡;二指克勞狄斯偽裝的言行和托詞麻痹了群臣,“使得整個(gè)王庭又聾又瞎”,政務(wù)出現(xiàn)紊亂,政體趨于癱瘓[7]114。《捕鼠器》演出的舞臺(tái)變成了政治法庭,演員成了控訴方,觀眾都成了法庭上的陪審團(tuán),臺(tái)上臺(tái)下對(duì)克勞狄斯的所作所為進(jìn)行控訴、揭露和審判。克勞狄斯不敢再往下追憶,他的心靈在震蕩,他的人性在回歸。
(二)偽裝的懺悔
震撼之余,克勞狄斯的人性有所回歸,開(kāi)始懺悔,對(duì)上天坦言:“哦,我的罪惡的戾氣已經(jīng)上達(dá)于天;我的靈魂上負(fù)著一個(gè)原始以來(lái)的詛咒。”[5]358-359克勞狄斯此時(shí)感到用罪惡換來(lái)的王位像一朵帶刺的薔薇,感到自己所犯罪行已為天地不容,呼喚道:“我因?yàn)椴恢缿?yīng)該從什么地方下手而徘徊歧途,結(jié)果反弄得一事無(wú)成。”[5]359他把罪惡歸為自己的墮落,向天空伸出那只種下罪惡之果的手:“要是這只可詛咒的手上染滿了一層比它本身還厚的兄弟的血,難道天上所有的甘霖,都不能把它洗滌得像雪一樣潔白嗎?”③[5]359
但克勞狄斯的欲火不能熄滅,到手的俗物難以舍棄:“現(xiàn)在還占有著那些引起我的犯罪動(dòng)機(jī)的目的物;我的王冠、我的野心和我的王后。非分攫取的利益還在手里,就可以幸邀寬恕嗎?”[5]360他試圖以祈禱來(lái)減輕罪惡感,以懺悔救贖自己,一方面安撫因戲中戲演出引發(fā)的自我良心譴責(zé),另一方面從心理規(guī)避因罪行而衍生的懲罰。他既貪婪又現(xiàn)實(shí),深知只能去擁有現(xiàn)在,他懺悔的言語(yǔ)只能“滯留在地上”,而“永遠(yuǎn)不會(huì)上達(dá)天界。”[5]363克勞狄斯不愿屈下“頑強(qiáng)的膝蓋”向上天祈禱,他不能丟棄運(yùn)用偽裝和罪惡行徑奪來(lái)的一切,他要繼續(xù)統(tǒng)治這一方國(guó)民,他至死認(rèn)為,只要再發(fā)動(dòng)一場(chǎng)博弈,就能消除心中的大患,就可享受已在手中的“利益”。
注釋:
①引文譯文選自朱生豪先生的《莎士比亞全集》(六卷本),作者略作改動(dòng)。英文版《哈姆萊特》選用湯普森和泰勒注釋的阿登版(2016),并在戲劇文本引文規(guī)范的基礎(chǔ)上做了調(diào)整,將原本的幕次、場(chǎng)次以及行數(shù)替換為頁(yè)碼。全文中引文標(biāo)注對(duì)應(yīng)英文版《哈姆萊特》頁(yè)碼。
②小福丁布拉斯率兵去爭(zhēng)奪的是“一小塊徒有虛名毫無(wú)實(shí)利的荒瘠土地”,而波蘭人為保疆衛(wèi)國(guó),早已布防好了以迎擊來(lái)犯之?dāng)场U鞣ケ緹o(wú)意義且代價(jià)巨大,借道只是幌子。挪威軍隊(duì)的真實(shí)意圖在劇末得到印證:小福丁布拉斯從波蘭班師道經(jīng)艾西諾城堡,正值丹麥宮廷中一片慘景,他輕易獲得的不僅僅是父親當(dāng)年輸?shù)舻耐恋兀钦麄€(gè)丹麥國(guó)。
③《麥克白》中有類似的話語(yǔ),如:殺害了鄧肯的麥克白心虛氣短,帶有負(fù)罪感時(shí)懺悔道:“大洋里所有的水,能夠洗凈我手上的血跡嗎?不,恐怕我這一手的血,倒要把一碧無(wú)垠的海水染成一片殷紅呢。”麥克白的此句懺悔曾是文學(xué)批評(píng)的對(duì)象,原文中的詞語(yǔ)被語(yǔ)言學(xué)者作為研究早期現(xiàn)代英語(yǔ)的范例。從寫(xiě)作年代考查《哈姆萊特》寫(xiě)于1601-1602年期間,《麥克白》則為1606年,那么,后者在前者的基礎(chǔ)上有所提升,顯得更有氣勢(shì)。但同一意思的不同說(shuō)辭也體現(xiàn)了人物在性格上的差異和因身份不同而行為方式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