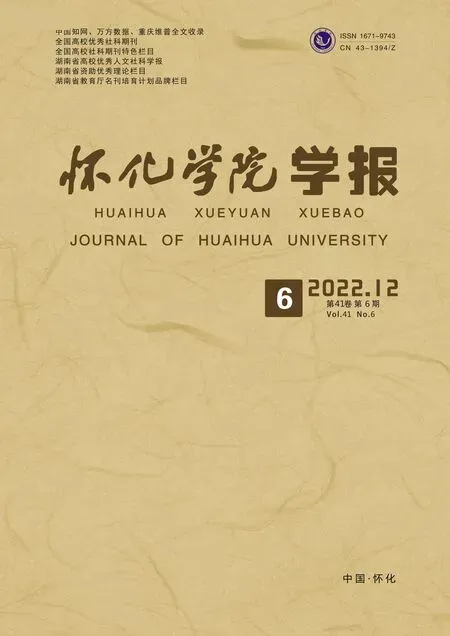《閱微草堂筆記》近二十年研究綜述
陳宏娟, 王 琳, 吳 波
(1.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湖南 長沙 410013; 2.湖南農業大學人文與外語學院,湖南 長沙 410128)
《閱微草堂筆記》作為中國文言小說史鏈條上不可或缺的一環,學術界對其研究的關注度卻經歷了一個由低到高的動態過程。自其成書出現至20 世紀80年代以前,除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對《閱微草堂筆記》有過專題性論述外,其研究更多的是附著在“仿聊齋”類型作品的只言片語式列舉。但20 世紀80年代以后,受改革開放思潮的影響,學術領域煥發出新的面貌與活力,學界對于《閱微草堂筆記》的研究也呈現出回溫態勢,首先是紀昀及《閱微草堂筆記》的價值受到學者們的青睞,各種具有創新性和學識性的論文不斷涌現;其次還出現了一系列的研究專著,比如吳波先生撰著的《〈閱微草堂筆記〉〉研究》因其具備“視野寬闊,論說全面,鉤沉抉隱,新見迭出”[1]等特點,在學術專著中具有顯著意義。總結近二十年來《閱微草堂筆記》的研究歷程,創獲頗多,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系統論述。
一、創作主體研究細致深入
對一部具備文學“四要素”的小說作品而言,創作主體自身要素的研究顯得尤為重要。21 世紀以來,學者們著眼于紀昀的生平經歷、學術思想以及創作心態等問題陸續發表論文、專著,這為《閱微草堂筆記》研究提供了充分的條件。
(一)紀昀家世生平與《閱微草堂筆記》關系研究
自20 世紀80年代以來,研究紀昀的文章有增無減。周積明先生撰寫的《紀昀評傳》一書,在“生平篇”中詳細地記述了紀昀的生平事跡,但關于紀昀家世生平與其創作《閱微草堂筆記》之間的關系,所涉論述并不多。吳波先生則通過對文獻資料爬梳,在其撰寫的《紀昀的家世及其對〈閱微草堂筆記〉創作的影響》一文中就家族影響與紀昀創作《閱微草堂筆記》的關系進行了深入且翔實的論述,指出:一方面崇實黜虛、經時濟世、崇尚儒學、恪守禮法,重人事、輕天道的家族思想對紀昀創作有很大影響;另一方面紀氏家族事跡又是《閱微草堂筆記》重要的題材來源。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學者還關注到紀昀編修經歷對其創作《閱微草堂筆記》的影響,周廣玲[2]便從創作時間以及皇權至上兩個思路深入分析了紀昀編修經歷形成的價值觀對《閱微草堂筆記》所構建的社會、政治的影響。這為作家作品研究拓寬了思路,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學者分別從紀昀的家世、生平行實等方面來更深入地研究《閱微草堂筆記》,角度多樣,論證充分。
(二)紀昀創作心態與《閱微草堂筆記》關系研究
紀昀從一開始斥責小說“誣蔓失真”“猥鄙荒誕”到晚年有意識地作起小說,這一變化就不得不提到其晚年創作心態的轉變。學者們沿著這一思路,對個中原因進行思考。首先一點,認為其親友的相繼離世讓他感到孤獨與悲傷,周積明先生在《紀昀評傳》中詳細論述了與其一起編修《四庫全書》的好友如戴震等相繼離世對其打擊之大。其次,皇權至上時期位極人臣的心理壓力,這一點吳波先生指出:紀昀的心理壓力主要來自乾隆皇帝以及當時同朝為官的同僚們,《閱微草堂筆記》就是這種境遇與心境下的產物[3]。這種君臣之間矛盾而又復雜的關系,加深了紀昀小說創作的動機。該文對紀昀的晚年心態進行了深入的挖掘,此后不少學者就這一點進行挖掘,如宋世瑞在其相關論文中就創作心態的原因論述基本沿襲了吳波先生的觀點,但進一步分析了其在創作中的應對策略。最后,日益激化的社會矛盾促使其進行小說創作,紀昀作為一個懷有濟世之心的知識分子,創作《閱微草堂筆記》不可避免地帶有某種社會目的,很多學者在其論述中都能關注到其所處的時代背景,所以在關涉思想內蘊的研究過程中,很多學者把《閱微草堂筆記》看成是“勸懲”之作。
(三)紀昀學術思想與《閱微草堂筆記》關系研究
在“考據”與“義理”并重的乾嘉學風的多重影響下,紀昀往往以學者的態度從事小說創作。顧芃森[4]從思想和創作模式兩個方面深入探究了“紀昀‘崇經’‘重考據’的學術思想,與‘乾嘉學派’的治學思想與方法的同源性。”這對從外因解釋《閱微草堂筆記》中的學術思想以及學術價值具有重要意義。針對紀昀創作《閱微草堂筆記》的小說觀,據不完全統計近二十年來研究論文達20 余篇,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學者宋世勇認為紀昀的小說創作不是徹底反對虛構,而是建立在“理”的基礎上的。此后,董昕瑜、許彰明、于潔等人的研究成果都關注到紀昀將筆記小說劃歸子部的這一事實,對紀昀的小說理論進行了全面的研究,從而對《閱微草堂筆記》的創作進行準確的把握。這里值得一提的是陳文新在《文言小說審美發展史》中對紀昀將筆記小說劃為子部的三點考慮:針對傳奇體小說和宋以降的白話小說,清理筆記小說,保持其純潔性;對筆記小說的虛構內容有一定程度的認可;負有“議”即知道生活的責任[5]。基于這些理論研究,將有助于我們更好地把握紀昀的學術思想以及《閱微草堂筆記》勸懲意識和虛構創作的特點。
二、文本解讀的多重文化趨勢
21 世紀以來,學者們更多著眼于文本解讀,對《閱微草堂筆記》的研究在廣度和深度方面,較之前都是有所發展的,甚至呈現出跨文化研究態勢。
(一)《閱微草堂筆記》中的宗教文化研究
21 世紀以來,有關文本中宗教文化的研究得到更多關注。此類研究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方面:一類是對其涉及宗教內容的分類評述,如焦泰平和楊亮等人的相關論文,對“因果報應”故事進行分類評述并討論紀昀小說創作的真實目的。這類文章在對內容的梳理層面為后來學者從事相關研究打下了基礎。一類是將《閱微草堂筆記》中表現出的宗教思想作為研究的著眼點。如韓希明先生的《試論〈閱微草堂筆記〉的宗教觀》[6]一文客觀分析了作品對儒釋道諸教內容的態度,認為其奉儒學為至尊,以佛教和道教為其補充,肯定了《閱微草堂筆記》中宗教對于民眾的教化作用,但對其流于說教的原因闡述過于簡略。最后一類是從宗教與文學、文化的關系層面進行研究,蔣小平撰寫的《雍容·有益人心·儒道佛整合——〈閱微草堂筆記〉之三層解讀》,運用英國伽登文學作品分層理論,將《閱微草堂筆記》由表及里分為五個層次,闡釋了《閱微草堂筆記》在雍容外表下是有益人心的形象觀念層面和儒道佛整合的目的,是一篇比較有深度的文章,對其他學者的研究具有啟發性意義。總而言之,《閱微草堂筆記》的宗教文化內容對于研究紀昀及其周圍文人的宗教文化觀,當時宗教存在的狀態等重要性不容小覷,之后的學術研究仍然具有研究空間。
(二)《閱微草堂筆記》中的社會倫理研究
中國傳統文化本質上是進行民眾教化,因而《閱微草堂筆記》中“勸懲”的政治理想,具有強烈的倫理道德色彩。在這一文化闡釋研究視角下,韓希明先生系列論文便深入探討了《閱微草堂筆記》對文人精神的批判,認為《閱微草堂筆記》于倫理道德問題雖有變通,但不離正統之初衷。韓希明先生孜孜不倦地對《閱微草堂筆記》中關涉社會倫理的內容進行解讀與挖掘,基于此類既得成果,推動了不少研究者對這一文化闡釋的關注,如何天杰先生在《倫理道德的悖論——從〈閱微草堂筆記〉非道德化的一面說起》[7]一文關注到《閱微草堂筆記》中與紀昀創作目的不相統一的“非道德”化的東西,認為《閱微草堂筆記》揭示了道德架構自身的矛盾,但并非向必然與合理性進行責難,該文為社會倫理學研究提供了一個殊途同歸的思路。與上述不同的是,有學者注意到《閱微草堂筆記》對正統合理性之發難,如姜素媛等肯定了《閱微草堂筆記》對傳統倫理道德的質疑,認為紀昀是借助倫理道德來緩和社會矛盾。總之,通過《閱微草堂筆記》所構建的社會風貌,可以體察封建末世傳統倫理道德松弛的趨向,對社會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三)《閱微草堂筆記》中的狐妖文化研究
《閱微草堂筆記》文本中涉及狐仙筆記的多達130 多篇,進入21 世紀,關于《閱微草堂筆記》中的狐妖研究仍然不絕如縷,總結起來大致可以分為兩類研究層面,一類是集中在“狐”內容的分析和思想傾向的評價上,認為紀昀借狐妖影射現實,構建理想社會。如王琪玖、周明華和張思莉等人的早期論文都持此觀點,他們通過探討狐的來源、修煉及禁忌和形象特征等若干方面,分析其對清代社會本質的抨擊。但上述更多的是從內容層面分析,涉及狐文化的審美藝術所述不多。一類是從文學和文化的雙重角度闡述狐妖形象所代表的文化意蘊,吳波認為“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中精心塑造狐貍這一形象,實際上是借此為載體,寄寓他對于整飭現有秩序,呼喚傳統道德與人文精神回歸的理想的渴望。”[8]在這之后依然有不少研究論文就狐與人類世界的關系進行孜孜不倦的探討,但沒有跳出前面學者的觀點,創新價值有限。
(四)《閱微草堂筆記》中的民俗文化研究
《閱微草堂筆記》文本中涉及很多城隍傳說、民間故事等內容,使得民俗文化的研究占有一定空間,因此很多學者著重于探究其中的民俗傳統和鄉土風情。筆者通過梳理發現,研究民俗更多的是為探究倫理施教服務。如魏曉紅先生分別在《〈閱微草堂筆記〉中的城隍故事分析》、《淺談〈閱微草堂筆記〉中的雷神》和《論〈閱微草堂筆記〉中扶乩與文人士大夫生活》三篇文章中深入分析了《閱微草堂筆記》的城隍神崇拜、雷神崇拜以及扶乩文化所蘊含的民俗文化,進而揭示出紀昀筆下古老的故事類型是以民間文學的表現手法,達到委婉諷刺與勸懲的目的。近年來,對于《閱微草堂筆記》民俗文化的研究過程,我們可以發現其呈現出專門化和細致化的特征。“專門化”表現在出現了不少直接以民俗作為整體研究的碩士論文,較早關注的是張思莉《論紀昀筆下的民俗》一文,該文不是簡單的演繹民俗文化,而是看到了《閱微草堂筆記》所抒發的人文情懷。魏曉紅博士的論文《〈閱微草堂筆記〉研究》在研究《閱微草堂筆記》民俗故事演進的同時,也在不斷考察其中主題的流變,這有利于更好地了解民俗全貌。上述幾篇學位論文都具有一定的文獻和理論價值,為《閱微草堂筆記》研究奠定了基礎。“細致化”是指除去古老的主題外,更有從夢境、婚嫁詞語、“放焰口”施食惡鬼等故事角度分析民俗文化,如張偉麗的《清代民俗化特征及其成因——以〈閱微草堂筆記〉為中心》不失為一篇由點及面,展示“放焰口”民俗的佳作。
(五)《閱微草堂筆記》中的地域文化研究
《閱微草堂筆記》中的地域書寫更多的是對滄州、西域、新疆的自然風情的描寫,對這一文本的研究將涉及文獻學、民俗學、文學、歷史學、傳播學等多個學科。關于新疆書寫,一開始學者們是以研究《烏魯木齊雜詩》為主,以《閱微草堂筆記》作為補充論證。近二十年來,學界逐漸將二者相對照,結合起來研究。吳波先生在其論文中說:“《烏魯木齊雜詩》以豐富見長,但多粉飾之意,《閱微草堂筆記》以深刻取勝,真實而頗見洞察力”[9]。吳波先生高度肯定了西域之行對其將邊疆的地域風情攬入筆記小說中的意義。李辰則從新聞傳播的角度看《閱微草堂筆記》對新疆地區風土人情的介紹,開辟了一個新的研究點。
三、文體敘事研究的深入與新變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所述:“惟紀昀本長文筆,多見秘書,又襟懷夷曠,故凡測鬼神之情狀,發人間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見者,雋思妙語,時足解頤;間雜考辨,亦有灼見。”[10]168這種文體的敘事傾向,一直都受到學者的廣泛關注,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關于文體敘事研究仍然是學界的關注點,并且呈現出中西敘事理論合流的趨勢。
(一)文體敘事研究的深入
紀昀作為一個著書家,在創作《閱微草堂筆記》時極力摒棄文采雕琢的“炫才小說”,追求“尚質主理”的“學人小說”,表現出了不同以往的獨特風格。因此,采用中國傳統敘事角度進行研究也取得了頗豐的成果。一是多以紀昀小說觀作為邏輯起點分析其風格的形成,就成因探尋而言,論者從社會心理進行探討,認為是受復古的社會思潮影響,或將其歸結為是一種“體卑的心態”;就敘事得失而言,論者普遍認為其拘泥于所謂的“著書者之筆”,缺乏一種空靈與圓潤。二是將其置于中國古代文言小說發展的歷史進程中,通過對魏晉志怪與唐宋傳奇等小說類型的比較中分析其文體風貌,認為它追蹤晉宋,具有質樸凝練、簡淡妙遠的敘事風格。龍鋼華和陳文新都認為《閱微草堂筆記》以子部議論為宗,陳文新還作了深入分析,認為《閱微草堂筆記》是一部不同于傳奇小說的“淵源于子部敘事傳統的經典”[11],關注到其“在敘事上反對過度虛構,敘述服務于議論,用簡淡數言的方式陳述故事梗概”與“傳奇小說的區別是鮮明的”。其致力于建立與完善子部小說的敘事規范,這一研究具有較強的新穎性和學術價值。
(二)文體敘事研究的新變
隨著新世紀西方小說理論研究不斷取得新進展,不少學者著眼于現代小說觀,因而對紀昀的敘事方法提出了褒貶不一的看法。一部分學者看到《閱微草堂筆記》的敘事模式與西方敘事學的一致性而給予褒揚,如楊義的《〈閱微草堂筆記〉的敘事智慧》[12]一文論述了《閱微草堂筆記》具有西方文藝理論中的“元小說”特征——所謂“反文學、或超文學的敘事方式”新意迭出,令人耳目一新。當然,也有一部分學者對其敘事方法提出批評,認為非敘事化的特點不構成小說文體形式。陳中偉在《〈閱微草堂筆記〉的敘事視角》等相關論文中認為《閱微草堂筆記》在對情節和線索敘事化的要求上呈現出“敘事視角的異化”特征。這是對紀昀小說觀批評得較為嚴重的一種觀點了。也有學者就學界對《閱微草堂筆記》文體敘事的辯駁,提出中肯的見地,如張泓《〈閱微草堂筆記〉文體辨析》一文認為“應該把我國古代‘小說’中符合中西小說觀的作品加以區分,采用不同的評價標準,才不會有失公允。”[13]這一觀點不但對《閱微草堂筆記》研究具有借鑒意義,對我們從事中國古代小說研究都具有啟發意義。
四、版本與評點研究新發現
《閱微草堂筆記》自成書起,在傳播的過程中衍生出了眾多的版本和評點。就版本與評點的梳理對《閱微草堂筆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然而21 世紀以前關于這一方面的研究處于缺失的狀態,之后學者關注到這一問題,尤其是隨著新材料與新文獻的發現,更加推動了版本與評點研究的價值,取得了一些顯著的成就。
(一)版本問題研究
不同的版本對研究小說原貌存在一定的影響,版本問題成為疏通其他研究的一個基本點。學者們越來越意識到對其動態爬梳的重要性,以往關于版本研究的論文更多的是就不同時期版本的簡單羅列,關于各個版本之間的差別與聯系則鮮少論及,北大胡光明先生則在其《〈閱微草堂筆記〉的版本與評點研究》參考王穎的劃分,從時空維度將之大致分為三個段落:“單種抄本、刻本的分寫流傳,五種合刻本之流傳,從選本產生到多種版本形式。”并且細致梳理各種合刻本之間的版本源流關系,對于窺見版本的全貌具有重要的意義。梁振剛先生利用數據統計的方法,首次將研究視角投向境外,對海外的版本流傳情況也做了統計追溯。文章論據詳實,極具說服力,足見《閱微草堂筆記》在海內外已形成了較為廣泛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吳波先生在對版本問題的關注與研究過程中,展現出其對新材料發現與運用的敏銳學識,其撰文《國家圖書館藏〈灤陽消夏錄〉單行抄本及其文獻價值》,通過文獻對比得出“該抄本是《閱微草堂筆記》版本體系中最早、最原始、最能夠反映出創作原貌的本子”;“對于了解《閱微草堂筆記》及紀昀的思想創作過程具有重要的作用”[14]。該文的發表,對于學界及專家致力于研究紀昀思想等方面提供了又一新證據,將《閱微草堂筆記》的研究又向前推進了一步。
(二)評點問題研究
關于《閱微草堂筆記》的評點研究,與其他研究的大量論文和著作相比,則略顯冷落。較早關注的有吳波和胡光明兩位學者。首先,胡光明先生的碩士論文在第一部分對《閱微草堂筆記》的版本狀況進行考察之后,進一步考察了《閱微草堂筆記》評點的狀況,對不同評點本反映的社會價值進行了深入闡釋,這是對《閱微草堂筆記》評點的一次較為全面的梳理與總結。與此同時,吳波先生在《〈閱微草堂筆記〉“四大家”評點論略》一文中指出,“自嘉慶年間以來,坊間對《閱微草堂筆記》的評點亦概不少見,而最為突出的則是徐捷、翁也存、徐時棟、王伯恭四家。”同時還對四家評點進行了說明,吳波先生概覽式的研究,為學者們研究《閱微草堂筆記》的評點提供了思路和角度,具有很強的學術價值。近期,吳波先生和肖新華先生立足于新文獻,合力撰寫《新發現天津圖書館藏“秋皋”評點〈閱微草堂筆記〉殘卷論析》一文,指出“秋皋”評點在目前所能見及的諸家評點中字數最多、體量最大、內容最為豐富。這打破了以往學界提出以“四大家”評論為宗的觀念。該文對新文獻的挖掘更加證實了《閱微草堂筆記》在當時社會中的影響并不遜色于《聊齋志異》等小說,以及它在中國小說批評發展進程中的重要一步。總體而言,雖然《閱微草堂筆記》的評點研究得到了部分學者的重視,但仍然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課題。
五、相關作品的比較研究
21 世紀以前,《閱微草堂筆記》與同類作品的比較研究已經屢見不鮮了,然而近二十年來關于其與同類作品的比較研究仍然是學界關注的熱點之一。比較對象除了熱門的《聊齋志異》外,還包括《新齊諧》、六朝志怪小說以及外國小說等。
據不完全統計,此時期關于《閱微草堂筆記》與《聊齋志異》的比較研究達30 余篇,涉及思想內容、作家心態、藝術特色與美學風格、形象研究等眾多方面。就思想內容而言,其在眾多論文中都有表達,總結一下便無外乎《聊齋志異》是蒲松齡寄托孤憤之作,而《閱微草堂筆記》是宣揚封建倫理道德,勸善懲惡之作。就作家創作動機而言,吳波先生在學術論文中就二者藝術特色及美學風格進行了論述,從而得出“《閱微草堂筆記》是一部‘勸懲遣懷’之作,富于濃郁的文化氣息,而《聊齋志異》是一部‘孤憤’之書,表現的是強烈的‘平民意識’”[15]這一結論。近年來對于二者的形象研究包括商人、文人、鬼狐、下層文人、妒婦悍妻形象、塾師形象等眾多方面,但更多的還是停留在文本解讀的層面,理論深度與創新意義不足。
早在20 世紀20年代,魯迅先生在其《中國小說史略》論及《閱微草堂筆記》時就說該書是“尚質黜華,追蹤晉宋。”[10]168這一觀點對21 世紀著眼于二者研究的學者具有啟發性意義,吳波先生從追蹤晉宋與踵事增華兩方面進行比較。在論述中更是充分肯定《閱微草堂筆記》對魏晉小說的超越,認為其立足于現實,更講究章法,讀起來更富有韻味,這些觀點的提出不乏膽識與創新。在此之后,關于二者的比較,在研究觀點上形成了吳波先生這樣的一個共識,而更多的是在研究思路上進行發揮,如王文君的碩士論文《〈閱微草堂筆記〉與六朝筆記小說比較研究》附以闡釋學、接受美學、敘事學等理論為支撐,對二者作縱向比較。《閱微草堂筆記》與六朝志怪小說關系研究,體現了中國文言小說在發展過程中的一種繼承與創新的內在要求。
關于《閱微草堂筆記》與《新齊諧》這兩部文言筆記小說的比較研究進入新世紀才逐漸成為研究熱點。何懿率先運用新的文化視野從題材,作者思想和藝術風格三方面對二者進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這對后來學者們正確認識二者價值,比較得失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借鑒作用。此后,學界對二者的比較由宏觀向微觀比較研究發展,有揭示其反理學的不同,如張泓《〈閱微草堂筆記〉與〈子不語〉反理學傾向之異同》;還有學者就二者所構建的鬼神世界進行比較,如袁靜君《〈新齊諧〉和〈閱微草堂筆記〉鬼神世界對比研究》一文對二書中的鬼神題材展開專項研究,打破傳統研究集中在思想價值、藝術特色、比較研究的層面,豐富了作者小說觀、鬼神觀等其他方面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
隨著比較文學研究方法的興起,有論者將《閱微草堂筆記》與外國文學作品進行比較,張國清的《中西作品中狐形象—〈閱微草堂筆記〉與〈伊索寓言〉之比較》和張森的《熱忱與冷峻的背后—〈老實人〉和〈閱微草堂筆〉的文化意蘊初探》為有代表性的兩篇學術文章,前者從“狐”形象的差異性著眼,小中見大。后者則從作家對社會的批判方式入手,體會附著在文學作品背后的理想、情感、心態等方面既相似又不同的文化意蘊。二人以比較文學的眼光拓寬了研究的思路,為后來學界相關比較研究提供了借鑒。總之,在與外國文學作品比較參照時,學者們各有創見,開拓了更為廣闊的學術視野,在更深廣的文化背景下有助于我們較為準確地揭示《閱微草堂筆記》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意義。
六、滄州鄉梓情懷研究接續
進入21 世紀,隨著學術界對紀昀及其《閱微草堂筆記》研究的深入與重視,我們可以發現紀昀的故鄉河北滄州在研究和宣傳等方面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在紀昀的故鄉至今活躍著一批辛勤的研究者,他們一方面彰顯對鄉梓文人紀昀的深厚崇敬之情;一方面寄希望于此以弘揚滄州優秀的地域文化,自發組織成立了相關學會,如“紀曉嵐研究會”。他們在相關負責人的帶領下,在文獻的搜集與整理、實物的考辨與保護以及文本的研讀與點校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并率先編輯出版了紀昀的研究專刊——《紀曉嵐研究》,方便了學者的研究工作。他們還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權威報刊相繼出版了《紀曉嵐遺物叢考》《獅城探秘》《滄州考古錄》《閱微珠語》等一系列相關著述,在推動紀昀及《閱微草堂筆記》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其次,滄州師范學院主體單位在紀昀及其《閱微草堂筆記》研究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通過知網所刊載的關于紀昀的學術論文來看,單《滄州師范學院學報》就刊載了40余篇,在刊載紀曉嵐研究文獻和推動紀曉嵐研究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按發文數量單位排名,滄州師范學院對紀曉嵐的研究排在第一位,對推進紀昀及其《閱微草堂筆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同時對豐富滄州本土文化做出重要貢獻。
七、近二十年文本整理豐富多樣
學者們的研究重視推動了《閱微草堂筆記》文本整理工作,陸續出版了一批校點精良、形式多樣的文本。首先按照收錄數目可以分為全本和選本:全本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汪賢度點校的《閱微草堂筆記》,該本以清嘉慶五年盛時彥合刊本為藍本,與其他各本一并參校,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好的本子,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選本如曹月堂選評、周美昌注解的《評注〈閱微草堂筆記〉》。這些全本和選本都經過學者們精良的點校,為《閱微草堂筆記》的研究提供可靠的文本支撐。其次按照語言形式可以分為文言本和白話本,文言本作為主要形式就不做展開,白話本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邵海清等譯白話全本《閱微草堂筆記》以及施亮如校譯的《白話〈閱微草堂筆記〉》。與文言本不同的是,白話本更適合大眾閱讀。最后按照文本樣式還可以分為純文本和插圖本,插圖本早在民國時期就已出現,近二十年來隨著印刷術的發展,圖畫制作更為的精良如1995年華夏出版社和2008年萬卷出版公司出版的兩種,通過圖文并茂的形式,滿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值得注意的是,除上述文本之外,2007年,臺灣還出現了介于學術研究與大眾普及讀物之間的兩本著作:宋記遠編著的《52個你所不知道的〈閱微草堂筆記〉之謎》、黃辰淳編著的《一百四十則〈閱微草堂筆記〉故事中的生命意義》,這兩本書除了提供給研究者一些新思路外,比起同類的大眾普及著作要嚴肅得多。總之,這些對于《閱微草堂筆記》的普及與研究均具有重要的意義。
八、結語
《閱微草堂筆記》作為清代很有影響力的一部筆記小說,得到了學者們的廣泛關注。筆者在對其近二十年研究的系統總結過程中,發現該研究呈現出學者的專業化特征,有一批學者如吳波、韓希明、魏曉虹、張偉麗、張泓等致力于對其專、精、細的研究,并且一些觀點可謂是別開生面,對后來的研究者而言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同時其研究面之廣,除已經提到的還涉及司法學、醫藥學、經濟學等多學科,這無疑給之后的學者留下了許多再研究、再創新的空間。總而言之,利用《閱微草堂筆記》所涌現出來的多元化研究,不僅對于《閱微草堂筆記》本身與紀昀具有重要意義,對于中國小說史的研究也具有深遠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