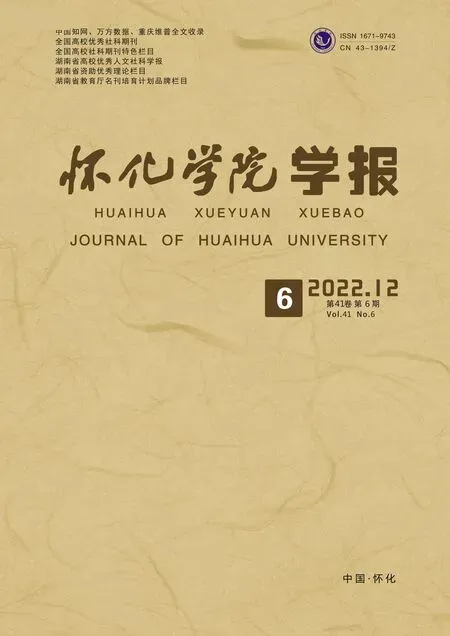理雅各《論語(yǔ)》英譯誤譯研究
李 鋼, 李海軍
(1.湖南科技學(xué)院,湖南 永州 425199; 2.長(zhǎng)沙學(xué)院外國(guó)語(yǔ)學(xué)院,湖南 長(zhǎng)沙 410022)
理雅各(James Legge)是第一位系統(tǒng)將“四書(shū)五經(jīng)”譯成英文的漢學(xué)家。他的“四書(shū)五經(jīng)”英譯本《中國(guó)經(jīng)典》(The Chinese Classics)出版后,“獨(dú)步歐美漢學(xué)界,被尊為絕對(duì)權(quán)威”[1]。它被多次再版,至今仍然是英語(yǔ)世界不可替代的漢學(xué)經(jīng)典。劉重德先生在校注了理雅各翻譯的《大學(xué)》《中庸》《論語(yǔ)》后認(rèn)為,理雅各《四書(shū)》譯本“譯筆嚴(yán)謹(jǐn),忠于原作”[2]。
理雅各本人精研中國(guó)語(yǔ)言文化,且有王韜、何進(jìn)善等中國(guó)學(xué)者襄助,因此《中國(guó)經(jīng)典》譯文質(zhì)量在當(dāng)時(shí)屬于上佳水平,受到廣泛贊譽(yù)。即使過(guò)了100 多年,《論語(yǔ)》又出了大量的新譯本,當(dāng)代有些學(xué)者對(duì)理雅各《中國(guó)經(jīng)典》的譯文質(zhì)量還是持贊賞態(tài)度,認(rèn)為其“譯筆嚴(yán)謹(jǐn)”[2]“忠實(shí)而神妙”[3]“細(xì)膩忠實(shí)”[1]。不過(guò),也有學(xué)者指出,“盡管理雅各的譯文有上述諸般后人難以超出的優(yōu)點(diǎn),但智者千慮,必有一失,理雅各的翻譯,正如任何翻譯家的作品一樣,不可能是完全無(wú)誤的”[4]。
理雅各《論語(yǔ)》英譯本(Analects)位列《中國(guó)經(jīng)典》第一卷第一本,在《中國(guó)經(jīng)典》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據(jù)丁大剛[5]的研究,理雅各《論語(yǔ)》英譯分別有1858年樣書(shū)本、1861年初版本、1867年普及本、1893年修訂本等四個(gè)版本。其中,1861年初版本較1858年樣書(shū)本、1893年修訂本較1861年初版本都有不同程度的修改,由此可以看出理雅各翻譯態(tài)度的認(rèn)真。但即使如此,譯本中還是存在一些誤譯,這點(diǎn)已有劉重德[2]、樊培緒[6]、岳峰[4]等學(xué)者指出。
理雅各《論語(yǔ)》英譯出現(xiàn)誤譯,主要原因是中文的復(fù)雜性以及理雅各自身認(rèn)知的局限性。理雅各雖然是當(dāng)時(shí)漢學(xué)家中的佼佼者,很熟悉中國(guó)語(yǔ)言和文化,但他畢竟不是中國(guó)人,從小沒(méi)有浸潤(rùn)于中國(guó)語(yǔ)言文化之中,因此,他的中國(guó)語(yǔ)言文化知識(shí)還是相對(duì)有限。此外,由于《論語(yǔ)》是用先秦時(shí)期的語(yǔ)言寫(xiě)成,言簡(jiǎn)意賅,言少意多,即使不少中國(guó)學(xué)者,理解也存在一定的困難。理雅各翻譯《論語(yǔ)》時(shí),中國(guó)有關(guān)《論語(yǔ)》的注疏不勝枚舉,其中不少的注疏存在誤解。因此,理雅各英譯《論語(yǔ)》時(shí),雖有王韜、何進(jìn)善等中國(guó)學(xué)者襄助,還會(huì)參照前人的注疏成果,但因?yàn)樽约旱恼J(rèn)知局限,有時(shí)可能誤解原文,導(dǎo)致譯文失誤。此外,譯文表達(dá)時(shí)的偶爾大意,也會(huì)造成理雅各《論語(yǔ)》英譯時(shí)的誤譯。因此,筆者擬在前人學(xué)者的基礎(chǔ)上,以楊伯峻的《論語(yǔ)譯注》和許淵沖的《論語(yǔ)》英譯本(Thus Spoke the Master)為參照,認(rèn)真比讀《論語(yǔ)》原文和理雅各的譯文,指出理雅各《論語(yǔ)》英譯中一些誤譯。
一、詞語(yǔ)理解偏差導(dǎo)致的誤譯
漢語(yǔ)詞語(yǔ)一詞多義現(xiàn)象頻繁,同一詞語(yǔ)在不同的語(yǔ)境中具有不同的意義,這在文言文中尤其明顯。對(duì)于譯者來(lái)說(shuō),一詞多義現(xiàn)象是翻譯過(guò)程中的“陷阱”,一不留神就會(huì)掉下去,這在漢學(xué)家譯者身上表現(xiàn)得尤其突出。近代以來(lái),不少漢學(xué)家在英譯中國(guó)典籍時(shí),因?yàn)闆](méi)有考慮詞匯出現(xiàn)的語(yǔ)境,過(guò)于從字面上理解原文,有了不少不應(yīng)該出現(xiàn)的“經(jīng)典”誤譯。例如,亞瑟·韋利翻譯陶淵明的《責(zé)子》時(shí),將原詩(shī)中的“二八(十六歲)”譯為“eighteen”、將“行志學(xué)(十五歲)”譯為“does his best”;翟理斯翻譯《聊齋志異》中的《嬰寧》時(shí),將“自分化為異物(自以為要死了)”譯為“I…quite changed from what I was”;阿連壁翻譯《聊齋志異》中的《嬌娜》時(shí),將原文中的“小子初學(xué)涂鴉”譯為“he prefers to drawpictures of crows on his paper”。以上兩位都是漢學(xué)家中的泰斗,翻譯時(shí)也難免誤解原文產(chǎn)生誤譯。同他們一樣,理雅各在翻譯《論語(yǔ)》時(shí),有些地方也因理解偏差導(dǎo)致譯文失誤。
例1:……邦無(wú)道免于刑戮……(公冶長(zhǎng)第五)
譯文:…and if it were ill-governed,he would escape punishment and disgrace…[7]172-173.
根據(jù)楊伯峻[8]41的解釋?zhuān)靶搪尽钡囊馑际恰靶塘P”。而理雅各將“刑戮”理解為“刑罰和恥辱”,譯為“punishment and disgrace”,譯文增加了原文沒(méi)有的“恥辱”之意。許淵沖[9]40將“邦無(wú)道免于刑戮”譯為“nor would he be punished in an ill governed one”,準(zhǔn)確傳達(dá)了原文的含義。
例2:……子路使門(mén)人為臣……(子罕第九)
譯文:…Tsz-l u^ wished the disciples to act as ministers to him…[7]220
根據(jù)楊伯峻[8]89的解釋?zhuān)白勇肥归T(mén)人為臣”的意思是“子路命孔子的學(xué)生組織治喪處”,其中“使”的意思是“命”。而理雅各將“使”理解為“希望”,譯為“wish”,理解有偏差。許淵沖[9]74-75將“子路使門(mén)人為臣”譯為“Zi Lu asked some disciples to act as official mourners”,將“使”譯為“ask”,基本能夠傳達(dá)原文的意思。
例3:……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鄉(xiāng)黨第十)
譯文:…h(huán)is countenance appeared to change,and his legs to move forward with difficulty…[7]228
根據(jù)楊伯峻[8]96的解釋?zhuān)吧纭钡囊馑际恰懊嫔娉智f重”;“足躩如”的意思是“腳步也快起來(lái)”。而理雅各將“色勃如”譯為“his countenance appeared to change”(臉色立即改變),譯文不太精準(zhǔn);而將“足躩如”譯為“his legs to move forward with difficulty”(步履艱難),則完全和原文意思相反。許淵沖[9]80將“色勃如”和“足躩如”分別譯為“he looked solemn”和“quickened his steps”,忠實(shí)傳達(dá)了原文的意思。
例4:……人而無(wú)恒,不可以作巫醫(yī)……(子路第十三)
譯文:…a man without constancy cannot either be a wizard or a doctor…[7]272
根據(jù)楊伯峻[8]139的解釋?zhuān)拔揍t(yī)”是一個(gè)整體“不應(yīng)分為卜筮的巫和治病的醫(yī)兩種”。而理雅各將“巫醫(yī)”理解為“巫師或醫(yī)生”,譯為“a wizard or a doctor”,和原文意義有偏差。許淵沖[9]114的譯文是“witch-doctor”,很好地傳達(dá)了原文的意思。
例5:……龜玉毀于櫝中……(季氏第十六)
譯文:…when a tortoise or piece of jade is injured in its repository…[7]307
根據(jù)楊伯峻[8]171的解釋?zhuān)褒斢瘛敝械摹褒敗敝腹艜r(shí)用來(lái)占卜的“龜殼”。而理雅各將“龜”譯為“a tortoise”,則將原文中的“龜殼”變成了譯文中的“烏龜”,譯文明顯有偏差。許淵沖[9]143的譯文是“a tortoise shell”,十分忠實(shí)。
典籍英譯過(guò)程中,要想避免詞語(yǔ)理解偏差產(chǎn)生的誤譯,譯者首先要加強(qiáng)中國(guó)語(yǔ)言文化水平的修養(yǎng)。因此,譯者還需要查閱各種相關(guān)參考書(shū)籍,尤其要利用“無(wú)所不包”的互聯(lián)網(wǎng),在此基礎(chǔ)上進(jìn)行細(xì)致的語(yǔ)境分析,這樣才能從一個(gè)詞語(yǔ)眾多的義項(xiàng)中找出其最恰當(dāng)?shù)牧x項(xiàng),準(zhǔn)確譯出原文含義。
二、句子理解偏差導(dǎo)致的誤譯
漢語(yǔ)文言句式結(jié)構(gòu)復(fù)雜多樣,再加上其為意合語(yǔ)言,有時(shí)會(huì)省略主語(yǔ)等一些句子成分,并且漢語(yǔ)文言詞約義豐。這些會(huì)給譯者,尤其是漢學(xué)家譯者帶來(lái)一定的困難,使他們?cè)诶斫庠木涫綍r(shí)稍不留神就會(huì)發(fā)生偏差,導(dǎo)致誤譯,如:
例6:……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冶長(zhǎng)第五)
譯文:…Yen P'ing knew well how to maintain friendly intercourse. The acquaintance might be long,but he showed the same respect as at first…[7]179
根據(jù)楊伯峻[8]47的解釋?zhuān)熬枚粗钡囊馑际恰跋嘟辉骄茫瑒e人越發(fā)敬重他”。而理雅各將其理解為“相識(shí)久了,他仍然像開(kāi)始那樣尊敬別人”,譯文有偏差。許淵沖[9]44的譯文是:“The longer their friendship lasts,the more they respect him”,準(zhǔn)確傳達(dá)了原文的意思。
例7:……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第十二)
譯文:…Is this practice of perfect virtue from a man himself,or is it from others[7]250?
根據(jù)楊伯峻[8]121的解釋?zhuān)盀槿视杉海扇撕踉眨俊钡囊馑际恰皩?shí)行仁德,全憑自己,還憑別人嗎?”這是一個(gè)反問(wèn)句,表示肯定的意思。而理雅各將反問(wèn)句理解為一般疑問(wèn)句,譯文意思和原文相差不少。許淵沖[9]98的譯文是“Benevolence depends on oneself,not on others”,用肯定句取得了原文反問(wèn)句的效果。
例8:……惜乎,夫子之說(shuō)君子也……(顏淵第十二)
譯文:Tsze-kung said,“Alas!Your words,sir,show you to be a superior man.”[7]255
根據(jù)楊伯峻的解釋?zhuān)跋Ш酰蜃又f(shuō)君子也”的意思是“真遺憾,夫子您這樣談?wù)摼印薄6硌鸥鲗⑵渥g為“Alas!Your words,sir,showyou to be a superior man(夫子啊!您的話表明您是為君子)”,譯文和原文的意思相差懸殊。許淵沖[9]101的譯文為“It is a pity that you should have said that”,言簡(jiǎn)意賅地表達(dá)了原文的意思。
例9:……君子恥其言而過(guò)其行……(憲問(wèn)第十四)
譯文:…The superior man is modest in his speech,but exceeds in his actions…[7]286
根據(jù)楊伯峻[8]153的解釋?zhuān)熬訍u其言而過(guò)其行”的意思是“說(shuō)得多,做得少,君子以為恥”。而理雅各將其理解為“君子言語(yǔ)謙虛,但行動(dòng)超過(guò)言語(yǔ)”,譯文完全沒(méi)有將原文“恥”的意思傳達(dá)出來(lái)。許淵沖[9]125將其譯為“An intelligentman is ashamed that his words outturn his deeds”,精準(zhǔn)傳達(dá)了原文的含義。
例10:……雖蠻貊之邦,行矣……(衛(wèi)靈公第十五)
譯文:…such conduct may be practiced among the rude tribes of the South or the North…[7]295
根據(jù)楊伯峻的解釋?zhuān)半m蠻貊之邦,行矣”的意思是“即使到了蠻貊地區(qū),也可以行得通”,“行矣”的主語(yǔ)是人。而理雅各的譯文中,主語(yǔ)成了“言忠信,行篤敬”這種行為(such conduct),譯文和原文有偏差。許淵沖[9]133的譯文為“You would behave well even among uncivilized tribes”,較好地傳達(dá)了原文的意思。
例11:……吾友張也為難能也……(子張第十九)
譯文:…My friend Chang can do things which are hard to be done…[7]344
根據(jù)楊伯峻的解釋?zhuān)拔嵊褟堃矠殡y能也”的意思是“我的朋友子張可以說(shuō)是難得的了”。而理雅各將其中的“為難能也”錯(cuò)誤理解為“能夠做一些難做的事情”,譯文“my friend Chang can do things which are hard to be done”和原文意義有不小的差距。許淵沖[9]169的譯文為“It is difficult to get a friend as good as Zi Zhang”,基本能夠傳達(dá)出原文的含義。
要避免典籍英譯過(guò)程中因句式理解偏差導(dǎo)致的誤譯,譯者首先要熟練掌握文言句式,尤其是一些特殊的文言句式。此外,譯者應(yīng)該詳細(xì)分析句子發(fā)生的語(yǔ)境,能夠知道原文句子中省略了什么成分,知道原文中某個(gè)詞語(yǔ)具體表達(dá)什么含義,這樣才能保證譯文之“信”。
三、譯文表達(dá)導(dǎo)致的誤譯
準(zhǔn)確理解原文后,譯者表達(dá)譯文時(shí)也應(yīng)該特別小心仔細(xì)。因?yàn)椋g文表達(dá)時(shí)一個(gè)標(biāo)點(diǎn)符號(hào)的誤用、一個(gè)語(yǔ)言表達(dá)位置的誤放,都可能導(dǎo)致譯文出錯(cuò),最終導(dǎo)致前功盡棄。如:
例12:……五十以學(xué)《易》,可以無(wú)大過(guò)矣……(述而第七)
譯文:…I would give fifty to the study of the Yi,and then I might come to be without great faults…[7]200
根據(jù)楊伯峻的解釋?zhuān)拔迨詫W(xué)《易》”的意思是“到五十歲學(xué)習(xí)《易經(jīng)》”。而理雅各將其譯為“I would give fifty to the study of the Yi”,將其回譯過(guò)來(lái)即為“用五十年學(xué)習(xí)《易經(jīng)》”。許淵沖[9]59將其譯為“to study the Book of Change after fifty”,是正確的譯文。筆者認(rèn)為,理雅各在正確理解原文上應(yīng)該沒(méi)什么難度,可能是表達(dá)時(shí)一時(shí)大意所致。
例13:……飯疏食,沒(méi)齒無(wú)怨言……(憲問(wèn)第十四)
譯文:…(was taken from the chief of)the Po family,who did not utter a murmuring word,though,to the end of his life,he had only coarse rice to eat.”[7]278
根據(jù)楊伯峻的解釋?zhuān)苤偈莻€(gè)有才干的人,他奪走了伯氏駢邑三百家,但能夠讓伯氏雖然“吃粗茶淡飯,直到老死也沒(méi)有怨言”。比較理雅各的譯文和原文,可以發(fā)現(xiàn)理雅各應(yīng)該正確理解了原文,但是在表達(dá)方面有待商榷:“to the end of his life”宜移到“utter a murmuring word”之后和“though”之前,否則譯文的意思變成了“直到老死都是吃粗茶淡飯”。許淵沖[9]120的譯文則準(zhǔn)確清晰地傳達(dá)了原文的意思:“…the head of the Bo family lived on coarse food without a word of complaint till he grewold and toothless”。
要避免譯文表達(dá)時(shí)盡量不出現(xiàn)或少出現(xiàn)失誤,譯者須萬(wàn)分小心,容不得一絲馬虎,心中時(shí)刻記住譯界名言“You can never be too careful in translation(翻譯怎么仔細(xì)都不過(guò)分)”。譯文表達(dá)完成以后,一定要認(rèn)真檢查,首先原文譯文對(duì)照檢查,然后再單獨(dú)仔細(xì)檢查譯文,看是否存在漏譯和誤譯。
我們?cè)诖瞬淮懊粒赋隼硌鸥鳌墩撜Z(yǔ)》英譯中一些瑕疵,并非想否定他的翻譯功績(jī)。100 余年來(lái),理雅各的翻譯功績(jī)已經(jīng)是舉世公認(rèn)。他的譯文中即使有一些瑕疵,也毫不影響他的《中國(guó)經(jīng)典》散發(fā)出的熠熠光輝。此外,我們應(yīng)該對(duì)早期漢學(xué)家翻譯介紹中國(guó)文化時(shí)的瑕疵有“理解之同情”。在當(dāng)時(shí)的歷史條件下,譯文中出現(xiàn)一些瑕疵是情有可原的,無(wú)損于他們向西方成功翻譯介紹中國(guó)文化的功績(jī)。但是我們也應(yīng)該坦誠(chéng)指謬,這樣可以完善他們的譯文,并讓后來(lái)譯者從中吸取教訓(xùn),避免或少犯類(lèi)似的錯(cuò)誤,推動(dòng)中國(guó)文化更好地“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