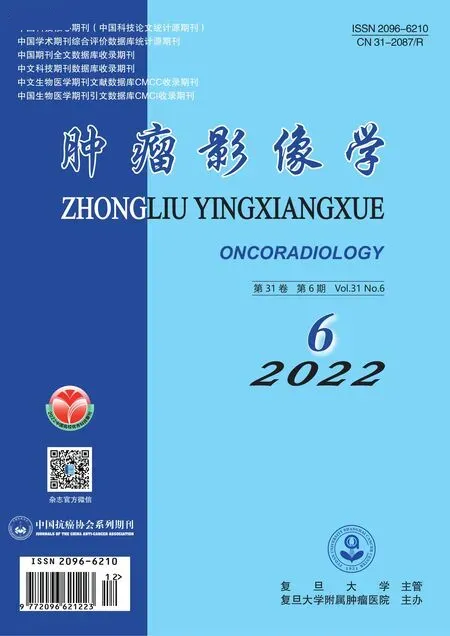聲觸診組織成像量化技術鑒別診斷非腫塊型乳腺病變良惡性的臨床價值
于鵬麗,孔文韜,薛海燕,王 穎,張一丹,龔 黎
南京大學醫學院附屬鼓樓醫院超聲醫學科,江蘇 南京 210008
乳腺癌是中國女性最常見的惡性腫瘤,近年來發病率增長迅速,且呈年輕化的趨勢。超聲檢查在乳腺癌的早期診斷中起著重要作用,目前已成為中國乳腺癌篩查的首選影像學方法。非腫塊型乳腺病變是指病灶與周邊實質及對側乳房相同區域的超聲表現不同,但在兩個不同掃查方向上均不具有空間占位效應,缺乏明確邊界和形態[1]。其中惡性病變又稱為非腫塊型乳腺癌(non-mass breast cancer,NMBC),占乳腺異常的9.21%[2],缺乏典型的影像學表現,迄今沒有統一的影像學診斷標準,常規超聲檢查極易漏診或誤診[3]。聲輻射力脈沖彈性成像(acoustic radiation force impulse elastography,ARFI)是一種基于剪切波超聲彈性成像的技術,可獲得組織彈性的定量特征,能夠鑒別乳腺病變的良惡性[4]。ARFI中的聲觸診組織成像量化(virtual touch tissue imaging quantification,VTIQ)作為一種新型超聲彈性檢測技術,可對病灶進行定性和定量同步分析,通過計算局部形變后產生的剪切波速度(shear wave velocity,SWV),反映病變部位組織的彈性定量特征,有助于鑒別病變的良惡性[5]。本研究旨在探討VTIQ技術在診斷非腫塊型乳腺病變良惡性中的臨床應用價值,提高NMBC的檢出率和診斷符合率。
1 資料和方法
1.1 研究對象
回顧并分析2018年8月—2021年7月于南京大學醫學院附屬鼓樓醫院診治的非腫塊型乳腺病變患者203例(共207個病灶)。患者均為女性,年齡23~77歲,平均年齡(44.1±12.0)歲,病灶均經組織學穿刺活檢術或手術后病理學檢查確診。術前均進行了常規超聲及VTIQ檢測,記錄患者完整的資料。排除標準:① 患側乳腺有病灶穿刺史、手術史或化療史;② 囊性病灶;③ 患者處于孕期及哺乳期。本研究由2名具有5年以上超聲診斷經驗且熟練掌握VTIQ技術的醫師完成。所有患者均已簽署知情同意書。
1.2 儀器與方法
1.2.1 儀器
采用德國Siemens公司的Acuson S3000彩色多普勒超聲診斷儀,使用線陣探頭9L4,頻率4~9 MHz;內置ARFI技術軟件,可行VTIQ檢測及分析。
1.2.2 檢查方法
患者取平臥位,行常規乳腺超聲檢查,記錄病灶方位、數量、大小、形態、內部回聲模式、鈣化及血流等特征,血流信號根據Adler分級標準進行分級。選取病灶最大切面啟動VTIQ模式,將病灶置于感興趣區(region of interest,ROI)中心位置,包括病灶及部分正常腺體組織,囑患者屏氣,按“update”鍵,依次顯示VTIQ質量模式和速度模式圖。重復采集圖像2~3次,當質控模式質量最高(圖像呈分布均勻的綠色)時表示彈性成像質量穩定。在綠色質量模式圖像背景下,轉換成速度模式圖,可直觀顯示SWV分布,從高到低依次為紅色、黃色、綠色、藍色。將ROI置于病灶內部不同位置,包括速度最高及最低區域、周邊及中央區域。SWV量程為0~10 m/s,選用5~10個取樣框,記錄病灶內SWV的最大值(Vmax)、最小值(Vmin)及平均值(Vmean)。
1.3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23.0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以表示,計數資料比較行χ2檢驗。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比較良惡性組間SWV各參數的差異。以病理學檢查結果為金標準,繪制受試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線,計算曲線下面積(area under curve,AUC),確定最佳診斷截斷值。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 果
2.1 病理學檢查結果
207個非腫塊型乳腺病灶中,惡性組病灶98個,其中導管原位癌29個(29.6%),導管原位癌伴局灶浸潤16個(16.3%),浸潤性導管癌8個(8.2%),浸潤性導管癌伴原位癌25個(25.5%),導管內癌8個(8.2%),浸潤性小葉癌6個(6.1%),黏液癌2個(2.0%),淋巴瘤2個(2.0%),浸潤性微乳頭狀癌2個(2.0%);良性組病灶109個,其中導管內乳頭狀瘤11個(10.1%),炎性病變48個(44.0%),腺病36個(33.0%),纖維腺瘤14個(12.8%)。
2.2 臨床資料及常規超聲特征比較
惡性組的年齡明顯高于良性組,良性組與惡性組患者的年齡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良性組超聲特征以片狀低回聲為主要表現,惡性組則以內部微鈣化為主要表現(P<0.001)。惡性組的血流信號分級較良性組增高(P<0.001)。病灶大小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970,表1,圖1、2)。

表1 非腫塊型乳腺病變臨床資料常規超聲特征比較

圖1 良性組(患者,女性,54歲,漿細胞性乳腺炎,范圍約2.2 cm×1.2 cm)超聲圖像

圖2 惡性組(患者,女性,52歲,導管原位癌,范圍約2.8 cm×1.4 cm)超聲圖像
2.3 兩組病灶VTIQ檢測結果比較
兩組間病灶SWV的Vmax、Vmin及Vmean值比較,惡性組均明顯高于良性組,兩組間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01,表2)。
表2 兩組非腫塊型乳腺病變SWV測值比較±s

表2 兩組非腫塊型乳腺病變SWV測值比較±s
組別 Vmax/(m·s-1) Vmin/(m·s-1) Vmean/(m·s-1)良性組 3.65±1.27 2.20±0.68 2.89±0.86惡性組 7.23±2.20 3.22±1.26 4.98±1.44 P值 <0.001 <0.001 <0.001
2.4 SWV值對非腫塊型乳腺病變良惡性診斷效能分析
以病灶SWV的Vmax、Vmin及Vmean值繪制ROC曲線,AUC分別為0.905、0.772、0.891(圖3)。Vmax取5.29 m/s為截斷值時診斷靈敏度及特異度分別為82.4%、90.1%;Vmin取3.69 m/s為截斷值時診斷靈敏度及特異度分別為50.1%、88.9%;Vmean取3.88 m/s為截斷值時診斷靈敏度及特異度分別為81.1%、89.1%。以上結果顯示,Vmax和Vmean診斷非腫塊乳腺病灶良惡性的靈敏度和特異度均較高,Vmin的特異度較高,但靈敏度較低(表3)。

圖3 非腫塊型乳腺病變SWV值的ROC曲線

表3 SWV值對非腫塊型乳腺病灶良惡性診斷效能的比較
3 討 論
乳腺癌在影像學表現上分為腫塊型和非腫塊型,NMBC在影像學上沒有明顯空間占位效應,病灶缺乏明確的形態和邊界,往往存在一定的漏診現象,是乳腺病變影像學檢查的重點和難點。超聲檢查是NMBC的重要篩查手段,其主要的超聲表現為片狀低回聲區、結構扭曲、彌漫性或散在分布的微鈣化區、導管內實性回聲、伴或不伴后方聲影、腫大的淋巴結等[6],這些征象可以單獨或合并存在。由于受到儀器性能、檢查手法、病灶位置深度、病灶是否進入血管生長期等因素影響,既往研究[7]普遍認為常規超聲診斷NMBC的靈敏度高,但特異度低,血流豐富與否亦不能作為超聲診斷的依據。因此,聯合使用超聲彈性成像技術,可提高常規超聲對乳腺病變診斷的準確度,提高檢出率[8]。研究[8-11]證實,常規超聲結合超聲彈性成像技術對非腫塊型乳腺病變的診斷有較好的特異度和陽性預測值,有助于非腫塊型乳腺病變的診斷,同時可減少不必要的活檢。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NMBC在病理學特征上具有很強的異質性,不同的彈性成像方式、不同的ROI選擇,或將導致彈性模量結果的偏差。ARFI技術中的VTIQ技術與傳統彈性成像技術相比,SWV的測量范圍增寬,ROI選取更為精準,同時減少了操作者由于手的壓力釋放所引起的組織形變對結果的影響,具有較高的可重復性和較低的操作者依賴性[12-13]。
本研究采用VTIQ技術測定非腫塊型乳腺病變的SWV,并進行比較,惡性組的Vmax、Vmean和Vmin值都明顯高于良性組,兩組之間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01),與既往研究[14-15]剪切波彈性成像在腫塊型乳腺病變診斷中的結論一致,也與乳腺病變的病理學特點相符:良性病灶質地較疏松,組織硬度較低且分布較均勻;惡性病灶向周圍組織浸潤性生長,纖維組織增生較活躍,反復壞死與修復,使得組織硬度較高且分布不均勻。有研究[8,14]認為,非腫塊型乳腺病變良惡性病灶間的Vmax和Vmean差異有統計學意義,但Vmin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本研究結果顯示,Vmax和Vmean在鑒別診斷非腫塊乳腺病灶良惡性中的靈敏度和特異度較高(Vmax82.4%、90.1%;Vmean81.1%、89.1%),Vmin的特異度較高,但靈敏度較低(88.9%、50.1%),提示Vmax和Vmean診斷效能較高,Vmin的診斷效能較低。這也證實了相關研究[9]的結果,認為Vmin在鑒別診斷中也有一定的價值,但不建議將Vmin作為單獨診斷指標。
本研究中,VTIQ在診斷非腫塊型乳腺病變存在一定的假陽性和假陰性。以Vmax和Vmean診斷界值為標準,假陽性有9例,其中漿細胞性乳腺炎2例,肉芽腫性乳腺炎4例,導管內乳頭狀瘤2例,腺病合并導管內乳頭狀瘤1例;假陰性7例,其中導管原位癌4例,浸潤性導管癌伴原位癌2例,黏液癌1例。假陽性病變以炎性病變為主,原因可能是部分炎性病變中伴有微小鈣化,病灶硬度增加。有研究[16]表明,鈣化與非腫塊型乳腺病變的假陽性相關。假陰性病灶中以導管原位癌為主,導管原位癌的腫瘤細胞未突破基底膜,僅在導管小葉單位內增殖,與浸潤性癌相比硬度偏低[17-18]。
綜上所述,彈性成像VTIQ技術測定非腫塊型乳腺病變SWV,對其良惡性的鑒別診斷具有重要臨床價值,病灶的Vmax和Vmean具有較高的診斷效能,可提高NMBC的檢出率及診斷準確度,亦有助于減少不必要的活檢。由于部分乳腺病變及其周圍組織的硬度并不能完全反映病變的病理學特征,因此在臨床實際工作中,需要結合患者的病變特征并排除相關因素,適當地利用VTIQ技術來診斷非腫塊型乳腺病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