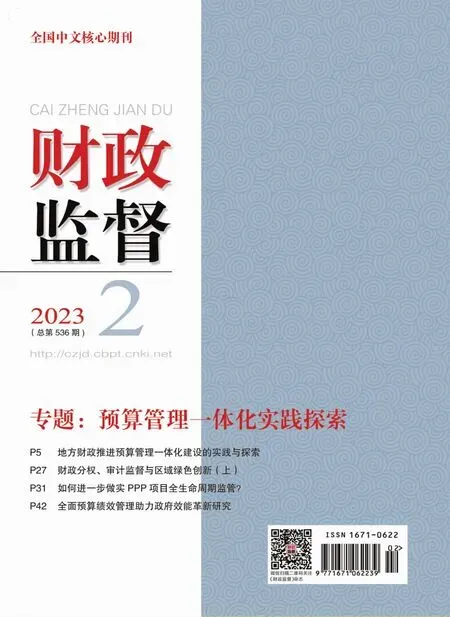財政分權、審計監督與區域綠色創新(上)
●裴 育 劉志威

裴育,經濟學博士,南京審計大學教授、副校長。現任教育部財政學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財政學會理事、中國成本學會常務理事、江蘇省國際稅收研究會副會長、江蘇省預算與會計研究會副會長等,江蘇省“青藍工程”學術帶頭人、“六大人才高峰”項目人選、“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主要從事財稅理論與政策、財政審計、財政風險管理等領域的研究和教學工作。主持或參與國家級、省部級項目20多項,在國家權威或核心期刊發表學術論文90多篇。
一、引言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發展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進入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正在從高速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要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以創新為動力,同時實現綠色發展。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了“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2015年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就形成了綠色、創新、協調、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加快建立綠色生產和消費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導向;黨的二十大報告再次強調污染防治攻堅向縱深推進,綠色、循環、低碳發展邁出堅實步伐,到2035年廣泛形成綠色生產生活方式,美麗中國目標基本實現。
2015年國務院明確提出“放管服”改革思想,李克強總理在2020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上提出“放管服”改革向縱深推進。2020年我國營商環境質量明顯提升,市場法治化水平顯著增強(宋林霖、何成祥,2018),“放管服”中“放”涉及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權力劃分,“管”則涉及監管方面的內容。在中國的發展改革路程中權力分配與監管結合才能促進經濟健康高質量發展。
綠色技術的特征就是節約能源,減少對于生態環境的污染。綠色技術創新便可以理解為“減少環境污染、減少污染性原材料和能源使用的新技術、新工藝和新產品”(齊紹洲、林屾和崔靜波,2018)。根據微觀經濟理論,只有減少原材料才符合企業成本最小化行為,其他目的利于整個社會環境而不符合企業個體的利益需求,所以,企業并不會主動進行綠色技術創新。這時候就需要政府進行干預,合理分配整個社會福利與企業福利來鼓勵或督促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特別是中國政府在資源配置中起到相當大的作用,能夠影響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Guan和Chen(2011)的研究表明政府政策干預對區域創新系統運行效率具有重要意義。
財政分權主要是指財權和事權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分配關系,不同財政分權形式會影響政府行為和財政支出結構。關于財政分權與綠色創新之間關系的研究并未形成統一結論,存在不利和有利兩種觀點。
由于地方官員晉升考核機制,財政分權引起了地方競爭增強反而不利于地方綠色治理,主要以犧牲環境的方式發展經濟(杜俊濤等,2017)。同時,各地政策規定不同,企業可以選擇環境規制較弱的地區進行生產,反而不利于實施嚴厲的環境規制地區綠色經濟發展(沈坤榮等,2017)。Pearce(1991)的“雙重紅利”理論認為,環境稅能倒逼企業節能減排,并促進企業提高生產技術水平,從而帶來環境紅利。游達明、歐陽樂茜(2020)驗證了波特假說,認為適當的環境規制措施有利于企業綠色創新效率,而Porter(1995)認為環境規制能夠倒逼企業開展綠色創新,綠色創新產生的效益能夠抵消環境規制帶來的額外成本形成創新補償效應。宋馬林等(2013)認為環境規制推動了技術進步并帶動了整體生態效率的提高。
而從政府自身角度出發,也存在不同的觀點。余泳澤(2011)認為政府補貼缺乏有效的跟蹤評估與監督機制、政府意愿與企業創新意愿不一致;肖文和高林榜(2014)發現尋租行為會讓政府資源配置行為發生扭曲。范如國、吳婷和樊唯(2022)建立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污染企業三方博弈模型,認為地方政府由于政策執行成本、經濟利益等問題容易與當地污染企業合謀從而導致當地綠色創新效率下降,中央政府需要加強自身監督作用,逐步實現督政制度化、常態化。為了防止政府行為帶來的不利后果,需要對政府進行監督以更好地發揮其資源配置以及對于綠色技術創新的支持激勵效果。
已有研究主要考慮的是財政分權對于地方綠色創新的影響以及作用機制,從具體環境政策、環境規制出發考慮其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并沒有考慮監督在其中發揮的作用。本文的貢獻體現在四個方面:第一,研究了財政分權對于地方綠色創新能力的影響,補充了當前對于相關方面的研究;第二,引入監督機制,研究監督在財政分權對于地方綠色創新能力影響中所起的作用,拓展了當前財政分權與綠色創新能力的研究;第三,研究了財政分權影響地方綠色創新能力的作用機制,同時考慮了審計監督在其中起到的作用;第四,研究了不同地域審計監督與財政分權作用于綠色創新能力的效果,為如何提高分權與監管的效果提供了參考。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一)財政分權對綠色創新能力的影響
從地方財力角度來看,楊陽等(2016)的研究發現,財政分權早期階段的地方財權大導致地方收入增速快,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地方財權下降、地方經濟增速下降。財政分權高的地區往往經濟實力更強,能夠影響地方政府偏好。而楊志安等(2018)的研究發現財政分權對東部地區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和技術進步具有顯著促進作用,而西部地區則表現為抑制作用,進一步證實了這一點。財政分權對于綠色創新具有顯著影響,且具有區域異質性。
從公共服務角度來看,適度的財政分權能夠降低交易成本,優化資源配置來提升公共服務效率(劉飛等,2020)。科技創新行為尤其是綠色技術創新具有正外部性,公共服務效率的提高能夠降低信息收集成本,本區域的其他創新個體能夠更加容易地享受到創新行為的外溢性。
從區域創新效率角度來看,吳延兵(2017)認為地方政府存在“重生產、輕創新”的自利性偏好,所以會降低創新方面的投入,導致區域內部創新資源配置的市場與政府“雙失靈”,抑制了區域創新效率的提升(Zou和Zhang,1999)。但是“重生產”偏好也會從基礎建設方面帶來溢出效應而促進區域創新,如高鐵的開通顯著提高了區域創新水平(卞元超等,2019)。
從政府偏好角度來看,傅勇(2010)認為,在中國式財政分權的影響下,地方政府不愿提供經濟收益較低且財力消耗較大的非經濟公共品。李政等(2018)通過省級面板數據發現財政分權雖然綜合提升了區域創新效率,但是抑制了政府創新偏好。也有學者發現財政分權有利于提高地方政府對于科技創新的偏好,周克清等(2011)的研究發現科技創新實際上具有經濟性公共物品屬性,財政分權能夠提高地方財政科技投入水平。
從不同角度看待財政分權與區域綠色創新之間的關系能夠得到不同的結論,所以,根據現有文獻分析得到財政分權能夠影響區域綠色創新,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財政分權促進地區綠色創新發展。
假設2:財政分權抑制地區綠色創新發展。
(二)審計監督影響區域綠色創新
根據委托代理理論,中央政府可以視為委托人,地方政府可以視為代理人。中央政府為了保證地方政府充分發揮自身能力需要對其進行監督。
在企業創新研究中,伍林蓉和王瑋(2022)的研究發現:多個大股東數量與企業創新行為之間呈現“倒U型”關系,從監督角度來說監督存在一個閾值,低于閾值時企業監督行為促進企業創新行為,高于閾值時則表現為抑制作用。王營和馮佳浩(2022)認為綠色債券能夠強化企業監督機制,進而促進企業綠色創新。趙曉霞(2020)發現審計監督與中小企業創新投入之間顯著正相關并且能夠增強互聯網眾籌與中小企業創新投入之間的相關性。
從政府角度來看,省級預算審查監督條例立法能夠顯著抑制地方政府預算支出和決算支出規模(楊進、化汝婷和龔小蕓,2022)。來自上級監督的強化同時會增加政府承受的壓力,過強的監督甚至會極大約束地方政府的工作風格和行為(李振和王浩瑜,2022);上級政府的監督形成地方政府壓力會促使政府(特別是財力受限的政府)選擇“先污染,后治理”策略(龔旻、錢津津和張帆,2021)。
從已有文獻來看,監督對于綠色創新的作用也存在不同的聲音。考慮到本文研究的審計監督是上級對下級的監督,其目的受到上級中央政府意愿的影響。而本文選擇2010—2016年的數據,此時中國正處于高速增長轉型為高質量發展階段,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仍偏向于經濟中高速發展,所以提出假設3:
假設3:審計監督抑制了區域綠色創新發展。
綜合上述文獻單獨對于財政分權與監督作用于綠色創新的研究,考慮二者的協同效應。根據財政分權理論,地方政府掌握更多的當地信息,能夠更好地分配當地資源;但是權力過大的同時缺乏監督機制也會產生諸如尋租、腐敗、政府間過度競爭等問題,損害了地方政府在資源配置上的效率,從而不利于區域綠色技術創新,所以提出假設4:
假設4:審計監督與財政分權協同作用能夠促進區域綠色創新。
三、研究設計
(一)變量界定
1.被解釋變量:地方綠色創新能力。本文選用全國29個省份①綠色發明專利和實用新型專利申請量代表地方綠色創新能力。為了剔除省份規模對于地方綠色創新申請數量的影響,選擇使用每千人綠色專利申請量表示省級綠色創新水平(GInn)。
2.解釋變量:財政分權(Frd)。現有文獻對于財政分權變量的選擇并不統一,主要包括財政收入分權、財政支出分權和財政自給度(或自給能力),三者代表的邏輯和事實不同所以不能混用(江紅莉和蔣鵬程,2019)。本文選擇使用財政自給度作為財政分權變量。因為財政自給度是衡量區域財政收支關系的變量,一定程度上體現出區域政府對于中央財政的依賴程度,依賴程度低的政府能夠更自由地支配本地財政收入。

3.調節變量:審計監督。審計監督對于政府運行情況有著巨大影響,中國式財政分權體系下配合適當的審計監督能夠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本文參考楊賀、鄭石橋(2015)的研究,使用省級審計覆蓋率代表審計監督。由于審計覆蓋率只能部分代表監督情況,所以對數據進行處理,對每一年各省的審計覆蓋率取均值,高于均值的省份代表強監督取值1,低于均值的省份代表弱監督取值0。

4.控制變量:參考了吳延兵(2019)和陳斌、李拓(2020)的研究,選擇以下控制變量。
(1)產業結構。一是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ind)。高污染企業往往屬于第二產業,需要進行綠色技術升級。二是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ser)。第三產業具有創新活力,占比越高往往技術創新水平越高,因此影響到綠色技術創新。
(2)金融發展。進行創新活動需要投入資本,除了政府的支持之外企業也需要進行投入。企業投入綠色創新活動的資金來源可以是銀行等融資機構。所以選擇地區人均年末貸款額(fin)和人均年末存款余額(dep)進行表示。
(3)地方政府偏好(v)。本文用地方政府在科技和環境上的財政支出占一般預算支出的比例表示政府對于創新和環保方面的重視程度,占比越高表明地方政府對于綠色創新方面的支持力度越大,反之則越小。變量匯總見表1。

表1 變量釋義及描述性統計
(二)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以我國29個省份2010—2016年的數據為樣本進行實證檢驗。數據來源于《中國審計年鑒》《中國基本單位統計年鑒》、CNRDS數據庫、ESP數據庫和CSMAR數據庫。
(三)模型設定
基于現有文獻研究以及假設,探究財政分權、審計監督以及二者的協同效應對區域綠色創新的影響,設定以下基準回歸模型:

其中,i表示省,t表示時間;GInnit表示省級綠色創新能力;Frdit表示財政分權;Ckit為控制變量,包括代表地區產業結構的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代表地區金融水平的年末金融機構人均貸款余額(萬元)、年末金融機構人均存款余額(萬元),代表地方政府偏好的環境偏好(%)、創新偏好(%);Vi、Vt分別表示地區固定效應和時間固定效應;ηit為隨機誤差項,β、λ為待定參數。
考慮到監督在整個過程中發揮的作用以及與財政分權共同產生的影響,設定以下回歸模型:

其中Xit為監督;Frdit×Xit表示監督與 財政分權的交乘項。其他參數含義同模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