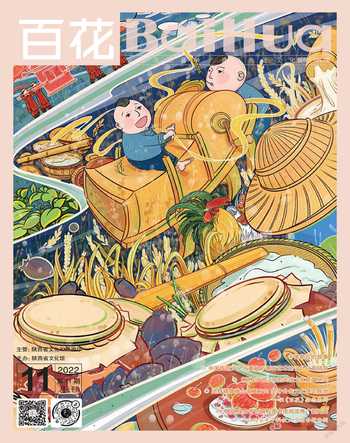原始主義視野下的山水田園詩
景建軍

摘 要:山水田園是中國古代詩歌創作中最主要的表現內容之一,由此也衍生出了眾多的詩歌流派和詩歌大家,影響深遠,在中國詩歌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從中國古代山水田園詩產生的歷史背景及其發展歷程來看,其中明確蘊含著原始主義的傾向,而把握原始主義傾向是我們全面認識古代山水田園詩思想意義的關鍵所在。
關鍵詞:古代詩歌;山水田園詩;原始主義;傾向
詩歌是中國古代文學的標志性文體,這其中,山水田園詩源遠流長,內容豐富,不但涌現出了像陶淵明、謝靈運、謝朓、王維、孟浩然等一批成就卓然的大家,其也成為古代文學創作中最為重要的詩歌流派之一。山水田園詩的影響不僅僅體現在詩歌創作的題材和藝術表現手法上,更為重要的是,它對后世文人的審美情趣、生活道路和文化人格都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成為古代文人揮之不去的精神情結。詩人筆下的山林草木、白云溪澗、農夫漁父等典型詩歌意象,都蘊含著極為豐富的文化能量,其中之一便是強烈的原始主義傾向。
一、文學創作層面上的原始主義內涵
所謂“原始”并非時間概念,而是一個文化概念。原始主義是一個較為寬泛的概念,特指某種有著原始傾向的創作態度與藝術風格。從廣義上看,原始主義是一種尚古崇樸的文化現象和社會思潮;從狹義上看,它是一種以用原始來批判現代文明為主要特征的文學思想和創作傾向。文學創作中的原始主義傾向是人們對人類文化發展的兩端,即源頭和現狀進行反省與選擇的一種文化心態。它可以指人們追懷往古、返璞歸真的天性,也可以指懷疑文明、回歸自然的文化思潮,還可以指用原始來對比和批判現實的文學創作傾向。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發展,人們對于自然及社會的認知和駕馭能力也在不斷地提升,人們創造出了日益繁榮和理性的“第二自然”(相對于第一自然——本真自然的人工自然)。雖然這是人類支配和控制自然力量的體現,是社會進步和發展的必然趨勢,但人類對它日益加重的依賴又使它逐步成為統治和束縛人的客觀力量,反過來又禁錮和支配著人的精神發展。尤其是在社會處于動蕩或轉折的特殊歷史時期,人們對傳統秩序和價值觀的信仰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動搖,人類所創造的物質文明和理性化秩序反倒使人們在精神上感到失落、迷茫甚至是窒息。這一切又必然會導致人們對于“第一自然”的向往和對精神領域的關注。這就“從根本上孕育了返回原始的情緒意向”。[1]自然與社會的分離、對立以及文明向原始的尋找和返歸也就成為原始主義創作的基本母題。
二、原始主義傾向在古代山水田園詩中的
發展與演進
從中國古代詩歌創作這個角度來看,作為人類精神文化重要體現的文學在人類社會中產生以后,“自然”也就隨之被納入到了人們的視野之中,并進而成為詩歌創作中最早也是最常見的題材之一。《詩經·君子于役》中對于“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的描述,屈原《九歌·湘夫人》中“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的慨嘆……從這些中國早期的詩歌創作中,我們似乎已經看到了山水田園詩的萌芽和因子。當然,它們更多是以生活的襯景或比興的媒介這樣一種輔助的面目出現,還遠遠沒有成為詩人觀照的獨立客體和審美對象,而真正意義上的山水田園詩則是隨著魏晉以來文學自覺時代的到來而出現的。從陶淵明到王維,歷經300余年,山水田園詩才作為一個具有豐厚內涵和巨大影響的詩派崛起于文壇,并從此對后世文學創作及無數文人學士的思想情感產生了全方位的深刻影響。
在中國古典詩歌發展史上,山水田園詩的繁盛大都出現在社會動蕩和轉折的特殊歷史時期,這絕不是偶然的。固然我們也可以從其他一些方面找到其發生和繁盛的理由,例如對傳統文人影響最大的儒家思想鼻祖孔子就曾說過“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這樣的話。[2]先秦老莊的道家思想對“自然”的極力推崇以及后來將儒家的“名教”與老莊的“自然”結合起來的玄學及玄言詩的興起,也造就了具有獨特文化風采的“名士風范”,并成為后代文人士大夫爭相效仿的精神生活模式。這些無疑都對山水田園詩的出現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從根本上說,傳統文人士大夫人生價值的失落以及對現實的困惑、懷疑和否定才是山水田園詩興起和繁榮的真正原因,而促使其出現的社會前提恰恰是時代的動蕩和轉折。從古典詩歌的發展軌跡上看,山水田園詩大致歷經了以六朝、唐代和元代為代表的三個較為典型的發展階段。由于各個歷史時期的社會環境有所不同,其中所蘊含的原始主義傾向自然也呈現出了些許差異。
(一)山水田園詩的濫觴——對自然的觀照
六朝是中國古代文學自覺時代的開始,也是山水田園詩的創立時代,正如劉勰在《文心雕龍·明詩》中所說:“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這是一個征伐連年不休、朝代更迭頻繁的大動蕩時代,也是一個信仰危機、傳統價值觀迷失的時代。漢代以來確立起來的一整套完備的專制思想在相當一部分文人士大夫的心目中轟然倒塌了,傳統的理性化的精神束縛也已失去了原有的統治力量,這就為山水田園詩提供了一個絕佳的發展契機。
陶淵明是田園詩的真正開創者。陶淵明的一生中常常交織著出與處的矛盾。一方面,傳統儒家思想的熏陶在他的精神世界中打上了深刻的印記。濟世弘道的理想、貞剛弘毅的人格成為他人生思想的底色,這也使得他創作出了一些諸如“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怒目金剛般的作品。另一方面,世道的昏暗、玄學的勃興、家學的陶冶,尤其是其外祖父東晉名士孟嘉“漸近自然”思想的影響,又培育了他“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的人生觀和藝術觀。“思想的矛盾沖突處,正是藝術精神的發生處”[3],陶淵明的田園詩正是反映了他所經歷的這種人生矛盾。“梅柳夾門植,一條有佳花”“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相見無雜言,但話桑麻長”,陶淵明筆下躬耕田園的生活,絕非一般意義上的“田父”生活,也不僅僅是在追求“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的天倫之樂,而是在淡遠平和的風貌下,將生活境界升華為生命境界,用具象的、感性的詩歌語言表達著人生哲學的命題。這些恬靜、質樸、和諧的詩歌意象當然就不僅僅是對田園的直觀描摹,更是對無情現實的觀照和否定。
陶淵明的田園詩一改前代詩歌重在詠物言志,將自然景物作為比興和象征烘托的做法,而是寓興寄于自然,其筆下的青松、芳菊、歸鳥、孤云,無一不帶有人格的魅力,從而創立了中國古代文人理想的田園模式,為后代的田園詩開拓了極高的精神境界。
同時代的開山水詩之先河的謝靈運也是如此。雖然他的山水詩沒能擺脫玄言詩的消極影響,也沒能跳出王國維所說的“有我之境”,但其細膩工麗的自然描繪,也同樣表現了對自然的鐘情、欣賞與思辨。“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潛虬媚幽姿,飛鴻響遠音”“朝旦發陽崖,景落憩陰峰”,在對自然的觀照中表現出了對現實的態度,從這一個側面也體現了原始主義情結。他與陶淵明共同拉開了中國古代山水田園詩的輝煌序幕。
(二)山水田園詩的合流——對人生的觀照
唐代特別是盛唐時期所開創的宏圖偉業將封建社會的發展推向了極致。國力強盛、兼容并蓄的盛世氣象鑄就了唐代士人積極、樂觀、包容、自信的精神面貌。同時,佛、道思想地位的提升,終南捷徑和隱逸之風的盛行,客觀上也成就了山水田園詩發展的黃金時代。這個時期,山水詩與田園詩逐步合流,這不僅是兩類題材的兼容并包,更是精神層面的合流,即人生觀、藝術觀的高度融合。
作為這個時代代表詩人的王維、孟浩然等人,其所處時代與人生際遇與六朝文人大不相同。恢宏的盛唐氣象標志著封建社會已邁上了發展的頂峰。從表面上看,六朝和唐代山水田園詩的孕育環境似乎有著天壤之別,但二者的精神實質可謂異代而神通。以王維為例,前代陶淵明對其人生思想及審美情趣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秋風日蕭索,五柳高且疏。望此去人世,渡水向吾廬。歲晏同攜手,只應君與予。”(王維《戲贈張五弟諲三首》)“酌醴賦歸去,共知陶令賢。”(王維《送六舅歸陸渾》)詩中對陶淵明的仰慕之情可謂溢于言表。事實上,王維所處的時代正是李唐王朝開明政治落下帷幕的當口,大約以張九齡黯然罷相、李林甫專權為界,面臨著重重危機的李唐王朝開始走向衰落。面對朝堂之上的險惡環境,歷經安史之亂的人生風波,驚魂未定的王維開始對政治仕途感到失望和厭倦,在他的眼中,曾經是公正清明、充滿希望的政治生活已不再有什么真誠、自由、善良和平靜可言。于是,他開始把自己的人生追求寄于藝術的山水田園,以現實的自然萬物為材料和形式,謳歌他所追求的理想“樂土”,追尋那已經消逝的質樸、自由和恬靜的原始情結。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詩人所鐘情的終南山水田園已不再是對自然萬物的單純描繪再現,而是作者精神世界、理想世界的展示。正如西方哲人所說的那樣:“人由對象而意識到自己,對于對象的意識,就是人的自我意識,你由對象而認識人,人的本質在對象中顯現出來。對象是他的公開的本質,是他的真正的、客觀的我。不僅對于精神上的對象是這樣,而且,即使對于感性的對象,情形也是如此。即使是離人最遠的對象,只要確是人的對象,就也因此而成了人的本質之顯示。”[4]
王維的《田家》一詩就很有代表性:舊谷行將盡,良苗未可希。老年方愛粥,卒歲且無衣。雀乳青苔井,雞鳴白板扉。柴車駕羸牸,草屩牧豪豨,夕雨紅榴折,新秋綠芋肥。餉田桑下憩,旁舍草中歸。住處名愚谷,何煩問是非。
這首詩的起首兩句已經很清楚地點明了這是一個十分貧窮的農家,但接下來對農村景物和勞動場景的描寫卻情調沖和,甚至還使用了像“紅榴”“綠芋”這樣一些色彩鮮明的字眼,絲毫不見對勞頓愁苦的嗟怨。倒是結尾兩句道出了該詩的主旨:這里的人們如此淳樸自得,自然也就沒有紛繁的世俗之爭了。顯然,作者筆下的田園風貌并非是現實的真實再現,而只是他精神寄托的家園,是充滿功利、欺詐和沖突的現實世界的對立面。“渡頭燈火起,處處采菱歸”(《山居即事》)、“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依”(《渭川田家》),所有這些都是詩人所理解和渴望的萬物眾生應當具有的和諧的理想境界。
值得注意的是,王孟詩派包括李白、杜甫這些詩壇巨匠的山水田園詩,總體上都呈現出清明朗逸的藝術風貌,其間絕少有悲苦哀怨的色調,這也是盛唐氣象在藝術創作中的折射。雖然由盛而衰的社會變化和個人坎坷的人生際遇會使其中偶爾混雜著些許傷感苦悶的情調,但這些從根本上都源自建功濟世理想的失落和對世事無常的慨嘆。自信、寧靜、激昂和灑脫依然是山水田園詩的主旋律,這頗有些“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身在江湖,心存魏闕”的味道了。唐代的詩人們已經將觀照的視角從自然轉移到了人生,這也正是唐代山水田園詩有別于前代創作的重要特征。
(三)山水田園詩的演進——對社會的觀照
宋元以后,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已盡顯疲態。伴隨著這種社會的變化,山水田園詩也隨之發生了深刻的轉變,這其中尤以元代最具代表性。
在元詩的發展過程中,經歷了對宋、金詩風的反思和批判,經歷了南北復古詩風的匯合,“宗唐得古”的詩風由興起到旺盛,成為一代詩壇的潮流,因此才有了瞿佑在《鼓吹續音·自題詩》中的“舉世宗唐”之說。山水田園詩的發展也是這樣,只不過元代的山水田園詩較之唐代,已有“別樣意味”了。
弗萊在《作為原型的象征》一文中曾說:“詩只能從別的詩中產生。”沈德潛在《唐詩別裁集·凡例》中也說:“唐人詩雖各出機杼,實憲章八代。如李陵《錄別》開《陽關三疊》之先聲;王粲《七哀》為《垂老別》《無家別》之祖武;子昂原本阮公;左司嗣音夫彭澤。揆厥由來,精神符合。讀唐詩而不更求其所從出,猶登山不造五岳,觀水不窮昆侖也。”表面上看,他是在觀流溯源,是說后作在領受前代作品的澤溉。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他又指出了詩歌在情趣和題材方面相互沿襲的事實。對于元代山水田園詩而言,情況也是如此。
元代表現山水林泉、高人隱士的作品之所以蔚然成風,當然也同時代的變化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模山范水、神仙道化、歸隱避世之所以成為傳統文學創作的重要主題,與其社會動蕩、民族歧視、士人卑微、文化交融的大格局、大背景息息相關。
以身為仕宦、頗有政績的吳師道的《野中暮歸有懷》為例:野田蕭瑟草蟲吟,墟落人稀慘欲陰。白水西風群雁急,青林暮雨一燈深。年豐稍變饑人色,秋老誰憐倦客心?酒禁未開詩侶散,菊花時節自登臨。
該詩起首二聯借“野田”“人稀”“西風”“暮雨”的意象極言秋之蕭瑟,“一燈深”又寫出了詩人的孤苦與無助。結尾二聯雖言豐年,但毫無欣喜之意,饑色依舊。作者自比倦客,正值登高賞飲時節,卻詩侶星散,黯然神傷。全詩色調慘淡,情感愁傷,既表現了詩人對于國事民生的憂慮,也發出了倦于仕途、前程無望的悲嘆。詩歌褪去了前代山水田園詩澄凈明麗的理想色彩和氣度,這在矛盾尖銳、士人淪落的元代,其社會批判的指向是非常明確的。
元代傳統文人備受壓抑和苛虐,其人生理想與殘酷現實之間存在著巨大的落差。這樣,山水田園也就自然成了他們絕佳的避風港,成為他們潔身自好、醫治創傷的所在。在山水林泉的陶冶中,追懷昔日的夢想,找尋著失落的理想與無情現實之間的平衡支點。同時,山川林泉、自然風物也成了昏暗社會、混亂現實的參照和對立面,寄托著詩人強烈的現實感受。
三、結 語
綜上所述,在中國詩歌史上綿延千載的山水田園并不單純是詩人描繪的客體,人們之所以如縷不絕地吟詠著山水田園,既是人們審美意識覺醒的體現,也同人們崇古慕俗、返璞歸真的原始情結有關。尤其是在崇尚“以一總多、言外之韻”的中國古典詩學里,其意義功能絕不僅限于直接的字面含義,它已經成為一個蘊含豐富的文化實體,而原始主義傾向正是其中重要內涵之一。正如金代大詩人元好問在《論詩絕句》中所說的“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在社會處于動蕩和轉折的歷史時期,人們往往難以回避現實與內心理想的沖突,于是,詩人們不得不在創作題材上作出相應的調整,盡可能地避開喧囂的官場和紛繁的世俗,向山水田園轉移并進而謳歌“原始”的質樸與和諧,以藝術的手法構建桃花源式的烏托邦理想。詩人筆下的山水田園始終是現實的潛在對立面,從中表現出了明確的尚古價值取向。這也正應驗了車爾尼雪夫斯基所說的那句名言:“那些為生活所折磨,厭倦于跟人們交往的人,是會以雙倍的力量眷戀著自然的。”從本質上講,原始主義是對人類歷史及文化發展的一種深刻反省,它力圖證明人類在發展進步的同時,也在失去著什么。把握了這一點,也許會有助于我們更加全面地解讀和認識山水田園詩的思想價值。
(咸陽師范學院)
參考文獻
[1] 方克強.文學人類學批評[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354.
[2] 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0:224.
[3] 錢志熙.魏晉詩歌藝術原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439.
[4] 韋勒克,沃倫.文學理論[M].劉象愚,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