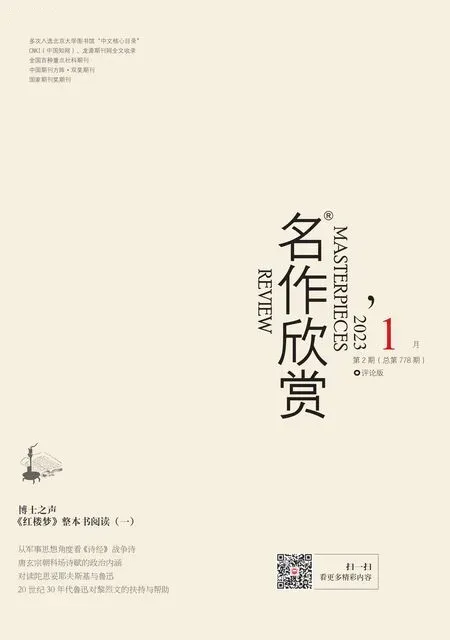論張煒《我的田園》中的流浪意識
⊙張馨之 [大連外國語大學,遼寧 大連 116044]
20 世紀80 年代物質文明的發展牽動文學價值標準的變遷,面對不斷異化的文學市場和現代化社會帶來的精神壓迫,張煒通過書寫流浪意識,進行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救贖。他堅守文學的傳統理想,向往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他以流浪的姿態傳達其對于高度物欲主義的反抗,描繪出一代傳統文人對人文精神的執著守望。
一、流浪意識的載體
流浪是由人們主動或被動進行的一種四處流轉、行蹤無定的行為,張煒于《我的田園》中的流浪書寫更多強調著知識分子們出于理想主義而展開的集體追尋,他們聽憑深埋心底的原始欲望,抵御著世俗的虛無與濁垢,不斷跟隨心中的理想漂泊。書中羅列了許多各有特點的流浪者形象,比如不安于一處的拐子四哥、遠離城市的肖瀟和羅玲以及最著重刻畫的主人公寧伽等。從地質學院到零三所、雜志社,再到葡萄園,寧伽在流浪的過程中始終堅持自省,面朝著精神深處的信仰而不斷尋覓。
張煒對于寧伽的內心世界進行了大量的描繪,對于寧伽而言,他肩負著家族的遺恨和尋覓真相的使命,回想起那個為了心中的理想而一生奔波于革命事業、最終卻含冤而死的父親寧柯,他的情感由最初的懵懂不解到后來感同身受。隨著年齡的增長,擺在寧伽面前的世界變得愈加復雜,他在內心的指引下流浪與體味,逐漸對父親心底所堅守的流浪信念和革命理想有了更深的理解與觸動。寧伽反思與繼承上一輩人的流浪精神,因此當自己也成為父親,在無數個奔跑尋覓的夢里,他時常回憶起那個小小的孩童——他的兒子小寧。
孩童形象的塑造不僅傳達了寧伽對于父親復雜情感的遷移和對兒子的思念與美好情感的向往,更蘊藏著他對人性的思考和世俗背面的忖度。在色調灰暗沉重的夢境里,寧伽腦海中的小寧卻顯得異常純粹和富有生機,小寧同許多其他孩童一般身材單薄,因此即便身置世俗的牢籠,也可以輕易掙脫。純粹自由的靈魂不受世俗桎梏,如同千千萬萬個曾經年幼的成人,而當寧伽回憶起自己故去的童年和已逝的外祖母、母親時,恍知早已不覺間流浪于這條沒有終點的道路。曾經追逐和試圖理解父親的寧伽,在夢中為兒子指明了海洋的方向,他將自己對于自由的向往和理想信念的追求寄托給下一輩人,而后仍舊繼續著這漂泊的帶有悲情意味的一生。
不僅僅是寧伽,張煒筆下的流浪者們幾乎都擁有著不可動搖的信念,他們漂泊于異土他鄉,反抗和抵御著心靈的困獸。葡萄園和園藝場將這些知識分子聚集到一起,任他們盡情構筑心底的永寧鄉,許多個向往自由的靈魂交織于野地,在這片清新自然的田園里譜寫出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奏章。雖然真正的永寧鄉并不存在,城市的工業文明和鄉村的封建落后終將打破流浪者暫時的棲居,但他們對于理想信念和心靈家園的堅守與追逐永不消弭。他們承載著一代文人永不言棄的精神,不斷地進行著自我反省、自我超越,于孤寂中不輟探尋。
人性險惡丑陋的一面隨時間鋪展,物質社會中的苦難構建催生流浪的根源,工業文明下快速發展的城市可能藏污納垢,繁華背面是人們對于物欲的過度追求。桎梏人們身體和精神的壓迫愈加沉重,堅守傳統文學和道德信仰的高山難以攀登,生活的苦痛成為造就流浪者的大力推手,促使更多人深思人性的本來面目和人生真正的追尋。
二、流浪意識的恒久性
寧伽對于精神家園的永恒堅守成就他不斷流浪的步伐,這種追尋是循環式的流浪,每一次棲居都成為其永恒中的節點,流浪者經歷過理想歸宿的幻滅,準備著又一輪的探尋。
寧伽的每一次出發都有其無法回避的動因與本質內涵,精神上的空虛驅使他不斷深思與追尋,面向仍未求得的精神家園,不懈地展開著一次次的自我救贖。他消磨于城市的幾十年間,不堪忍受現代工業文明背面的喧囂與浮躁。當大多數人都疲憊地擱淺在世俗的牢籠里,被動地承受著生活的苦難時,便會有一批不止歇的人勇于尋求光明的出路。因此,當寧伽偶然間遇見那片無人開墾的野地,他無法抑制自己心中對于回歸原野、擁抱自然的強烈渴求,毅然決定離開城市,奔向遠方那個屬于自己的田園。
他渴望得到這片葡萄園,同時將其視作自己脫離苦難、救贖心靈的精神寄托。這種渴求承載著他對現代化社會中橫行的物質主義與精神異化的深深抵觸以及一種無畏的理想主義與犧牲精神。
張煒反思現代工業文明催生的焦躁和重利之風氣,不忍見到原本美好的自然和純粹自由的人性走向陷落,因而于文字中呼吁人性對于回歸本源、堅守精神家園的執著追求。
在寧伽的內心深處,始終供養著這樣一座純潔而神圣的烏托邦,其心靈對于真善美的執著追求與軀體所承受的苦難與壓迫對撞沖擊,促使他不斷深省反抗,并堅守心中美好的信仰。他無數次地奔走流浪,堅守著寂寞與孤獨,甘愿陷入這場艱難痛苦的精神斗爭中。葡萄園的出現揭開了寧伽內心的最后一層罩布,使他不再遮掩與忽視自己心底的呼求。過往的一切構成他流浪出走的原動力,精神的空虛逼迫他繼續追尋。
棲居葡萄園之后,寧伽淪陷于對大自然的狂熱癡迷中。與城市的生活不同,作者對于田園風貌以及鄉村風土人情的描寫是反復而細致的,田園的寧靜自由與城市中彌漫的物欲異化形成鮮明對比,野地里自然的美感呼之欲出。張煒不遺余力地刻畫出這樣一個恬淡美好、人人向往的田園生活,因此,一種慢節奏的古樸田園色調隨之緩緩滋生。
寧伽在這片土地上結識了各類同樣不堪世俗困擾的流浪子弟和久居鄉村、才華橫溢的避世人杰,他們意氣相投,彼此心心相印。在葡萄園的修繕初期,拐子四哥因為寧伽一句簡單的詢問,便帶著妻子萬蕙和大狗斑虎毅然離開了他們原本的家,轉而與寧伽共同打理起這片荒廢已久的田園;而與寧伽相識園藝場的肖瀟等人,更是時常出入并留宿于葡萄園中,連同四哥招來的兩個年幼瘦弱的幫工一起,他們在田野上度過了無數個快活自在的日夜。他們如同沒有血緣關系的家人,自然地相識、熟絡,結成一個和睦龐大的家族。他們之間所產生的感情真摯而坦然,如同這片青蔥肆意的野地,不摻利益,不問將來。
這塊不大不小的野地仿佛被時空遺忘,完美重現了一種田園牧歌式的情懷。鼓額對葡萄園的依賴、羅玲與肖明子之間自然滋生的愛意……在這里,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系都變得淳樸而和諧,人性天然的真善美縈繞在土地上方,大自然的神圣感發揮得淋漓盡致,它們共同構成了一個不論階級、貧富、外表,處處充滿包容與友好的理想社會。
然而,理想難以永存,暫時的棲居總會走向終點。村頭頭老駝的勒索、葡萄園納稅所經歷的坎坷、幾次侵犯鼓額的“鷹眼”、撲朔迷離的恩怨……城市文明緩緩鯨吞著這個隱秘的角落,鄉村的落后也緩緩浮出,父仇的迷霧縱橫交錯,寧伽終究無法安逸于此,于是打點行裝,跨越千里繼續追尋。
這是一種無處可去、也無家可歸的悲涼之感,寧伽無數次追憶過往的溫情,疲憊的軀體永遠不被內心允許而停止前進。最終,上一輩的故事邁向結尾,小木屋里的老革命家毛玉也病逝床前。寧伽回到葡萄園中休憩調整,于短暫的棲息過后,準備著迎接下一次的追尋。
幾十年間,寧伽不斷地逃避和漂泊,他的流浪是輪回式的奔跑,始終前行在對于社會與精神理想的探索之中,承受著信仰的一次次幻滅,他也從未放棄對自我的心靈救贖。寧伽形象的塑造繼承著作者本人的憂思,他成為20 世紀80 年代末和90 年代初社會變遷下不甘于被異化的傳統文人的投影,濃縮著當時人們內心的無奈與迷茫。
張煒反思現代物質社會對于文學和人性的負面影響,反復重申對理想藝術、崇高信仰和人生真實價值的不斷追求,這種尋覓是中國知識分子心靈深處的堅守。他們沉思著一個民族的精神發展,清醒地漂泊于無處可歸的前路。
三、流浪意識的形成因素
(一)物欲膨脹下的現代化
20 世紀80 年代末到90 年代初現代工業文明的快速發展突出了人與自然的矛盾,即人性的真善美、文學的藝術性和物質文明發展所產生的新型價值標準與消費主義之間的矛盾沖突。
文學市場陷入嚴重利益化與物質化的情狀,部分人們逐漸淪陷于精神上的寡淡與虛無之中,思想被物欲主義和資本色彩不斷洗刷,人性本有的美好品質被世俗消磨。
社會對人的異化引起了一干知識分子的高度憂慮,張煒也開始更加深入地探尋人與世界相處的方式。他心懷濃厚的憂患意識,將其痛心疾首的沉思和對時代發展的高度責任感都傾注于文學創作之中。他在小說里傳達的不僅是崇高的理想主義,更含有對于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精神歸宿、人生價值的評判標準、人與世界的關系和歷史發展方向的思考。
(二)傳統文人的道德觀念
張煒作為一位傳統的知識分子作家,他高度重視文學的詩意性與藝術性。由于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熏染,他不僅具備儒者典型的傳統審美理想,更是多次在其創作中抒發人與萬物和諧為一的道家理念。
張煒的許多小說中都存在著充滿自然氣息的棲居地,塑造出多個向往自然、心懷理想、抵觸功利世俗的重要角色。他傾向于追尋個人心中的理想信念,關注文學中所傳達的人性的“真、善、美”,重視小說語言、意趣和主旨的深度與廣度的塑造。
20 世紀80 年代末社會思想與文學發展的轉變為當時的中國傳統文人帶來極大沖擊,張煒思想中對自由和獨立人格的追求、對于文學傳統價值的堅守促使他不斷反省沉思,不斷將沉重的呼喚交付文學創作,渴望以筆喚醒迷失于物質社會的傳統道德與傳統文化。
寧伽是張煒思想的一個縮影,全書以他的觀念轉變和漂泊生活為中心,描繪了一個城市的出逃人、歷史的流浪者的心路歷程和他不斷面臨的種種困境與抉擇。換而言之,即為物欲主義思潮下理想主義的掙扎與探索。寧伽作為人文思想的代表,一直飽受著精神內耗的摧殘,他在現實與自由的去留中斗爭,在情感與人倫道德的羈絆里掙扎,他苦苦尋覓著人生存在的真正意義,以一種沉默卻不被動的姿態不斷引導我們對社會發展的軌跡拋出質問,并對于時代的應有之義進行深重反思。
寧伽這一人物與小說《月亮與六便士》的主人公斯特里克蘭有很強的相似之處,他們都被認為是當時社會的“流浪者”,不為優越的物質打動,只為心中所追尋的信念不斷漂泊。而他們之間的不同是,寧伽未能完全脫離世俗,依然懷有無法忽視的憂患意識。
張煒是歷史廣闊土地上的一個精神流浪者,他抵觸世俗的功利虛浮,不滿于現代工業文明發展所帶給人們的精神枷鎖和對美好自然的沖擊與蠶食。物質世界涌動的焦慮與浮躁使他無法停留,也無法克制自己流浪與尋覓的欲望。他懷念過去文人筆下樸實自然的文學,渴望回歸精神上的純粹和人性的本來面貌。他清醒地打量與揣度著社會的發展態勢,其心中對于人類社會的反思與批判造就他不朽的文學創作。
而寧伽身上的憂患意識,部分體現在他所背負的世俗苦難和沉重難言的家族秘辛之中,他一直掙扎于現實砸來的新一輪的考驗和自己內心深處的訴求之間,因為憂患,所以追尋。
他向妻子形容自己“不能老待在一個地方,那樣就會憋悶得生病”。不難設想,一個充滿理想與人文精神的知識分子如果不再抵御世俗的腐化和精神的惰性,他將永遠停留在原地,最終完全陷落于虛無。寧伽代表著生命的永不止息,象征著精神家園的永恒存在,如同永動的圓鐘般無法停擺,他終將奔跑在尋覓的路上。
數十年心靈的漂泊,離鄉的浪子最終拋下城市,邁向那個綴滿葡萄的理想之地,然而他最終沒有得到那片本以為自由美好的田園。寧伽看似擺脫了世俗帶給人的異化和精神摧殘,但隨著時間推移,物質文明的暴風卻終究會席卷上這片遙遠的村落。但寧伽心靈中的“野地”不會被世俗消磨,它是20 世紀90年代知識分子們執著堅守的精神家園,他們將跨過一道道爬滿葡萄的里程碑,繼續追尋人生的意義。
四、結語
張煒的流浪思想并非一蹴而就,社會的變遷不斷挖掘著他對理想主義與人文精神的進一步思考。他質問20 世紀90 年代社會所盛行的高度物質化的荒誕思想,探索人文精神的來路與歸處。張煒立于時代浪尖最灰暗的一端,清醒地凝望著社會思潮的動蕩,他堅守心底的信仰,永遠流浪著、追尋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