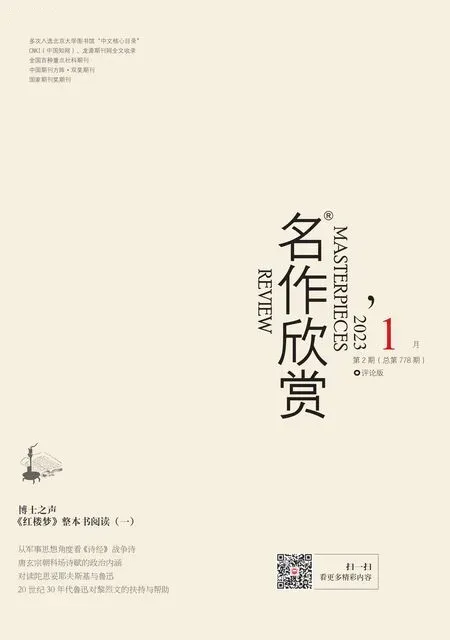論高校圖書館經典名著在大學生中的傳播作用
⊙祁文軍 [太原師范學院,太原 030002]
大學是一個國家和社會文化與科學教育的核心,是高水平專業人才培養、優質文化傳播的主要場所,其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國家科學文化“軟實力”的水平。其中,高校圖書館則是實體化的人類知識文明貯存庫,對于優秀的文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著作的保存,以及在大學生群體中傳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而受到當今網絡媒體興起、“實用主義”的社會價值觀念和單一評價標準導致“功利主義”盛行等因素的影響,高校圖書館中的經典名著作品“無人問津”、名著相關講座等活動參與學生寥寥無幾的狀況日益凸顯,圖書館硬件設施與館藏書量也逐漸成為單純衡量其級別層次的量化指標,難以真正起到進行通識教育、提升人文素養的作用。
本文筆者將以上述現象為出發點,主要聚焦文學類經典名著,闡述現今經典名著在青年人特別是大學生群體中傳播的現狀,分析大學生閱讀名著的現世意義以及為什么高校圖書館要承擔起在青年群體中傳播經典作品的責任,并就“如何進行名著閱讀推廣”針對高校圖書館方面提出建議。
一、高校圖書館在經典名著推廣與傳播中所面臨的困境
根據復旦大學“世界讀書日經典文本閱讀情況調研”結果,超半數高校學生三個月內的“經典文本”每月平均閱讀量不足一本,遠低于某西方國家大學生平均每周500 頁到800 頁的閱讀量,由此,名作閱讀與欣賞在我國大學生中的現狀可見一斑。筆者認為,高校圖書館想要改變這一現狀,在推廣經典名著閱讀有以下阻礙。
(一)電子化閱讀方式使閱讀內容快餐化、娛樂化
如今的在校大學生大多被稱為“互聯網原住民”的“Z 世代”,他們出生于1995 年至2009 年,在其身心成長、建立對于世界認知的重要時期內,網絡技術以驚人的、超越任何20 世紀科幻文學或電影中想象邊界的速度發展和普及。“不在‘上網’,而是活在‘網上’”,是對“Z 世代”青年的精準刻畫。因此,他們的閱讀方式和閱讀習慣無疑會受到網絡化、電子化的影響。
互聯網最突出的標簽是其便捷性,原因之一是它顯著提高了信息和知識可及性,降低獲取知識所需成本,但也使得閱讀與娛樂的邊界模糊不清,而這般“混淆”打破了名著閱讀需要的“儀式感”。名著經典閱讀往往要求讀者充分置身故事情節之中,通過與作家筆下人物的處境、情感發生共鳴來理解情節背后的內涵與意義;抑或是在自身體驗與作家觀點的碰撞中,產生新的觀點和認知。這些都需要投入一定的注意力和情緒成本,以及足夠的思考量才能完成。而基于手機、平板電腦等智能終端的屏幕閱讀以“短時間”“碎片化”為特征,習慣了“無紙化閱讀”的年輕人也較難獲得純粹、不被打擾的嚴肅作品閱讀體驗。
如今不少高校圖書館為順應屏幕閱讀趨勢,也開始提供“kindle”“超星閱讀器”等電子化閱讀設備的借出服務,但借閱熱度并不高。而在不久前,亞馬遜稱將于2023 年6 月30 日在中國停止Kindle 電子書店的運營,這一決策表明其對于國內電子閱讀器市場缺乏信心。對于將“閱讀”與自帶娛樂屬性的“電子產品”融合這一想法實現的難度,我們也從中得以窺見。在網絡化、電子化閱讀成為潮流的背景下,名著閱讀推廣難以基于這一載體達到理想的效果。
(二)網絡文學流行和經典文學的式微
的確,“人類需要故事”,而如今人們獲取這些“故事”的方式已經由紙質出版物轉變為網絡文學。網絡文學雖是在互聯網發展普及基礎上出現的新興文學形態,但以其中故事、人物為原型改編的影視作品而進行的成功的全媒體營銷案例已不在少數。網絡文學憑借其豐富跌宕的情節、復雜架空的設定,已經能夠滿足人們對于新鮮感、想象力甚至獵奇的全部需求。通俗的語言表達和普適的情感情緒,讓網絡文學對于讀者來說意味著更低的精力投入和更快更容易達到的共鳴。
誠然,網絡文學是時代和科技的產物、大眾的選擇,并且其中也不乏反思現實的優秀作品,但其終究是重“情節”、重“閱讀快感”,而輕“語言”、輕“內涵”的文學類型,與傳統的文學經典相去頗多。當今年輕群體作為前者主要的受眾群體,習慣于網絡文學的閱讀后可能會將“小說”與“故事”混為一談,局限于網絡文學提供的閱讀舒適區內,而再難以接納文學性、藝術性更強的作品。此外,大眾趨向于將名著經典與“晦澀艱深”等價,這樣的偏見將會加深青年群體對經典的畏懼、排斥心理。高校圖書館需要基于此進行正確和充分的引導,甚至可以嘗試將熱門網絡文學與相似題材的經典名著對比討論,開展講座或交流會,從相似中消除距離感,從差異中激發閱讀興趣,達到在高校學生中推廣名著閱讀的目的。
(三)高校圖書館“自習館化”現象
如今高校圖書館“自習館化”的現象愈發凸顯,甚至不少圖書館自習座位“一座難求”,而文學名著閱覽室“無人問津”;入館人次增加,但并未帶來紙質圖書借閱量和電子閱覽室使用量的上升,可見大學生閱讀積極性普遍不高。
筆者認為,這是由于名著經典閱讀需要投入一定的時間和專注力,但在對學術水平提升、履歷豐富等直接增加個人競爭力方面,大學生無法在短期內見到直觀成效。因此,在單一的學生評價體系下,競爭壓力日漸增大、焦慮情緒在高校校園中蔓延,以及在社會層面盛行的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不斷向大學校園滲透,有針對性的專業課學習或科研能力提升對當今大學生往往更具有吸引,而圖書館藏書也逐漸淪為營造“自習館”氛圍的道具和擺設。
二、大學生閱讀經典的意義以及高校圖書館承擔名著推廣責任的必要性
經典名著在大學生群體中的推廣面臨著上述諸多困境,但閱讀此類作品對于青年群體成長發展具有不可或缺的意義,因此推廣名著閱讀十分必要,這也是高校圖書館應當承擔的責任。
(一)大學生閱讀經典的意義
1.個人層面:培養文學審美和形成價值取向
“日光之下并無新事”,經典名著不僅承擔了展現人類文明足跡中文學和藝術高峰的重任,更記錄了先人智者對永恒議題的探討與追問。當科技發展的紅利使我們的物質、生理需求大體得到滿足,人們對更高層次的精神、自我實現需求日益凸顯,特別是正值世界觀構架、自我意識成型關鍵時期的大學生,不論是開闊視野、培養文學審美,還是認識自我、形成正確價值取向,在經典名著中進行自我教育都十分關鍵。
(1)閱讀名著對認識文學的審美意義
筆者認為,即使在不同歷史時期,對何為“優秀”故事、文學作品的評判蘊藏在人類共同的基因之中。這些經歷時間的篩選被賦予“經典名著”標簽的作品,必定處于各個時代特定審美內涵的交集之中,得到普通大眾和專業學者的廣泛認同。此外,身處不同歷史、社會背景的作者也一定會受其影響,甚至將一些經典作品奉為圭臬,有意或無意地對其進行著模仿和再創作。
因此閱讀這部分經典名著等同于直接地找到后世優秀作品的“本源”,了解經典的文學情節、人物設定、敘事結構,再從多數人共同的文學審美中逐漸明確自己的文學品味與志趣所在。若能在瀏覽當今時代的作品時,找到曾經閱讀過的經典名著的印記,對年輕讀者來說,無疑能夠提高閱讀信心和閱讀興趣,減輕與文學的隔閡感。對青年文學愛好者群體來說,閱讀經典名著,可以說是認識文學的“捷徑”。
(2)閱讀名著對形成價值取向的意義
從“古希臘哲學三賢”對世界起源的探討,到誕生于一戰后的存在主義對人生意義的追問,不論是依托文學創作為某個群體發聲,還是哲學流派中對人類終極命題的探索,作家和智者不斷思索著蘊藏在我們基因之中亟待解答的永恒議題、困惑是否有普適答案。這些跨越時空的回答,使得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的成長有道可尋,避免沉溺于虛無主義的深海之中。
例如,我國傳統文學經典《詩經》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木蘭詩》中花木蘭替父從軍,《紅樓夢》中林黛玉以《葬花吟》悲花悲己,等等;19 世紀的外國名著《傲慢與偏見》《簡·愛》《小婦人》,等等。從中能深刻體會其表達女性群體對形成獨立人格、實現個體價值,以及追求與男性同等的社會存在空間的訴求,這些主題之于當今毫不過時,甚至與近來熱議的“女性意識”“女權主義”等社會議題十分契合。
時下因為缺乏意義感,“空心病”在青年人群體中日益蔓延,而加繆的隨筆《西西弗神話》基于存在主義思想對人生目的的拷問,其思想仍有很強現實意義和借鑒價值。該作品講述了古希臘神話人物西西弗一次次推動巨石上山,到達山頂后巨石又再次滾落的故事。這樣重復的、極致的苦役象征著人生“荒誕”的本質;但西西弗不屈服于命運,正視荒誕,毅然反抗。他推石上山所走的每一步、他存在的每一刻都刻畫著生命的意義,最終達到精神上的自由,并獲得生命的激情和幸福。如今的大學生群體,若能同西西弗對命運堅定的反抗一般,接納荒誕和意外,必定獲得生命熱情、實現精神自由。
2.信息時代背景下:閱讀經典有利于提高青年人獨立思考能力
“信息化”是認識和探討有關當今高校學生相關議題時無法回避的元素,在之前的闡釋中,已經提及互聯網對當代大學生閱讀內容、閱讀習慣的巨大影響。除此之外,置身于信息爆炸的網絡之中,虛假信息和極端言論層出不窮,如何明辨是非,如何避免成為網絡戾氣的助長者、網絡暴力的參與者,是對用戶的信息辨識能力、獨立思考能力,甚至人性中對于善與惡的認知和自我約束的嚴峻考驗。而名著中不乏對人性進行深入探討的優秀作品,閱讀這些作品,能幫助他們在“多數即正義”的網絡環境中,守住底線,避免在無意識中成為造成雪崩的“惡”的雪花之一。
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的代表作《羅生門》就以簡練的情節敘述,犀利展現了“人性的善與惡可以在瞬間轉變”這一主題。這部短篇小說講述一位家仆在荒涼凋敝、尸橫遍地的羅生門下避雨,偶遇以拔死人頭發為生的一位老婦人,于是同樣身處困境的家仆惡性大發,剝下老婦人的衣服逃離了羅生門的故事。置身于網絡這個匿名的背景中,人內心種種幽暗的情緒可能會被釋放。該作品警示并教導作為互聯網用戶主力軍的大學生群體,必須對藏匿于自身的“惡”的部分保持警惕,即對熱點事件中心的當事人保持冷靜、理性辨別,避免為網絡暴力事件的推波助瀾。
(二)高校圖書館在名著傳播中發揮作用的必要性
高校圖書館作為校內的文化服務機構,不僅是大學的藏書樓,在對學生的人文素養熏陶、通識教育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方面,圖書館是對全體學生開放的知識資源庫,不同的專業背景、培養層次,只要具備一定的信息檢索能力,都能在圖書館搜尋到任何學科的經典或前沿信息。這對于構建學生完善的知識體系、實現文理學科滲透十分重要。高校圖書館可以組建專門的名著導讀活動小組,定期舉辦活動,培養學生閱讀經典的興趣、幫助學生形成閱讀意識。特別是理工科為主的高校,圖書館在名著經典推廣中需肩負起應盡的責任。
另一方面,對學生來說,大學時期是彌補中小學應試教育階段人文素養缺乏的最佳時期,學生的閱讀成本低、可及性高,高校圖書館閱讀材料豐富,并且是經過了一定篩選的優質閱讀內容。在一定的引導下廣泛閱讀,特別是對經過歷史沉淀的經典名著有一定涉獵,對于學生未來發展、個人幸福感提升都有重要意義。
三、高校圖書館推廣經典名著閱讀的可行措施
(一)將名家導讀講座與學生分享會相結合
講座是目前圖書館進行文化傳播的主要途徑,但由于講座嘉賓吸引力缺乏、內容乏味以演講者單方面輸出為主等原因,這類名著導讀推廣活動往往參與率不夠理想。高校可以將名家導讀講座與學生能夠自由發言的分享會相結合,提高學生的參與感和收獲感。
(二)將經典名著推廣融入進當下熱點話題中
當今大學生普遍對社會新聞、國際局勢相關話題都有較高的關注度和參與討論的熱情,因此,可以以此為依托,推出“從名著視角出發看社會熱點”系列公眾號推送,通過與高水平新聞評論員約稿合作、鼓勵學生以及知名校友投稿等方式,增加學生對經典作品的認知,從中體會其厚重內涵和文化底蘊。
(三)定期開展名著改編電影、戲劇展播活動
選擇經典名著改編的電影、舞臺劇錄像等進行播放,以融入了視聽、光影的藝術形式拉學生與名著的距離,也可以在展播后舉辦該部名著原作的進一步交流分析,激發學生的閱讀興趣。
四、結語
著名歷史學者、作家許倬云這樣解釋閱讀的意義:“拿全世界人類曾走過的路,都要算我走過的路之一。要有一個遠見,能超越你未見。”閱讀能夠使生命的廣度和長度充分延伸,而經典名著閱讀則讓讀者目睹人類文明中最閃耀的群星,同時這些光輝歷經數個世紀,對當代個體和社會的發展仍有指導意義。大學生需要名著,高校圖書館應承擔起學生與經典作品之間的橋梁和媒介作用,讓經典閱讀在高校校園中薪火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