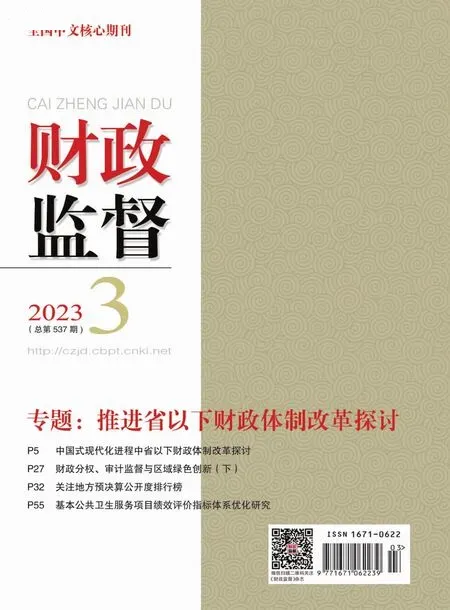財政分權、審計監督與區域綠色創新(下)
●裴 育 劉志威
四、實證分析
(一)基準回歸分析
本文使用stata16.0軟件首先對變量進行了Pearson檢驗,檢驗結果表明變量間的相關系數較小且多低于0.5,表明計量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線性,本文基準回歸模型成立。
接下來再對模型(1)進行檢驗與分析。首先使用Hausman檢驗確定使用“固定效應”還是“隨機效應”模型,經檢驗P值為0.000,選擇使用固定效應模型。對模型(1)進行回歸,得到回歸結果如表2第(1)列所示。
根據回歸結果可以看到財政分權變量與區域綠色創新的回歸系數為-2.69,在10%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說明財政分權變量的提高不利于區域綠色技術創新,驗證了研究假設1和假設2。原因可能是財政分權衡量的是地方財政權力大小,財政權力大的地方政府能夠更大程度按照自身意愿選擇財政資金予以使用。與此同時,2010—2016年間還未強調經濟高質量發展,所以地方政府可能更加重視短期能帶來效益的項目而忽略了對于綠色創新的支持,所以回歸系數為負。
控制變量方面,年末人均金融機構貸款余額、政府對環境與科技偏好和區域綠色創新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這是因為創新主體還是企業,地方金融發展越好越有利于企業、相關機構獲取研發資金,政府對于環境方面和科學技術方面的偏好也決定了在環保與創新方面的投入與關注程度,所以,以上控制變量都顯著有利于區域綠色創新。
為驗證假設3、假設4,對模型(2)進行回歸,結果如表2第(2)(3)列所示。表2第(2)(3)列中財政分權的回歸系數均為負且都在10%顯著性水平下顯著。監督方面選擇的是虛擬變量,0代表弱監管,1代表強監管。回歸結果都為負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我國2015年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17年黨的十九大提出經濟高質量發展,所以,中央政府對于綠色創新方面的重視程度是逐年上升的,在2010—2016年這個階段更加重視經濟發展速度;而地方政府受到中央政府的監管壓力,考慮到政治激勵、區域競爭等因素,會更加重視短期經濟收益而忽視長期的綠色創新發展。
財政分權與監督的協同作用為正且分別在5%和10%顯著性水平上顯著。二者單獨作用對于區域綠色創新都是抑制作用,而二者協同則對綠色創新具有促進作用,表明了二者協同能夠一定程度上矯正二者單獨作用帶來的負面影響。財政分權衡量的是地方政府自主權力的大小,而監管則是對這種權力的限制。地方政府對于地方信息掌握得更加準確,給予其一定權力能夠更好地發揮地方優勢資源。但是地方權力過大又會產生政府企業合謀、腐敗等問題,如地方發展依賴某些高污染高排放企業而放任其不進行或消極進行綠色創新的行為。所以,中央進行適當的監督能夠矯正這種行為。二者協同一定程度上激勵了地方綠色創新發展,產生了“1+1>2”的效果。
(二)穩健性檢驗
1.增加變量。參考周兵、劉婷婷(2022)的研究,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與地區規模會對綠色發展產生影響。所以,選擇使用省級國內生產總值(GDP)和地方人口規模(pop)表示地方經濟發展與地方規模。對數據進行處理取對數,結果如表2第(4)列所示,二者回歸結果均顯著且為正。根據黨云曉等人(2018)的研究,環境污染對居民幸福感產生負面影響。所以,人口規模越大對于良好環境的需求也就越高;而經濟發展越好的地區,政府和民間往往擁有更多的財力進行長期投資工作,所以促進了綠色創新能力發展。
2.更換變量。為驗證上述實證結果的穩健性,替換解釋變量審計監督強度(X)為各省審計單位數(X1)。回歸結果如表2第(5)列所示,解釋變量的更換并沒有改變基準回歸得到的結果,二者單獨發揮作用時依然不利于區域綠色創新技術的發展,而二者協同作用則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二者單獨作用時產生的負面影響。

表2回歸結果
(三)進一步分析
1.作用機制檢驗。財政分權是一種權力的分配機制,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對于地方的約束,增加地方自主性使其能夠根據自身情況來選擇財政資金的使用。但是地方權力過大也可能會產生尋租腐敗行為、加劇地方之間的競爭,也有可能不利于地方財政預算資金的充分使用。根據唐齊鳴、王彪(2012)的研究,財政自主度會顯著影響地方財政支出效率;而監督則是對于地方行為的一種約束,根據上官澤明等(2020)的研究,財政審計能夠約束預算機會主義,也能夠對地方政府產生威懾(楊賀,2015),規范其行為準則。這二者共同作用可以改善地方政府財政資金的支出效率,財政資金支出效率高意味著相同資金的情況下能夠產生更多的收益,政府對于綠色創新的支持行為也會更加有效,產生的收益也會更多。
由此可以推斷,財政支出效率(Eff)在監督與財政分權同綠色創新能力的關系中起到了中介作用,由于本文研究的是綠色創新問題,參考了范慶泉(2015)、潘文卿(2015)等人的研究,將教育、醫療衛生、文化體育與傳媒、社會保障、環境保護等方面的支出界定為具有消費性的財政支出,代表財政支出效率。參考劉江會、王功宇(2017)的研究,使用DEAMULTI-STAGE方法測度財政支出效率,對指標進行正規化處理后最終構建出地方政府產出效率,選擇規模效率作為衡量財政效率的指標。指標構建如表3所示。

表3指標構建
根據溫忠麟、葉寶娟(2014)的研究,設定以下模型檢驗中介效應:

首先,檢驗財政分權與監督及二者協同對于區域綠色創新能力的影響,該步驟在基準回歸中完成。接下來驗證上述三者對于財政支出效率的影響,考察模型(3)中β1、β2、β3的顯著性。最后考察財政支出效率在監督和財政分權同區域綠色創新關系中發揮的中介效應,檢驗模型(4)中α1、α2、α3、α4的顯著性。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

表4中介效應回歸結果
通過回歸結果可以看到β1、β2、β3、α1、α2、α3、α4均顯著。根據符號的正負性,監督與財政分權項均不利于財政支出效率的提高,而二者協同作用則有利于財政支出效率的提高。β1×α4、β2×α4、β3×α4與α1、α2、α3相同,表明財政支出效率在這個過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2.異質性檢驗。不同地區風俗文化以及初始稟賦不同,所以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之間的關系會產生些許差異。將本文使用的29個省份劃分為東、中、西部三個地區分別進行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東部地區省份往往較為富裕,政府財政能力往往較高,對于整個地區的影響會更大,政府間的競爭也會更加激烈。所以監督單獨起作用時,可能會限制地方的自主性,加劇地區間的競爭壓力,從而不利于政府進行綠色創新方面的長期投入;財政分權單獨起作用時,地方自主性過大,地區更加富裕,更容易產生尋租腐敗等問題,而且同樣也會激化不同地區的競爭,不利于區域綠色創新能力的提高。而二者協同作用時,監督是對于財政分權體系下地方政府行使權力的一種約束,合理的監督與財政分權體系的搭配能夠在充分發揮地方信息優勢以及自主性的前提下保證地方政府在既定的規則下行使權力,從而有利于區域綠色技術創新的發展。
相比于東部地區,中部地區地方政府財力及其對于整個區域的影響力都小于東部地區地方政府。回歸結果中的監督與財政分權指標都顯著且為負,二者單獨作用時系數的絕對值都小于東部地區的絕對值,表明在中部地區監督與財政分權單獨作用時對于區域綠色創新的影響力較東部地區更小;二者協同作用時回歸結果為正,但是也偏小,同樣是因為中部地區政府影響力較東部地區更小。
西部地區的回歸結果三者都不顯著,可能是因為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較差,導致地方政府無力支持綠色創新發展,所以在回歸結果上表現為不顯著。

表5異質性分析回歸結果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以我國29個省份2010—2016年的數據為樣本,檢驗了財政分權、監督效果以及二者協同對于區域綠色創新能力的影響。研究發現:
第一,財政分權體系下地方財政自主性越強,越不利于區域綠色技術創新發展;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過強的審計監督也不利于地方區域綠色技術創新發展;如果二者協同發揮作用,則顯著促進了地方綠色技術創新,一定程度上說明二者協同發揮作用可以部分抵消二者單獨發揮作用時對綠色技術創新所產生的抑制作用,表現出了“1+1>2”的效果。
第二,財政支出效率在財政分權和審計監督影響區域綠色創新的過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進一步分析發現,首先檢驗作用機制,選擇財政支出效率作為中介變量。財政分權和審計監督二者單獨作用時顯著抑制了財政支出效率的提高,而二者協同作用時則促進了財政支出效率的提高,財政支出效率的提高能夠顯著促進區域綠色創新。在異質性檢驗中,將29個省份分為東、中、西部地區,分別進行回歸分析,結果表明東、中、西部地區審計監督與財政分權對于綠色創新的影響受到地域的影響。在東部地區二者單獨的抑制作用以及協同發揮的促進作用都顯著大于中部地區發揮的作用,同時二者協同發揮的促進作用在東部地區遠大于中部地區,而西部地區三者均不顯著。
根據上述結論,提出兩點政策建議:
第一,在當前“放管服”改革深入推進的背景下,要酌情考慮財政分權體系下中央與地方權力的劃分,盡量發揮分權體系下地方政府自主性,同時防止出現地方權力過大產生的不利影響,所以需要對地方政府進行適當的審計監督,合理搭配審計監督力度與分權配置,充分發揮二者協同對于綠色創新以及財政支出效率的促進作用,減少二者單獨作用時產生的抑制效果。
第二,重視不同區域的發展差距,適當安排審計監督與分權配置。同時重視落后地區經濟發展,提高政府在區域內的影響力,這樣才能更好地發揮出審計監督與財政分權協同對于綠色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