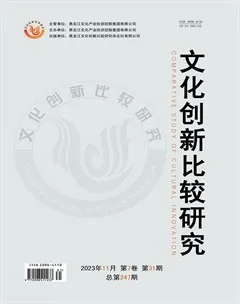從三種張力中走進古希臘
——對《楊布里科斯著〈畢達哥拉斯的生平〉》的一些補充說明
沈小龍
(衢州學院,浙江衢州 324000)
畢達哥拉斯是古希臘著名的數學家和哲學家,他把非物質的、抽象的數界定為宇宙的本原,認為“萬物皆數”“數是萬物的本質”。他的數本源論及其衍生的理念論和共相論對柏拉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并進而持續影響了西方哲學和神學的發展。即將出版的譯著《楊布里科斯著〈畢達哥拉斯的生平〉》(以下簡稱《畢達哥拉斯的生平》)的原著者楊布里科斯(Iamblichus)是3—4 世紀重要的新柏拉圖主義哲學家。譯著是根據1818 年在倫敦出版的英譯本譯出的,英譯者是英國翻譯家、新柏拉圖主義者托馬斯·泰勒(Thomas Taylor,1758—1835 年),他也是第一個用英語完整地翻譯了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全部著作的人。譯著標題雖說叫作《畢達哥拉斯的生平》(Life of Pythagoras),但在原標題下方也有小字 “or Pythagoric Life”。這也就是說,把該書稱作一本描寫“畢達哥拉斯式生活” 的書也是合適的,而且從書中內容來看此言非虛。書中除了描述畢達哥拉斯的生活軌跡、哲學和宗教思想、政治和哲學實踐等內容之外,還描述了許多畢達哥拉斯門徒的事跡,他們不顧生死安危也要堅守他們的 “畢達哥拉斯式生活” 的態度讓人動容。因此,拋開該書作為重要哲學和歷史文獻的價值不談,僅就了解古代希臘的社會風貌、生活狀態而言,該書都大有可讀之處,甚至當作一般的名人傳記來閱讀,也并無不可。
現在一提到哲學,恐怕馬上就會將其與晦澀難懂、門檻甚高的印象聯系在一起。實際上,哲學也無非是人們從生活實踐中得到的認識。《畢達哥拉斯的生平》就很好地呈現出哲學誕生之初的狀態:它與宗教、政治、倫理、科學、巫術,甚至所謂 “魔法” 之間的界限都是模糊不清的。而那個現在看起來蒙昧的古代社會,實際上在懵懵懂懂的摸索之中孕育著改變未來的巨大力量,而這種摸索顯然不可能脫離古人的生活實踐。換而言之,如今人們看起來神乎其神、難以置信的事情,在當時時代背景下卻離人們的生活并不那么遙遠。所以,如果用某種生活化的眼光去看待該書、看待哲學,恐怕才更容易理解古人的思想。當然,閱讀樂趣也會多很多。
在國內讀者的認識當中,畢達哥拉斯的名字可以說是耳熟能詳的,因為國內中小學數學課上或多或少會提到他。但是在準備出版《畢達哥拉斯的生平》的時候,筆者意識到,這種對畢達哥拉斯及古希臘的耳熟能詳只是一種極為流于表面的印象,對于真正理解畢達哥拉斯及其學術思想并沒有太多幫助。為此,本文試圖從地理觀念、宗教觀念和政治觀念3 個方面提供一些信息上的補充,以期能夠幫助讀者更好地閱讀。
1 由地理觀念而來的海洋與陸地之間的張力
首先必須了解希臘人的地理觀。希臘的地理環境不像我國,希臘人的地理觀也與國人的地理觀大相徑庭。我國最早的地理古籍《山海經》[1]所描繪的是一個東西南北都能走上上萬里也還是陸地的大陸,而大陸之外是遼闊的大海。這一圖景構成了 “天圓地方” 的傳統認知。而這一認知是以陸地為主軸的,就如同在山海經所展現出來的那樣,從中原出發往東西南北四個方向途經萬里之遙(古人在地理上自然是不夠精確的)之后才是大海。大海是大地的邊緣,也是人們認識和生活世界的極限,在大海之外的事物似乎都是只能想象無法去探索求證的。
然而,希臘由于身處地中海獨特的地理單元,人們眼中的大陸顯然不如海洋廣闊,但他們所處的海洋也絕非我國古書中所描述的,是一望無際的、只能憑空想象的海洋。準確地說,希臘人所處的地理環境是 “山海相連” 的。歐洲南部的一個個半島由于其多山的地理構造形成了一片片相對于大陸獨立的地理單元,但卻又被風平浪靜的地中海整合為一個完整的區域,地中海(Mediterranean)的意思本來就是 “陸地中的海洋”,再加上巴爾干半島擁有崎嶇漫長的海岸線、遍布高聳的山地,但河流短小、平原面積很小,這些情況使得希臘人早早地將目光投向大海,并且早早地知道了大海之外并不完全是大海,還有更廣大的陸地。
不過,地中海沿岸的民族眾多,僅僅一個 “靠海吃海” 的理由是無法激勵希臘人離開象征穩定的大地而走向殖民地中海沿岸之路的。實際上,地中海獨特的氣候也是十分重要的影響因素。在我國主要農業產區,氣候四季分明,雨熱同期,大部分年份降水集中。而在地中海沿岸,不僅各季節降水量差異巨大,而且雨季是冬季,旱季是夏季,不同年份的降水量也相差甚遠。根據查爾斯·弗里曼的《埃及、希臘與羅馬:古代地中海文明》[2]的說法,愛琴海北部的城鎮卡瓦拉(Kavala)在20 世紀60 年代的時候年降水量最高達897 mm,最低僅有252 mm。這個城鎮在古代叫作尼亞波利斯(Neapolis),并且研究顯示,當地在古典時代的氣候和今天相差無幾。這樣的氣候,顯然不可能像古代中國那樣,期待每年季風所帶來的降雨和隨之而來的豐收(盡管間或有災年,但相較而言更穩定),并且計算出收成。所以說,希臘人恐怕很難像中國人那樣狂熱地將土地視作穩定收益的象征。另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戰國時代的日本。日本和我國東部同樣屬于季風氣候,當時衡量一個大名的實力計量標準用的是 “石高”,即這個大名所擁有的土地一年所能產出的糧食數量的預期。顯然,這樣的預期在古代希臘是行不通的。此外,像《呂氏春秋·上農》[3]中那樣明確地把農業稱作本業、商業稱作末業的看法也恐怕更難獲得支持者。
既然土地并不能很好地保證收益,那么出海冒險去搏一搏運氣,就更容易成為一個有吸引力的選項。公元前3 世紀的希臘詩人就寫過《阿爾戈英雄紀》[4],描述了伊阿宋為首的一眾希臘英雄,乘坐阿爾戈號,進入黑海尋找金羊毛的冒險故事。當然,冒險所需要的動機有了,經驗和技術也不可或缺。在這方面,四海為家、到處探險的腓尼基人很早就掌握了遠航的技術,并充當了包括希臘人在內的地中海航海民族共同的老師。根據希羅多德在他《歷史》[5]中的記載,腓尼基人早在埃及法老尼科二世(Necho Ⅱ)所處的時代就完成了環繞非洲的壯舉。通過對腓尼基人造船技術和航行技術的吸收,大海在希臘人眼里不再是一種限制,而是一條帶來知識、財富和希望的路。正是通過海洋這條路,希臘四大部族(愛奧尼亞、伊奧利亞、亞該亞、多利亞)不斷遷出,最終遍布地中海沿岸,形成了希臘世界。
在《畢達哥拉斯的生平》書中,可以看到航海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如畢達哥拉斯的父親靠航海致富、畢達哥拉斯靠航海游離各方獲得了智慧并創立了畢達哥拉斯學派、來自地中海沿岸各地的人們通過航海拜入畢達哥拉斯學派門下等。可以說,想要進入希臘人的內心,就要先意識到海洋在他們心目中的地位。但是,也不能忽視的是,斯巴達人恰恰不熱衷于航海,許多城邦的公民資格也是看公民是否擁有城邦附近的土地(若失去這塊土地就失去了公民權)。海洋和陸地,是希臘文明的第一種張力。
2 由文化觀念而來的父與子之間的張力
希臘人的文化觀念也與中國人大不相同。其中尤其突出的是關于倫理方面。閱讀古希臘的神話傳說,人們會發現,希臘許多神教似乎有一條 “弒父” 的主線。根據赫希俄德的《神譜》中的描述,克洛諾斯推翻了自己的父親天空之神烏拉諾斯的統治之后才坐上了第二代神王的寶座。第三代神王宙斯是克洛諾斯的兒子,他同樣在擊敗了克洛諾斯之后才奠定了其眾神之王的地位。公元前5 世紀由索福克勒斯所創作的著名悲劇《俄狄浦斯王》[6]中,主人公俄狄浦斯也最終弒殺了自己的親生父親。由于該故事本就取材于膾炙人口的傳說,所以可以認為,俄狄浦斯的弒父這一情節在希臘人的認識當中是有相當基礎的。
這種 “弒父” 行為在中國傳統觀念里,是被視為大逆不道的。儒家思想作為中國傳統宗教文化觀念的集大成者,大致上是強調君臣父子之間的倫常秩序的。而如果要跳出這種秩序(打破顯然更是艱難),則意味著要付出極大的代價。例如,在哪吒的傳說故事中,哪吒路見不平殺死了龍王三太子,其父李靖就要大義滅親。哪吒 “剔骨還父,割肉還母” 之后終于得以蓮花托生,卻最終仍要受制于李靖的寶塔。另一個廣受歡迎的反抗者孫悟空,則索性設定成無君無父,純粹從天地靈氣中生成。然而即使這樣,孫悟空也最終逃不過如來佛的手掌心,扛不住唐僧念的緊箍咒,不得不走上西方取經的 “證果” 之路。
因此,盡管東西方的傳統中,都同時擁有 “尊老”的傳統,也同時擁有 “棄老” 的陋習,但顯然在古希臘,人們耳濡目染這些關于 “弒父” 的古老傳說,對此固然認為是某種悲劇,卻暗暗給自己留下了一些辯解余地。中國民間宗教雖然很早就被塑造過,但是后世對于三綱五常、君臣父子、上慈下孝秩序范式的強調,仍然可以溯源而上。可以說,中國傳統文化相比希臘更為維護父權制。而按照弗洛伊德的說法,希臘文化中這種對父權的不以為意,最終誕生了包括民主制度在內的西方現代文明。
西方的民主制度究竟是不是和他們的 “弒父” 情結有關,筆者認為還需要更為深入的思考和論證,但是至少可以明顯感受到東西方對待父親權威的態度是非常不同的。在中國傳統文化當中,對父親的權威就算偶有反抗,但最終采取的都是一種順應或者順從的態度。而在希臘傳統文化中,父與子之間更呈現出一種搖擺于服從和反抗之間態度。
這種不同其實相當好理解。已在上文提到中國和希臘地理環境的不同,從而使得兩地呈現出所謂“大陸文明” 和 “海洋文明” 之間的差異。實際上,這樣的差異使得兩地的生產方式大不相同,尤其是財富積累的方式大不相同。在中國傳統認知中,積累財富與增置土地是分不開的,因為經商本身就意味著風險,有虧損的可能,而土地所帶來的收益是相對穩定的。在《史記·貨殖列傳》[7]中有 “以末致財,用本收之”的說法,反映出在中國傳統認識當中,就算通過經商獲得了收益,也要購置土地來保值。然而,土地財富的流動性遠遠不如商業財富,在大多數場景下,土地產權的大規模變動都是因為繼承(如果不算改朝換代的話)。這使得父親相對兒子擁有壓倒性的財富,這種經濟權力使得兒子不得不順從父親。
在希臘傳統中,由于人們更多地被鼓勵通過航海、經商等冒險來獲得財富,這使得父與子之間的經濟力量對比并不總是那么一邊倒。例如,梭倫出身于沒落貴族家庭,靠自身經商才逐漸致富;庇西特拉圖在兩次被流放后在希臘北漂泊數年,通過經營礦山而致富;在《畢達哥拉斯的生平》中,畢達哥拉斯的父親是通過在海外經商而致富的(幸運的是,由于他的早逝,畢達哥拉斯不用面對來自父親的強大經濟權力)。又由于希臘本土土地生產能力低下,使得財富的多少與家族繼承之間的相關性下降,以父權為底色的貴族權力也就因此出現了動搖,新興階級的興起擁有了更多可能。父與子之間關系的變化是希臘文明的第二種張力。
3 由政治觀念而來的民眾與精英之間的張力
上文已提到某些發軔于文化傳統卻最終影響了政治的議題。但是,回過頭來說,盡管兒子通過冒險等行動增加了自身的力量,但父親并非完全無力。土地而來的權力仍然在希臘社會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不僅從希羅多德、修昔底德等人的文獻記載中可以得知大多數城邦在早期都曾形成過某種長老(元老)議事制度,在《畢達哥拉斯的生平》中,進一步得知一個城邦(或者說殖民地)最初都是通過熟人紐帶形成的。這些長老(元老)后來慢慢演變成貴族。但是由于海外貿易等商業或者說冒險行動,在某些地方,貴族們的相對力量下降了。新興勢力的上臺,所依靠的力量自然與舊有勢力不同,于是在強調土地、血緣等因素之外,又多了一項新的標準,即財產。以財產多寡來分割政治權力的典型案例與象征,就是梭倫改革。
梭倫改革可以說為雅典式的民主制度開辟了道路,但公民大會與貴族(元老)之間的矛盾也就此突出。但是,財產的多寡在商業文明中本身就不那么穩定,因為它取決于很多不確定的因素,這些因素又相當程度上可以歸結為運氣。一個普通公民完全有可能因為經濟地位的變化而在政治上轉變立場。這使得政治家為了迎合公民大會,也經常見風使舵。在這種左右搖擺的政治角力之中,雄辯術被大量利用以煽動民眾、獲得支持,而反對派則自詡理性以對抗這種狂熱。一種民主(民粹)主義與精英主義的張力悄然產生。這里,尤其需要認識到,民眾并非天然擁護民主制度,他們完全有可能被僭主的承諾所誘惑而反對民主制度;貴族也并非必然是精英的代言人,貴族為了獲得權力一樣可以完全導向民眾。在此之上,更應該認識到,僭主完全可能為民眾的福祉鞠躬盡瘁,而民主(民粹)派的執政官也完全可能為了個人利益而出賣全體公民。這種黑白混雜、立場多變的政治,才是古希臘政治的底色。
但是,在其中可以像現代左右政治那樣,描繪出某種光譜。斯巴達始終更看重土地,因此斯巴達人最為保守,長期由貴族把持政權(經歷民主政治和僭主政治的時間都相當少);雅典商業最為發達,在政治上最為激進,民主派長期執政,甚至僭主統治時期都不敢廢除民主派的改革成果,反而要去進一步維護。而具體到個人,大致可以看到,許多知識分子通過理性判斷,認識到了民主滑向民粹的弊端,因此都秉持精英主義的立場,而他們所斥責的對象通常是民粹派(自然少不了對民粹派進行抹黑,當然許多指責也確實是事實),連帶對民主政治也多有批評。許多政治家(立法者)是支持民主(民粹)派的,因為在實際政治運作中,只有這樣才能通過公民大會上臺執政,當然很多人上臺之后就成了僭主。
盡管畢達哥拉斯自己在早年為了逃避僭主政治而逃到了米利都,但是他的很多觀念卻是精英主義的。他的這種精英主義影響了他的門徒,并且最終讓畢達哥拉斯學派被克洛同的民粹主義所反噬。但他的立場實際上流傳到了柏拉圖[8]那里,并經由柏拉圖傳遞給了亞里士多德[9]。柏拉圖提出了 “哲人王” 的概念[10],而亞里士多德則提出他的理想政治框架:城邦是一個公社(共同體),其成員主要生活在城市之中,并依靠周邊的土地來養活整個公社。這種政治框架在亞里士多德的時代顯然已經離現實越來越遙遠了,但他們各自在學說中提出了關于 “什么是好的政治(治理)”,即 “什么是善政” 這樣一個議題,其影響直至今日。而這是他們及他們尊奉的祖師畢達哥拉斯對于當時混亂又不成熟的早期民主制度所得出的深刻反思,與民主制度一樣,是在民眾與精英之間的張力之中所結出的碩果。
4 結束語
當人們在閱讀西方古典文獻的時候,實際上很難避免以下兩點:一是以現代人視角去揣摩古代人;二是以東方人視角去揣摩西方人。但是如果時刻注意這種東西古今的差別,放下某些先入為主的意識,那么將會大大有助于理解。在此基礎之上,如果再盡量多地從各種渠道攝取不同的信息,然后運用理性去蕪存菁,那么相信面對再難的文本,都可以將其克服,并從中獲得助益。此外,還需特別注意的是,包括《畢達哥拉斯的生平》在內的許多西方古典文獻是以一個非常不完美的狀態傳遞的:一部分原因是文本中存在著大量的語言錯誤;另一部分原因是譯者想要找到敘述事情之間的關聯;還有部分原因是許多不同地方的引用細節采用了非常相似的用詞。《畢達哥拉斯的生平》 里描繪的畢達哥拉斯的生平是一個美德與智慧得到最大圓滿的樣本,這是可以在當前狀態下由人去獲得的。因此,《畢達哥拉斯的生平》表現出不摻雜愚弄的虔誠、不沾染惡習的情操、不利用詭辯的科學、不夾雜傲慢的德行;表現出在理論上的莊嚴和崇高,卻沒有在實踐中退化;表現出在智識上的活力,讓其擁有者對于神性的見解更為高尚,并升華了其自身的神性。這或許也是筆者再次推薦這部即將出版的譯著的理由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