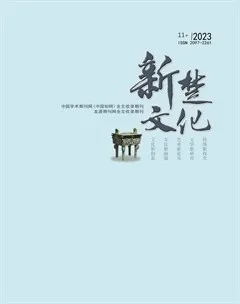荀子“化性起偽”思想的辯證意蘊
劉暢
【摘要】荀子以“性惡論”為基礎,認為人之性本惡,因此進一步提出了“化性起偽”的方法論,旨在通過后天教化和努力完善人性,實現“善”的道德人格。荀子“化性起偽”的理論觀點中蘊含著豐富的辯證法思想,“化”強調了從“性之惡”到“性之善”的矛盾轉變,“偽”強調了道德實踐與道德能動的重要性。“人之惡”可以通過“化性起偽”的方法論達到“虛壹而靜”的高尚境界,最終實現自身道德修養的提升和“善”人格的塑造。
【關鍵詞】“化性起偽”;性惡論;主觀能動性
【中圖分類號】B222.6 ?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7-2261(2023)32-0004-03
【DOI】10.20133/j.cnki.CN42-1932/G1.2023.32.001
荀子作為戰國晚期儒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在我國倫理思想發展史上占據著不可替代的地位。與儒家另一位杰出代表人物孟子主張的“性善論”不同,荀子基于當時農業經濟快速發展、諸侯割據爭霸、思想領域百家爭鳴的時代背景環境下,提出了“性惡”的人性論,并在“性惡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化性起偽”思想。站在馬克思主義哲學視角下分析荀子的“化性起偽”思想,更能體現其思想中帶有唯物主義的進步性,對我國先秦時期政治統治和整體倫理思想體系的完善起到了深遠影響,對當代社會的發展也提供了寶貴的理論基礎。
一、“性惡”:“化性起偽”之根
針對孟子以“四心”為“四端”的“性善論”,荀子提出了“性惡論”的思想主張,并在“性惡論”的思想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化性起偽”的人性論。“孟言性善,欲人之盡性而樂于善;荀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勉于善,立言雖殊,其教人以善則一也”[1]。在孟子的性善論中,孟子將“四心”,即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作為仁義禮智的四端,認為人性是與生俱來的善,是人作為動物卻又區別于動物的根本原因,進而強調“四心”的重要地位,以此來加強對人們的道德教化,提升人們的道德修養,進而實現社會的和諧和政治統一。而荀子則提出了與之相對的“性惡論”,雖然荀子也主張人性是與生俱來的,但荀子的“性”更多強調人們的自然本性,“生而有好利”“生而有惡疾”“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這些都屬于人的自然本性,因而也就無所謂善惡。所謂的“善”并不是與生俱來的,是通過后天環境的改善和人為努力教化等途徑實現的,是經驗的而非先驗的。“荀子關于‘人性思考的落腳點是基于儒者對‘善的執著追求,而其‘化性起偽理論的提出則是為‘性惡尋求救贖”[2],最終實現“性惡”到“性善”的良性轉化,完成高尚完整人格的塑造。
二、“從善”:“化性起偽”之意
荀子以“性惡”作為其思想體系的出發點,認為人們如果對與生俱來的天性不加以控制,肆意妄為,就無法做到善,更難以達到圣人的境界。荀子的“化性起偽”思想為人們求善提供了有效途徑,強調人們可以通過后天教化來改變先天的惡,通過外在環境和外部力量,遵循由外到內的發展途徑,促使人們向著善發展,從而實現整個社會的和諧與善。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角度來看,荀子的“化性起偽”帶有一定的唯物主義的進步性,對當時文化背景下的倫理思想產生了深遠影響。
“性”,在荀子那里解釋為“人的自然本性”,“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3]。在荀子看來,這種只有通過后天人為努力而發展向善的本性才是人之性。這種自然本性在生活中的外在表現形式就是人們生理本能和各種情欲,這些情欲本身是惡的,阻礙著人們向善,但同時這些情欲又是可控的、可變的。荀子對性、情、欲做出了一定的解釋,“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性是人們一出生就帶有的自然本性,情是性的實際內容,而欲是人們情和性在生活中的外在表現。人們無法實現“善”的根本原因就是性、情、欲的存在。
“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3],荀子“化性起偽”中的“偽”可以理解為后天的人為努力和作用。荀子強調對先天與后天進行區分,否認孟子的“人生而性善”的人性論,反對將“性善”認為是一種先驗性的存在。在荀子看來,人生來性惡,對仁義禮智并不了解,因而也就無法言善,而偽的作用就在于讓人們充分發揮人所特有的主觀能動性,對自身的自然本性進行改造,強調的是人們從自然的本性的惡向善的一個改造和完善的過程,即人們在生活中所表現出的善行、所存在的善性都是后天人為努力的結果。從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認識論來看,“偽”體現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在實踐過程中的重要性。人作為動物又區別于動物的根本是人所獨有的意識的存在,人們的意識具有自覺性、目的性,因此,人們能夠在意識的指導作用下,自覺地采取適當的行為,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進而認識世界、改造世界。荀子通過強調“偽”對“性”的教化作用,以激勵人們對“性”進行合理控制和發展,實現善的人格。
從唯物主義辯證法的視角來看,荀子“化性起偽”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聯系觀、發展觀和矛盾觀的理論內涵。從聯系觀來看,“性”作為人的自然屬性而存在,“偽”則是強調人的社會屬性的重要性,“性與偽相輔相成,一為本始的材質,一為禮義道德的加工”[4],二者相互聯系,相互作用。一方面,“性”是“偽”的重要前提和基礎,沒有“性”,“偽”就失去了主觀能動性的客體;另一方面,沒有“偽”,人們的“性”仍然是惡的,人們就無法實現由惡到善的轉變。從發展觀來看,荀子的“化性起偽”實現了對“惡”的棄和“善”的揚,通過“偽”的揚棄實現了人們從“好利”“好聲色”到“善”的發展。從矛盾觀來看,“化性起偽”強調通過“偽”指引人們向善,在人們發揮主觀能動性的同時實現了人由惡到善的轉變,將矛盾雙方善與惡進行一定條件下的轉化,帶有一定的辯證法意義。
三、“去惡”:“化性起偽”之道
荀子主張通過“化性起偽”的途徑促使人們去惡趨善,去除人們身上與生俱來的惡性,克服人們的“好利”“縱欲”之惡,積極發揮人作為人的主觀能動性,對人們的情、欲通過后天的人為作用加以控制和改造,“故圣人化性而起偽,起偽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5]。人們通過內修與外化的雙重路徑的結合從而完善自我,培養自我的向善人格,進而促進社會秩序的和諧穩定和政治統治的長遠發展。
(一)尊師重道
荀子在“化性起偽”的過程中強調“師”的重要性,將教師的地位上升到與天同等高度的地位。尊師重道的倫理思想在儒家思想體系中一直占據著重要地位。“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荀子強調人的發展離不開教師的引導和教育,教師在人們修身養性的過程中扮演著引導教化的重要角色。由于人們一生下來就性惡,所以人們在修善過程中就需要教師來指點迷津,循循善誘,因材施教,通過教師對于善的引導,讓人們意識到自身的惡和向善的重要性,進而對自身行為進行調節和規范,使自身行為符合善的要求和意義。
教師在對人們進行教化的過程中,主要是通過為人們灌輸善的意義和價值,首先從思想意識層面進行引導,使人們樹立向善的思想意識,進而在生活實踐活動中踐行善的原則,實施善行。荀子認為如果社會上的每個人都知善行善,那么也就達到了理性社會的境界。知善而后行善蘊含著意識與實踐的辯證關系,反映了意識對實踐活動具有反作用,“知善”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無論是對于社會個體的道德實踐而言,還是對于統治階級的政治實踐而言,都產生了一種積極的意識引導作用,推動人們向善發展,完善自我人格。
(二)隆禮重法
荀子認為,人生來性惡,如果每個人對自身的性、欲、情無法加以控制與改善,對自身的所言所行不加以后天的道德規束,縱容其肆意發展,那么人性就會一直處于惡的地步,也就無法實現善,無法成為圣人。因此,荀子重視禮在教化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認為禮是人們去惡趨善的必要手段和關鍵環節,也是人之為人并進而成為圣人的最終目標和最高境界。“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荀子認為,圣人之所以為圣就在于,圣人認識禮,重視禮,嚴格遵循禮的教化,按照禮的道德要求來約束自己的自然本性,規范自己的言行舉止,進而實現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偉大理想。另外,禮也被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禮被認為是統治階級進行政治管理的重要手段,通過禮對君臣的言行加以規范,在尊卑等級的制度基礎上加以禮的倫理訴求,從而使“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促進社會和諧有序地發展。
荀子在強調禮的同時也看到了法在“化性起偽”中的重要性,進而主張隆禮重法。人們的自然本性不僅需要禮的教化,也需要法的外力輔助,借助法的強制作用和懲戒作用,對人們的欲望、利益形成一定的外在約束機制,使人們遵守倫理道德規范,使其自身符合善的價值標準。荀子的法適用于社會上的一切人,無論王公貴族還是平常百姓,都要嚴格遵守法的規定,法無貧富貴賤之分。荀子的法不是法家的嚴刑峻法,更多意義上是作為禮的補充和輔佐手段而存在,通過強制作用對人的行為加以約束,從而培養善,發展善。
荀子的“隆禮重法”思想中的“禮”和“法”,利用唯物主義辯證法,從矛盾觀的主次要方面來看,一方面,荀子繼承發展儒家的禮義思想,將禮看做是“化性起偽”的主要途徑,無論是個人秉性修養還是統治階級治國理政,都不能離開禮的教化,以禮為教化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雖然也強調了“法”的重要性,但荀子的法更多的是包含著禮和道的意義,主要作用是對施行禮的過程中所存在或所造成的缺陷進行彌補,作為治國理政的輔助手段而存在,因此,以法為教化的次要方面。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往往決定事物的根本性質,因此,從禮和法的主次方面的地位來看,荀子更側重于通過禮的引導與教化啟發人們,規范人們的言行舉止,最終實現社會的和諧有序發展,與荀子整體的社會政治思想相統一。
(三)虛壹而靜
“所謂虛,謂心能兼容萬物;所謂壹,謂心能兼知不偏;所謂靜,謂心能澄明清凈”[6]。在荀子看來,要想實現人們“化性起偽”,不僅需要通過外在環境的改善和外力作用的施加,而且還需要人們從主觀層面進行內在道德修養的覺悟和提升,如此一來,就使得人們通過內外兩方面的修養規范,摒棄自然本性的惡而最終實現圣人人格的善。
首先,“虛”。荀子認為人們要想增強自身道德修養,就要不斷積累,不斷接受新知識,完善自我的本性。按照荀子的“性惡論”,人們一出生是不知道德和人性的,因此也就不具備道德和善性。但人們通過后天的學習與教化,獲得了關于自我本性的一定認知,也就實現了道德認知從無到有的過程,但認識具有反復性、無限性和上升性,盡管人們對于自身本性的惡和圣人人格的善有了一定的認識,但關于善的道德發展是永無止境的、無限發展的,而且在提升自我道德修養的過程中,人們往往由于受到客觀環境的限制或主觀能力的不足,導致對于善的認識存在一定的不足。因此,“化性起偽”就需要加強自身道德修養的完善與積累,不斷學習新知識,逐步培養自身的善性,最終實現自我量變到質變的人格發展。
其次,“壹”。荀子在這里所要強調的是專一性與多樣性之間的協調發展。人們在后天的學習過程中,會受到各種各樣的外在因素的影響,由于人們獲取到的認識具有多樣性和復雜性,因此人們也就無法使這些知識和認識和諧統一。“壹”就要求人們在進行內在自我道德提升時,做到集中精神、思想專一地對待,否則就會在認識過程中由于不專一導致思想分散,最終產生對于道德認知和本性修養的片面性認識,阻礙人們人格上的完善和向善。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認識論來看,人們只有對善的內在發展規律加以深刻認識,尊重善的發展規律,以此為基礎,充分發揮人們的主觀能動性對自我本性進行合理性地改造,最終實現自身道德修養的提升和社會的和諧穩定發展。
最后,“靜”。“靜”是相對于“動”而言的。荀子認為心無時無刻處于動的狀態,時刻支配著人們的行為。荀子主張的“靜”就是“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即不讓做夢和胡思亂想擾亂人們原本的思緒和認識,使心始終居于平靜的狀態。人們只有在“靜”的環境和狀態下,才能夠保持自我思想的有序性、條理性,在保持穩定、理性的思想基礎上,才能夠作出正確的、符合善的倫理價值的行為判斷和行為選擇,使自己更接近圣人人格和境界。荀子“靜”的主張中蘊含著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運動觀以及二者之間的唯物辯證關系。荀子看到了“動”的絕對性和“靜”的相對性,人們始終處于運動變化的發展過程中,無論是個人的心性修養的培養過程,還是整個社會秩序的建立,都無法離開動而存在發展,但人心善性的培養和社會和諧秩序的建立不僅僅需要“動”,更需要“靜”,排除各種各樣的外在干擾,進而完善本性,實現修身養性的發展目標。
荀子的“化性起偽”思想無論是在當時諸侯割據的戰國時期,還是當前新時代發展環境下,對人們思想道德意識的提升和自身優良道德品行的培養,以及教育發展和治國理政等方面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崇‘偽論的理論意涵正在于,承認‘德性中的‘性不是人的本質所固有的,而是人的某種正在生成的東西”[7],“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一個具備高尚品格的善者盡管生來“性惡”,但可以通過后天的“偽”做到聞、見、知、行的統一,“化性”以“去惡”,“起偽”以“從善”,最終實現個人、社會,乃至國家的道德至善。
參考文獻:
[1]羅檢秋.近代諸子學與文化思潮[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2]杜治平,劉惠.荀子“化性起偽”之路徑探究[J].人民論壇,2016(17):212-214.
[3]張國風.荀子箴言[M].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4.
[4]鄭臣.從“化性起偽”到“隆禮重法”——荀子內圣外王思想初探[J].湖北社會科學,2016(02):109-113.
[5]方勇,李波.荀子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5.
[6]陳林.“化性起偽”何以可能——荀子工夫論探析[J].道德與文明,2012(02):75-84.
[7]鄭治文.荀子崇“偽”論對孔子禮學意義的開顯及其倫理意蘊[J].齊魯學刊,2022(06):1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