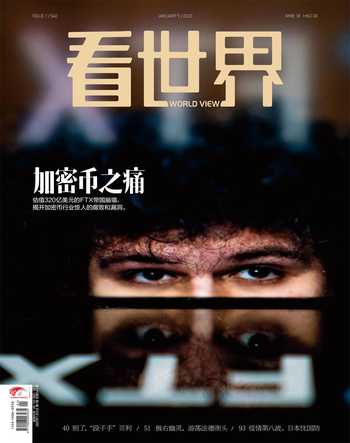美國大學里,另類的種族主義
陳科宇

美利堅大學Kogod商學院的學生們在上課
上學期某一天,關系較好的非洲裔同學跟我抱怨說,“質性研究方法”課程的期中作業評分低于預期,懷疑教課的老教授對她論文中關于黑人形象的研究懷有偏見,因此壓低分數。我建議她多跟同班其他非洲裔的同學交流一下分數,看是不是都出現壓分的情況。
要知道,在美國的課堂上,因為自己的種族出身而對自己的成績乃至課堂上的不同遭遇提出疑問,是老生常談。可實際情況呢?
語言上的無心之失
美國的公立大學博士生項目里,“教育學”幾乎成為各系首個學期的必修課程。由于博士生項目是為了培養畢業后在高校里任職的老師,一些身兼助教工作的博士生也免不了教一些本科基礎課程。為了應對多元化的美國課堂,博士生也需要“教育學”培訓。

2022年10月31日,平權法案的支持者要求華盛頓特區最高法院審查哈佛大學和北卡羅來納大學針對種族問題的招生政策
該課程強調,老師不要說出傷害學生感情的話。究竟什么是“傷害學生感情”?來自不同社會環境的我,也是在跟同學們的八卦談話中,才略知一二。
比如,“質性研究方法”的老教授的確對語言有點不敏感。比如,在某次課上她講到了閱讀內容,文章是20世紀30年代傳播學家對希特勒上臺前的演講的質性研究。當講到納粹迫害猶太人的歷史,教授就直接講道:“你們看,我們可以從文章中揣測出,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的政策傾向。”我當時心里就估摸著,布置的閱讀材料中大段的“仇恨猶太人”的語言描述,連聽到德語都覺得不適的以色列同學,心里一定受到“震動”。
這樣“傷害學生感情”的案例,能否佐證對于老師的“種族主義”指控?其實,“種族主義”更多取決于“受害者”的自我認知,往往“言者無心,聽者有意”。“質性研究方法”老教授因為對教學語言的“不敏感”,“得罪”的不僅僅是以色列同學,還有信奉伊斯蘭教的沙特女同學。
老教授的研究領域為伊斯蘭激進主義,無意之間,會讓對宗教敏感的同學認為,教授把伊斯蘭教與恐怖主義掛鉤。盡管大家都知道她并無“惡意”,但沙特女同學跟我們私下抱怨道:“教授本該提一句,伊斯蘭激進主義并不代表全部的伊斯蘭教。”可見,即使教授無意針對其他少數族裔或宗教信仰的人士,有的同學依然心生芥蒂。
何為逆向種族歧視
在美國課堂上,“種族主義”已經超越原本的“敵意或歧視”范疇。有些看似對少數族裔群體的“善意”行為,在少數族裔人士看來,自己基于“種族”因素成為區別化優待的對象,也屬于“種族主義”范疇。
美國政府在1960年推出的“平權法案”,給予“膚色、宗教、性別或民族出身”等少數群體或弱勢群體優待,防止社會環境中對上述群體的歧視行為,從而糾正歷史上的明顯歧視。該法案引起的爭議在于,非少數族裔認為這是針對他們的反向歧視,社會在入學、就業招聘過程中,公然基于種族身份偏袒某個群體。
近年來,“平權法案”在少數族裔群體中也引起一些不滿。他們認為,“平權法案”基于的假設是,少數族裔“技不如人”,需要通過“偏袒性”政策措施,將他們的社會地位拔到與主流族裔人群一樣的高度。有少數族裔同學曾經說道,某學校當年提供定向的獎學金,吸引她選擇該校的博士項目。但她婉拒了獎學金,原因是她認為,這是針對她的族裔身份提供的所謂“優待”,評定指標是基于她的族裔身份而不是其它能力。她并且懷疑,該項目是利用她的族裔身份,來粉飾、證明學校的“包容性”與“多樣性”。
“種族主義”更多取決于“受害者”的自我認知,往往“言者無心,聽者有意”。
據她猜測,兩位教授很可能是“利用”她,用擔任她導師來為自己的簡歷添彩。
“多樣性”,無論是種族還是性別,當下成為美國大學以及其它社會機構自我標榜的優越指標。圍繞著“多樣性”做文章,成為機構或個人打造多元化“人設”的重要任務。大學院系努力將少數族裔納入教職或招生指標,比如,缺少亞裔招亞裔、缺少非裔招非裔填補職位空缺,從而向社會證明機構在擁抱“多樣性”。這樣的機制,無形中也會鼓勵或激勵個人,精心耕耘自己的“多樣性”履歷,以獲得更高的社會認可,即使他們可能并非出于真心。

2022年4月26日,美國休斯敦,一名非洲裔學生在萊斯大學圖書館讀書
“政治正確”矯枉過正
非洲裔女同學也提到,兩位白人男性教授有意爭取指導她的博士畢業論文。在她看來,兩位教授都已經拿到正教授的職稱,研究領域也并非與非洲族裔相關,輔導她的畢業論文沒有任何經驗。據她猜測,兩位教授很可能是“利用”她,用擔任她導師來為自己的簡歷添彩。
通常情況下,教授的學術簡歷上會羅列出指導畢業論文的學生,以及畢業論文題目。作為白人男性教授,簡歷上出現非洲裔學生的名字以及黑人文化領域的相關研究,自然會為自己打造“包容性”與“多樣性”的名聲,在美國學界更能受到青睞。
然而,無論是教授不注意課堂“種族”語言,還是教授利用種族多樣性為自己貼金,相關現象都體現出美國社會種族問題方面的困境。某些社會個體對種族語言的不敏感,引起少數族裔成員的不適。與此同時,另一些社會成員表現出對“少數族裔”的青睞,利用與“少數族裔”的良性互動為自己的職業發展鋪路。社會機構利用“少數族裔”打造“多樣性”的形象,更容易得到社會接納,而這會讓“少數族裔”產生“被利用”的認知。
在“種族多樣性”成為社會常態準則的環境下,少數族裔的個體感受越來越受到重視。他們對“種族歧視”及“偏見”的現象也更為敏感。他們對于覺察到的惡意或非惡意的語言行為感到不適,并且對看似“善意”或“良性”的社會行為也感到不適。
總之,凡是以“種族身份”為標準,將“少數族裔”區別于其他“主導族裔”的語言或行為,無論“善意”或“惡意”,都有可能受到“少數族裔”群體的拒絕。這樣的困境,折射出美國社會中改善“種族平等”的無所適從。針對少數族裔的社會歧視偏見會引起不滿,偏向少數族裔、旨在阻止歧視偏見的政策法案也會招致不滿。究竟應該制定怎樣的政策呢?
責任編輯何任遠 hry@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