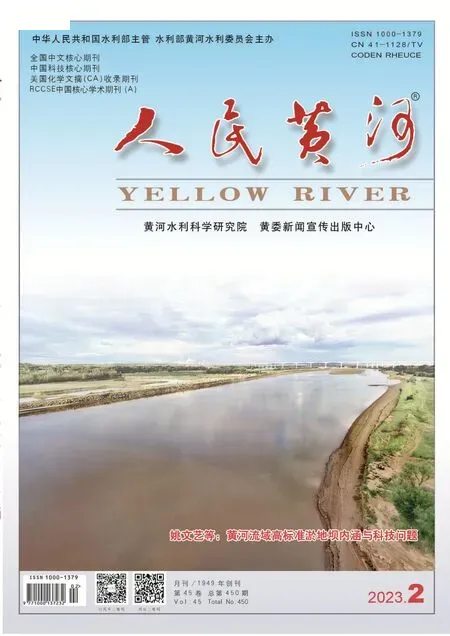基于RSEI的張掖市甘州區(qū)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動態(tài)評估
張曉山,張旺鋒,高新宇,韋建芳,劉 影
(1.蘭州大學(xué) 資源環(huán)境學(xué)院,甘肅 蘭州 730000;2.蘭州市城鄉(xiāng)規(guī)劃設(shè)計研究院,甘肅 蘭州 730000)
1 引 言
生態(tài)環(huán)境不僅是人類生存發(fā)展的基礎(chǔ)條件,還是經(jīng)濟社會可持續(xù)發(fā)展的保障。科學(xué)客觀的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評價可以對生態(tài)系統(tǒng)起到鑒定、診斷、引導(dǎo)、激勵、治理等作用[1]。在當(dāng)前的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評價方法中構(gòu)建評價指標(biāo)體系的方法較普遍,如岳思妤等[2]基于PSR模型對甘肅省涇河流域農(nóng)村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進(jìn)行評價,發(fā)現(xiàn)該流域農(nóng)村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逐漸趨于好轉(zhuǎn);Zhang等[3]采用層次分析法對五壘島灣國家濕地公園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進(jìn)行評價,發(fā)現(xiàn)五壘島灣國家濕地公園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總體良好;岳樹梅等[4]從公眾參與視角分析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hù)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從搭建法律平臺、細(xì)化獎懲機制等方面提出了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hù)舉措。2015年環(huán)境保護(hù)部發(fā)布的《生態(tài)環(huán)境狀況評價技術(shù)規(guī)范》(HJ 192— 2015)中提出用生態(tài)環(huán)境狀況指數(shù)(EI)來評價區(qū)域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狀況。廖晉一等[5]基于EI指數(shù)評價了2013年和2016年合肥市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狀況,結(jié)果表明2013年和2016年合肥市平均EI值均大于60,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整體良好。但采用EI指數(shù)時存在權(quán)重確定主觀性強及數(shù)據(jù)獲取較難的問題,關(guān)于該指數(shù)的應(yīng)用還處在探索階段。隨著遙感技術(shù)的迅速發(fā)展,基于遙感影像的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評價方法愈發(fā)被學(xué)者們重視,如姜仁貴等[6]融合多源數(shù)據(jù)構(gòu)建了黃河流域灌區(qū)生態(tài)環(huán)境演變仿真系統(tǒng),該系統(tǒng)提供灌區(qū)多源信息融合、生態(tài)環(huán)境監(jiān)測等應(yīng)用服務(wù),可為灌區(qū)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hù)提供決策支持;徐涵秋[7]采用遙感技術(shù)提出遙感生態(tài)指數(shù)(RSEI),基于該指數(shù)分析了福州市主城區(qū)的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變化情況,發(fā)現(xiàn)該指數(shù)的表征效果較好且具有數(shù)據(jù)容易獲取、不受人為因素干擾的優(yōu)點。RSEI指數(shù)被國內(nèi)外學(xué)者廣泛應(yīng)用到城市[7-12]、流域[13-15]、沙漠[16-17]、草原[18]、自然保護(hù)區(qū)[19]、礦區(qū)[20-21]等的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評價。
受干旱、風(fēng)沙、水資源短缺等因素的制約,張掖市甘州區(qū)生態(tài)環(huán)境面臨土地沙化、鹽漬化、地下水水位下降、草場退化等諸多問題。甘州區(qū)坐落于祁連山、黑河濕地2個國家級自然保護(hù)區(qū),加大這2個國家級自然保護(hù)區(qū)的保護(hù)與修復(fù)力度、筑牢國家西部重要生態(tài)安全屏障是張掖市甘州區(qū)面臨的生態(tài)建設(shè)主要任務(wù)。基于此,本文選擇甘州區(qū)為研究區(qū),基于Landsat遙感影像采用RSEI指數(shù)對1991—2020年甘州區(qū)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變化規(guī)律進(jìn)行研究,利用地理探測器分析其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影響因子,以期為西北干旱區(qū)綠洲城市及其他區(qū)域的綠色發(fā)展提供參考。
2 研究區(qū)概況
甘州區(qū)位于河西走廊中部,巴丹吉林沙漠南部邊緣,祁連山北麓,屬青藏高原、蒙古高原的過渡地帶,氣候?qū)俚湫偷臏貛Т箨懶詺夂颉5乩硖卣鞅憩F(xiàn)為“兩山夾一盆”,由南部祁連山、北部合黎山與龍首山、中部走廊平原組成,地勢為南北高、中間低,海拔為1 400~2 000 m。甘州區(qū)不僅是國家西部重要的生態(tài)安全屏障,更是綠洲經(jīng)濟社會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承載區(qū),近年來黑河流域生態(tài)治理、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hù)區(qū)生態(tài)修復(fù)取得了有效進(jìn)展,甘州區(qū)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明顯提升,但因其地處西北干旱區(qū)仍受諸多因素制約,生態(tài)環(huán)境承受壓力極大,保護(hù)綠洲生態(tài)環(huán)境、堅持走綠色發(fā)展道路、筑牢國家西部重要生態(tài)安全屏障任務(wù)依舊艱巨。
3 數(shù)據(jù)來源與研究方法
3.1 數(shù)據(jù)來源
選取甘州區(qū)1991—2020年6—9月共7期的Landsat遙感影像(云量低于5%)作為主要數(shù)據(jù)源,Landsat遙感影像具有時間序列連貫性較好的優(yōu)點,同時6—9月甘州區(qū)植被生長狀況良好,不同區(qū)域的植被覆蓋度差異較為明顯,便于RSEI的計算。Landsat遙感影像及數(shù)字高程模型(DEM)數(shù)據(jù)源自地理空間數(shù)據(jù)云,人口數(shù)據(jù)源自《甘州區(qū)統(tǒng)計年鑒》。
3.2 遙感生態(tài)指數(shù)(RSEI)
遙感生態(tài)指數(shù)(RSEI)是在4個生態(tài)指數(shù)的基礎(chǔ)上通過主成分變換得出的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評價指標(biāo),4個生態(tài)指數(shù)包括綠度(NDVI)、濕度(WET)、干度(ND?SI)、熱度(LST)[9],各生態(tài)指數(shù)的計算公式見表1。

表1 遙感生態(tài)指數(shù)計算公式
在對NDVI、WET、NDSI、LST進(jìn)行耦合形成RSEI指數(shù)之前,需進(jìn)行歸一化處理,公式為

式中:NIi為指標(biāo)歸一化處理結(jié)果;Ii為第i個像元值;Imin、Imax分別為像元最小值、最大值。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對歸一化處理后的4個生態(tài)指數(shù)進(jìn)行耦合,得到第一主成分PC1,即未經(jīng)標(biāo)準(zhǔn)化處理的初始遙感生態(tài)指數(shù)(RSEI0)。對RSEI0進(jìn)行標(biāo)準(zhǔn)化處理,得到RSEI,公式為

式中:RSEI0min、RSEI0max分別為RSEI0的最小值、最大值;RSEI值范圍為0~1,數(shù)值越接近1表示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越好[11]。
3.3 景觀格局指數(shù)
采用景觀格局指數(shù)對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空間格局變化狀況進(jìn)行描述和分析,使用Fragstats 4.2軟件計算景觀格局指數(shù),其包括斑塊密度(PD)、最大生態(tài)景觀斑塊指數(shù)(LPI)、景觀形狀指數(shù)(LSI)及集聚度指數(shù)(AI)4個指數(shù)。
3.4 空間自相關(guān)
空間自相關(guān)常被用于研究時空格局演變,分為全局自相關(guān)和局部空間自相關(guān)兩種類型,分別用全局Moran′s I指數(shù)、局部Moran′s I指數(shù)表示。采用GeoDa軟件計算甘州區(qū)的Moran′s I指數(shù)并繪制LISA聚類圖。
3.5 地理探測器
地理探測器是一種探測空間分異性以及揭示其背后驅(qū)動因子的統(tǒng)計學(xué)方法,由因子探測器、交互探測器、風(fēng)險探測器和生態(tài)探測器4個探測器組成[22],本文使用因子探測器和交互探測器分析各因子對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的影響程度。
4 結(jié)果與分析
4.1 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時間序列變化分析
統(tǒng)計計算的1991年、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2020年甘州區(qū)RSEI值分別為0.306 9、0.294 0、0.297 2、0.324 2、0.337 3、0.354 3、0.368 0,這7 a的RSEI值一直較小,1991—2020年RSEI值整體在0.2~0.4范圍內(nèi)波動上升,表明甘州區(qū)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較差,但保持改善向好的趨勢。
參考《生態(tài)環(huán)境狀況評價技術(shù)規(guī)范》(HJ 192— 2015),依據(jù)RSEI值把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劃分為5個等級:差(0~0. 2)、較差(0.2~0. 4)、一般(0.4~0. 6)、較好(0.6~0. 8)、好(0.8~1. 0),在此基礎(chǔ)上統(tǒng)計甘州區(qū)各典型年的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等級面積及占比(見表 2)。

表2 1991—2020年甘州區(qū)各典型年的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等級面積及占比
由表2可知,在時間尺度上,甘州區(qū)整體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等級屬好的面積占比先下降后持續(xù)上升,到2020年面積為827.57 km2、占比為22.61%;較好等級面積占比在10%上下波動;一般等級面積占比在2010年之前變化較小,2010年之后迅速下降到2.35%;較差等級面積占比整體波動上升,從1991年2.38%上升到2020年8.54%;差等級面積占比整體表現(xiàn)為下降趨勢,從1991年65.58%下降到2020年55.83%,該等級的面積占比較大,使甘州區(qū)整體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等級較低。1991—2020年甘州區(qū)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較好和好這2個等級的面積占比之和從26.11%上升到33.28%,而較差和差這2個等級的面積占比之和從67.96%下降到64.37%,表明30 a內(nèi)甘州區(qū)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整體呈好轉(zhuǎn)趨勢。
1991—2020年甘州區(qū)各典型年的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等級分布見圖1,可以看出,甘州區(qū)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等級為較好的區(qū)域集中于甘州區(qū)中部,中部走廊綠洲盆地是甘州區(qū)主要的農(nóng)耕區(qū),地勢平坦、土地肥沃,黑河貫穿全境,灌溉條件便利,因此該區(qū)域植被覆蓋度高、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較好。等級為一般和較差的區(qū)域位于綠洲北部的城鎮(zhèn)居民點附近,人類活動不可避免地會破壞生態(tài)環(huán)境。等級為差的區(qū)域位于北部平山湖蒙古族鄉(xiāng)、三閘鎮(zhèn)紅沙窩村北山坡灘以及南部神沙窩灘、安陽灘、新廟灘等地,這些區(qū)域地貌以荒漠戈壁、裸巖沙地為主,植被覆蓋度低,因此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差。

圖1 1991—2020年甘州區(qū)各典型年的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等級分布
4.2 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空間格局變化分析
4.2.1 景觀格局變化特征
1991—2020年甘州區(qū)生態(tài)環(huán)境景觀格局指數(shù)(PD、LPI、LSI、AI)平均值的變化情況見圖2,1991—2010年甘州區(qū)總體生態(tài)環(huán)境景觀格局較穩(wěn)定,2010年以后總體生態(tài)環(huán)境景觀格局變化較大,表明在甘州區(qū)發(fā)展過程中生態(tài)環(huán)境景觀斑塊數(shù)量增加,生態(tài)環(huán)境景觀格局趨于復(fù)雜,破碎化程度逐漸提高。

圖2 1991—2020年甘州區(qū)生態(tài)環(huán)境景觀格局指數(shù)變化情況
具體來看,等級為差的景觀格局PD和LSI在2010年前變化不大、2010年之后先上升后下降,LPI在21%上下波動,AI穩(wěn)定在97.5左右,表明差等級對應(yīng)的生態(tài)環(huán)境景觀格局斑塊在空間布局上較為集聚,景觀格局內(nèi)部以少量大斑塊為主,2010年之后斑塊破碎化程度有所提高,景觀異質(zhì)性增強;較差等級的景觀格局PD和LSI波動較大,而LPI和AI變化不明顯,說明較差等級的生態(tài)環(huán)境景觀格局斑塊先朝著破碎化方向發(fā)展后轉(zhuǎn)向集聚化發(fā)展;一般等級的景觀格局指數(shù)變化最明顯,表明一般等級的生態(tài)環(huán)境景觀格局在30 a內(nèi)發(fā)生了明顯變化,斑塊破碎化程度持續(xù)提高;較好等級的景觀格局變化與較差等級的極為相似,斑塊布局也是先朝著破碎化方向發(fā)展后轉(zhuǎn)向集聚化發(fā)展;好等級的景觀格局指數(shù)變化不明顯,表明這個等級對應(yīng)的生態(tài)環(huán)境景觀格局較穩(wěn)定。
4.2.2 空間自相關(guān)
采用500 m×500 m的單元格網(wǎng)分析甘州區(qū)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的空間自相關(guān)并繪制LISA聚類圖(見圖 3)。

圖3 1991—2020年甘州區(qū)各年度的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LISA聚類圖
由圖3可知,1991—2020年甘州區(qū)Moran′s I指數(shù)都大于0.7且z(I)統(tǒng)計值(表示Moran′s I指數(shù)是否顯著)都高于臨界值(為1. 96),通過了顯著性水平為5%的檢驗,說明甘州區(qū)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的空間分布并不是完全隨機的,而是存在顯著的相關(guān)性。整體上甘州區(qū)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較好的高-高聚類區(qū)主要分布在中部綠洲,而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較差的低-低聚類區(qū)分布在北部、南部未利用地。2015年之前甘州區(qū)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的空間分布較穩(wěn)定,2015年之后雖然中部高-高聚類區(qū)范圍擴大,但內(nèi)部不顯著區(qū)域及低-高聚類區(qū)也明顯增多,表明2015年之后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較好的中部綠洲高-高聚類的穩(wěn)定性變差,這與該時期城鎮(zhèn)建設(shè)用地面積擴大有一定關(guān)系。
從局部來看,30 a內(nèi)變化最明顯的區(qū)域有南端花寨鄉(xiāng)和安陽鄉(xiāng)(圖3紅色框),1991—2020年南端花寨鄉(xiāng)和安陽鄉(xiāng)呈現(xiàn)高-高聚類—不顯著—高-高聚類—不顯著—小范圍高-高聚類的空間集聚狀況,表明此區(qū)域的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穩(wěn)定性極差,極易受到自然及人為因素的擾動,原因是安陽鄉(xiāng)和花寨鄉(xiāng)海拔超過2 000 m,水資源匱乏,生態(tài)環(huán)境較脆弱;1991—2020年中部張掖市城區(qū)及工業(yè)園區(qū)(圖3綠色框)不顯著區(qū)域逐漸擴大,原因是30 a內(nèi)隨著建設(shè)用地不斷擴大以及人類活動加劇,此區(qū)域的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逐漸下降且范圍逐漸擴大;2005年西北部烏江鎮(zhèn)(圖3黃色框)形成高-高聚類合圍之勢,此處靠近黑河,土地肥沃,加上國有林場持續(xù)推進(jìn)植樹造林工作,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改善明顯。
4.3 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動態(tài)變化分析
為對甘州區(qū)30 a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變化進(jìn)行深入分析,把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的變化程度分為極度惡化、重度惡化、中度惡化、輕度惡化、基本不變、輕微改善、一般改善、明顯改善、顯著改善9個等級,在此基礎(chǔ)上統(tǒng)計1991—2020年甘州區(qū)各時段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各級變化面積見圖4(未統(tǒng)計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基本不變的面積)。1991—1995年甘州區(qū)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改善面積(輕微改善、一般改善、明顯改善、顯著改善的面積之和,下同)占8.07%、惡化面積(極度惡化、中度惡化、重度惡化、輕度惡化的面積之和,下同)占12.24%,1995—2000年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改善面積占9.72%、惡化面積占9.44%,2000—2005年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改善面積占12.92%、惡化面積占5.64%,2005—2010年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改善面積占11.38%、惡化面積占5.66%,2010—2015年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改善面積占16.72%、惡化面積占10.73%,2015—2020年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改善面積占14.17%、惡化面積占13.47%。30 a內(nèi)甘州區(qū)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整體呈改善趨勢,其中改善面積為7.62 km2、占比為20.81%,以輕微改善為主;惡化面積為3.42 km2、占比為9.35%,以輕度惡化和中度惡化為主。

圖4 各時段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各級變化面積
1991—2020年甘州區(qū)各時段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各級變化空間分布見圖5。

圖5 各時段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各級變化空間分布
由圖5可知,1991—1995年甘州區(qū)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整體表現(xiàn)為惡化,其中惡化區(qū)域主要分布在南端安陽鄉(xiāng)和花寨鄉(xiāng),輕度惡化區(qū)域遍布整個綠洲,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改善的區(qū)域較少,主要分布在綠洲西北部國有林場、龍首山以及東部、北部外圍;1995—2000年甘州區(qū)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明顯改善的區(qū)域有平原堡國有林場、黑河附近以及東南部堿灘鎮(zhèn)石崗墩灘,一般改善、輕微改善的區(qū)域集中在中部綠洲以及南端安陽鄉(xiāng)、花寨鄉(xiāng)少部分區(qū)域,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惡化的區(qū)域分布在北部龍首山以及南端安陽鄉(xiāng)、花寨鄉(xiāng)大部分區(qū)域、東部堿灘鎮(zhèn)綠洲部分區(qū)域以及中部綠洲外圍小部分區(qū)域;2000—2005年甘州區(qū)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明顯改善,尤其體現(xiàn)在南端花寨鄉(xiāng)、安陽鄉(xiāng)以及東部堿灘鎮(zhèn)、西北部沙井鎮(zhèn)、烏江鎮(zhèn)、黑河附近,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明顯變差的區(qū)域集中在中部城區(qū)以及東部堿灘鎮(zhèn)和上秦鎮(zhèn)的國有林場;2005—2010年甘州區(qū)中部綠洲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整體明顯改善,僅北部東大山國有林場、城區(qū)附近、黑河部分區(qū)域以及南端安陽鄉(xiāng)、花寨鄉(xiāng)部分區(qū)域有所惡化;2010—2015年甘州區(qū)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改善區(qū)域和惡化區(qū)域分布較為分明,中部綠洲大部分區(qū)域及東大山國有林場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惡化,而綠洲東北部、東部外圍及南端花寨鄉(xiāng)、安陽鄉(xiāng)部分區(qū)域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改善;2015—2020年甘州區(qū)中部城區(qū)及附近的新墩鎮(zhèn)、長安鄉(xiāng)、梁家墩鎮(zhèn)、上秦鎮(zhèn)以及南端安陽鄉(xiāng)、花寨鄉(xiāng)部分區(qū)域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惡化,綠洲西側(cè)、東側(cè)以及東大山國有林場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改善。
4.4 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影響因子探測分析
4.4.1 單因子探測分析
引入地理探測器揭示影響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的因子,以RSEI為因變量,選取人口密度、海拔、綠度、濕度、干度、熱度6個指標(biāo)為自變量(因子),單因子探測結(jié)果見表3(其中q值代表影響因子對RSEI的影響程度,q值越大說明影響力越大)。整體來看,1991年、2000年、2010年對甘州區(qū)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影響最大的因子都是干度,這與甘州區(qū)超過一半的區(qū)域為荒漠戈壁等未利用地有關(guān),大面積植被覆蓋度較低的土地導(dǎo)致干度值較大,而2020年的主導(dǎo)因子變?yōu)榫G度,原因是隨著“關(guān)井壓田”政策、“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的提出,促進(jìn)了甘州區(qū)生態(tài)建設(shè),綠洲逐漸向外圍擴展,使綠度的影響力超過了干度的。

表3 單因子探測結(jié)果
從1991—2020年各指標(biāo)因子對應(yīng)的q值變化情況來看,在所有因子中人口密度的q值偏小,但數(shù)值在逐漸增大,表明人類活動對甘州區(qū)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的影響較小,但影響力在逐步提升;在所有因子中海拔的q值最小且隨時間變化不明顯,說明甘州區(qū)“兩山夾一盆”的地形對甘州區(qū)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的影響較小;1991—2010年綠度和濕度的q值波動較小,2020年明顯減小,說明受降水等因素的影響,中部綠洲植被覆蓋度下降,對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的影響有所降低;1991—2010年干度的q值超過0.95,到2020年驟降到0.822 3,說明1991—2010年大面積的荒漠戈壁制約著甘州區(qū)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的提高,而2020年甘州區(qū)未利用地面積有所減小,使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明顯提升;1991—2020年熱度的q值先增大后減小,表明氣溫對甘州區(qū)的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較重要,但影響力在下降。
4.4.2 多因子探測分析
通過交互作用探測可反映出多因子交互作用對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的影響,相比單因子,雙因子的交互作用增強了對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影響的解釋力,分別將甘州區(qū)4 a的RSEI與6個因子進(jìn)行交互作用探測,得出結(jié)果見圖6。1991年、2000年、2010年、2020年對甘州區(qū)RSEI影響最大的雙因子分別是濕度∩綠度、干度∩綠度、干度∩綠度、濕度∩綠度,此外綠度與其他所有因子的交互q值都明顯增大且都大于0.9,這說明綠度與其他因子的交互作用對甘州區(qū)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的影響很大。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人口密度和海拔對甘州區(qū)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的影響較小,但雙因子交互作用下兩者交互q值明顯增大,說明受地形的影響,人類活動對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的干擾能力明顯增強。以上結(jié)果表明,綠洲是甘州區(qū)維持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的關(guān)鍵,而綠洲之上的人類活動影響著綠洲,從而影響甘州區(qū)整個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并且這種影響力在逐漸增強,因此需要重視人類活動對甘州區(qū)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的影響,充分發(fā)揮其有利的一面,減弱其造成的負(fù)面影響。

圖6 多因子探測結(jié)果
5 結(jié) 論
基于甘州區(qū)1991—2020年7期Landsat遙感影像,利用RSEI指數(shù)對甘州區(qū)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進(jìn)行動態(tài)評估,得出以下結(jié)論。
(1)30 a內(nèi)甘州區(qū)RSEI在0.2~0.4范圍內(nèi)波動上升,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整體較差,但呈改善向好的趨勢。30 a內(nèi)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較好和好這2個等級的面積占比之和增長了7.17%,主要分布于甘州區(qū)中部綠洲,而較差和差這2個等級的面積占比之和減少了3.59%,主要分布于北部平山湖鄉(xiāng)及南部神沙窩灘、安陽灘、新廟灘等地。
(2)30 a內(nèi)甘州區(qū)生態(tài)環(huán)境景觀斑塊數(shù)量增加,生態(tài)環(huán)境景觀格局趨于復(fù)雜,破碎化程度逐漸提高,這種變化在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等級為一般、較好、較差中表現(xiàn)最明顯。
(3)甘州區(qū)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在空間上存在顯著相關(guān)性,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較好的高-高聚類區(qū)主要分布在研究區(qū)中部綠洲,而質(zhì)量較差的低-低聚類區(qū)集中在北部、南部未利用地,2015年之前甘州區(qū)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的空間分布較為穩(wěn)定,2015年之后雖然甘州區(qū)中部的高-高聚類區(qū)范圍逐漸擴大,但內(nèi)部不顯著區(qū)及低-高聚類區(qū)也明顯增多,表明2015年之后中部綠洲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較好的區(qū)域高-高聚類的穩(wěn)定性變差,這與這一時期城鎮(zhèn)建設(shè)用地大面積擴展有一定的關(guān)系。
(4)30 a內(nèi)甘州區(qū)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明顯改善,其中改善面積為7.62 km2、占比為20.81%,以輕微改善為主;惡化面積為3.42 km2、占比為9.35%,以輕度惡化和中度惡化為主。
(5)從單因子探測結(jié)果來看,30 a內(nèi)對甘州區(qū)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影響最明顯的因子是綠度和干度,人口密度的影響在逐漸提高;從多因子交互探測結(jié)果來看,所有因子交互作用都表現(xiàn)出雙因子增強效果,綠度與其他因子的交互作用對RSEI空間異質(zhì)性的解釋力最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