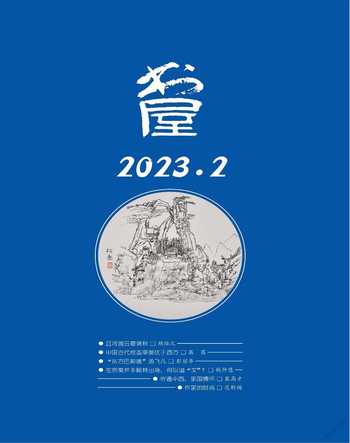且將微云寄清秋
一
自1984年5月4日第一次踏上深圳這塊熱土起,我已經(jīng)在這里生活了將近四十年。這是我最后的精神家園,我將在這里終老,回歸大自然。
我到深圳大學(xué)來本身就是一件新鮮事。清華大學(xué)副校長張維院士受當(dāng)時深圳市市長梁湘之邀,擔(dān)任深圳大學(xué)創(chuàng)校校長,他請北京大學(xué)派人來興辦文科。1984年元旦,張維院士請錢遜(錢穆之子)邀我和湯一介去他的清華園寓所會見。他開門見山告訴我倆,北大常務(wù)副校長張學(xué)書答允支持深圳大學(xué),由他來挑選北大學(xué)人去辦中文系和外語系。他已邀請英語系李賦寧辦外語系,想請我和尚在美國的樂黛云來辦中文系,發(fā)展新學(xué)科,請湯一介辦國學(xué)研究所。當(dāng)時,湯一介和我都已在培養(yǎng)研究生,開設(shè)新課,忙得不可開交,如何去得了深圳?張維院士見多識廣,思路開闊,他當(dāng)時就為我們出了新招:“你們?nèi)瞬挥谜{(diào)離北大,可以采取半年在北大半年去深大輪換的新辦法,照顧兩邊。在深大可以物色一個青年教師當(dāng)副主任,處理日常事務(wù)。你們的責(zé)任是審定學(xué)科方向,設(shè)置教學(xué)課程,挑選合格教師。”張維院士的這一新招已經(jīng)屬于新事新辦了,我們從來沒有想過。
張維院士還勸我和湯一介去深圳看一看,實(shí)地考察一下。1984年五一節(jié)前,我到廈門參加一個國際學(xué)術(shù)研討會,應(yīng)正在負(fù)責(zé)創(chuàng)建汕頭大學(xué)的羅列教授之邀去汕頭看看,就決定乘此機(jī)會也到深圳走一趟。張維院士寫了一封親筆信,讓我?guī)еヒ娨言谏钲谪?fù)責(zé)建校的常務(wù)副校長羅征啟。5月4日我抵達(dá)深圳,深圳大學(xué)尚無校舍,校園正在蛇口半島的粵海門開建,羅征啟主持的深大辦事處設(shè)在寶安縣政府的舊地。他一見我就勸我和湯一介夫婦趕快來,催促樂黛云快回國。當(dāng)時,他說了深圳的許多優(yōu)勢,有一句話深深打動了我:“深圳是個沒有開發(fā)的處女地,就像一張白紙,可以畫出最新最美的圖畫。你們可以充分發(fā)揮你們的聰明才智!”說來也巧,我們在剛搭建起來的鐵皮房里用餐,竟碰上了李澤厚、蔣孔陽、劉綱紀(jì)三位也在此吃快餐。我們在廈門一起參加了國際學(xué)術(shù)研討會,他們應(yīng)廣東省社會科學(xué)院院長張磊之邀,也來深圳考察,他們?nèi)欢脊膭游襾砩钲冢诖私⒁粋€國際文化交流的平臺,他們的想法和北大副校長季羨林的想法高度一致,都想以深圳為基地,促進(jìn)國際文化交流。
我回北京和湯一介一說,他當(dāng)機(jī)立斷,決定去深圳,也催促樂黛云趕快從美國回來。1984年9月,張維院士親自帶了我們八個人乘飛機(jī)到廣州,深圳大學(xué)派了一輛中巴把我們接到深圳,這八個人是清華大學(xué)的童詩白(任電子系主任)、汪坦(任建筑系主任)、唐統(tǒng)一(任圖書館長),中國人民大學(xué)的高銘暄(任法律系主任),北京大學(xué)的李賦寧(任外語系主任)、湯一介(任國學(xué)研究所長)、樂黛云和我。如今,這八個人中只有三人尚在,一個是高銘暄,今年已九十四歲高齡,2019年榮獲國家授予的“人民教育家”稱號。一個是樂黛云,今年已九十二歲高齡,在北大朗潤園安度晚年。我最小,也即將進(jìn)入九十歲。
我和湯一介夫婦沒有辜負(fù)季羨林的囑咐。在1984到1986的三年間,以深圳大學(xué)為依托,很快初建了一個國際文化交流的平臺,先后召開了中國比較文學(xué)學(xué)會成立大會、國際文化交流座談會、海外華文文學(xué)暨港澳臺文學(xué)國際研討會。按照與北大當(dāng)初的約定,湯一介、樂黛云在1987年都回到了北大,我卻遲遲不歸。1987年元旦,我到清華園張維院士寓所拜年,他又和我作了一次長談,勸我留在深圳大學(xué),繼續(xù)為發(fā)展人文學(xué)科做貢獻(xiàn)。我接受了他的建議,從此落戶深圳。我讀副博士研究生時的同窗好友嚴(yán)家炎幫了我的大忙,給予我最大的諒解,看我決心要留深圳,助我讓北大放行,我深為感激。
我在北大三十五年,實(shí)現(xiàn)了“讀萬卷書”的美夢,卻未能履踐“行萬里路”的另一個美夢。在美麗的燕園,我只是閉門讀書,很少外出,從未出過國門。改革開放之初,李澤厚邀朱光潛、楊辛和我去昆明參加中華全國美學(xué)學(xué)會成立大會,我才得以第一次乘飛機(jī)出京。后來參加了數(shù)次學(xué)術(shù)活動,都是應(yīng)好友之約方才出行。
特區(qū)成立之初,目標(biāo)就是要建設(shè)成開放的國際化城市。什么是國際化?如何國際化?大家都不明白。因此,深圳一開始就鼓勵我們抓住機(jī)會到各地考察。
我在1986年5月從深圳出發(fā),跨過深圳河、羅湖橋,到香港中文大學(xué)做客,在新亞書院會友樓住了一個多月,和香港學(xué)者進(jìn)行學(xué)術(shù)交流。當(dāng)時香港尚未回歸,能去中文大學(xué)進(jìn)行學(xué)術(shù)交流的學(xué)者甚為稀少,先是朱光潛應(yīng)邀與錢穆會面,然后王瑤、杜琇夫婦去待了一個多月。我先去香港把他倆接回深圳,我就接續(xù)王瑤去訪學(xué),成為新亞書院從北大接去的第三位學(xué)人。我在中文大學(xué)作了題為“中國美學(xué)的新變”的學(xué)術(shù)報告,和饒宗頤、李達(dá)三、袁鶴翔等相識,從而開始了和香港學(xué)界的長期交往。
自1987年落戶深圳,我就頻繁出入于香港。深圳主管文化教育的副市長鄒爾康特批,給我辦了一個港深特別通行證,憑此證可以隨時去香港,省去了一些煩瑣手續(xù)。在香港回歸之前的那些歲月里,香港中文大學(xué)有什么我感興趣的重要的學(xué)術(shù)活動,袁鶴翔等打一個電話過來,我就可以跨過羅湖橋,乘上香港的輕軌火車直奔沙田,就像我從北大乘32路汽車到王府井的文聯(lián)大樓一樣方便。我若出國,也無須再從北京轉(zhuǎn)機(jī),只要就近從香港啟德國際機(jī)場出發(fā),非常方便。
我們出去考察,回來后不僅要寫一個考察報告,還常和市領(lǐng)導(dǎo)決策層當(dāng)面對話、交流看法。每年元旦或春節(jié),市委書記或市長就會帶領(lǐng)市政府、人大、政協(xié)的領(lǐng)導(dǎo)在市政府聚會,邀請我們參加,同時要求我們對深圳今后的發(fā)展各抒己見,以提供參考。當(dāng)時的領(lǐng)導(dǎo)層都很尊重我們這些人的意見。跨入新世紀(jì)后第二年,深圳文藝界紀(jì)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我當(dāng)時兼任深圳市作家協(xié)會主席,特請時任深圳市委書記黃麗滿參加。她不僅來了,講了話,還和我們共進(jìn)晚餐。我和她坐在一起,旁邊還有主管人事的白天。那晚,我滔滔不絕地向她說起深圳大學(xué)今后的發(fā)展。當(dāng)時,校領(lǐng)導(dǎo)正要換屆,我向她建議,此次換屆也要創(chuàng)新,不要再由廣東省教育廳派校長來,而從深大內(nèi)部選拔。我詳盡為她分析了利弊,目的是要促進(jìn)深大的跨越式發(fā)展。沒有想到,她真的聽進(jìn)去了,當(dāng)即要白天去深大調(diào)查研究,向她報告后做最后決定。之后,白天廣泛聽取了師生意見,最后由黃麗滿決斷,從深大副校長中選拔了一位當(dāng)校長,這是深圳的一次創(chuàng)新,實(shí)為難得。
深圳大學(xué)究竟應(yīng)該怎么辦?當(dāng)時也是摸著石頭過河,確有不少創(chuàng)新之舉。
我和樂黛云來深圳的最初三年,每人每年只在此主持半年的工作,未曾深思如何改進(jìn)教學(xué)。那三年,樂黛云開設(shè)比較文學(xué)課,我開文學(xué)概論課,引進(jìn)了一些青年教師開基礎(chǔ)課,如古典文學(xué)、現(xiàn)代漢語、古代漢語等。好些課程都是請北大的教師來講,誰講得好,就請誰來。我們請黃修己來講了一年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請張鐘講了一年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外國文學(xué)沒人教,我們就請了北大西語系的孫鳳城來講了一年。當(dāng)時,我和樂黛云在北京和深圳之間飛來飛去,王瑤開玩笑說我們是“空中飛人”,深大人說我們是“飛鴿牌”。1987年,湯一介、樂黛云都回北大了,我決定留在深大,成“永久牌”。
我留深大之后不久,市里主管文化教育的副市長鄒爾康跟隨梁湘去做海南省副省長了,接任他的副市長林祖基是愛好文學(xué)的文友。我們常交談,很投機(jī)。林祖基很誠懇地和我作了一次長談。他說,在深大辦中文系,不能照搬北大模式,北大是重點(diǎn)學(xué)校,為國家培養(yǎng)高層次人才,深圳亟需的是中西兼通的實(shí)用人才,不可能都去研究比較文學(xué)、國學(xué)、美學(xué),所以專業(yè)不能分得太細(xì);但知識要廣博,中西兼通,貴在應(yīng)用,要能說能寫,適應(yīng)國際化的需要。我覺得林祖基說得很在理,認(rèn)真地考慮了中文系的發(fā)展前途。就在當(dāng)年6月,我腦海里涌現(xiàn)出了“國際文化交流”幾個字。夏天,我回北京,特地去中關(guān)園拜訪了北大國際政治系的創(chuàng)始人趙寶煦,向他請教把中文系擴(kuò)建為國際文化系前途如何?趙寶煦一聽,連聲叫好。他告訴我,北大國際政治系畢業(yè)的學(xué)生很少能進(jìn)入政治和外交領(lǐng)域,很多人只能從事國際文化交流,把中國的文化介紹出去,把外國的文化介紹進(jìn)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擴(kuò)大,需要更多人來參與國際文化交流,若深大辦國際文化系,實(shí)乃國內(nèi)首創(chuàng),是大好事。
1987年深秋,我在深大海濤樓住所草擬出了一個將中文系擴(kuò)建為國際文化系的方案。我把這個系的教學(xué)方針定為“貫通中西,應(yīng)用為主”,為深圳培養(yǎng)中西兼通的應(yīng)用人才,以適應(yīng)外向型國際化城市建設(shè)的需要。全系分為四個專業(yè):中英文秘書、對外漢語、大眾傳播和旅游文化。當(dāng)年年底,我把這個擴(kuò)建方案送交已接任張維的第二任校長羅征啟,等他審批。我想,好事多磨,可能需要反反復(fù)復(fù)來來回回打磨好幾次。是否能辦成,也不知道。沒有想到,1988年新年剛過沒幾天,羅征啟帶了那方案跑到我辦公室來對我說道:“你這改革方案很大膽,把中文系擴(kuò)建成國際文化系,思路很好。深圳講創(chuàng)新,允許試驗(yàn)。你是系主任,我校長尊重你的意見,就照此辦理。咱們不用再報教育部,今年招生,就用國際文化系的名義招。你再寫一個招生簡章。”我一聽,真?zhèn)€是心花怒放,想不到深圳辦事效率如此之高。隨后,我很快起草了一個國際文化系1988年的招生簡章,當(dāng)年就按我分的那幾個專業(yè)來招生了。《深圳特區(qū)報》的副總編許兆煥看了國際文化系的招生簡章,特地寫了一篇新聞報道,發(fā)表在《光明日報》第一版上,稱贊這一壯舉乃是國內(nèi)首創(chuàng),北大只有國際政治系,到深大才有國際文化系。
那時候,系主任和校長的責(zé)權(quán)分明,系主任的責(zé)權(quán)甚大。張維校長早就和我說清楚了:系主任有權(quán)決定辦系方針、專業(yè)設(shè)置、課程安排,甚至教師的聘任也由系主任定。系主任決定聘請什么人來任課,只需把名單告訴人事處,就由人事處到市里去辦手續(xù)。我和樂黛云共同主持中文系時就從北大調(diào)來了好幾位青年教師,如章必功、劉小楓、郁龍余、景海峰、榮偉等,擴(kuò)建為國際文化系后,我又從北京師范大學(xué)、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復(fù)旦大學(xué)等調(diào)進(jìn)了一些研究生,如吳予敏、吳俊忠等。這些年輕人后來都成了深圳大學(xué)的棟梁之材,如章必功當(dāng)了校長,郁龍余成為首任文學(xué)院院長,吳予敏成了傳播學(xué)院院長,景海峰做了人文學(xué)院院長,吳俊忠當(dāng)了社會科學(xué)處處長,等等。
國際文化系所設(shè)置的那幾個專業(yè)方向都是我經(jīng)過調(diào)查研究才定下的,而且咨詢過林祖基、馬志民等。這些專業(yè)都是當(dāng)時深圳亟需的,后來成為深圳大學(xué)人文學(xué)科發(fā)展的新增長點(diǎn)。國際文化系建成后數(shù)年,我不再擔(dān)任系主任了。二十世紀(jì)九十年代初期,蔡德麟當(dāng)了校長,特別重視深大的學(xué)科建設(shè),自任學(xué)術(shù)委員會主任,請我當(dāng)學(xué)術(shù)委員會副主任、人文社會科學(xué)委員會主任。我就主要關(guān)注起深大人文學(xué)科的發(fā)展了。后來,深大加快學(xué)院建設(shè),成立了很多學(xué)院,國際文化系的好幾個專業(yè)方向都成了新的增長點(diǎn),以大眾文化傳播專業(yè)為基礎(chǔ)發(fā)展成為傳播學(xué)院,由蔡儀的美學(xué)博士吳予敏任院長;以對外漢語專業(yè)為基礎(chǔ)發(fā)展成留學(xué)生教學(xué)部,后改為國際交流學(xué)院,由郁龍余任主任,后為院長。
二
深圳大學(xué)要大力發(fā)展旅游文化專業(yè),把文化和旅游結(jié)合起來,促進(jìn)國際文化交流,使深圳向國際化方向發(fā)展。這是華僑城掌門人馬志民為我出的主意,我覺得是高明之舉。我和馬志民相識是在1986年春夏之交客居香港中文大學(xué)新亞書院時。一次,香港作家聯(lián)會會長曾敏之邀我參加香港作家的交流活動,在維多利亞海港作泛舟夜游。在游輪上,我遇見了馬志民,他修長個兒,年紀(jì)和我差不多,剛過五十歲,神采奕奕,一口流利的普通話,略帶廣東口音。他是道地的深圳寶安人,被派駐香港多年,經(jīng)營香港的中國旅行社。他聽說我在深圳大學(xué),就很有興致地和我交談起來。他以為,促進(jìn)國際交流最方便快捷的方式就是發(fā)展國際旅游。深圳靠近香港,就要利用香港這個國際化城市的優(yōu)勢來大力發(fā)展國際旅游。他主持的華僑城開發(fā)就是為了開拓國際旅游。他說他已向當(dāng)時的市委書記、市長梁湘提供了一個發(fā)展方略,希望把深圳發(fā)展為一座吸引人的國際旅游海濱城市,和香港相互呼應(yīng)。為此,深圳亟需培養(yǎng)大量既懂中國文化又通西方文化的國際旅游人才。他希望將來能和深圳大學(xué)合作。我一聽,覺得他說得很有道理。我也希望深圳能發(fā)展成為一座國際旅游海濱城市,把深圳的美充分展現(xiàn)出來。
馬志民的一番話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同他一起磋商過把中文系擴(kuò)建為國際文化系的想法。他極為贊賞,并建議我把旅游文化列為一個專業(yè)方向,他愿參與教學(xué),介紹他多年從事國際旅游的經(jīng)驗(yàn),一同探索如何在深圳開拓國際旅游事業(yè)。深圳那時能提供旅游的地方還不多,東部可去的只有沙頭角中英街,市內(nèi)新辟了銀湖旅游中心,蓮花山公園正在興建,華僑城正在開發(fā)民俗文化村、錦繡中華等項(xiàng)目,蛇口有了由明華輪改建的海上世界。馬志民向我說了他的一個近期開發(fā)計劃,想把華僑城和蛇口的海上世界連接起來,開辟一條旅游小火車道,中經(jīng)深圳大學(xué)、南油大廈,再到海上世界。那時的華僑城、深圳大學(xué)、南油大廈、海上世界都緊靠后海灣,前邊是大片濕地,沿岸有很多紅樹林,大規(guī)模填海是后來的事。馬志民想把后海灣這一大片地方都開發(fā)為旅游勝地。深圳大學(xué)是一所開放的大學(xué),不建圍墻,正好可以成為一個旅游景點(diǎn),重點(diǎn)發(fā)展文化設(shè)施。他愿出錢幫深圳大學(xué)創(chuàng)建一個藝術(shù)走廊,重點(diǎn)建設(shè)雕塑園,從華僑城開小火車過來只要幾分鐘。我聽了他的設(shè)想,覺得事關(guān)重大,牽涉到深大今后發(fā)展的方向,必須要由他親自與深大校長溝通。于是,當(dāng)年秋天,我把馬志民請來,直接和羅征啟見面商談。羅征啟聽了馬志民的計劃,興致勃發(fā),這正和他想把深大建設(shè)成沒有圍墻的開放大學(xué)的想法不謀而合。他當(dāng)時就對馬志民說:“您把這設(shè)想具體化一下,提出具體措施,我們再找機(jī)會作進(jìn)一步策劃。我請胡教授和您保持聯(lián)系。”
自從羅征啟對馬志民做了這個許諾之后,我對旅游文化這個專業(yè)特別重視,希望為深大的發(fā)展添加一個新的生長點(diǎn)。我請郁龍余擔(dān)任這個專業(yè)的主任,他立即開設(shè)旅游文化概論的課程。國際文化系副主任章必功自告奮勇,開設(shè)了一門過去從沒有人開過的新課,叫中國旅游史,第一次對我國的旅游歷史作了全面梳理。我還支持郁龍余成立了旅游文化研究所,把北京大學(xué)著名的文化地理學(xué)家侯仁之的弟子陳傳康教授請來講授文化地理。陳傳康是我在北大時的病友,他患胃潰瘍,常住校醫(yī)院。我患胃炎,二人常住同一病室,有過多次深談。他是粵東人,熟悉深圳一帶的山山水水。在馬志民的支持下,由他主持對深圳的海岸和山峰作了一次全面考察。馬志民想向市政府提出一個開發(fā)東部海岸的計劃,請陳傳康帶著一批專家考察。我和郁龍余沾他們的光,有時跟著一起去大鵬灣,領(lǐng)略了更多美景,滋長了更多山水情,體驗(yàn)到深圳真是個難得的好地方。
1989年元旦,馬志民和我談了他創(chuàng)建旅游學(xué)院的設(shè)想。他規(guī)劃在華僑城內(nèi)留出一塊地給旅游學(xué)院,由他出資興建,希望我們以旅游文化專業(yè)為基礎(chǔ),幫他發(fā)展成為深圳大學(xué)內(nèi)一個獨(dú)立學(xué)院,專為深圳培養(yǎng)中西兼通的國際旅游人才。我把這設(shè)想告訴了羅征啟,他聽了就說:“這是好事啊!對華僑城、對我們深圳大學(xué)都好,何樂而不為!”
后來,馬志民所說請深大來創(chuàng)辦旅游學(xué)院的計劃因故夭折。中央僑辦指令下屬暨南大學(xué)到深圳找馬志民,決定由暨南大學(xué)從廣州派人來籌建旅游學(xué)院。深圳大學(xué)也就失去了這一大好時機(jī)。但我和馬志民所建立的友誼卻常在,一直保持著聯(lián)系,直到他去世,我至今仍時常懷念著這位特區(qū)初期的著名改革者。
三
1992年元旦后,八十八歲高齡的鄧小平第二次來到深圳,再次肯定了深圳辦特區(qū)是正確的方針,要繼續(xù)辦下去,只能辦好,不能辦壞。這就激勵了深圳人再次振奮精神,開啟了第二次創(chuàng)業(yè)。新晉校長蔡德麟是位哲學(xué)教授,擔(dān)任過安徽大學(xué)常務(wù)副校長,教育經(jīng)驗(yàn)豐富。他懂得要想提升深大的水平,必須從抓學(xué)科建設(shè)著手。他迅速調(diào)來十三位中年骨干教授,包括蘇東斌、余其銓、魏達(dá)志等,作為學(xué)科帶頭人,從事學(xué)科建設(shè);新建了全校的學(xué)術(shù)委員會,他自己兼任主任,副校長應(yīng)啟瑞任副主任,抓自然科學(xué)建設(shè)。他找我談了幾次,要我擔(dān)任學(xué)術(shù)委員會副主任、人文社會科學(xué)委員會主任,要大力發(fā)展人文學(xué)科。他告訴我,他去清華園拜訪過張維院士,這位創(chuàng)校校長就對他說過,要我在深大人文學(xué)科發(fā)展中多發(fā)揮作用。新、老校長的美意,我甚感激,也頗為遲疑,因?yàn)槟菚r我即將跨入花甲之年,要退休了。
我已做好了退休的準(zhǔn)備。深圳是個年輕的城市,是年輕人施展聰明才智的好地方。為了使城市年輕化,深圳人事部門已定下法規(guī),公教人員到了六十歲就一律退休。1993年5月我就要到六十,到時就退。我在深大校園里住了八年多,我住的海濤樓在后海灣北側(cè)海濱,門前濕地上有大片紅樹林,后邊是杜鵑山,東邊是游泳池。我每天都能游泳、賞海景。但按照建設(shè)規(guī)劃,這片濕地即將被填埋,變?yōu)槠降兀俳ǜ邩谴髲B,紅樹林將消失。馬志民沿海灘建小火車旅游通道的設(shè)想將化為烏有。1992年冬,我戀戀不舍地搬離了海濤樓,移居到福田崗廈村和皇崗大道之間的一塊三角地——深大新村。這個住宅小區(qū)是市房管局專為深圳大學(xué)教職工建的,分給二十世紀(jì)八十年代來參與深圳第一次創(chuàng)業(yè)的人員居住,共十一棟。我們這些快退休的教授和校長、書記等一起遷入了高職樓(第十一棟),都已心滿意足,皆大歡喜了。不久,我的大女兒、女婿從德國回到了清華大學(xué),在清華園也有了較好的寓所,女兒勸我退休后可以兩棲,往返于深大新村和清華園。
正當(dāng)我做好了退休準(zhǔn)備時,1993年春天,國務(wù)院學(xué)位委員會給我和深圳大學(xué)發(fā)來了一個文件,通知已通過我的文藝學(xué)博士生導(dǎo)師資格,和暨南大學(xué)副校長饒芃子教授合作,從當(dāng)年起可以招收博士研究生了。蔡德麟校長與我同住一棟樓,見我就說這是大好事,咱們深圳大學(xué)有了建校以來自行產(chǎn)生的第一位博士生導(dǎo)師,他要立即打報告給人事局,不能讓我退休。人事局遵照“特區(qū)特辦,新事新辦”的方針,要深圳大學(xué)每年都要打一次報告,聲明為培養(yǎng)博士生每年都延聘。這一來,我本該在1993年退休,卻從此一再延聘,直到2004年我七十一歲時方得退休。
我自1993年起,仍然每天乘學(xué)校班車去深大,除帶研究生、研究文藝美學(xué)和文化美學(xué)之外,還承擔(dān)學(xué)術(shù)委員會副主任、人文社會科學(xué)委員會主任的職務(wù),參與深大的人文學(xué)科建設(shè)。蔡德麟是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的教授,重視人文社會科學(xué),對于深大的人文學(xué)科發(fā)展我們常有交流。我一直主張,深圳大學(xué)文學(xué)院不要照搬其他大學(xué)的模式,局限在文史哲的框架,應(yīng)該另辟蹊徑,以適應(yīng)深圳向國際化城市發(fā)展的需要。我還是沿著國際文化系的發(fā)展思路,力主把中文系和外文系、傳播系相結(jié)合,培養(yǎng)國際文化交流人才,把中國文化向外傳播,也把外國文化介紹進(jìn)來。中文系和外文系是兩端,通過傳播這一中介,相互融合、互相促進(jìn)。我還向他說明,這是受老一輩學(xué)者的啟發(fā)。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后,西南聯(lián)大的教授們回歸清華、北大,聞一多、馮至、朱光潛、盛澄華等曾有過一次討論,主張重組中文系、外文系,把中國文學(xué)和外國文學(xué)兩大專業(yè)合為一個系,叫文學(xué)系;把中國語言和外國語言合在一起,成立語言學(xué)系。這個改革難度太大,未能付諸實(shí)踐。深圳大學(xué)是新校,不妨一試,把中文系和外語系放在一個學(xué)院,中外溝通。蔡德麟覺得我說得有道理,后來深圳大學(xué)成立文學(xué)院,真的把中文系、外文系、傳播系放在一起,由研究印度文化的郁龍余任院長、熟悉俄國文化的吳俊忠任院黨委書記。之后,吳予敏接著當(dāng)院長,又發(fā)展出傳播學(xué)院,也由他當(dāng)院長;郁龍余又去新建的留學(xué)生教學(xué)部(國際交流學(xué)院前身)當(dāng)主任。
自1993年到2013年,我在深大擔(dān)任了三屆學(xué)術(shù)委員會副主任、人文社會科學(xué)委員會主任,共二十年。謝維信卸任校長后,新任校長章必功仍然請他當(dāng)學(xué)術(shù)委員會主任,我和牛憨笨院士仍任副主任。直到2014年新校長李清泉接任,我和謝維信都退任了,由牛院士承擔(dān)學(xué)術(shù)委員會主任之職。遙想當(dāng)年,我和牛憨笨、倪嘉纘兩位院士年歲最大,一起參加了接待愛爾蘭總統(tǒng)等的來訪,留下了不少校園照片,被稱為“深大三老”。如今只剩下我和倪嘉纘院士,兩人也已難得一見。老熟人馬志民、王子武、蔡德麟、楊廣慧、葉華明等已陸續(xù)逝世,鄒爾康、林祖基也已難得見到了,真是自然規(guī)律不可抗拒。
令我稍感欣慰的是,我先后培養(yǎng)的十一屆文藝美學(xué)博士生都學(xué)有所成,卓有成就。我的第一位博士生王列生取得學(xué)位后,先是去了中央黨校任教,后成為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文化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我的最后一位博士生祁艷進(jìn)了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從事博士后研究,探索藝術(shù)和科技相結(jié)合的創(chuàng)新之路。留在廣州的,分別在暨南大學(xué)、華南師大、廣州美院等校任教,不時在開拓新學(xué)科領(lǐng)域。從文藝美學(xué)、中國古典美學(xué)分別向音樂美學(xué)、繪畫美學(xué)、設(shè)計美學(xué)、文化美學(xué)等領(lǐng)域推進(jìn)。留在深大的李健專心鉆研中國古典美學(xué)和文藝學(xué),如今擔(dān)任深圳大學(xué)美學(xué)與文藝批評研究院副院長,與院長高建平搭檔,在學(xué)科建設(shè)、學(xué)術(shù)研究與交流方面做了不少事。黃玉蓉也留校,如今是人文學(xué)院教授,探索國際文化交流的創(chuàng)新之路。
四
人生易老天難老,我在快到八十歲的那幾年尚能遠(yuǎn)行。2010年,我應(yīng)太湖世界文化論壇之邀,參加了首屆國際學(xué)術(shù)研討會,重返故鄉(xiāng)蘇州和無錫,瞻仰了錢穆故居。那年我還和同窗好友嚴(yán)家炎夫婦及著名歌唱家李光羲夫婦一起去了俄羅斯,參加中國漢語文化年的國際交流活動,來回于莫斯科、圣彼得堡之間,泛舟伏爾加河和波羅的海,實(shí)現(xiàn)了年輕時的美夢。我還應(yīng)第十八屆世界美學(xué)大會之邀,去北京參加了一千人的國際研討會,會務(wù)組本要我主持“文藝美學(xué)”論壇,但我主動要求主持“自然美學(xué)”論壇。此后的兩三年里,我還曾分別去了香港和澳門參加音樂節(jié)或藝術(shù)節(jié),還去了上海參加上海藝術(shù)節(jié)。到八十歲以后,我已漸感精力不濟(jì),難再遠(yuǎn)行。承蒙深圳市委宣傳部支持,海天出版社在2015年為我出版了《胡經(jīng)之文集》五卷,三百萬言。廣東省委宣傳部、省社科聯(lián)授予我“廣東省優(yōu)秀社會科學(xué)家”的稱號。中山大學(xué)出版社為我出版了《胡經(jīng)之自選集》。山東文藝出版社為我出版了《胡經(jīng)之美學(xué)文選》,列入“中國現(xiàn)代美學(xué)大家文庫”(收入蔡元培、王國維、朱光潛、宗白華、蔡儀、蔣孔陽、李澤厚、汝信等十五人的美學(xué)文選)。
我最后一次遠(yuǎn)行是在2015年秋冬之交。感恩北大三十五年的栽培,《胡經(jīng)之文集》出版后,我去北大向母校贈書,主持北大藝術(shù)學(xué)院的王一川和主持中文系的金永兵在北大國際交流中心為我舉辦了“《胡經(jīng)之文集》研討會”,張炯、錢中文、杜書瀛、吳泰昌、陳熙中等都來了,但缺了同窗好友嚴(yán)家炎。我在八十歲之前,每次回北京,家炎兄一定約好了程毅中(中華書局副總編、浦江清弟子)、劉學(xué)鍇(唐詩專家、林庚弟子)、陳振寰(語言學(xué)家、王力弟子)等幾位同窗,找一家優(yōu)雅的酒店,共進(jìn)午餐、相聚憶舊。可從俄羅斯回來不久,他就去了加拿大溫哥華,難得再見,我不禁黯然神傷。自此,我就無力再去北京了。別了,我居住了三十五年的北京!
我真的成了“深圳居士”。特區(qū)成立四十周年之際,《中國藝術(shù)報》為深圳文藝四十年出了一個特刊,記者喬燕冰對我作了專訪,標(biāo)題就叫《從“嶺南游子”到“深圳居士”,在這里構(gòu)筑精神家園》,發(fā)了整整一版。2019年,深圳大學(xué)授予我“榮譽(yù)資深教授”的稱號,深圳市文化藝術(shù)界把我和祝希娟、王子武、但昭義等遴選為德藝雙馨的“文藝名家”。
感恩深圳。我在這里的晚年享受到了改革開放的成果,每天都能感受到“三樂”。在人生的最后,更體驗(yàn)到了天、地、人三位一體的真、善、美的人生境界。人的一生,一要生存,二要發(fā)展,三要完善,正如馬克思所說,人的終極追求就是“人類的幸福和我們自身的完美”。人的一生就是要不斷提升自己的境界,正如恩格斯所說,人的第一次提升是人在物種關(guān)系中的提升,第二次提升是人在社會關(guān)系中的提升。我接著說,人還會有第三次提升,那就是人在文化關(guān)系中的提升,成為五個文明協(xié)調(diào)發(fā)展的“文明人”。費(fèi)孝通早先說過,人不斷從生物人提升到社會人,進(jìn)而提升為文化人。我認(rèn)為,這個“文化人”還是改稱為“文明人”更佳。“文明人”更接近于馬克思所說的“自由個性”。
最后,我想起了英國著名作家勞倫斯的幾句話,忍不住還是寫出來,作為最后的結(jié)尾。勞倫斯在1925年所寫的《道德和小說》中說:“我們的人生是因?qū)崿F(xiàn)我們自身與周圍充滿生機(jī)的宇宙之間的純潔關(guān)系而存在的。這就是我怎樣拯救自己的靈魂的,即通過實(shí)現(xiàn)這一純潔關(guān)系,我與另一個人,我與其他人,我與一個民族,我與一個種族的人,我與動物,我與樹木或花草,我與地球,我與天空、太陽和繁星,我與月亮之間的這種無限純潔的關(guān)系,就像天空中的繁星,或大或小。這種關(guān)系為我們每個人創(chuàng)造了永恒。”最后,他作了這樣的歸結(jié):“這一切就是我們的人生和永恒:我與整個宇宙之間的微妙而完美的關(guān)系。”這正是我如今所說的,人和世界要建構(gòu)成和諧美好的關(guān)系,以人為本,動態(tài)平衡,融真、善、美為一體的自由境界正是人生達(dá)到最佳平衡狀態(tài)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