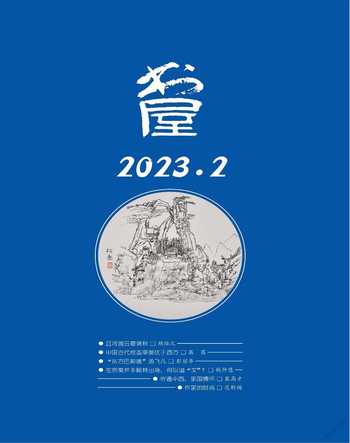見識《愧郯錄》
張建智
《愧郯錄》是一部考證筆記,共一百一十七則,書名取自《左傳》:“郯子來朝,仲尼問官之事。言通知掌故,有愧古人也。”
作者岳珂(1183—1243),相州湯陰(今屬河南)人,抗金名將岳飛之孫,岳霖之子,是岳飛后裔中名聲較著的一位,官至權(quán)戶部尚書、八路制置茶鹽使。南宋著名學(xué)者,著述頗豐,著有《愧郯錄》《棠湖詩稿》《寶真齋法書贊》《桯史》和《金佗粹編》等書。
《四庫全書總目》稱《愧郯錄》“大致考據(jù)典贍,于史家、禮家均為有裨,不可謂非中原文獻之遺也”。“于史家、禮家均為有裨焉”。著名藏書家周越然也評說:“記宋代之制度,多為史志所未備者。”說明了此書于史料價值上的重要性。
《愧郯錄》詳細記載了宋代的職官制度、輿服制度、禮儀制度、宗室制度、科舉制度、宗教史料、經(jīng)濟和科技等,似宋代一部百科全書式的書。在此,我只略談有關(guān)科技方面的一些記載,因從一個社會的科技的發(fā)展最能看出一個社會制度的現(xiàn)實狀況。
宋代科技發(fā)展較快,四大發(fā)明中印刷術(shù)、造紙術(shù)、火藥、指南針都在宋代得到巨大發(fā)展,并傳播到國外。《愧郯錄》卷九《場屋編類之書》就涉及印刷術(shù),正是至宋代,印刷技術(shù)革新,印刷業(yè)已有相當(dāng)成就,推動了科舉“時文”類書籍的大量印行,宋代文化的發(fā)達也促進了印刷業(yè)迅猛的發(fā)展。
如卷一十三《指南記里鼓車》記述了燕肅指南車和吳德仁指南車的結(jié)構(gòu),此書對燕肅指南車的內(nèi)部構(gòu)造、部件尺寸和制造方法都有較詳細的記載,為后人復(fù)原指南車提供了具體的文獻依據(jù)。
在《愧郯錄》卷五《五齊三酒》中則記載了宋代宮廷釀酒之法:“今醅酒,其齊冬以二十五日,春、秋十五日,夏十日。撥醅甕而浮蟻涌于面,今謂之撥醅”,“接取撥醅,其下齊汁與滓相將,今謂之醅芽”,“既取醅芽,置蒭其中,其齊蔥白色入焉,今謂之帶醅酒”。又說,“冬一月,春、秋二十日,夏十日,醅色變而微赤”,“冬三十五日,春、秋二十五日,外撥開醅面觀之,上清下沉。”
這是對宋代釀酒業(yè)已發(fā)展到一個很高的水平的記載。而酒名亦有不同,如“朝廷因事而醞造者”稱作“事酒”,“逾歲成熟蒸醞者”稱作“昔酒”,而“同天節(jié)上壽燕所供臘醅酒者”則稱為“清酒”。對于各類酒都有詳細記述,這便是反映了當(dāng)時人民的生活水平之高。估計“清酒”可能從那時傳至日本。
當(dāng)然,《愧郯錄》保存了不少反映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的資料。卷一十五《祖宗朝田米直》中說到,宋太宗前期,“米一斗十余錢,草一圍八錢”;神宗熙寧年間,在蘇州一帶,“一貫錢典得一畝田,歲收米四五六斗”“斗五十錢”;南宋寧宗嘉定七年時,“江鄉(xiāng)田,上色可收谷四石”,可見宋代糧食價格的演變和江南畝產(chǎn)的數(shù)據(jù)在此書中有所反映。
我在靜嘉堂閱《愧郯錄》時,一部保存完好的善本宋刊放在書桌上,然而當(dāng)一卷卷翻閱此書時,令我驚詫的是,這部古舊的宋版書卻補進了手抄的十頁特殊的書紙。這是靜嘉堂庫藏宋版書,可謂一個奇跡出現(xiàn)在我眼前了。
我發(fā)現(xiàn)有白色極薄的影寫紙緊緊粘貼在這宋版書《愧郯錄》框行清晰的書頁上,而手寫體字跡是那么秀雅剛勁。一頁頁無框無行的影寫紙,這究竟是誰的手跡呢?為何不想法刊印后,補進此書的缺頁呢?是否因為這按明抄本影寫的小開本紙與宋刊的大開本,在版面上之差異,明顯且不協(xié)調(diào)?
但唯有邊款上留存著的“據(jù)吳興周氏言言齋藏澹生堂抄本補寫”一行小字,方可讓今日之讀者和藏書研究者還可去追蹤這藏書史上的一段因緣。為此,我把這視為藏書史上的一段佳事,在電話中告知了上海的周炳輝先生,他正是言言齋主人的孫子。而電話那頭傳來的話語,除了一段能讓人勾起永遠品味、永恒追憶的書緣外,似有那說不盡的悵然之感。
但此奇巧書緣,還得從張元濟先生說起。
1992年,在日本出版的《靜嘉堂文庫宋元版圖錄》對《愧郯錄》所補缺的十頁特意做了注解說明:“由張菊生先生提供。”這八個字,無疑也構(gòu)成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美談。張元濟為編《四部叢刊》選擇了當(dāng)時最好的善本古籍,除商務(wù)印書館的涵芬樓藏古籍外,又費盡心思遍訪海內(nèi)外收藏家、公私所藏的宋元明舊槧。而當(dāng)擬影印宋版《愧郯錄》時,張元濟先生發(fā)現(xiàn)眾多善本均缺而不全。其中卷一缺少四頁,卷五缺四頁,卷七缺兩頁。共計缺十頁書。
為此,張元濟是不死心的,于是去了日本靜嘉堂,他多么希望在陸氏皕宋樓舊藏中能找到這些缺頁。可令他失望的是,靜嘉堂陸氏舊藏《愧郯錄》也同樣也缺此十頁。
1930年春,張元濟得知周越然在上海以重價購得一部《愧郯錄》,便急前往觀看,發(fā)現(xiàn)此本系祁氏澹生堂余苑本,系明人寫本,有澹翁手跋,且有毛子晉、季滄葦、朱錫鬯等印記。可惜只存首七卷,是個殘本。可是,令他激動不已的是,雖然只有半部書,但是各種刊本所缺的那十頁竟然在周越然所得的這個殘本中發(fā)現(xiàn)了,這真似“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確實讓張元濟興奮不已。于是他趕緊請人依原書款式寫補各頁。結(jié)果,所補各頁正好前后相銜接,這才得以完璧整部《愧郯錄》。
為此,張元濟非常感謝周越然先生,并不無感慨地說:
……友人周君越然購得祁氏澹生堂鈔本半部,余聞之往假,開卷則此十葉者宛然具在!因迻錄之。倩人依原書款式寫補各葉,前后適相銜接。雖卷五之第九至十二葉,仍有闕文,是本卷二“淳熙南衙”一則闕七字,卷四“魚袋”一則闕八字;卷六“仙釋異教之禁”一則共闕七字,祁本亦無可補,然大致要已具足。明清鼎革,忠敏遭難,藏書散盡,世極罕見。閱三百年于有人覆印之時,而是書忽出,且亡其半,而有此十葉之半部獨不亡,不可謂非異事矣。書此以識吾友通假之惠,并為是書慶幸焉。民國紀元二十三年元月。海鹽張元濟。
得書完璧,欣慰之情躍然紙上。
而言言齋主周越然也視此事為他一生藏書最欣慰的一件美事。八年以后的1942年9月2日,他在《古書一葉》中談到此事,興奮不已。他說:
宋岳珂《愧郯錄》十五卷,吳縣黃氏、常熟瞿氏、吳興陸氏,皆藏有宋本。黃、陸二氏之書早已散失,在人間與否不可知。瞿氏之書尚為其后人所守。查《蕘圃藏書題識》卷五,《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十六,《儀顧堂集》卷二十,知三氏之書,行格相同(半葉九行,行十七字),而缺葉之?dāng)?shù)(共計十葉)亦復(fù)相合——是三書同出一源也。宋以后重雕之本,有明岳氏校刻本、學(xué)海類編本、鮑氏知不足齋叢書本。鮑氏之書,行格一遵宋刊,校訂精詳,實為各書之冠,惟其缺葉與宋明清各本均同。豈世間竟無完本耶?民國十九年之春,余以重價購得此本于申江,即所謂祁氏澹生堂余苑本也,有澹翁手跋,且有毛子晉、季滄葦、朱錫鬯等圖記,系明人寫本。惜只存首七卷,不得稱為完璧。幸各本缺文均在此七卷,后來商務(wù)印書館編印《四部叢刊續(xù)編》,即借以校補,亦一大快事也。
張元濟卻沒有忘記遠在東京的日本朋友,他把這十頁的影寫件贈送給了靜嘉堂文庫。靜嘉堂文庫獲此珍貴資料,沒有去補刻,而是把張元濟提供的影寫紙原封不動直接粘貼在空白的書頁上。這是對張元濟的尊重,抑或是為后人珍惜這段歷史上不尋常之佳話。
周越然先生作為一名藏書家、《英語模范讀本》的著者,一生喜書、讀書并大量藏書,遇到正踏破鐵鞋無覓處的張元濟,都是為一部宋版《愧郯錄》的缺頁補闕,可謂機緣巧合,然對于一位藏書家來說,似又具必然性。
但世事難料,周越然的言言齋書樓地處上海閘北,他收藏的線裝書三千余種,一百七十八箱,包括宋元舊版、明清精抄還有西文圖書,約五千冊,有十大櫥,包括他貢獻于《愧郯錄》殘卷,卻在1932年日軍發(fā)動的“一·二八”戰(zhàn)火中終付之于一炬。
想起一部千年之書,不堪回首,如夢感傷,人與世共傷。遙想幾千年來,歷史上人類之戰(zhàn)爭對于天地人事之傷害多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