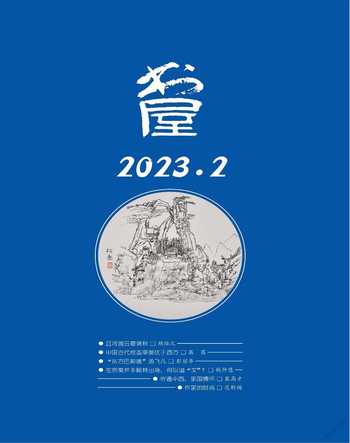慈禧太后的書法
李鵬
布蘭德、拜克豪斯在合著的《慈禧統治下的中國》一書中寫道:“葉赫那拉接受的是傳統教育……她精通詩畫,水平絲毫不遜于英國最著名公立學校的學生,十六歲就熟讀‘四書五經’,通曉滿文,熟讀二十四史。”而另一個英國人薩金特則認為:“至于教育方面,我們可以斷言,十五或十六歲時以秀女身份走進紫禁城的慈禧基本是個文盲,她的那點兒學問是進了皇宮以后才學到的。在此之前,如果說慈禧讀過什么書,那恐怕也只有《孝經》而已……事實上,直到不久前,《孝經》可能都是眾多中國男孩和女孩的唯一啟蒙讀物,無論他們是滿族人,還是漢族人。”
1861年,慈禧聯合恭親王奕訢等人發動“辛酉政變”,將咸豐帝臨終前指定贊襄政務的載垣、端華、肅順等八大臣革職問罪,開始她的第一次垂簾聽政。現存慈禧發動政變前預先親筆草擬的諭旨,短短二百三十八字中有十四個錯別字,如“朝政”訛作“朝正”,“再行”寫作“在行”,“朕意”誤為“朕議”,“竟敢”寫成“敬敢”等,而“朕仰體圣心左右為難所至,在山莊升遐”一句則壓根不通。慈禧很有自知之明,密諭的最后一句是“求七兄弟改寫”,即要求醇郡王奕譞對諭旨進行文字潤色加工。四年之后,慈禧又親筆書寫了革去奕訢一切差使的諭旨,同樣是別字連篇。
因此,若衡以檔案所存慈禧親筆擬寫的諭旨,她的文化水平并不高,所謂自小就熟讀儒家經典以及二十四史絕對不可信,倒是薩金特的說法可能更接近事實。
不過,對于慈禧的書法,相關著述幾乎是一致肯定。《慈禧傳信錄》先是提到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后,需要處理的軍中文件很多,由于慈禧太后“書法端腴”,咸豐帝“常命其代筆批答章奏,然胥帝口授,后僅司朱而已”。后文又聲稱作者曾在慈禧太后弟弟桂祥府邸見過很多慈禧及光緒帝的書畫作品,認為“后書以四十后為工,莊重凝秀,筆備王歐”,抬出王羲之和歐陽詢來類比慈禧四十歲以后的書法用筆,評價已經不能再高了。而外國人的著述,也許因為本來就對書法所知甚少,有關記述更是充滿溢美之詞。1903年,美國女畫家卡爾曾在美國公使夫人薩拉·康格的推薦下進宮給慈禧太后畫像,據她回憶:“有一天,我到宮中畫畫,正好碰到太后揮舞著一支形如巨椽的大毛筆,在一方大硯臺中頻濡筆端,待到墨色濃淡相宜,當即龍蛇競走、手不停揮,在紙上寫下一個大大的‘壽’字,觀其風采,鐵畫銀鉤,力透紙背,端的是遒勁有力,毫無美女簪花之感。有道是字如其人,太后的書法,如她的處事一般,果敢決絕。”
盡管現存一些鈐有“慈禧皇太后御筆之寶”的書法作品看上去確實功力非凡,但這些作品與原始檔案保存的慈禧親筆書跡之間有著天壤之別。前述兩道親筆諭旨,除了扎眼的錯別字外,其書寫也是歪歪扭扭,極為稚拙,與所謂“端腴”絲毫不沾邊,更別提什么“筆備王歐”了。因此,當代有史學研究者認為,跟所謂御筆繪畫是由繆素筠等代筆一樣,世傳慈禧御筆書法也是捉刀之作。慈禧的親筆及代筆之間的差異,倒是很符合啟功師戲謔的所謂“劣而不偽”與“偽而不劣”的關系。
實際上,慈禧書法有代筆并不是什么秘密。德齡公主在她的回憶中曾提到臘月二十四日慈禧要寫一些新年吉祥的祝詞:“一大早,我們就陪著太后到了大殿。太監們早鋪設好了大張的黃色、紅色、淺綠色的紙張。太后開始潑墨揮毫,寫了無非都是些‘福’字、‘壽’字。寫了一陣子,太后感到有些疲倦,就吩咐女官或者秉筆太監代為書寫。寫完之后分發給賓客與宮中大小官員。”《國朝宮史》卷五“典禮一”中載有“賞賜福字儀”,即進入臘月之后由皇帝御書“福”字賞賜內外大臣。這一儀式自康熙帝開始,代代奉行。德齡所述,與這一宮廷儀典很接近,不過由于要寫的字不少,工作量太大,慈禧親筆書寫一些之后,就讓人代筆。這些書法作品雖然是別人代筆,但只要鈐上慈禧的印,受賜者當然就視為御筆,覺得無上榮耀。慈禧此舉和歷代清帝賞賜御筆一樣,是一種籠絡內外大臣的政治手段。
中外文獻都記載了慈禧給外國人賜字的事情。瞿鴻禨(1850—1918),字子玖,號止盦,晚號西巖老人,湖南善化(今長沙)人。1900年,以“扶清滅洋”為口號的義和團進京,他們燒毀教堂,圍攻外國公使館等。后八國聯軍入侵,攻占北京,慈禧和光緒出逃。當此存亡危急之秋,瞿鴻禨“犯風雪抵行在所,兩宮召見,相向涕泣,遂命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充政務處大臣、國史館副總裁。既改總理衙門為外務部,班列六部,上特調公任尚書,授為會辦大臣”,一時很得慈禧寵信。1901年,《辛丑條約》簽訂。1902年,慈禧和光緒帝回到北京。經此一役,慈禧終于放下身段,努力修復與列強的關系。瞿鴻禨《超覽樓詩稿》對慈禧接見外國公使的場景有所記錄,可見當時除了參觀、宴會之外,慈禧還當著一眾外國公使的面,親自揮筆給每人寫了一幅“壽”字作為賞賜禮物。此舉在外國人眼里自然很新鮮,對于慈禧能寫這么大的字他們很吃驚,他們也知道這是太后表示格外禮遇的一種方式,因此,瞿鴻禨在詩里說“外臣鵠立驚殊遇,親見槐眉灑翰來”。通過現場書法表演,端居帝國權力頂端的太后走下云端,以一種看起來極為親切的行為在外國公使的眼里增加了個人魅力。
美國公使夫人薩拉·康格在1902年3月14日的信件中也專門提到了這次慈禧、光緒回鑾北京后對各國公使的接見以及隨后對公使夫人、孩子的接見:“幾天后,六個外國公使在覲見皇帝時遞交了國書。在中國的歷史上,外國公使第一次從正門踏進紫禁城。同樣也是第一次,在與皇帝的外交會晤結束后,公使們還受到了皇太后的接見。1月27日,全體外交使團的先生們被召見,儀式很正式,很體面,也顯得很恭敬。太后當時坐在御座上。2月1日,皇上和太后接見了外交使團的女士們、外交公使的夫人和孩子們。”實際上,這并不是慈禧第一次接見外交使團女眷。康格夫人在1906年11月4日信中說:“太后陛下第一次同意接見駐華公使的夫人們是在1898年12月13日。為了爭取這次覲見,外交使團和大清朝廷之間進行了多次斡旋,花了大約兩個月的時間才促使太后第一次接見七國駐華公使的夫人……從1902年皇室回京后,太后又數次接見了各國駐華公使夫人。”顯然,1898年第一次接見外交使國女眷時慈禧很不情愿,但1902年之后,無論她內心真實想法如何,至少在外交行動上她表現得更為積極了。正如英國公使夫人蘇珊·湯麗所說,外界看到的是“不管自愿還是被迫,雖然保持著種種天朝做派,卻終歸還是向我們這些西方外交人員女眷伸出了橄欖枝的慈禧太后”。
這份熱情主動不僅體現在接見外交使團女眷的頻次上,也體現在接見時格外周到的禮節上。據蘇珊·湯麗的回憶,接見時的核心環節“是每位公使女眷依次走過去跟慈禧太后握手”,她很納悶“慈禧是從什么地方學會這套西方禮節的”。除了提前掌握西式握手禮節,慈禧更不會忘了中式的禮物饋贈:受接見的每位女士都獲贈一份貴重禮物,甚至連孩子們和翻譯人員的禮物也都考慮到了。
作為禮品贈給公使的慈禧書法被美國公使夫人薩拉·康格視為“精美的藝術品”,在她準備宴請宮里女眷時提前與中國刺繡一起被掛到使館墻上。1903年1月9日的信件中,康格夫人提到在一次接見中,慈禧專門為外交人員女眷題字:“太后給予你爸爸、美國政府、查飛將軍,還有美國士兵高度評價……她對大太監耳語幾句之后,說道:‘我給今天在場的每位女士準備了一幅字畫,我要在上面寫上“壽”和“福”的字樣。’于是我們又回到她的會客廳。她站在桌旁,揮筆題字,共寫了十八幅……我們都很喜歡并珍視她贈送的親筆題寫的書畫。”
慈禧這些努力沒有白費,她贏得了康格夫人的極大好感,后者因為對當時西方各類報刊上對慈禧的丑化感到不平,建議她找人畫一幅畫像送到圣路易斯博覽會公開展覽,“康格夫人向她做了好一番游說,說歐洲各國首腦的畫像都在那兒展出,其中包括大英帝國維多利亞女王的畫像,還說如果慈禧太后的畫像大量在海外流傳,也有利于糾正外人對她的錯誤印象”。這最終促成了美國畫家卡爾小姐進宮給慈禧畫像。此外,慈禧還把她的大幅照片贈給駐北京公使及各國首領。除了饋贈禮品、贈字、贈照片,據康格夫人1902年3月16日信中所說,慈禧甚至還在學英語。
薩金特在他的《慈禧太后》一書前言里提到義和團運動期間,在華西方記者和普通人都極為仇恨慈禧太后,但在慈禧生命的最后幾年以及去世后的兩年內,西方人卻開始稱頌、贊美她,“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在1902年至1908年的六年當中,慈禧太后不遺余力地挽回了曾經因為支持義和團運動所造成的消極影響,同時還成功將自己轉化為頗具維新色彩的人物,從而贏得了很多西方人的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