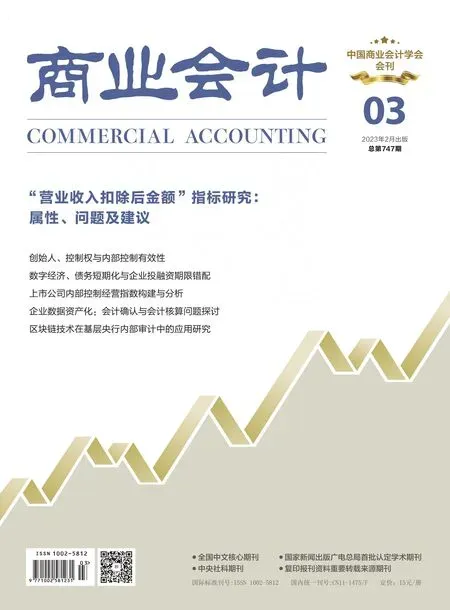稅收優惠政策、政府補助對企業研發投入的激勵效應分析
——基于信息服務業的實證研究
萬敏(南京財經大學紅山學院 江蘇南京 210000)
一、引言
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以下簡稱信息服務業)屬于第三產業,該類企業是研發投入最集中、創新最活躍、輻射帶動作用最強的行業之一,具有技術更新快、產品附加值高、資源消耗低等突出特點。目前信息服務業所享受的稅收優惠政策主要體現為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所得稅稅率優惠政策等。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是指將研發費用作為費用類項目從收入中扣減,在稅前據實扣除的基礎上,加成一定的比例扣除。若為制造業企業,2021年以后享受的加計扣除比例為100%。若為科技型中小企業,2022年以后享受的加計扣除比例為100%。其他除負面清單規定的企業外,自2018年以后享受的加計扣除比例均為75%。關于所得稅稅率優惠政策,目前主要有:新辦軟件企業自獲利年度起兩免三減半、獲得高新技術企業認定后三年內減按15%的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集成電路產業和軟件產業高質量發展企業減按10%的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文化體制改革中經營性文化事業單位轉制為企業后稅率減免幅度為100%以及小微企業普惠性稅收減免政策。政府補助從會計核算的角度看,分為計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補助和計入營業外收入的政府補助;從政府補助的項目來看,與鼓勵創新相關的項目在名稱中會有“項目開發”“自主創新”“科技研發”“技術改造”“技術研究”“研發費用”“研發支出”“創新發展”等字眼。
探討不同稅收優惠政策以及政府補助對我國信息服務業企業研發投入的激勵作用,充分了解其對企業研發的影響,不僅有利于政府制定更為完善的稅收激勵政策,以發揮最大程度的激勵作用,也有利于通過促進信息服務業的發展帶動我國科技創新水平的提升。
二、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一)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與研發投入
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是在研發費用據實扣除的基礎上,再按照75%或100%的比例加計扣除。該政策的運用可以使存在研發費用的企業通過減少當期的應納稅所得額來減少企業所得稅。這一方面減輕了企業的所得稅納稅負擔,另一方面也減少了企業的現金流出。由于加計扣除的金額與研發費用呈比例關系,所以企業研發費用越多,所享受的政策優惠就越多。因此,該政策能夠促進企業增加研發投入,促進企業創新。學者對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的影響的探討,有從創新“投入-產出-收益”的創新鏈全視角進行的研究(馮澤等,2019;靳衛東等,2022),發現該政策的實施提高了企業創新投入、創新產出和創新收益;有從地區比較的角度進行的研究,發現該政策對企業研發的顯著激勵效應具有普適性,且對長三角經濟區的促進效果更顯著(崔也光等,2020);有從最新的加計扣除政策實施效果的角度進行的研究,如李宜航等(2022)研究發現2021年針對制造業企業加計扣除的兩項優惠政策實施以后促進了研發投入的提升,針對不同類型的主體影響不同。基于以上理論分析,本文提出:
假設1: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對企業的研發投入具有激勵作用。
(二)所得稅稅率優惠政策與研發投入
與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減少應納稅所得額不同,所得稅稅率優惠政策是從降低適用稅率的角度出發來降低企業的應納稅額。信息服務業企業若為新辦軟件企業、高新技術企業、重點軟件企業、文化體制改革中經營性文化事業單位轉化而來的企業、小微企業等,優惠稅率可能為0、10%、12.5%、15%、20%等情況。稅率降低的直接影響是企業的所得稅負擔減少,企業的現金流出減少,減少的幅度比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減少的幅度大。學者的研究得出的結論大致都是所得稅稅率優惠政策促進了企業的創新能力與研發投入,但在所得稅稅率優惠指標的選擇上存在差異。馬海濤等(2022)在選擇指標時,默認高新技術企業的稅率為15%,按照應納稅所得額與10%的乘積計算得到解釋變量。胡杰等(2022)將是否享受15%的優惠稅率這一虛擬變量作為解釋變量,探討了優惠稅率和加速折舊對研發投入的協同作用。徐建斌等(2022)以企業所得稅的法定稅率與實際稅負率之差衡量企業所得稅優惠,發現相對于其他數字經濟企業而言,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對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企業研發投入的激勵效應更為顯著。基于以上理論分析,本文提出:
假設2:所得稅稅率優惠政策對企業的研發投入具有激勵作用。
(三)政府補助與研發投入
與前兩種通過降低企業所得稅來減少企業現金流出的方式不同,政府補助是一種非常直接的激勵手段,能夠降低企業的創新成本,使企業在進行研發活動時有充足的現金補給。這一激勵手段能夠引導企業加大研發投入,實現企業創新。政府補助可以從多個角度鼓勵企業增加對科技創新的投入,有利于提高企業持續開展技術創新活動的信心(楊曉曉等,2020);政府補助帶動了企業研發投入的促進效果,在民營企業、東部、西部企業和高新技術企業樣本組中更加明顯(姚東旻等,2019)。陳心怡等(2022)以七大高新技術企業為研究對象,發現政府補助對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及儀器儀表制造業企業的創新激勵最為顯著。基于以上理論分析,本文提出:
假設3:政府補助對企業的研發投入具有激勵作用。
三、研究設計
(一)變量選取
本文將構建多元回歸模型對前文提出的假設進行驗證。
因變量為研發投入強度,其中研發投入是企業在自行研究開發過程中產生的全部支出,包含費用化的研發投入和資本化的研發投入兩類,用研發投入的自然對數衡量。
自變量為研發費用加計扣除強度、所得稅稅率優惠強度和政府補助強度三項。報表中與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相關的數據反映在附注中的“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的影響”一欄,該數據為負數,并考慮了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的比例和稅率的影響。為了消除負數和企業規模的影響以及數據過小的問題,用“|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的影響|/期末總資產×100”來衡量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的強度。在“會計利潤與所得稅費用調整過程”中有“子公司適用不同稅率的影響”這一項,該數據在計算所得稅費用的過程中可正可負,如果母公司適用稅率為25%,那么子公司適用不同稅率的影響數是負數,在這種情況下,稅率優惠等于子公司適用不同稅率的影響。如果母公司的稅率不是25%,則采用曲曉輝等(2022)定義的公式“利潤總額×(25%-母公司適用稅率)-子公司適用不同稅率的影響”來衡量所得稅稅率優惠。為了消除企業規模和變量數據過小的問題,用“[利潤總額×(25%-母公司適用稅率)-子公司適用不同稅率的影響]/期末總資產×10”來衡量所得稅稅率優惠強度。政府補助既包括計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補助,也包括計入“營業外收入”的政府補助,用“當期增加的政府補助/營業收入”來衡量政府補助強度。
本文在借鑒相關研究的基礎上,采用的控制變量為企業規模、資產負債率和總資產凈利率。
相關變量定義如表1所示。

表1 變量表
(二)數據來源
本文選擇了信息服務業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剔除特殊處理的企業,剔除數據不全和數據異常的企業,選取了125家真實享受了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享受了企業所得稅稅率優惠政策以及政府補助的企業2019—2021年的數據作為樣本進行研究,最終得到了375個觀測值。其中,反映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和享受了企業所得稅稅率優惠政策的指標都是從財務報表附注中披露的“會計利潤與所得稅費用調整過程”手工收集和計算獲得,其他指標的數據均來源于CSMAR數據庫或通過計算得到。
(三)多元回歸模型構建
本文構建以下三個模型來檢驗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所得稅稅率優惠政策以及政府補助強度對研發投入的激勵效應。
四、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從表2數據可知,從125家企業近三年的數據來看,研發投入占營業收入的比重,即研發投入強度的平均值是12.31%,遠遠超過了高新技術企業的最低要求3%,其中僅有13家(占比10.4%)企業的比重小于3%。企業研發人員占比的平均值是38.98%,遠遠超過了高新技術企業的最低要求10%,其中僅有6家(占比4.8%)企業的占比小于10%。基于以上數據分析可知,信息服務類企業在研發經費和研發人員的投入力度上,絕大多數企業都超過了高新技術企業的認定標準。但是這類企業研發的風險也很大,從研發投入資本化的比例來看,平均值是20.51%,其中有30家(占比24%)企業的研發投入近三年全部費用化,并沒有形成企業的無形資產。企業內部研發形成的無形資產占無形資產余額的比例平均值為30.05%。因此,該類企業的研發投入比例較高,但資本化率以及內部形成的無形資產占比不高。本文所研究的125家企業這三年均享受了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所得稅稅率優惠政策以及政府補助等優惠政策,但享受的程度差異很大。

表2 描述性統計
(二)實證結果分析
1.相關性分析。下頁表3反映的是各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從分析結果來看,自變量研發費用加計扣除強度(AD)、所得稅稅率優惠強度(TR)、政府補助強度(SUB)與因變量研發投入強度(R&D)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表明這三項優惠政策都對企業的研發投入有激勵作用。除此之外,控制變量企業規模(SIZE)、總資產收益率(ROA)與因變量研發投入強度(R&D)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說明企業規模越大,盈利能力越強,也越能激勵企業進行研發投入。控制變量資產負債率(LEV)與因變量研發投入強度(R&D)在5%的水平上顯著負相關,說明負債率越低、償債能力越強的企業越愿意進行研發投入。

表3 相關性分析
2.多元回歸分析。表4反映了不同稅收優惠方式及政府補助對研發投入影響的回歸分析結果。模型1僅考慮了研發費用加計扣除強度(AD)對企業研發投入強度(R&D)的影響,研發費用加計扣除強度(AD)的系數為0.445(t值為7.881),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企業享受了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能夠激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模型2僅考慮了所得稅稅率優惠強度(TR)對企業研發投入強度(R&D)的影響,所得稅稅率優惠強度(TR)的系數為1.343(t值為9.536),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企業享受了所得稅稅率優惠政策能夠激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模型3僅考慮了政府補助強度(SUB)對企業研發投入強度(R&D)的影響,政府補助強度(SUB)的系數為4.512(t值為8.479),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企業享受了政府補助能激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模型4將三種優惠政策全部放到了模型中,探討其與研發投入的關系。在該模型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強度(AD)的系數為0.198(t值為3.112),所得稅稅率優惠強度(TR)的系數為0.875(t值為5.438),政府補助強度(SUB)的系數為1.848(t值為2.884),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結合以上4個模型的分析結果可知,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稅率優惠以及政府補助對企業的研發投入均具有正向激勵作用,且激勵作用顯著。

表4 稅收優惠政策、政府補助與研發投入的回歸分析
(三)滯后一期的實證結果分析
考慮到稅收優惠政策、政府補助的激勵作用可能具有時滯性的特點,該部分選擇使用125家上市公司2019年和2020年的自變量和控制變量數據,分別與2020年和2021年的因變量數據進行相關性分析和回歸分析。
1.相關性分析。表5中反映的是自變量、控制變量與滯后一期的因變量之間的person相關系數。該分析結果大體與表3的分析結果一致。除資產負債率(LEV)與研發投入強度(R&D)負相關外,其他變量都與研發投入強度(R&D)在1%或5%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對比表3和表5中三個自變量與因變量的相關系數可以發現,自變量研發費用加計扣除強度(AD)(0.289>0.279)、所得稅稅率優惠強度(TR)(0.385>0.306)、政府補助強度(SUB)(0.355>0.261)與滯后一期的研發投入強度(R&D)的相關性更強。

表5 自變量與滯后一期的因變量相關性分析
2.多元回歸分析。表6中的三列數據分別反映了以研發費用加計扣除強度(AD)、所得稅稅率優惠強度(TR)、政府補助強度(SUB)分別作為自變量與因變量滯后一期的研發投入強度(R&D)之間的回歸分析結果。表6的分析結果與表4一致,同時也反映了稅收優惠政策、政府補助具有時滯性,能促進企業以后期間研發投入的增加。

表6 研發投入滯后一期的回歸結果分析
(四)穩健性檢驗
為了確保以上回歸分析的穩健性,本文通過替換因變量的方式進行了進一步的檢驗。在原來的模型中,因變量研發投入強度選擇的是研發投入的自然對數。在穩健性檢驗中,研發投入強度使用“研發投入/期末總資產”來衡量。
從表7的分析結果來看,自變量研發費用加計扣除強度(AD)、所得稅稅率優惠強度(TR)、政府補助強度(SUB)在模型1到模型3中,分別與因變量研發投入強度(研發投入/期末總資產)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而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該顯著性關系在模型4中依舊成立。以上的分析結果與表4一致,結論穩健。表8是自變量研發費用加計扣除強度(AD)、所得稅稅率優惠強度(TR)、政府補助強度(SUB)和滯后一期的因變量研發投入強度(研發投入/期末總資產)的回歸分析,結果與表6一致,結論依舊穩健。

表7 穩健性檢驗

表8 因變量滯后一期的穩健性檢驗
五、研究結論及政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文以同時享受了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所得稅稅率優惠政策和政府補助的信息服務業企業為研究對象,從財務報表中收集與這三大政策相關的數據,并分析了不同政策對研發投入產生的激勵作用。
研究表明,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所得稅稅率優惠政策和政府補助對企業當年的研發投入都有激勵作用。同時考慮到政策可能具有時滯性,因此在檢驗了這三大政策對未來一年的研發投入的影響后,發現這些政策對滯后一年的研發投入依舊存在激勵作用。在將因變量從研發投入的自然對數換成研發投入與期末總資產的比例后,研究結論依舊成立,結論穩健。
(二)政策建議
1.政府應制定和完善有利于信息服務業研發和創新的稅收優惠政策和政府補助。一方面,政府應擴大享受政策的主體范圍;另一方面,對信息服務業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和政府補助應有針對性地展開,對重點發展的企業應加大加計扣除比例和所得稅稅率優惠,適當增加補助項目和金額。政府在對企業開展稅收優惠的同時,也應給企業設定經營和財務目標,以充分發揮稅收優惠政策的激勵作用。
2.企業在享受政府的稅收優惠政策和政府補助的同時,應促進研發投入的資本化。稅收優惠政策和政府補助能減輕企業的納稅負擔,并減少企業的現金流出。因此,一方面,企業應積極響應政府的稅收優惠政策,使之符合稅收優惠政策的標準并享受政策;另一方面,應加大對研發人才的培養和研發經費投入的力度,在增加研發投入的同時,提高研發投入的資本化率和研發產出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