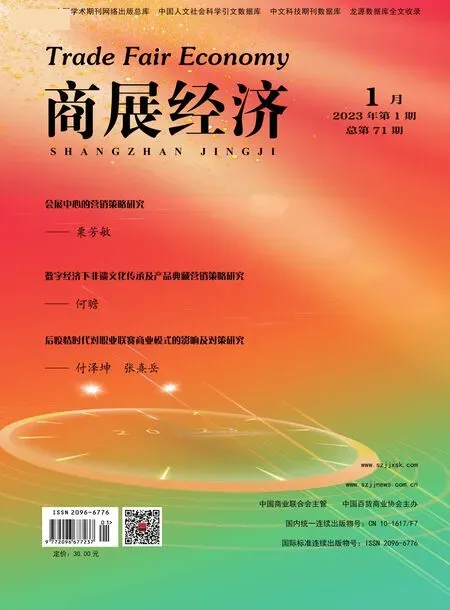直播帶貨的法律問題探討
趙芳世 劉海廷
(大連海洋大學 遼寧大連 116000)
隨著科技的飛速發展,線上購物從傳統電視購物和傳統電商發展為直播帶貨,近幾年直播帶貨行業呈現井噴式發展。直播帶貨行業總體來說,就是通過直播平臺,由主播向消費者展示商品的屬性特點并進行答疑,但直播帶貨發展的同時,也存在著諸多相關法律問題。因此,應提出解決問題的對策,從而促進直播帶貨這個新興行業的良性發展,推進經濟發展。
1 直播帶貨概述
直播帶貨總的來說,就是在直播娛樂項目,同時進行帶貨,在直播間,主播向消費者介紹商品,為消費者近距離展示商品。直播帶貨與傳統電商和傳統電視購物是有區別的,傳統電商是商家在電商平臺發布文字、圖片,把產品展示給消費者,消費者再通過平臺進行購買,而直播帶貨是委托主播用網絡直播的方式向消費者推銷商品。傳統電商僅以圖片和文字表現,而直播帶貨可以向消費者近距離展示商品,并且主播可通過彈幕回復消費者提出的問題,增強了與消費者的互動性。直播間也會經常設計有趣的環節吸引消費者,消費者在比較輕松舒適的環境中購物,迎合了當代消費者的心理。與電視購物相比,直播帶貨更加便捷,一個手機和支架就能支撐起整個直播間。電視購物不但需要受到電視臺的制約,而且電視購物只能局限于國內,直播帶貨卻不受地域限制。
中國商業聯合會于2020年6月8日發布了公告,由該會下屬的媒體購物專業委員會組織人員制定了《視頻直播購物運營和服務基本規范》和《網絡購物誠信服務體系評價指南》兩項標準,這是整個直播帶貨行業內首部全國性標準。緊接著,市場監管總局于2021年3月15日公布了《網絡交易監督管理辦法》,規范了網絡交易活動。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國家稅務總局、商務部等七個部門于2021年4月23日聯合發布了《網絡直播營銷管理辦法(試行)》,該辦法自2021年5月25日起正式施行,加強了網絡直播營銷管理[1]。直播帶貨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產生了大量消費者維權的問題,在此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網絡消費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一)》。
2 直播帶貨存在的法律問題
隨著互聯網的高速發展,電商行業快速興起,直播帶貨成為新型銷售模式。直播帶貨改變了人們的消費習慣,促進了經濟發展,但其中的法律問題也隨之而來,如主播對用戶購買的商品是否需要承擔法律責任、產品質量參差不齊、消費者維權難度大、直播平臺監管力度弱的認定問題。
2.1 主播法律責任不完善
對于主播的法律地位,學界主要分為三種觀點。
首先,將主播歸類為《廣告法》中的廣告代言人,主播在直播過程中對商品進行講解與推薦,主播具有代言人的責任。但要確認主播為廣告代言人,先要定義直播帶貨為廣告,而《廣告法》對廣告構成要件有明確規定,廣告得有廣告主委托,有資質的機構制作,要經過審核,要在有廣告發布權的媒體發布,直播帶貨并不符合這些條件[2]。
其次,將主播歸類為《電子商務法》中的電商,主播帶貨屬于電子交易,應承擔電商的責任。但主播法律主體是多種多樣的,并不能一概全論。
最后,把帶貨主播劃分為傳統電商工作人員中的銷售人員,當銷售商品發生問題時,由電商承擔法律責任,主播不承擔責任。這種觀點主要是將主播的直播帶貨行為視為一種職務行為,主播不承擔責任,但主播和電商之間不只具有雇傭關系,其關系是復雜多樣的,只把主播確認為銷售人員是不符合現實的。
此外,根據主播的實際地位確定法律責任。這是當下的主流觀點,但是存在著缺陷。主播會通過身份的轉變,以逃避法律責任,消費者維權難度系數加大。
以上表明了現有法律的不足,要求主播承擔責任具有一定的障礙,因為以上觀點都是立足傳統方式之上的,傳統方式之中,各個責任主體分工明確,界限明顯,但在直播帶貨中,主播通常同時擔任多重角色。以上述觀點確認主播的責任時,主播往往會通過身份轉變,逃脫法律責任,因此法律應明確規定主播帶貨行為的責任。
2.2 產品質量參差不齊,消費者維權難度大
在中國消費者協會2020年6月29日發布的“6·18消費維權輿情分析報告”中顯示,在這20天的監測期內,“直播帶貨”有關的負面信息竟然高達日均560條,監測期內總共高達11萬余條,其問題主要集中在信息不對稱、違規及虛假宣傳、售后服務缺乏保障等方面[3]。在直播帶貨中,最常出現的就是產品質量問題,例如某品牌的菜刀拍個蒜都能拍斷,消費者詢問客服,客服回答說:“抱歉,給你帶來不愉快的體驗,這個刀不能拍蒜的哦!”羅永浩曾在他的直播間進行帶貨,向消費者售賣過名為“花點時間520玫瑰禮盒”的商品,緊接著就有網友在其社交平臺發帖,反映了這個禮盒存在質量問題,網友在文章中描述了收到“花點時間520玫瑰禮盒”質量堪憂,其中有的花束已經損壞。再如,臭名昭著的“糖水燕窩”事件[4]。2020年11月,某著名網絡主播在直播間賣的燕窩被消費者質疑是糖水,社會影響惡劣。直播帶貨之所以盛行,往往是與其優惠的價格有關,消費者也喜歡購買促銷商品,但這些商品中存在大量質量參差不齊的假冒偽劣產品和三無產品。
質量參差不齊隨之而來的就是消費者維權問題。在消費者遇到產品質量問題時,帶貨主播、商家、直播平臺互相推諉,消費者難以維權。此外,《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網絡消費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一)》并沒有重新劃分消費者應該承擔的舉證責任,導致消費者在維權時拿不出有利的證據,在直播過程中,消費者也想不起要保存證據,對直播進行錄屏、拍照等。再就是收集證據的過程需要花費大量精力,所以消費者往往選擇不了了之,更加助長了這種不良風氣[5]。消費者舉證困難主要在于鑒別,如直播帶貨中的假名牌鞋與正品相似度極高,導致消費者很難區別。還有就是鑒定,消費者想要證明商品是假冒商品,要通過鑒定機構鑒定,但鑒定機構價格十分昂貴。再就是取證困難,雖然《網絡交易監督管理辦法》第二十條規定網絡直播服務提供者對網絡交易活動的直播視頻保存時間自直播結束之日起不少于三年,但第四十五條規定網絡交易經營者違反本辦法第二十條,法律、行政法規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法律、行政法規沒有規定的,由市相關部門責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將按照該辦法進行罰款。處罰力度極輕,僅是責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也僅被處一萬元以下罰款,所以導致直播間運營者有恃無恐,而消費者難以取證。
2.3 直播平臺監管力度弱
在直播帶貨行業中,直播平臺往往缺乏監管力度,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方面,直播經營者之間,主播和商家經常使用不正當的競爭手段獲取利益,不利于整個行業的發展。例如,在2020年5月28日—2020年6月19日進行的“618”大促期間,一個公司在直播平臺的多場直播中,將另一家公司的某產品與他們的某產品進行比較。在直播過程中,此公司的工作人員使用“不安全”“這個金屬的大疙瘩,他的濾網啊,說得難聽點,就能把人砸死”等不當用語對另一家公司的產品進行負面評價,從而產生不良的社會影響。
另一方面,商家和消費者之間,直播平臺是連接經營者和消費者的橋梁,平臺有義務承擔監管的職責。但當前情況是網絡直播帶貨中存在過分夸大、虛假宣傳、產品品質參差不齊的問題,針對這些問題,直播平臺卻沒有履行它應履行的監管職責。首先,因為直播帶貨的門檻準入比較低,任何人都可以進入,直播平臺沒有有效地審查主播和商家,導致這些不良主播和商家進行直播帶貨,欺騙消費者;其次,不良主播和商家會引導消費者通過微信、支付寶等其他平臺實現交易,平臺對此種現象缺乏監管,導致消費者上當受騙;最后,當商品有質量問題,消費者需要維權時,平臺沒有盡到協助的職責,比如沒有提供必要的信息和數據等,這就加大了消費者維權的難度。
3 完善直播帶貨法律問題的對策
3.1 完善主播法律責任
本文認為,想要完善主播的法律責任,就需要制定新的法律法規或對現有法律進行修訂,明確規定其法律地位,確定主播應該承擔的責任,彌補立法的缺失。
如果主播在直播過程中,利用自己獨有的形象和影響力對商品、服務向消費者介紹的,如李佳琦、薇婭、羅永浩等,那就應當認定為廣告代言人。對此類主播的處罰應根據《廣告法》第五十六條第二款、第三款規定,關系消費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服務的虛假廣告造成消費者損害的,廣告代言人應與廣告主承擔連帶責任;對于其他商品或服務造成消費者損害的,廣告代言人應知或明知廣告虛假而代言的,應與廣告主承擔連帶責任。
如果主播既是銷售商又是生產商,應當按照《電子商務法》的規定加以規范,如《電子商務法》第七十七條規定,電子商務經營者違反本法第十八條第一款規定提供搜索結果,或違反本法第十九條規定搭售商品、服務的,由市場監督管理部門責令限期改正,沒收違法所得,可以并處五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并處二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的罰款。
現實直播帶貨中,許多主播本就是生產商或銷售商的工作人員,或是生產商或銷售商委托主播進行直播,那么如果讓這類帶貨主播獨立承擔責任是不合理的,本文認為這類主播的直播行為可以認定為職務行為,那么就應由生產商或銷售商代替承擔法律責任,如果帶貨主播有過錯,生產商或銷售商就可以對其內部追償。
同時,應該規定帶貨主播有多重身份的情形,法律規定加以協調,解決責任競合和法律競合問題。總之,應明確規定帶貨主播的法律地位和法律責任。
3.2 加大直播帶貨過程中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
首先,《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二十三條規定,部分商品可以由經營者承擔舉證責任,但關于其他商品的還是由消費者承擔有關瑕疵的舉證責任。消費者和經營者在信息掌握程度上處于不對等的狀況,為了更方便消費者維護權益,本文認為可以修訂法律,適當將舉證責任倒置范圍擴大,由商家證明其商品不存在質量問題,如果商家無法證明,那就承擔不良后果。
其次,降低維權成本,各大互聯網購物平臺紛紛出臺了在線糾紛解決機制,如淘寶的“淘小二”和京東的“京東小二”等,很好地踐行了關于保障消費者退換貨、先行賠付的法律規定。直播帶貨也可以借鑒其他網購平臺,建立在線糾紛解決機制,發揮消費公益訴訟功能也能有效地降低維權成本,而且往往會對商家、平臺、主播產生一定的震懾力。
最后,應建立行業黑名單體系,實行信用評分制度,直播帶貨的商品出現質量問題,其分數達到規定的數值后,可對商家和主播進行警告或罰款,不整改或多次違規的可以拉入黑名單,并對社會公示。
3.3 加大直播平臺監管力度
直播平臺相較市場監管局,在信息掌握和技術運用方面更具優勢,所以應加大直播平臺的監管力度。針對直播經營者之間的不正當競爭,設置平臺規范。對于違反規范的直播經營者進行警告,對于嚴重違反或多次違反的直播經營者可以關閉其賬號并公示。直播平臺應提高準入規則,不能來者不拒,不符合平臺規范的直播經營者不準許其直播帶貨。對進入平臺直播的經營者應向平臺發送經營者信息和商品信息,直播平臺收到信息審核后,向消費者公示。當消費者權益受損,需要維權時,向直播平臺反饋,平臺應履行協助義務,提供經營者信息。若直播平臺不履行上述監管義務,則應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4 結語
直播帶貨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發展,而且極大地便利了消費者,可以說是促進了整個社會的發展,但存在著相應的法律問題。所以,應完善主播的法律責任,加大直播帶貨中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及加大直播平臺的監管力度,從而實現直播帶貨行業的穩定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