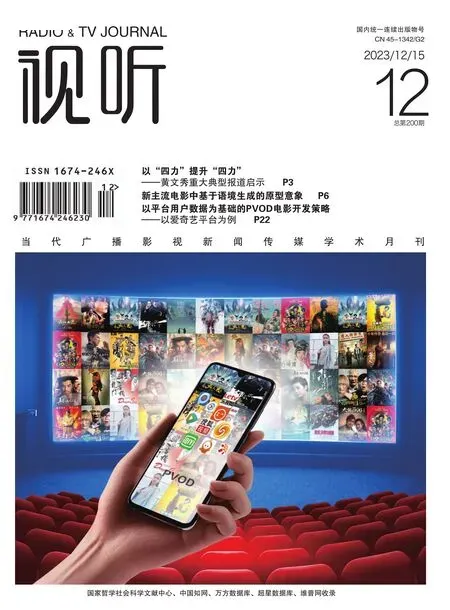論影像媒介中的“工匠”題材表達與建構向度
◎邵才俊 劉凱
影像很大程度上可以作為一種歷史文本的存在,反映與記錄著社會文化和意識形態的發展;同時,影像又在逐漸構建起一種公共身份,成為歷史敘事與集體記憶的社會范式。①作為傳播媒介的影像,其承載的主題意義與審美實踐不斷成為“民族意識”的折射,重塑著民族記憶與文化的傳播。
“工匠”作為一種特殊的身份主體,歷經社會文明的變遷,鍛造出豐富的道德氣質與價值取向。影像媒介圍繞“工匠”這一主體進行題材化思考,先后生產出不同形式的視聽呈現效果,這部分影像不僅反映出新時代工匠精神的現代性畫像,同時也展現出其獨有的美學特征。作為當下的一個現實性命題,當影像媒介與“工匠”題材進行熒幕結合時,一方面契合了當今時代語境下的主流意識導向,另一方面體現出重要的影像傳播價值與社會傳播意義。
一、影像媒介中的“工匠”書寫
(一)“工匠”文化記憶書寫
德國學者阿萊達·阿斯曼(Aleida Assmann)認為,在文化記憶的生成機制中,媒介發揮了重要的鏈接作用。其不僅能夠記錄文化隱喻,同時也能重構文化中的記憶鏈條。在人類社會的不同發展階段,文本、圖像和影像分別承擔著建構和傳承文化記憶的媒介使命,并以敘述、展覽和展演三種形式逐次呈現。②該論點清晰指出在視覺文化時代下影像媒介對民族文化記憶的重要塑造作用。
在中國歷史文化記憶的構成譜系中,“工匠文化”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工匠群體的職業身份、道德氣質以及當下社會風貌等因素的綜合影響下,“工匠”題材影像體現出濃重的民族文化記憶標識。作為重要文化記憶傳播媒介的中國電影,如《金牌工人》(2005)、《大路朝天》(2018)、《匠心》(2019)等,通過巧妙的敘事構思與豐富的影像符號展現出新時代語境下一個個薪火相傳的工匠傳承故事。這類影像在其深層結構上依托“工匠”題材的影像建構,追尋個體記憶與社會記憶的深度聯結,以此探尋工匠群體的獨特民族情感。可以看出,這一系列工匠題材影像在媒介藝術的傳播表達中,通過主題性的敘事傳播將其工匠群體的公共面貌與個體風骨融入時代發展的文化記憶中,不僅透視出新時代工匠精神的現代性畫像,同時亦體現出媒介影像對于民族文化記憶的自覺性表達。
影像往往通過敘事傳達進行文化形象的建構來完成民族歷史精神生活的想象性和情感性解釋,影像的傳播活動也同時成為國家文化形象得以建構的活動,以此來認識民族的歷史與民族文化的獨特性。③因此,從另一個維度來看,中國影像媒介中對“工匠”的題材化書寫,也不單單是對工匠群體薪火相傳的傳承故事書寫,還側重對其背后中國故事的民族想象書寫,因此其負載的文化記憶就更為可貴。在影像媒介傳播中,電影《袁隆平》(2009)、《天渠》(2018)、《中國醫生》(2021)等作品,在宏觀視角上聚焦于工匠主體的精神世界,剖析個體家國情懷的表達,通過工匠的主體視角展現出民族奮斗史上波瀾壯闊的“中國記憶”。這一系列蘊含“中國故事”的“工匠”題材電影文本所映現出的影像內涵與美學張力,構建起大眾集體對民族文化與國家意志的認同,并且以其獨有的話語方式完成對工匠文化的空間想象與意義填補。這對于堅定文化自信、傳播民族精神的社會導向來說,具有一定的文化推廣意義。
因此,中國影像媒介中對“工匠”的文化記憶書寫,不僅涵蓋了對工匠群體的職業技藝與道德意志的書寫,同時在宏觀視野上還串聯了大眾集體對時代精神與民族意識的眷注。就民族文化記憶的傳播而言,清晰表征出了工匠文化的真正內核所在,同時不失為題材化的銀幕表達呈現出民族性色彩。
(二)“工匠”題材影像書寫
題材化影像所傳遞出的視聽意象,通常與特定的情感訴求、生活方式、價值觀念與審美追求等存在某種象征性的關聯。在“工匠”題材影像的媒介呈現中,圍繞工匠群體的不同職業技藝、生活情感、生命哲學等進行多元化的本土表達,反映出典型的中國式審美追求,這種審美追求與中華文化基因形成對應關系,揭示出新時代語境下工匠公共群體的樸素生活觀念與美好理想追求。
電影《金牌工人》(2005)以全國道德模范許振超的先進事跡為原型進行改編,講述該人物圍繞碼頭安全生產需求,開展科技攻關的故事。其中,以許振超為代表的工匠群體以默默無聞的“最美奮斗者”姿態出現在銀幕上,影像通過對工匠群體日常化、生活化的敘事書寫,為工匠形象賦予了民間市井文化印記。影片還結合工人群體的樸素生活、工作情感與道德理想,彰顯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匠銳意拼搏、無私奉獻、敢于創新的時代風采,這無疑是對時代語境下的工匠品質最有力的呈現。在日益復雜的消費主義社會下,電影《匠心》(2019)中的青年設計師陸曦與臺商方寒冰為了一個建筑修復方案誤打誤撞回到自己故鄉木雕小鎮,并在爺爺的感染下重新學習、傳承木雕技藝,尋回當下社會年輕人所缺失的匠心精神。該片以木雕小鎮上的祖孫情感作為敘事支點,聚焦青年設計師陸曦的個體理想選擇與價值判斷,并將工匠精神的價值觀念與當下社會心理進行縫合,使得主人公以樸素、務實的工匠形象特征有效參與建構民族工匠精神與主流價值觀的傳播。此外,還有《鐵人》(2009)、《黃大年》(2018)等影像作品,同樣以平民化向度的底層工匠視角來展現新時期不忘初心,至誠報國的感人事跡,謳歌出這部分工匠群體在改革開放以后,借助自身持續鉆研與獨立堅守的精神特質,為我國科技事業帶來了巨大變化,由此塑造出新一代工匠群體的英雄形象。以上這一系列的題材影像將特殊時代語境下的社會文化心理、生命價值觀念與個體價值建構歸置于主題性的影像話語框架內,使得受眾集體能夠接受影像文本中的內在文化邏輯,產生對工匠文化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同,從而借助影像媒介再現了國家發展歷程中工匠力量的時代主旋律。
當然,除了以上相關影像文本外,對“工匠”題材進行表現的作品還有很多。但無論是何種形式的表現,工匠題材的影像書寫都是立足在民族文化的基因上進行的。因此,通過對影像媒介中的“工匠”題材呈現進行分析,亦能夠進一步探視出中國式現代化發展背后所蘊藏的工匠貢獻。
二、“工匠”題材影像的建構向度
(一)“工匠”題材的形象建構
電影是民族文化與價值觀念輸出的重要媒介,也是國家形象建構與傳播的重要載體。④因為負載了不同時代背景下的主流意識形態與價值觀念導向,“工匠”形象對國家與民族形象的表達來說亦是一種滲透式的塑造。因此,在對“工匠”形象進行影像化建構時,需要著重考慮兩個維度。
一是在微觀視角下聚焦于對工匠內在的主體形象建構。工匠的主體形象是貫穿影像始終的重要前提,其不僅能夠展示出工匠群體的真實生活,還能夠側面映襯出工匠群體的精神旨趣。因此,在對其藝術形象進行建構時,需要在尊重藝術真實的基礎上,進一步提煉出對工匠主體心靈世界的深層體悟。
由曲全立導演執導的記錄電影《璀璨薪火》(2020)通過影像鏡頭記錄了中國150多位非遺傳承人身體力行的傳承故事,生動展示出中國匠人細膩、精致的手工技藝與精益求精的職業精神。在工匠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該片從非遺傳承人的“自者”視角出發,將目光聚焦于工匠群體的日常瑣事,通過柴米油鹽等日常生活符號描寫,完成了對工匠人物身份的真實建構。其中不論是耕作的農人、辛勤的采茶人還是手作的匠人,影像都真實再現出工匠群體的私人空間與生活狀態,進一步展現出這部分人物群像簡單質樸、真誠專注的形象特征。在此基礎上,該片運用第一人稱的“自者”視角加以洞察工匠群體的精神世界,通過“筆墨紙硯”“金銀銅鐵”等物象化的手段揭示工匠主體的內在心理活動,并將隱匿、抽象的思想意涵借助視聽化的人物形象進行表現后,化為“他者”可以感知到的角色內在精神,從而引發觀影者的情緒效果,進一步推進了觀影群體對工匠人物故事的情感共鳴。通過這一影像文本案例可以看出,當工匠角色的身體符號貫穿于影像文本中時,通過對工匠主體的身份特征與心理特質進行深入刻畫,能夠進一步構建出更為多元、立體的工匠形象面貌。同時,能夠為影像主題融入特定的情感細節,賦予影像真實動人的觀影效果。
二是在宏觀視野上聚焦于對工匠外在的國家形象建構。“國家形象”的定位,是對一個國家進行形象建構的過程,是通過信息傳播有效接觸目標受眾群,在目標受眾心目中確立一個正面的、明確的國家形象的過程。⑤工匠群體在高技能的生產實踐中凝練而成的精神品質充分展示出了中國當下時代之美與精神之美。因此,在對其國家形象進行建構時,需要在深入工匠精神時代內涵的基礎上,進一步體現出新時代語境下負載民族價值立場的當代中國名片。
借助導演的審美再造,將工匠人物的形象刻畫融入崇高光環的時代語境中,并將工匠升格為能夠代表國家形象的公共群體符號,是“工匠”題材影像得以建構國家形象的具體路徑。由青年導演張穆執導的電影《女記者的日記》(2020)、《青春不悔》(2021)等影像,以紀實性的手法生動刻畫出脫貧攻堅戰中原型人物的工匠形象特征。影像通過對第一書記、大學生村官、退役軍人、科研工作者等人物群像的工匠品質塑造,詮釋出中國民眾無私奉獻、勇于擔當的新時代形象。綜觀這一系列電影文本中的工匠形象書寫,影像側重對歷史變遷中的國家記憶進行表現,直觀展示出各類工匠人物在各種不利條件下頑強克服困難、建設小康中國的精彩事跡。通過對這些電影文本進行分析,可以看出,工匠外在的國家形象建構,借助時代語境下的國家記憶來串聯個體庶民的倫理價值,進而逐漸完成對國家形象的潛移默化建構,這樣的方式可以成為題材影像中國家形象得以建構的重要實踐參考。
因此,圍繞“工匠”題材影像中的形象建構討論,唯有兼顧其內在與外在的雙重建構,才能完成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統一,以期最終能夠真正傳播好中國形象,傳遞出符合民族要義的中國式審美形象姿態。
(二)“工匠”題材的內涵建構
用影像建構的大眾對民族、國家歷史的集體認同,不僅能夠引導大眾對中國歷史的真實判斷,而且能夠完成國家對國民心理的現實導向。⑥從文化心理邏輯來看,“工匠”作為一個職業共同體,在實踐生產中淬煉出的“工匠精神”已然成為當下中國文化價值觀的一種公共性表達,其對于人類社會的發展具有現實性的精神驅動作用。因此,以“工匠”為表現題材,對其影像主題內涵進行建構時,著力點理應聚焦在對工匠群體的身份認同與歷史文化認同兩大層面上,進而完成媒介影像對受眾心理的精神引導,構筑成為民族文化海內外傳播的結構性力量。
首先,就其身份認同來說,“工匠”題材影像的身份認同往往體現在對工匠人物的職業選擇與職業價值的接受認同上。因此,在對其題材內涵進行建構時,需要對工匠共同體的職業身份、情感特質與職業價值等方面進行深層次的詮釋,讓觀影群體在影像故事中產生自我映射,進而深度構建出觀影群體對于工匠身份群體的積極情感。電影《那山那人那狗》(1999)中,兩代郵差員將個體選擇與職業熱忱融入鄉村發展脈絡中,父子兩代共同接力鄉村郵差事業的運行與發展,這樣的代際傳承故事感動了眾多觀影者,這也成為大眾對工匠群體身份認同的典型影像化表征。該片中,老郵差的兒子高考落榜后在父親的影響下回到大山里繼承父親的職業,繼續從事鄉村郵遞事業。這樣的故事架構在20世紀民風質樸的特定敘事語境內,無疑體現出大眾集體對鄉村郵遞員身份的認同接受以及對鄉村郵差價值的贊許與肯定。通過對這一影像進行分析,“工匠”題材影像的內涵建構可以借由影像中工匠角色的心理結構與社會表現為其身份價值賦予積極意義,再借由影像敘事的情感化流露揭示出工匠個體在社會網絡中的價值意義取向,使受眾在觀影過程中產生滿足、肯定、贊許等情感體驗,產生對工匠群體身份認同的觀影意識。
其次,就其歷史文化認同而言,作為建構歷史記憶的文化場域,電影通過對影像內容的篩選與表現,來完成對歷史文化認同的編碼。影像內容中的價值觀輸出是創作者有意識地訴說民族文化內涵的能指符號。按照這一思考路徑,我們在對“工匠”題材的影像內涵進行建構時,可以將其影像的主題、價值觀與工匠文化之間建立某種關聯,以此實現“工匠”題材影像對民族歷史文化進行傳播的媒介效能。電影《中國醫生》(2021)根據我國新冠疫情防控的真實事件改編,以援鄂醫護人員為原型,全景式地記錄了我國抗疫斗爭的社會圖景。該片在特定的時代語境下,將中華民族求實、協作、奮斗等精神意涵圓融于當今社會的時代信仰中,通過表現醫生、護士、志愿者等人物群像的感人故事,完成人與社會、人與時代的影像縫合。以人物群像的價值觀念與行為方式作為影像內涵表達與工匠文化傳播的實踐方式,在情感上形成了個體與民族文化的整合,這區別于其他主流電影“借助外部敵對勢力的戲劇性對立來建構‘中國性’的認同”⑦。《中國醫生》借助中國匠人自身的敬業精神與民族性的文化基因,在“人性”視角上折射出新時代語境下中國匠人愛國、敬業的家國情懷,讓觀眾產生價值觀上的共鳴,從而能夠真正產生對中國工匠文化的自覺自發性認同。
“電影觀眾的群體意識”(The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歷來是電影學研究的核心概念。⑧因此,在對“工匠”題材影像的內涵進行建構時,不僅需要基于對工匠的主體身份建立影像化的認同建構,還需要在此基礎上,依托影像內容的內涵輸出,進一步增強觀影群體對民族歷史文化的認同意識。唯有這樣,才能真正把握住題材影像的主題意義與影像內涵的內在邏輯,進而深化出“工匠”題材影像在新時代背景下的媒介傳播意義。
(三)“工匠”題材的敘事建構
賈磊磊認為,主旋律電影的敘事邏輯應當是建構一種具有國家意義的“影像本文”。由這種“影像本文”所體現的國家形象不僅顯現在電影的影像表層結構中,而且也會通過影像敘事體系與社會歷史之間產生的“互文性”呈現在觀眾的文化想象層面上。⑨按照這一路徑進行延伸,針對“工匠”題材的敘事建構,需要將工匠人物的個體經驗融入歷史格局下的社會發展語境中,使其作為社會歷史的真正在場者,以“小人物”的姿態體現與“大時代”之間的互文敘事關聯,進而透過工匠群體的微觀視角去記錄宏大的新時代風貌。
首先,應當實現典型工匠人物與歷史宏大命題的敘事縫合。在傳統的主旋律題材影像中,對于典型人物的敘事書寫,常常表現為“高大全”式的宣傳,敘事主體被抽象為負載意識形態宣傳功能的符號,缺少微觀視角下的“人物弧光”。而“工匠”題材電影《大路朝天》(2018)的成功之處,在于其摒棄了傳統過于直白的宏大敘事模式,采用工匠個體的平民化視角,將人物故事、時代記憶與社會生活形態等進行糅合,從而講述了改革開放40年來三代路橋工匠的情感歷程與時代變遷。在敘事上,影片以“小人物”為主線,利用路橋工匠家庭中人與人、人與物等情感意象作為敘事支點,介入“西部建設”這樣的歷史宏大命題中。這種文本之間的互文敘事串聯,使得影像不論是對大國工匠精神的刻畫,還是對歷史傳承主題的表達,都進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兼顧,這即是工匠個體經驗與歷史宏大書寫之間的一個影像平衡表現。而在這樣的題材敘事中,“小人物”與“大時代”已然形成了一對特殊張力,以典型工匠人物的故事去表現歷史的宏大命題,在時代語境中領略工匠群體的生活沉浮,二者相互推進,成為該類影像敘事縫合的有效方式。
其次,應當實現多元主題與價值主旨的敘事縫合。西方結構主義學者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evi-Strauss)曾經就“二元論”的問題指出,敘事體系內的二元對立式存在,適用于人類思維的普遍構成模式。《大路朝天》關注到了“小人物”生活中的悲歡沉浮,影像敘事圍繞四個基層工匠家庭中折射出的“生活與夢想”“工作與家庭”“小我與大我”等二元矛盾進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表現。這些矛盾基于社會生活的真實取向,影像在敘事上運用蒙太奇的手法將其合理統一到一個價值主旨上,即中國路橋建設。圍繞這一價值主旨,電影在關注工匠文化的同時,運用奉獻、傳承、敬業、廉潔等關鍵詞來揭示“小人物”的思想斗爭與生命追求,從而在側面對這一價值主旨做出了積極響應,為影像賦予了多元化的價值意義。面對“工匠”題材的敘事建構,在多元化的主題呈現中凝練影像價值主旨的深層觀照,依托歷史空間內工匠個體的價值訴說與理想追求,形成敘事結構中“小人物”與“大時代”的關聯性。這樣的縫合方式應當成為題材影像中敘事得以建構的有效話語方式。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影像中的社會歷史正是被影像話語建構出來的。敘事作為電影創作者對工匠人物故事與時代話語的提煉,蘊含了民族文化景觀的表征與國家形象的傳播。在“工匠”題材的敘事體系中,“小人物”以影像話語的方式參與到對當下社會性的建構,并與“大時代”產生時空交融。利用多元化的主題貼近影像價值主旨的深層意涵,實現影像作品對時代主流價值觀念的確認與肯定。借助這樣的敘事建構思考,能夠真正讓大眾集體在影像作品中品讀中國故事,領略民族精神。
三、結語
總的來說,“工匠”題材影像在媒介藝術的傳播表達中,體現出濃重的文化記憶色彩,反映出典型的中國式審美追求。這種審美追求在當下新時代的社會語境內,使得“工匠”題材影像具備了重要的影像傳播價值與社會傳播意義。從這個角度上來說,影像媒介中的“工匠”題材表達已經成為當下的一個現實性命題。同時,作為民族美學的影像化實踐,對其題材影像的建構又是一個歷史性的文化使命。只有多向度地進行題材影像的范式建構,并在人物形象、影像內涵與題材敘事之間相互形成多元互動,才能真正講好中國故事,播好時代之聲。基于此,中國“工匠”題材影像最終才能真正起到傳播中華文化、弘揚民族價值觀念的重要媒介意義。
注釋:
①李娟.影像媒介敘事中的民族集體記憶建構——以四部“南京大屠殺”題材的電影為例[J].中州學刊,2013(09):166-171.
②[德]阿萊達·阿斯曼.記憶中的歷史:從個人經歷到公共演示[M].袁斯喬,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7:132.
③李娟.國家文化形象的影像話語建構與傳播——以張藝謀及美國電影作品為例[J].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05):168-172.
④李娟.新世紀中國主流電影的敘事與國家形象建構[J].中州學刊,2015(11):157-162.
⑤劉繼南,何輝.中國形象:中國國家形象的國際傳播現狀與對策[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6.
⑥賈磊磊.重構中國主流電影的經典模式與價值體系[J].當代電影,2008(01):21-25.
⑦周素文,王瑩,夏妙月.和諧話語分析視角下新主流電影《中國醫生》的人性敘事[J].今傳媒,2023(07):93-96.
⑧⑨賈磊磊.影像國家的文化認同及其現實意義[J].文化藝術研究,2008(01):186-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