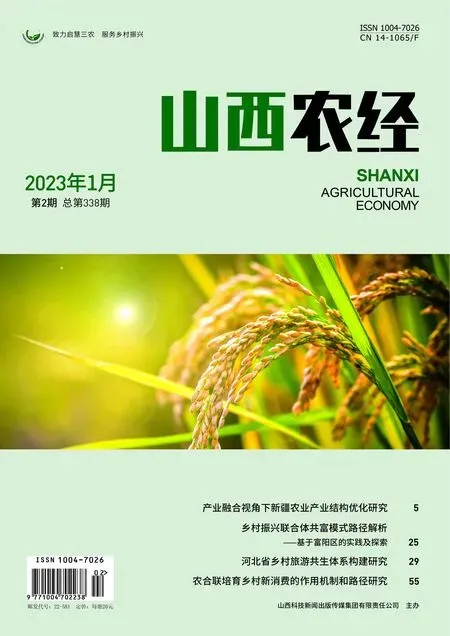河北省鄉村旅游共生體系構建研究
□徐運紅,劉亞飛,王華東
(河北工程大學,河北 邯鄲 056000)
隨著遠途游特別是出國游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日趨慘淡,短途型鄉村游迎來了發展機遇。國內學者唐獻玲(2021)判斷,隨著我國經濟社會不斷發展,鄉村旅游將逐步占領國內旅游市場。河北省作為我國農耕文明的發祥地之一,擁有豐富的“鄉村性”旅游資源。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發展“十四五”規劃明確提出,要利用資源優勢和環抱京津的市場區位優勢,主動對接鄉村振興、雄安新區、京津冀一體化等國家級戰略,打造具有較強市場競爭力的鄉村旅游產業。鄉村旅游產業的開發和運營是由多個參與主體共同完成的[1],各參與主體只有通過合作和整合資源,才能獲得最大的競爭優勢。
1 鄉村旅游共生體系的界定
不同于“回老家”式度假,現代鄉村旅游是指始于20 世紀80 年代,基于農村特有的“鄉村性”旅游資源,以當地政府、居民為參與主體,以企業化經營為運營形式,以城市居民為消費主體,沒有特定時間限制的新型旅游形式。
鄉村旅游產業具有較強的綜合性,在發展過程中,各參與主體之間形成了密切復雜的合作關系。自1879 年德貝里提出共生概念后,共生在旅游業中的應用前景引起了學界關注。鄒統釬(2006)首次提出“經營者共生”的鄉村旅游發展理念。周瑩(2018)、烏拉爾·沙爾賽開(2020)[2]、唐獻玲(2021)在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從平衡利益訴求的角度出發,提出以地方政府、旅游企業、當地村民、旅游者為共生單元的鄉村旅游共生體系,強調通過理順共生單元之間的利益關系,破除產業管理中職責不清、多龍治水的機制障礙,進而樹立命運共同體的發展理念。
基于此,文章認為鄉村旅游共生體系是指參與產業發展的各主體,通過構建特定的合作關系來實現資源共享,最終形成最大內生動力的發展系統。鄉村旅游共生體系分為鄉村旅游產業內部各參與主體之間的共生、鄉村旅游產業和外部其他產業之間的共生。文章研究的是以河北省鄉村旅游產業為代表的內部共生體系構建。
2 發展現狀
2.1 河北省鄉村旅游發展現狀
旅游產業發展決定于旅游資源的質量,旅游資源質量取決于資源種類的豐富程度[3]。截至2022 年7 月,河北省共有A 級以上鄉村旅游資源1 835 處,其中國家級鄉村旅游重點鎮8 個、重點村30 個、鄉村旅游精品路線3 條;有非物質文遺項目世界級6 項、國家級227 項、省級400 項。各地根據資源特點,結合當地市場發展趨勢,形成了不同的發展思路[4]。一是景區依托型,如保定清西陵景區以體驗“守陵人”生活為主題的帶有滿族風情的農家樂,專門接待來此實習采風的各傳媒院校學生。二是城市近郊型,緊盯短途一日游模式,以特色小鎮為主要形式,如衡水周窩村音樂小鎮、滄州郊區的明珠小鎮等。三是農業資源型,如魏縣“萬畝梨花節”、深州“密桃節”的踏青、賞花、采果等精品農業項目。四是民俗風情型,如涿鹿打造“中華三祖堂祭祖文化節”,以尋根祭祖的港澳臺同胞和海外華人華僑為主要客源。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前,河北省鄉村旅游發展迅猛,2019 年接待人數達2.05 億人次,占全省旅游接待總量的27%,綜合收入442.4 億元,年均增長超過40%[5]。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人們的出行和交通受到嚴格限制,旅游業在縮水6 成的情況下依然超過了2015 年發展水平,見表1。2021 年,旅游產業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緩和迎來復蘇,河北省13 市(含定州、辛集)1 324 家規模以上文旅企業,實現年營業收入968.3 億元,同比增長19%,同期全國平均水平僅15.9%[6];約11 300 個精品農家樂,接待游客1.15 億人次,綜合收入達323.5 億元。河北省憑借雄厚的旅游資源,積累了較大規模的市場體量,為鄉村旅游共生體系的構建奠定了現實基礎。

表1 2015—2021 年河北省旅游業發展數據
2.2 河北省鄉村旅游共生體系構建現狀
共生體系的核心內容是各參與主體之間的權責供需關系,也就是共生關系。目前在河北省鄉村文化旅游共生體系中,政府占據主導地位,通過行政職權,在為旅游企業提供公共服務和優惠政策的過程中實現監管,同時控制著當地資源的開發審批權;當地居民提供了產業發展的基礎即旅游資源、自然資源以及廉價勞動力,同時通過實際利益的獲取來評判地方政府的工作成效;旅游企業根據自身優勢,為鄉村旅游資源的開發提供了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在獲得經濟收益的同時,增加了當地的稅收,解決了當地居民的就業問題。因此,政府、當地居民和旅游企業三方為互利共贏的合作關系。游客作為鄉村旅游產品和服務的消費者,是產業質量的最終檢驗者,也是經濟效益的產生者,最終決定了產業的發展方向。綜上所述,河北省鄉村旅游共生體系是以地方政府、旅游企業、當地居民為締約三方,以游客需求和滿意度為發展走向的共生關系,見圖l。
3 河北省鄉村旅游共生體系存在的問題
3.1 共生單元呈現“散、亂、差”的狀況
分析河北省各市縣發布的經濟年報可知,除承德、正定、秦皇島等旅游資源豐富的地區外,多數地方政府因鄉村旅游開發難度大、見效慢等,目前只把鄉村旅游作為扶貧或者經濟發展的補充形式,對鄉村旅游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巨大作用認識不足,對鄉村旅游品牌化發展缺乏信心。同時,在劃定共生單位進入市場門檻時要求過低,對經營者資質的認定缺乏統一標準,加上河北省鄉村旅游共生體系的共生單元多數來源于鄉村,集約化、規模化程度不高,在缺乏統一布局規劃的情況下,呈現出“小、散、亂”的情況。比較典型的是雨后春筍般的特色小鎮建設,既造成資源浪費,又難以形成規模化的產業發展集群。
3.2 共生單元之間權責不清晰
在共生理論中,權責劃分反映了共生單元相互協作的本質規律,是維護共生體系正常運轉的基礎[7]。當前河北省鄉村旅游共生體系中,存在各共生單元因權責劃分不清晰而導致彼此“不信任”的情況。地方政府比旅游企業更關注社會效益,在旅游景區周邊公共設施建設、承擔社會責任等方面與旅游企業存在目標差異;旅游企業片面追求項目的推進速度和經濟效益,重視與政府的合作而忽視當地居民的主體地位;當地居民也會在項目開發的過程中出現“不誠信”現象,強制旅游企業提供合同之外的經濟補償,為達目的惡意阻礙施工甚至撕毀合同。
產生上述現象的原因是缺少協調產業內外關系的機制。政府制定的相關法律法規不完善,依靠旅游企業自發組織協調缺少權威性且不容易監管,導致整個行業權責不清、凝聚力不強,在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等突發情況時顯得有些手足無措。

圖1 河北省鄉村旅游發展的共生體系結構
3.3 共生模式創新性不強
各共生單元對共生理念的理解和運用程度是創新共生模式的關鍵。根據目前行業發展的形勢看,河北省鄉村旅游業對共生發展中“1+1>2”精髓的認識不成熟,鄉村旅游開發限于共生單元之間資源的簡單疊加,導致現有的共生模式創新性不足,旅游產品重復率較高。
目前河北省鄉村旅游產品中,休閑農業、農家樂占49.6%;旅游項目體驗套路雷同,多以民俗表演和吃農家飯開始,以采摘瓜菜和推售土特產結束,難以滿足人們對高品質服務的要求,容易產生“曇花一現”式產業效應。在縣級區域內的鄉村旅游市場,由于缺少權威組織或部門基于共生互補理念的行為監督和發展規劃,導致各共生單元在追求急、短、快的經濟效益或政績時,各自為戰開發旅游產品,造成項目重復建設。例如,漳河沿線村鎮已建成和規劃建設的花卉型游園超過20 家,其建筑多是模仿蘇州園林風格,院內布局相似,花卉品種雷同,尚未形成既相互銜接又各具特色的漳河兩岸景觀體系。
3.4 共生環境不完善
近年來,在政策大力支持下,有利于河北省鄉村旅游發展的共生環境正在形成,但與京、豫、贛、粵等旅游強省還有差距。一是存在法規不健全的情況。當前施行的行業規范制定層級不高、約束力不強,而且部分地方政府不考慮現實情況,具體執行條款照搬其他省、市,與當地實際情況結合不緊密。二是人力資源質量不高。鄉村旅游景區地處農村,管理人員以當地居民和基層干部為主,兼職性質居多[8],旅游產業管理經驗和服務意識不足,特別是缺少醫護、導游、安保、維護等保證景區正常運轉的專業人員。三是基礎設施不完善,服務質量差。旅游公路、廁所、服務中心等配套設施不完善,服務質量較差、層次較低,已經成為掣肘河北省鄉村旅游發展的重要因素。
4 河北省鄉村旅游共生體系優化建議
要解決當前河北省鄉村旅游共生體系存在的問題,必須考慮兩個大的時代背景。一是鄉村振興戰略的推動,即如何借助國家優惠政策和資金,擴大產業規模,提升產業效益。二是后疫情時代的影響,思考游客在新冠肺炎疫情后對旅游產品需求的轉變,即如何在產業低谷期完成行業的提質升級。
4.1 完善市場結構,打造產業集群
鄉村旅游的產業集群化是由大量被視為產業集點的經營實體構建而成。根據農村環境中特有的散漫性和封閉性,只有充分發揮地方政府的宏觀調配作用,才能實現各產業集點的優勢資源互補[9]。地方政府既要利用好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發展機遇,多思善謀,做好規劃設計,爭取更多政策和資金支持,又要引導旅游企業發揮自身優勢,加大在管理理念、創新技術等方面的投入力度,加大同產業鏈上各產業的合作力度,吸引市場資金的青睞和投入,打造以鄉村旅游為基礎的產業集群[10]。
打造產業集群,提升共生單元含金量是關鍵。建議淡化產業發展的范圍邊界,在完善產業內部共生系統構建的同時,嘗試擴大共生的范圍,同當地城鎮化建設、環境整治、休閑養老、直播電商等產業聯合,吸引培養更多高質量的共生單元。
4.2 構建利益協調機制,增強行業凝聚力
隨著鄉村旅游快速發展,各共生單元之間合作深度逐步加強,意味著會有越來越多由于權責不清帶來的利益沖突。因此,地方政府要利用自身公信力發揮中間協調作用,在法律和政策允許的范圍內,建立多渠道聽取各方利益訴求的溝通機制,理順各方的權責和利益關系。
通過獎懲政策的調節作用,增強企業參與當地發展的意愿,督促其積極投身到鄉村振興中來,主動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尊重當地居民的主體地位,鼓勵企業在保潔、保安等低薪崗位外,適當提供含金量較高的崗位給當地居民,以此增加雙方的信任。
針對當地居民自身素質的提升問題,可發揮鄉村集體主義下普法宣傳的作用,允許當地居民組建行業協會,幫助他們學會有組織地同政府和企業溝通交流,以法律途徑維護自身利益,在用自身實力取得企業青睞的同時,避免因粗暴表達行為影響自身形象和當地營商環境。
4.3 創新共生模式,提升旅游產品品質
共生模式是各共生單元之間合作的關系總和,決定著共生出的產品和項目的質量。眾所周知,2003 年非典過后,旅游業曾出現過集中暴發期。隨著新冠肺炎疫情逐漸緩解,必將迎來積攢式旅游消費快速增長期。因此,河北省鄉村旅游應抓住歷史機遇,通過創新共生模式,激發出各共生單元的發展潛力,相互交融優勢資源,產生能量聚合,快速完成產品和項目的提質升級,打造一批精品力作來迎接后疫情時代旅游黃金期的降臨。
一是依托豐富多彩的鄉村文化,定位省內短途旅游市場,選擇有突出特色的鄉鎮或村統一布局規劃,樹立當地居民的主人翁意識,通過讓利調動當地居民參與積極性。二是確定企業在技術方面的主導地位,通過公開招標選定有實力的旅游企業,重點審視其文創能力和營銷能力,鼓勵旅游企業對傳統旅游產品進行供給式改良,推陳出新,開發夜間鄉村游等河北省涉及較少的消費形式。三是以求大同、存小異為合作原則,利用網絡大數據平臺,及時分析歷年客源情況,實現信息共享。建議以縣為單位,著重推廣各共生單元都能參與的營銷方式,在滿足各自發展利益的前提下,畫出最大利益同心圓。
4.4 加強頂層設計,優化共生環境
作為共生體系構建的平臺,共生環境是維護行業發展的重要基礎。共生環境涉及在法規上的頂層設計和前期大量資金投入,因此在這部分重點從當地政府的角度提出建議,見圖2。

圖2 河北省鄉村文旅業共生體系頂層設計
一是完善管理法規制度。從法律角度保護共生體系正常運行,既要跟上國家大政方針變動節奏,又要考慮當地發展實際情況,特別是本區域內旅游企業和景區當地居民的利益和接受度。二是明確人才在共生體系構建中的核心作用。建立健全人才培育機制,重點選拔培養一批高素質本土管理人才[11],依托專業院校、社會組織,搭建學者交流平臺,加大“外腦”參與力度。三是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完善包括旅游專線在內的鄉間公路,加快實施農村廁所革命,允許私企參與旅游服務區基礎設施建設和經營。搭建溝通渠道,由政府牽頭建立正規的、官方賦予一定管理權限的行業協會,通過把部分溝通協調職責轉移到協會,提升對行業的協調服務作用。
5 結束語
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共生理論在鄉村旅游研究中是完全適用的,互惠共生是實現資源整合的理想發展模式。文章引入共生理論,通過產業內共生體系的構建來發現和解決問題。鑒于基層情況的特殊性,重點強調地方政府在共生體系中的主體作用,通過完善市場結構以打造產業集群、構建利益協調機制以增強行業凝聚力、創新共生模式以提升旅游產品品質、加強頂層設計以優化共生環境等措施,促進河北省鄉村旅游共生體系優化,為實現河北省鄉村旅游持續健康發展提供理論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