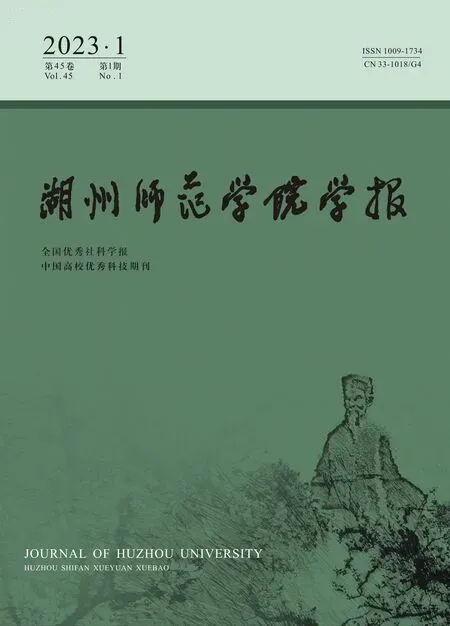俞樾《十二月花神議》考論*
程鵬瑛,張 靈
(1.淳安縣教育局,浙江 淳安 311700;2.上海師范大學 人文學院,上海 200234)
一、《十二月花神議》的創作與結構
現能搜索查閱到的《十二月花神議》,僅在清俞樾《春在堂全書》中的《曲園雜纂五十卷》及晚清蟲天子所輯的《香艷叢書》中有所收錄。
俞樾,字蔭甫,德清人。生平專意著述,先后著書,卷帙繁富,而《群經平議》《諸子平議》《古書疑義舉例》三書,尤能確守家法,有功經籍。其治經以高郵王念孫、引之父子為宗。俞樾于諸經皆有纂述,而易學為深,所著易貫,專發明圣人觀象系辭之義。著作統稱《春在堂全書》[1]13298。
俞樾在其《曲園雜纂》前記有一序,交代了其宅曲園建造之原因及該書所收文卷數與書名之簡由。《曲園雜纂序》曰:
東南底定之后,吳中花月之勝未減,曩時士大夫之宦成而歸及流寓于是者,各治第宅、啓園林,竹崦松臺,月汀星沼,極一時之盛矣。而余虱于其間,亦有曲園之筑,一勺之水,一卷石之山,猶棘林螢耀而與夫櫞木龍燭也。然吾園既小,不足以宴賓客,陳聲伎,則仍于其間,仰屋梁而著書,溫故知新,閑有所得,裒而錄之,得五十卷,每卷為一種。嗟夫。吾之力不能大吾之園,而吾之園顧能成吾之書,吾負園,園不負吾也。書成,因名之曰《曲園雜纂》。[2]
由此序可知,《曲園雜纂》五十卷中每一種均是俞樾在曲園中溫故知新時閑有所得之作,“感慨”曲園小之不能宴請賓客,陳列歌舞,卻能在空閑時仰屋梁而著書,這也不失為文人之雅興。《曲園雜纂》五十卷中前二十卷多為考據、評論、讀書之作,如卷三《達齋詩說》、卷十四《左傳古本分年考》、卷十八《讀吳越春秋》等。后三十卷既有唱和詩作,如卷四十一《吳中唱和詩》,又有日記如卷四十《閩中日記》,還有曲調如卷四十三《百空曲》等,而《十二月花神議》在該書中列為第四十四卷,也因是處在一個“雅俗”之間的位置。據此可猜測,《十二月花神議》大概是俞樾在曲園養生閑散時所創作之文。
《香艷叢書》共分二十集八十卷,書的署名作者為“清蟲天子”,書前有宣統元年輯者自序。據《室名別號索記》知“蟲天子”為烏程張延華,余則不詳。書中所收內容,特別是一些清人的著作,未見它書著錄,頗有價值,其所選內容是以香艷為主。《十二月花神議》在該書中編列在第十五集卷四,俞樾此作為何會被收錄編纂在此書中,或許是由于在文人眼中“花”多與“香艷”之事相連,又因男女花神也有其愛情相關之事。
后人對《十二月花神議》內容并無多大的考究,只是在討論花神或花朝節時會有涉及,但并未對俞樾為何作此文、如何定義這二十四位男女花神進行過細致研究。故而筆者對其想做一探析。
細看《十二月花神議》“議之上”的內容,“乃世俗所傳十二月花神,鄙俚不經,悠謬已甚”。這一句便道出了俞樾對民間所傳的各版花神的偏見,他覺得世俗所傳之花神大都庸俗不合常理,且荒誕,便想要重定花神。但《十二月花神議》主要在“議”,“議”則不可只有一人,因此該文定是在和友人商議之余而作。而在何種情況下才有閑情雅致重訂十二月花神,想必還是得先知人論世。“議之上”有交代俞樾與友人議定花神之事,即“吳下養閑翁乃議更定十二月花神,屬草稿未定,辱以示余”。這里提及了“養閑翁”,“養閑翁”為何許人也?在張劍等人所編、俞樾著的《俞樾函札輯證》中,有俞樾與其弟王同的書信,其中有涉及到“十二花客”一說:
同伯仁弟惠覽:
接手書,知興居佳勝。蘇州已得雪,未知杭州如何?湖上風冷,想未必能至小蓬萊吟眺也。十二月花客有一兩月不甚的確者,不知丁松兄所定如何?兄吳下度年,亦無佳況,記為兒童時以度年為最樂,老則徒增傷感耳。茲有寄撫藩書,求飭去。手此,敬頌年禧,并叩侍福。
愚兄功樾頓首,廿日[3]417
此信件中提到了“十二花客”,并且在后一句即問王同對十二花客的定議如何,在該札下面有提《十二月花神議》中養閑翁即為潘曾瑋,想必俞樾《十二月花神議》的創作其實是多人相互討論交流后的結果。《十二月花神議》“議之上”中說:“余適將有西湖之行,笑而諾之,未遑暇也。乃就養閑翁原議,以意參酌之。”這里所含之意則是養閑翁再議定十二月花神,俞樾僅參酌自己的意見在其中。可筆者在《俞樾函札輯證》發現,該書中收錄了其中回復潘曾瑋的三封函札,但卻并未談及十二花客,這令筆者有些疑惑。
那為何說潘曾瑋就是養閑翁呢?潘曾瑋(1818—1885),字寶臣,號玉泉,晚號養閑居士,江蘇吳縣人,大學士潘世恩之四子。著有《養閑年譜》《養閑草堂圖記》《詠花詞》《玉洤詞》等,養閑草堂為其故居。其曾孫潘景鄭在《寄漚剩稿》中有《養閑草堂圖記》跋一文,文中有提到潘曾瑋筑養閑草堂以自娛:
先本生曾祖季玉公,壯歲棄官,退隱故鄉,卜居于郡中西百花巷,筑養閑草堂以自娛。倩諸名流作圖記,觴詠優游,垂二十年。圖冊寶藏子義叔父所。[4]44
《十二月花神議》可分上下兩大部分,先以“議之上”開篇,交代寫作緣由,后再以正月至十二月為順序展示原議與俞樾后定之男花神,介紹完十二位議定后的男花神后配一位男花神的總領,此為上。“議之下”則先介紹女夷等女花神的傳說、典故等,再以正月至十二月為順序展示原議與俞樾后定之女花神。在考定花神人物中,俞樾考據學之功滲透前后,如其在《楓窗小牘》《庶物異名疏》《海錄碎事》等世人較少熟知的書中考據,作為所定花神的依據。因此看俞樾所定的各月花與神中多有令人不解之處,對世俗來說,由于過于牽強或冷僻,大部分花種及花神人物的選擇不會被廣泛接受。
二、《十二月花神議》對民間花神版本的吸收與改編
中國古代人民對神話故事有著特殊的情感,正如歷代以來的古典小說與傳說中所塑造的神仙、妖魔形象也都各具內涵。歷史人物被賦予神話色彩并會被大眾所接受的原因之一,大都是品質高潔之人會配有正面形象和良好寓意,奸邪小人則對應丑惡嘴臉。在民間,人民所推崇的風俗也由一些神話傳說或是文學作品的引申而沿襲至今,例如本文將要探討的“花神”,便有“花朝節”這一相關節日。有關花神的故事,在中國古代小說中時常見到,如《聊齋志異》《紅樓夢》《鏡花緣》中均有涉及。這些在民間頗受喜愛的文學作品,在對花神的刻畫上也都有著一定的繼承與吸收。
關于花神的起源,馮兆偉《神話與節日:神話、傳說與習俗的點線面》中說道:“花而有神,由來已久。《月令廣義》:‘女夷為花神,乃魏夫人之弟子。’”[5]114又《花木錄》:“魏夫人弟子善種花,號花姑,故春圃皆祀花姑。”[5]114這里認為魏夫人的弟子女夷或花姑為花神之源。關于“花神”所對應的人物,包括俞樾在《十二月花神議》中所定的花神及筆者搜集到的花神,民間共有六個版本,其中有男女混合版的十二月花神,也有男女各有十二位版的十二月花神,俞樾在其花神議中還定了男女各一位花神統領。
民間流傳的各版花神多少有些重復,這種現象可理解為花神的選擇存在大眾意愿與人物寓意的因素,同時也有定義者自身的情感因素。俞樾在《十二月花神議》中對花神的選擇有其獨特的“見解”。現將多版花神整理如下(見表1):

表1 各版本花神對照表
表1 (續)
由表1可見,在前五版花神中,一月主要以梅花為主,蘭花次之,且司一月梅花花神的所選之人為梅妃(江采萍)、愛國詩人屈原、北宋詩人林逋或是湯顯祖《牡丹亭》中的柳夢梅。梅妃是唐宋傳奇筆記中的人物,因在小說戲曲流傳中多受唐明皇的寵愛,且極其愛梅而為人所知。林逋則是因“疏影橫斜水清淺”之律及“梅妻鶴子”之稱為人所識。至于蘭花被當作一月主花并配以屈原為神,則可考慮蘭花品種上的原因,蘭花種類多,其中春蘭、墨蘭及寒蘭在一月有花期,屈原在《離騷》《九歌》等作品中多有涉及蘭花,如“朝搴阰之木蘭兮”“秋蘭兮青青”等,故而將屈原作為一月蘭花神。但屈原筆下多有秋蘭,因此在第三版男女混合花神中則把屈原列為司九月的蘭花神。柳夢梅主一月梅花神則主要出于湯顯祖筆下的愛情故事。其余月份花與對應的神也大都出于人物與此種花的淵源,比如花神所作的詩文、花神的生活際遇、花神的精神品格等是否與此花相關。
對應前幾版花神來看《十二月花神議》,在定花品種上,十二個月中大多數月份的花種和民間流傳的幾版一致。特殊之處僅有二月俞樾選蘭花、七月選雞冠花作為男花神之品種,可見在選花種這件事上俞樾較少獨出新意。但在定花神人物上,俞樾有其創新。如一月定何遜為梅花男花神,二月定屈平為蘭花花神,三月定劉晨、阮肇為桃花男花神,以及五月至七月、九月至十二月的花神選定。這幾位花神都是在民間流傳較少的,而俞樾與其友人商定花神的依據也多有文人學者踹弄學識之跡。
由《十二月花神議》“議之上”所云內容可知,俞樾以意參酌養閑翁十二月花神之定的手法大致不離詩詞經典。其對男女花神的議定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種:
一是以前代詩詞所載之事為選神依據。如正月梅花花神,養閑翁原議為林逋,因其所傳久矣。然俞樾卻云“考梁何遜愛梅成癖”,并在其后又附上杜詩,稱唐以前言梅花事,所艷稱者,固無如何水部。又提宋趙蕃詩“梅從何遜驟知名”,認為林逋為何遜的后輩,固當以何遜為司正月梅花之神。二月選蘭花,定男花神屈平。“奉屈子為神,則固滋蘭而又樹蕙者,接芳錯芬”化用了屈原《楚辭·離騷》中的“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歷來屈原與蘭花形象交織,文人又常以“蘭章”喻詩文之美,故定屈原為司二月蘭花之神頗有道理。原議司四月芍藥花為韓魏公主,但因自唐以來有“牡丹花王,芍藥花相”之說,俞樾改為牡丹花,而以謫仙為之神。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韻》有“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6]1629,稱李白為“謫仙人”,又因李白曾作三首《清平詞》,詞出唐玄宗與楊貴妃在宮中觀牡丹花一事。由此來看,俞樾定李白為四月牡丹花神也有其道理。再看前五版男女花神,有三版定四月牡丹花神為李白,概緣由如此。黃庭堅于《出禮部試院王才元惠梅花三種皆妙絕戲答三首》卷首有對蠟梅名稱的說明,蘇軾的《蠟梅一首贈趙景貺》也是寫蠟梅的佳詩,蘇黃二人對“蠟梅”一名的改用有一定的起始作用,故而俞樾定蘇黃為十二月蠟梅花神也有其理。
二是以史傳、志怪小說、詩詞兼考作為選神依據。如養閑翁原議司三月桃花男神為東方朔,但俞樾卻覺東方朔僅是愛桃之實而并非愛桃之花,故改定為劉晨與阮肇,此二人是東漢傳說人物,有艷遇之說,劉義慶《幽明錄》曾有記載,《幽明錄》乃是志怪小說集。五月之花世俗多選石榴花,花神多定鐘馗,概因石榴寓意多子多福,五月又處端午之時,陰邪之氣較重,而鐘馗善捉鬼,故被世俗選為五月花神。但養閑翁原議五月石榴花神為博望侯(張騫),因其出使西域得此種子回國,但俞樾考《博物志》知張騫并非從西域僅帶回石榴一種,還包括胡桃、蒲桃諸種,因此他覺得不能專之。故而轉選《舊唐書》中記載的孔紹安,因其有詩《侍宴詠石榴》一首。俞樾將孔紹安作為石榴花之神,實是有意來祭奠孔紹安。六月原議周敦頤為蓮花神,卻因其從祀尼山而不能盡花神之事,便以《南史·庾杲之傳》中韓偓與趙嘏二人詩中所贊頌的愛才士之人王儉代之。謝靈運雖有“初日芙蓉”之目,但也不過是在詩中所談論,并非事實,俞樾故而不取。七月原議鮑照因其賦作而定為秋葵花神,但又考《楓窗小牘》及其他詩歌,古人重雞冠花,以雞冠花目為后庭花,憐其系興亡,擬七月改用雞冠花,以陳后主為之神。陳后主的《玉樹后庭花》被稱為亡國之音,俞樾因憐陳后主以風流亡國,而以花賦予情思,配以花神補其“遺憾”。
三是以約定俗成或代名為選神依據。八月桂花男神為郄詵,或因郄詵曾有舉賢良之策且自視“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之說。九月菊花男神為陶淵明,大概因其詠菊多有彩,人菊性相近。石曼卿為十月芙蓉花神,概因其死后有成為芙蓉城城主的傳說。八月至十月花神論者均如原議,或是約定俗成且多為世人所接受之故。
在“議之下”的開頭一段,俞樾又云:“因亦就養閑翁原議,參酌之。以唐宮十眉圖,當羅虬九錫文焉。”唐宮里的十眉圖即為眉妝圖,據宋高承《事物紀原》引《雜五行書》:“朝宋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臥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額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經三日洗之乃落,宮女奇其異,競效之”,因故稱之為“梅花妝”或“壽陽妝”。因此,俞樾在定正月梅花女神時以《海錄碎事》中記載的壽陽公主與梅花之事為理。羅虬的九錫文即《花九錫》,文收錄在宋·陶谷《清異錄·花譜》中,該文雖短卻有著較為完善的插花理論。《花九錫》以“花”相襯,有花之影,多有可借鑒之處,難怪俞樾會提及羅虬文。
原議二月梨花,花神定謝道韞。但在定女花神時需考慮與花相關的藝術與傳說,又《釵小志》云:“阮文姬插鬢喜用杏花。”故二月選阮文姬為杏花女神。至于三月定桃花神息夫人、十月定薔薇花神麗娟均為俞樾允協于原議,概息夫人用情至深,后人建有“桃花夫人廟”之故。五月考《北齊書·魏收傳》所載魏安德王妃李氏之母宋氏薦二石榴于帝一事,以石榴多寓子孫興旺,因此定魏安德王妃李氏為石榴花神,有史證之事故較傳奇小說多為可信。
認為梨園傳唱西子采蓮之事久而化雅為俗,此即為俞樾棄西施為六月蓮花花神之因,轉而選晁采為神,僅是因欽定《全唐詩》有晁采與并蒂蓮一事,世間少有知者,定其為神也可為蓮花添一段佳話,但多以罕見之人與事來議卻難免有傷雅之態。
選擇歷史傳奇與筆記小說所載之事。如四月薔薇花神定麗娟,事見《賈氏說林》黃金買笑之典故;五月榴花以石醋醋為之,事出《博異志》;九月茱萸以賈佩蘭為花神,用《西京雜記》事;十月芙蓉花神定飛鸞與輕鳳,事見《杜陽雜編》。俞樾雖鉆小學,但在經典之外選傳奇與筆記小說之事來說理,難免有失大家之風。
俞樾對園藝相關古籍有所涉獵。如《花史》云李玉英采鳳仙花染指甲,韻人韻事,可作為七月備用之花與神。十一月山茶花神定楊太真,可考清代陳淏子《花鏡·花木考類·山茶》:“楊妃茶,單葉花,開最早,桃紅色。”又《廣群芳譜·花譜二十·山茶》:“張新《楊妃茶》:‘曾將傾國比名花,別有輕紅暈臉霞。’”十二月水仙花定梁玉清,按《瓶史》云:“水仙神骨清絕,織女之梁玉清也。宜即以梁玉清主之。”陳淏子的《花鏡》、汪灝等人的《廣群芳譜》、袁宏道《瓶史》、吳彥匡《花史》均是有關花卉或園藝之書,俞樾選此三種作為選花神之由,有新意但也有炫技之嫌。
俞樾在選古代才女為花神時,似乎也有考慮疏漏之處。八月考《唐書·太宗徐賢妃傳》有《擬小山篇》,因題指定為《離騷》,故而內容離不開幽巖、桂枝等與屈原相關的意象。但宋代李清照也有詠桂花之作,如《鷓鴣天·桂花》“暗淡輕黃體性柔”[7]892,此作將桂花之色香定位得當,遺憾屈原對桂花不甚了解,在《離騷》中也無贊美桂花之句,按俞樾選徐賢妃為八月桂花神之由,李清照也應入選。再看九月花神所定晉武帝左貴嬪,僅因九月不提菊花終有遺憾,左貴嬪有菊花一頌而封,卻未考慮到左貴嬪也有《芍藥花頌》《郁金頌》。《芍藥花頌》雖僅在《御覽》一百四十五引《左貴嬪集·目錄》,但《郁金頌》在《藝文類聚》八十一有存[8]146-147。至于《菊花頌》,其作者有爭議,《初學記》二十七存“英英麗質,稟氣靈和。春茂翠葉,秋耀金華”[8]146-147。按《藝文類聚》八十一以為傅統妻辛氏作,未知孰是。由此可猜想,俞樾選左貴嬪為九月菊花花神之由,一是早聞此《菊花頌》而卻未注意到左貴嬪還有其他頌花之作,二是在選此《菊花頌》時對所收古籍的考證有疏漏之處。
至于原議并無總領群花之神,而俞樾卻有意定之。佛、道之圣兼顧是俞樾在定群花總領時的一個關注點。男花神總領定佛教迦葉尊者,女花神總領定道教南岳魏夫人。迦葉尊者因其有“拈花一笑”而被視為佛心相印之選,于塵世之事一以貫之。魏夫人之事可見正史《南史·鄧郁傳》,《庶物異名疏》中云花神女夷是魏夫人之弟子,以魏夫人作為群花之神,花神弟子均歸其統攝,也就不用懼怕神話傳說中的“封夷”(風神)或是妖精“十八姨”。《聊齋志異》中有關風神花神的一篇《絳妃》,俞樾對此或許也有借鑒。
三、花神議下所反映的文人審美情趣
世人皆愛美,圣人亦如是。而如何定義“美”,則與美之定義者的審美情趣相關。莊子以道為美,中國古代美學還以心靈意蘊的物化為美,以儒家道德的物化為美,實即以主體心靈意識的對象化為美,如“花妙在精神”之類[9]101-107。理學家朱熹對“美”存在的根源問題也有其經典表述。明代是一個反叛理學、重新為情欲伸張權利的時代,提出以“情”為美。清代是一個實學昌盛的時代,以“道”為美與以“情”為美、以“心”為美與以“文”為美多元交匯,相互兼顧[9]101-107。
清代中葉興起儒學新思潮“乾嘉漢學”。“實事求是”是乾嘉學者所共同尊奉的治學理念,主張將義理與考據相結合,遵循漢代經學研究軌儀。而俞樾作為樸學大師,多受乾嘉學派治學理念的影響,因此其審美情趣在根本上也就有“考據學”的影子。研究通俗文藝,俞樾也是以考據家特有的方式進行。如《小浮梅閑話》和《茶香室叢鈔》就是他這方面研究成果的匯集。本文考論的《十二月花神議》,對花神的選擇與花品種的選擇也是如此。
尚雅是文人審美的一個普遍特征,文人不屑于追求世俗喜好,而對古意情有獨鐘。而崇古的背后,彰顯的是文人的雅好與對世俗趣味的鄙視[10]17。
袁宏道在其《瓶史序》中對“花”之藝術、“花”對文人雅士的意義,以及作此《瓶史》的原因做了交代:
夫幽人韻士,屏絕聲色,其嗜好不得不鐘于山水花竹。夫山水花竹者,名之所不在,奔競之所不至也。……嗟夫,此隱者之事,決烈丈夫之所為,余生平企羨而不可得者也。幸而身居隱見之間,世間可趨可爭者既不到,余遂欲欹笠高巖,濯纓流水,又為卑官所絆,僅有栽花蒔竹一事,可以自樂。[11]
對于如何選擇花卉及插花的美學原則,袁宏道在《瓶史·花目》中有言,其中又以《詩·大雅·蕩》“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來說明。俞樾在定義《十二月花神議》的十二月女花神梁玉清時,便有借鑒袁宏道的《瓶史》。
從古至今,文人詩詞賦作中有關“花”之作品數量浩瀚,情感寄于花身,由花而出則成花語,從而也就賦予了花各種寓意。觀俞樾一生,“花”的影子時常出現。
俞樾進京赴試時,曾國藩任主考,詩題為“淡煙疏雨落花天”。俞樾寫出了“花落春仍在”的驚人之句,曾國藩深為賞識,列部試第一名[12]234。俞樾蘇州寓所主室“春在堂”之名概就由此“花落春仍在”之句演繹而來。俞樾之妻文玉在得知俞樾部考第一后,在其信中回了一首與“花”相關的詩:“耐得人間雪與霜,百花頭上爾先香。清風自有神先骨,冷艷偏宜到玉堂。”加之俞樾故居曲園之景,必少不了花草古木,石林流水。《俞樓雜纂序》中云“廣栽花木,小有泉石”,此處也提到了花木與泉石,可見“花”對于俞樾來說是意義非凡的。《春在堂詞錄》中有涉及“花”之詞,如:
蝶戀花·題蒯子范太守行看子
大好梧桐庭院里。修竹娟娟,幾席涼于水。掃地焚香閑坐此,韋蘇州后先生矣。老帶莊襟誰得似。一片冰心,寫上云藍紙。看取方池清見底,亭亭立者花君子。[13]
金縷曲
花信匆匆度,算春來,瞢騰一醉,綠陰如許。萬紫千紅飄零盡,憑仗東風送去。更不問,埋香何處,卻笑病兒真病絕,感年華,寫出傷心句。春去也,哪能駐。 浮生大抵無非寓,漫流連、鳴鳩乳燕,落花飛絮。畢竟韶華何嘗老,休道春歸太遽。看歲歲、朱顏猶故,我亦浮生蹉跎甚,坐花陰,未覺斜陽暮。憑彩筆,綰春住。[13]
前一首提到了“花君子”,后一首詞提到了“花信”,均與花有聯系。花中四君子是梅、蘭、竹、菊;關于“花信”,南朝宗懔《荊楚歲時說》中有“始梅花,終楝花,凡二十四花信。”歷來與花信相關的作品有《浣溪沙·十二花信》《十二花信詩》。對比十二花信之花,俞樾在《十二月花神議》中所選的花種除了六月蓮花、七月玉簪花及雞冠花與十二花信之花有所不同,其余月份的花種都是相同的。《十二月花神議》中花種的選定或許也受到了十二花信的影響。
在俞樾的友人中,潘曾瑋是值得注意的一位,筆者發現俞樾為潘曾瑋的詩文集題過名,如《自鏡齋詩鈔》《自鏡齋文鈔》及《詠花詞》都有“俞樾題”或是“曲園居士俞樾題”等字或蓋的印章,這說明二人關系甚好。前文提到的養閑翁即是潘曾瑋,《十二月花神議》乃經二人或多人商議后成型,由此可知潘曾瑋對“花”定有了解,其也有自身的審美情趣。試看《自鏡齋詩鈔題詞》:
自鏡齋詩鈔題詞
冰雪聰明厭綺羅,自然吟詠葉天歌,清能澈骨豪逾靜,淡欲無言少己多。
余事尚能籌組練,憂心何術挽江河,詩懷想共新春展,開到庭梅第幾窠。
讀玉洤居士《自鏡齋詩》奉題一律。時同治乙丑初春,小住吳門金太史巷,吳平齋之抱罍室,上元前后大雪不得出,今日二十,似有晴意,道州蝯穸何紹基草齋中,梅花磊落而英姿多,故有末句。[14]
題詞中提到了吳平齋與何紹基二人。吳平齋(1811—1883),字少甫,晚號退樓,工書畫篆刻,書學顏真卿,善畫水山、花鳥,篆刻宗秦漢,功力深厚。何紹基(1799—1873),字子貞,別號東洲居士,晚號蝯叟。通經史,精小學金石碑版。書法初學顏真卿,尤長草書。吳平齋與何紹基二人在書畫以及篆刻碑刻上都有一定的造詣,而潘曾瑋與此二人交友,想必原因之一便是三人的情趣相似。
試賞潘曾瑋幾首與“花”相關的作品:
詠白桃花
昨夜東風露井旁,輕寒初換舊霞裳。仙資不與劉郎識,素面偏宜虢國妝。
柳絮盈盈春有淚,棃云漠漠夢俱涼。深情千尺隨流水,洗盡嫣紅也斷腸。[14]
浣溪沙·題簪花第二圖
紅玉豐姿碧玉年,好花初放月初圓,不矜雕飾出天然。
可有素心諧鳳侶,休將幽怨讬鹍弦,靈犀一點屬誰邊。[15]
潘曾瑋幾首有關“花”的作品,大多是在與友人宴飲時所作,友人們在暢談古今時又借賞花來傳達情感。此外,作詩詞時往往或所選之地有花,或是景中無花但心中有花,花之雅趣無處不在。如:
四月十二日艮庵主人攜尊三松堂賞婆羅花續七老之會順之兄即席賦七律二首
即次其韻
清和天氣獲恢臺,相約看花挈榼來。華頂佛香剛照座,耆英高會許同杯。
一百五日韶光過,三萬六千懷抱開。此是人生行樂事,年年七老幸叨陪。
宗風何必問誰家,不賞尋常優缽花。主客一時能脫灑,風塵當日悔粉葩。
閑中真樂應無盡,靜裹長生詎有涯。酒國詩壇休冷落,后期觴詠興猶賒。[14]
齊天樂·詠白秋海棠和竹樵方伯(節選)
珠簾半卷西風裹,娉婷最憐嬌影。籬角叢叢,墻陰脈脈,素質天然幽靜。冰魂睡醒,看一種柔情,淡妝臨鏡。凈洗鉛華,翠屏金屋夢俱冷。
滿江紅·庚辰三月廿又七日許星臺方伯招同王耕余蘇伯庚汪川如費幼亭彭南屏
諸君子賞牡丹即席填此(節選)
莫道春闌,還勝似、艷陽芳序。人識是,使君高會,德星重聚。賢擬竹林陪嘯詠,地臨薇省聊簪履。況庭前、開偏牡丹花,留春住。[15]
從上列的幾首詩或詞題可以看到潘曾瑋的部分交友圈,其中有艮庵主人、竹樵方伯、王耕馀、蘇伯庚、汪川如、費幼亭、彭南屏等人,這些人多數是有官位的。竹樵方伯、費幼亭等人與俞樾也有所交往,俞樾還曾寫過《長壽仙·壽竹樵方伯六十》等詞。因此從潘曾瑋的交友活動中還能隱約了解到俞樾的交友圈。
詩詞中有提到婆羅花和優缽花,此兩種花均與佛教文化相關。《大智度論》等佛經中有關于婆羅花的記載,《大藏經》中有“身體香潔如優缽花”等故事的記載,而潘曾瑋及其友人相互唱和時談及這兩種花,說明在他們的交友圈中有信佛之人,或是他們與佛僧多少有所交往。對于自然之花,則有提到白桃花、白秋海棠、牡丹花等。自然之花與佛教之花在潘曾瑋詩詞中的出現,或許可視為其對于生活之樂與人世之艱的兩種態度。
總而言之,“花”在俞樾及其文人圈子中是必需品,閑時有賞趣,唱酬時有雅趣。因此,《十二月花神議》的創作與成型也或多或少彌漫著文人交游唱和的閑雅趣味。這種審美情趣不同于莊子的以“道”為美,不同于朱熹對美的追根溯源,也不同于明代以“情”為美,轉而注重多元交匯、相互兼顧之美,同時在乾嘉漢學的影響下,對美的考證也有一定的時代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