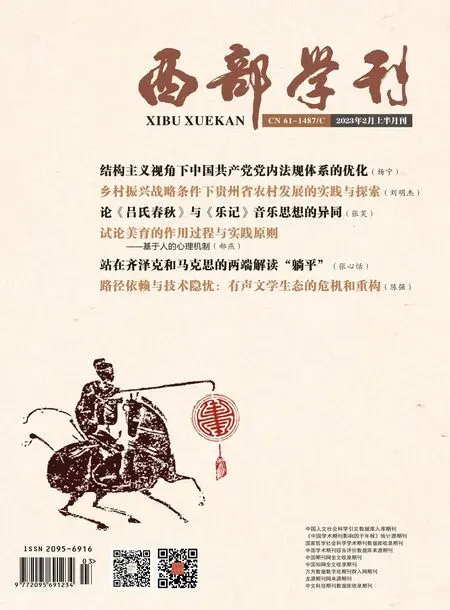孫中山的民生史觀及其局限性芻議
粟 凱 龐 楠 姚思泉
孫中山是中國近代史上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其民生史觀從哲學角度對民生進行了新的詮釋。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讓身處困境之中的孫中山從馬列主義中發現了新的希望,于是在1924年他對其“三民主義”思想進行了新的詮釋,重點強調“歷史的重心”是“民生”。這一新的詮釋在后來被稱之為是孫中山的“民生史觀”。從哲學基礎上看,孫中山繼承中國傳統哲學中“太極”的宇宙論以及“知行關系”的認識論,以近代西方進化論為核心,具有可貴的唯物主義偏向性;從主要內容看,注重民生,強調民生是歷史的重心,將民生視為社會進步的根本動力,這種詮釋,使得其民生史觀具有了認識世界以及認識社會規律的方法論意義。然而,由于孫中山對唯物主義的認識和理解不夠深入導致了英雄史觀的偏向性,貶低了人民群眾的覺悟以及主觀能動性。
一、孫中山民生史觀的哲學基礎
孫中山十分關注和重視作為歷史主體“人民”的地位,他的民生史觀的產生有豐厚的哲學基礎。在孫中山看來,于國家的政治層面,統治者要將“養民”放在突出位置,認為是否重視“養民”關系到國家的興盛、政權的穩固與否等。這一觀點契合中國古代儒家的政治思想,如《尚書·五子之歌》中的“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孟子·離婁》中“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等儒家治國思想。在孫中山的民生史觀中能發現他關于未來美好社會的一種設想:“所有人民之衣食住行四大需要,國家皆有一定之經營,為公眾謀幸福。至于此時,幼者有所教,壯者有所用,老者有所養,孔子之理想的大同世界,真能實現。”在認識論方面,孫中山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哲學中“知行”關系的觀點,在現實需要的基礎之上對它進行了新的詮釋。
(一)宇宙論
在宇宙論上,孫中山一方面繼承了中國哲學中的“太極”觀念,并從唯物主義角度進行了新的詮釋,認為“太極”是世界的原初物質,另一方面他受到西方近代自然科學進化論的影響,將宇宙、生命及人類社會分為三個階段:物質進化之時期、物種進化之時期、人類進化之時期。這三個階段的劃分,關系到人類起源和生命起源的問題,在哲學界長期以來就是科學的唯物主義與宗教唯心主義兩個不同派別斗爭和爭論的一個基本問題。孫中山根據生物進化論的觀點,通過對人類起源與發展的三個階段的劃分,表明地球處于并將長期處于自然演進的過程中,人類只是自然演進在漫長而又悠久的歲月之后出現的。這是具有濃厚唯物論和無神論色彩的觀點。
物質進化之時期,孫中山認為作為原質的“太極”運動生成電子,無數的電子在運動的過程中相互吸引而凝聚在一起,形成所謂元素;無數的元素結合在一起形成了所謂物質;最后,地球的形成正是無數的物質聚集。在這里他是肯定物質作為一種世界的原初物質是先于意識的,具有明顯的唯物主義色彩,體現著唯物主義一元論的宇宙觀。
物種進化之時期,孫中山將西方近代自然科學發現的生物基本結構細胞創名為“生元”,據此進一步提出“生元說”,認為生物之原始為“生元”,即細胞,“生元說”肯定生物進化由低級到高級的演化順序,進而從根本上否定“神創說”。他在生命現象和精神現象的問題上不可避免地表現出時代的局限性,未能正確地理解精神或者意識是人腦的一種特殊物質機能以及對客觀世界之反映的一種產物,故而他并不能正確理解物質與意識的關系問題。
人類進化之時期,孫中山認為這一時期是物種進化的終點,是人類之自身進化階段,在“生元說”的基礎上否定了“神創說”,并將這種反對神權的認識與其革命思想相結合,強調“神授之君權”必將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所戰勝。在否定君主之政治權力是神授的基礎上,必然將目光轉向“人民”,在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時發表的宣言中可以看到,他明確提出“國家之本,在于人民”,這種轉向從根本上來說就是要把原有的以“君主”為中心變為以“人民”為中心。
(二)認識論
發生于1913年的癸丑之役亦即“二次革命”的失敗,給革命黨人造成了不利的影響,有的人產生了“紙墨之力終究不如刀槍之靈”的感慨,這反映出革命黨內部出現了關于“知之非艱,行之維艱”的錯誤認識,事實上關于“知行”關系的討論,正如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關于物質與意識之間關系的討論一樣,一直都是中國哲學中認識論所關注的重點,只是中國古代哲學家往往更關注道德的體悟與實踐。
孫中山在跳出中國古代哲學家關于“知行”關系局限的同時,針對當時的現實情況,對“知”與“行”賦予了新的理解。在孫中山的新解中,“知”不再是道德的體悟,而是用一種理性思維形成的對客觀世界的一種認識;“行”則是指范圍廣闊的人類活動,包括社會生產、科學研究、日常生活及革命活動等。基于這一新的理解,孫中山對知行關系進行了新的探討,提出“行先知后”的觀點,這一觀點符合唯物主義關于實踐決定認識的觀點,具有現代認識論的特點。據此孫中山將人類“知行關系”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不知而行(認識始于實踐);行而后知(實踐得到的經驗可上升為理論認識);知而后行(理論認識可以指導實踐)。
基于其“行先知后”的認識論原則,孫中山指出“知難行易”,針對當時革命黨內部關于“知之非艱,行之維艱”的認識,強調“行之非艱,知之維艱”。其內涵一是如“知行關系”發展的第一階段“不知而行”所說明的不知亦能行,證明行易于知;二是雖然“行而后知”,但如不思考,則行亦無知,證明知難于行,同時強調“知而后行”,即用思考后得來的理論認識指導實踐則事半功倍。這一認識肯定了正確認識的來之不易,但過分夸大“知難”,而這種夸大導致孫中山根據經濟學分工原理而提出“分知分行”的觀點,這實際上是將人進行等級劃分,認為這世界有人天生圣賢“先知先覺”,有人愚笨“后知后覺”,更有人昏昧“不知不覺”,所以在社會歷史的發展過程之中,就是由少部分的“先知先覺”者,預先對社會問題想出來許多辦法,帶領著“后知后覺”者與“不知不覺”者去推動社會歷史的發展,人民群眾很重要,但如果沒有“先知先覺”者的領導,人民群眾就無法自覺推動歷史的發展,這一劃分隱含著“英雄史觀”的傾向性。
二、孫中山民生史觀的內容
孫中山的民生史觀具有豐富的內容,根據建立在西方近代自然科學進化論基礎之上的宇宙論,他認為物質是進化的、物種是進化的、人類亦是進化的。這種對于“進化”的認識成為孫中山民生史觀的重要內容之一,但是客觀來看,孫中山民生史觀的主要內容是他對“民生”的理解。關于民生,孫中山是這樣說的:“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眾的生命。”[1]167從這段話中不難看出在孫中山這里“民生”首先是一個時代的政治經濟中心,其次它體現了人們渴望生存的訴求,正是這種訴求推動著社會的發展。因此可以將孫中山民生史觀的主要內容概括為兩點:“民生”是“歷史的重心”;“民生”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
(一)歷史的重心
在這一時期孫中山之所以提出并強調所謂“民生”是“歷史的重心”,正是因為在當時的社會中所流行的唯物史觀在“歷史的重心”方面所提出的相關理論,在他看來,唯物史觀中“物質”才是歷史的重心之觀點是錯誤的,究其原因是因為孫中山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淺嘗輒止,他沒有看到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所構成的生產方式的變革才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因”[2]。他直觀地認為“馬克思以物質為歷史的重心是不對的,社會問題才是歷史的重心,而社會問題中又以生存為重心,那才是合理”[1]176-177。因此,在孫中山當時的認知中,生存是社會問題的重心,社會問題是歷史的重心,于是經過推理,所謂民生問題,其實質就是生存的問題。
既然民生問題的實質就是生存的問題,那么對于所謂“民生問題”的理解和解決,就不能偏重于道德、感情層面了,要從經濟層面著手,解決民生問題的實質,也就是滿足生存的需要。在這種理解的基礎之上,孫中山認為人類生活的程度,在文明進化之中,可以分作三級:第一級是需要。人類的需要得不到滿足以至于不能生活,或者是能得到部分需要但不能充分滿足,也只能是半死不活,因此他認為需要的滿足是人生存所必須的。第二級是安適。安適是在人類需要得到充分滿足的基礎之上去追求安樂、舒適。第三級是奢侈。奢侈是在安適的基礎之上的極致追求。在孫中山看來,解決民生問題不是要解決“安適”或者“奢侈”,而是解決人類生存所必須的“需要”。
(二)社會進化的原動力
孫中山認為“民生”體現了人們渴望生存的訴求,也正是這種訴求推動著社會的發展,他說:“古今人類的努力,都是求解決自己的生存問題;人類求解決生存問題,才是社會進化的定律。”[1]177孫中山的民生史觀首先是肯定社會進化的,并且在他看來,這種進化是一種必然的趨勢,而他在這里提到的定律,事實上也就是規律的意思,是事物在變化發展的過程中共生共長的關系,這也是某種必然的趨勢。在這里他的思路是:“人類只有不間斷地求生存,社會才有不停止地進化。而這種不間斷進化的根本原因,也就是人類不間斷之求生存。
在孫中山看來,地球處于并將長期處于自然演進的過程中,不僅自然界處在這樣一個不斷演進的過程中,人與人類社會也同樣如此,是一個由簡入繁、由低到高,連續且不間斷發展進化的一個過程。他用帶有濃厚進化論色彩的標準把人類史由古及今進行了四個時期的劃分:“第一時期,人與獸相爭,非是用權,用氣與力。第二時期,人與天相爭,乃是神權。第三時期,人同人相爭,國與國相爭,此民族與彼民族相爭,乃是君權。及至今日之第四時期,于國內相爭,人民與其君主相爭。在這一個時代之中,簡而概括則為善人與惡人相爭,公理與強權相爭。及至今日之時代,民權漸生且日益發達,可稱作民權時代。”[3]
孫中山還提出:“人類本身求解決自己的生存問題,才是社會進化的定律。”這一觀點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唯物史觀有著顯著的區別。在唯物史觀中,社會的基本矛盾才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而孫中山顯然是用生存欲望和需求等社會意識層面的內容取代了物質層面的社會勞動實踐,將意識層面的東西視作是“第一性”的,然后將民生歸于意識。這就否定了物質層面的社會存在決定思維層面的社會意識,也否定了生產力對生產關系的決定作用,更沒有看到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才是社會發展與進步的決定性力量。
三、孫中山民生史觀的局限性
作為時代的產物,孫中山的民生史觀毋庸置疑地受到那個時代所代表的階級以及自身認識的影響,其理論是有局限性的,這種局限性在與唯物史觀和英雄史觀的比較中表現得更為明顯。
(一)孫中山的民生史觀與唯物史觀
孫中山的民生史觀與唯物史觀的關系總是若即若離,一方面受其影響,另一方面背道而馳。針對近代中國民生問題,孫中山提出經濟上“均分地權”“控制資本”等措施,表現出他對勞動者的同情,具有一些唯物主義的特征。但是他用生存欲望和需求等社會意識層面的內容取代了物質層面的社會勞動實踐,將意識層面的東西視作是“第一性”的,然后將民生歸于意識,把人類求生存的這種“愿望”當作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從而陷入了社會意識決定論,具有濃厚的唯心主義色彩。
孫中山的民生史觀所存在的內在之矛盾,就在于他看到了歐美資本主義社會在發展的過程中所出現的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所以在一定的范圍內,孫中山認為要實現社會革命需要一定的武力。但在終極意義上他是反對“階級斗爭”的,他提出:“階級戰爭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是社會當進化的時候發生的一種病癥。”[4]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孫中山提出了“互助原則”用來取代“競爭原則”,即“階級戰爭”,具體到近代中國的國情,他認為當時的中國人都處在貧窮的階段,區別只是一般貧困和特別貧困,既然都是處于貧窮階段,因此就不需要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戰爭”和“無產專制”。這一觀點充分顯示了資產階級的軟弱性與妥協性,同時說明孫中山沒有意識到在近代中國特殊的歷史條件下,是需要采用“階級斗爭”以及“暴力革命”等手段實現“無產專制”的。
(二)孫中山的民生史觀與英雄史觀
孫中山的民生史觀事實上與英雄史觀是存在著聯動關系的,這一聯動主要基于他根據經濟學分工原理而提出的“分知分行”觀點,將人進行等級劃分。在他看來,人類文明以及世界的發展和進步,是“先知先覺”者先于社會的發展就預想出了方法推動社會的發展,并為此做出眾多貢獻;而“后知后覺”者是社會的大眾群體,先天稟賦不足,沒有創造發明能力,只能隨著社會發展的大潮;“不知不覺”者則更是需要別人的引導,不能“知”只能“行”。雖然孫中山并未對這三者的人數進行描述,但“先知先覺”者畢竟只可能是少數。在這一觀點下,少數“先知先覺”的“英雄人物”帶領著大多數的“后知后覺”者和“不知不覺”者推動歷史的發展,這一觀點與“英雄史觀”一樣,極大地貶低了人民群眾的覺悟以及主觀能動性。
四、結語
雖然孫中山的民生史觀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些歷史的、時代的局限性,但應該看到他在國家的政治層面,要求統治者將“養民”放在突出的位置,認為是否重視“養民”關系到國家的興盛與否、政權的穩固,這些觀點是值得肯定的。他強調從經濟層面著手去反思歷史、審視現實,強調統治者要關注并且解決民生問題。他以進化論為基礎,將人類社會的歷史視作是人類求生存、謀發展的歷史,對民生問題進行新的解讀和詮釋,作為一種認識和理解社會的方法論,仍然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