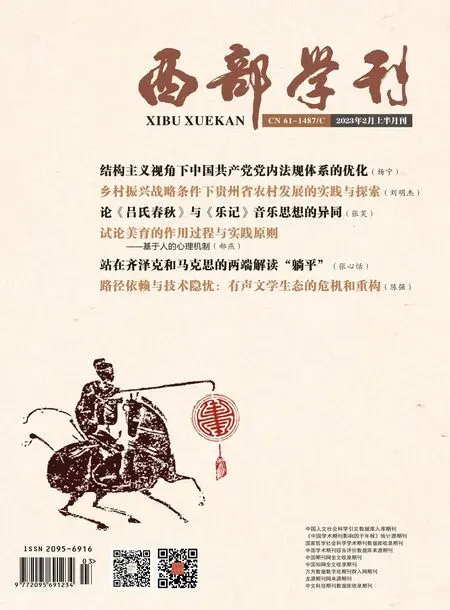路徑依賴與技術隱憂:有聲文學生態的危機和重構
陳 強
從廣義的有聲文學來看,人類自進行口語傳播活動起,所進行的以公眾為受眾的、以文字誦讀為核心的行為,都含括在有聲文學的范圍內。狹義的有聲文學所指的是音頻媒體的一個類別,以出版物或者網絡文學原文或改編內容為文字來源,以演播者單播、雙播、多播為表現形式,以有聲書、廣播劇、有聲劇等藝術形態存在的一種“市場化”的音頻產品,這也是本文所指涉的有聲文學的內涵范圍。
有聲文學的平臺發展經歷了大眾傳媒時期的廣播電臺、互聯網時期的網站和社交媒體時期的智能移動終端三個階段。有聲文學具有音頻產品的基本屬性“伴隨性”,其在社交媒體時代更能適應用戶的使用場景,在資本和技術的賦能下,有聲文學的傳播生態得以形成。但是,歷經了大眾傳媒時期和互聯網時期的有聲文學,因為作為其文本來源的傳統文學和網絡文學在“傳播媒介、創作主體、創作過程和作品文本層次”[1]上遵循著不同的邏輯,使當前的有聲文學生態形成了兩種路徑依賴:出版物有聲文學路徑和網文有聲文學路徑。前者遵循文化邏輯,以社會效益為傳播效果評價標準;后者遵循資本邏輯,以經濟效益為傳播效果評價標準。兩條有聲文學生態路徑的長期分野,是有聲文學生態的最大危機,抑制著有聲文學生態圈的生長。同時,在當前有聲文學生態的參與者之外,從事TTS(Text to Speech)即“文本轉語音”技術研發的高科技公司對于TTS的突破性進展,使有聲文學生態面臨著重構的隱憂與契機。有聲文學應該適應互聯網技術與生態的迭代頻率,以更開放的思維反思當前的路徑危機,應對TTS所帶來的技術隱憂。
一、有聲文學生態的危機:兩條路徑依賴
運用生態學原理對新聞傳播現象進行闡釋可以追溯到芒福德、麥克盧漢等媒介生態學或傳播生態學。從概念上來看,傳播生態指的是“信息技術、各種論壇、媒體以及信息渠道的結構、組織和可得性”[2],包含信息技術、傳播范式和社會行為三個維度。有聲文學生態就含括了以流媒體、大數據為代表的智能移動終端技術維度,以文字版權、音頻錄制、后期制作到平臺上載等流程為代表的傳播者音頻生產維度,以用戶點擊、付費收聽等流程為代表的傳播效果評價維度。當前的兩條有聲文學生態路徑在技術維度均依賴智能移動終端作為傳播平臺,所以這一維度的一致性較強,但在傳播者音頻生產維度和傳播效果評價維度上存在著巨大分野。需要申明的是,兩條有聲文學路徑并不是涇渭分明的,已經顯現出日益增長的交叉融合趨勢,而這兩種路徑的交叉融合是使有聲文學生態擺脫傳統路徑依賴的可能因素。
(一)以商業邏輯為主:網文有聲文學路徑
在前互聯網時期,有聲文學就開始受益于網絡文學的發展,它能夠在社交媒體時代“野蠻生長”也是由于網絡文學海量文本與海量用戶所帶來的強大驅動力。有聲文學生態與互聯網生態進行深度結合的結果就是形成了當前的網文有聲文學路徑,這一路徑遵循的“商業邏輯”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因其掌握巨量的互聯網音頻流量受到資本追逐,遵循這種路徑的有聲文學生態充滿活力;另一方面,其在傳播效果評價上以“商業邏輯”為核心思路的考量成為網文有聲文學路徑的缺陷。
1.傳播者音頻生產維度
作為有聲文學生態的音頻生產維度,是由多個階段構成的整體生產流程。從文字版權評估采購起始,分發至音頻平臺為終點,這一維度以多主體為特征。在文字版權采購階段,要對文本進行以變現能力為核心的評估;在音頻錄制階段,要考量有聲書演播者在平臺的流量,評估有聲書上線后的用戶規模。出于成本控制的原因,當前網文有聲文學對于音頻制作階段較為輕視。經過上述流程,最終生產出了網文有聲文學成品,以音頻平臺買斷版權或者付費收聽分成的形式進入到音頻平臺的分發階段。
2.傳播效果評價維度
網文有聲文學成品進入到音頻平臺分發之后,就到了傳播效果的評價階段。與大眾傳媒時代傳播效果評價的模糊性與非可視性不同,社交媒體時代的“數據屬性”使傳播效果評價相對精確,并具有高可視度。音頻平臺的社交媒體屬性為用戶提供了態度表達的網絡接口,同時用戶的收聽行為也會在音頻平臺以數據的形式呈現。網文有聲文學的傳播效果評價以數據為基準,點擊率、留言量與有聲書的營收表現呈正相關關系,音頻平臺付費收聽模式興起之后,單本有聲書的營收表現成為網文有聲文學傳播效果評價的核心標準。
(二)以文化邏輯為主:出版物有聲文學路徑
與網文有聲文學與生俱來就帶有互聯網基因不同的是,出版物有聲文學發軔于大眾傳媒時代廣播電臺的《小說連播》類節目,具有悠久的文化積淀。出版物有聲文學作為大眾傳媒時代的產物,發展到社交媒體時代后,在生態路徑上卻一直遵循著大眾傳媒時代的文化邏輯。在傳播者音頻生產維度上,考量文本寫作的深刻性、音頻錄制與制作的高藝術水準;在傳播效果評價維度上,以“社會效益”為核心考量標準,但這種以文化邏輯為主的有聲文學生態卻在互聯網生態中出現了“水土不服”的問題。
1.傳播者音頻生產維度
相較于網文有聲文學,在這一維度的生產流程上出版物有聲文學與前者基本一致,都要經歷文本版權、音頻錄制、制作、平臺分發等幾個流程。與網文有聲文學不同的是,在對文本版權的評估上,要進行以文本作品的文學性、藝術性為核心的“文化邏輯”考量。在文字版權的獲取方式上,相較于網文有聲文學的商業采購,出版物有聲文學更加多元,除商業采購外,還可以與文字版權持有方以文化項目的方式進行非盈利性合作。在國內外出版物有聲文學領域通行的模式是“出版商開始自建音頻部門,而非依賴音頻制作和發行公司從事有聲書制作發行業務”[3],文字出版機構本身就持有版權,通過自有的音頻部門或者與制作公司合作進行有聲書的生產。這種多元化的文字版權獲取方式,雖然會考量經濟成本,但在更大程度上是以文字作品的質量為基準。在音頻錄制與制作上,出版物有聲文學基本承襲了大眾傳媒時代廣播電臺的《小說連播》類節目的藝術衡量標準,使出版物有聲文學的聽覺質量總體處于較高水平。
2.傳播效果評價維度
即便出版物有聲文學在各地廣播電臺有著較長的播出歷程和較大的聽眾規模,但在社交媒體時代,音頻平臺依然是出版物有聲文學的主要傳播載體。在傳播效果評價維度上,出版物有聲文學雖然會將營收情況納入考量范圍,但考慮到出版物有聲文學在文字版權階段就沒有遵循商業邏輯,而是遵循“文化邏輯”,所以,目前出版物有聲文學的傳播效果評價以“社會效益”為核心考量標準。這種標準下的出版物有聲文學,作品質量可以充分保證,但商業元素的缺位,抑制著互聯網生態中出版物有聲文學的活力。
(三)兩條路徑割裂的破局:IP理念
一個良性的有聲文學生態應該是智能移動終端技術、傳播者音頻生產和傳播效果評價三重維度共生的關系,當前有聲文學生態兩條路徑的現狀對于有聲文學的發展所造成的傷害是巨大的,最為明顯的是商業邏輯與文化邏輯的割裂,形成了“高點擊量有聲作品藝術水平不高”與“高藝術水平作品點擊量不高”的兩重畸形現象,且廣泛存在于有聲文學領域。當前學界與業界均已經意識到了兩條路徑的割裂所引發的問題,迫切希望尋找一個能夠兼顧商業邏輯和文化邏輯的切入點,“兼具文化屬性和經濟屬性”[4]的“IP”理念就是有聲文學生態中兩條路徑加以匯流,使危機得以破局的重要抓手。作為英文“Intellectual Property”(知識產權)的縮寫,IP被移植到文化產業之后,主要指的是“一種文化產業的優質內容資源”[4],這種基于“優質”IP理念的運行邏輯,對有聲文學領域的適用會催生出深度融合有聲文學生態兩種路徑,兼顧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有聲文學作品。值得期待的是,從文本作品來看,以入選國家新聞出版署2020年“優秀現實題材和歷史題材網絡文學出版工程”的小說《重卡雄風》為代表的,具有深刻意涵和較高寫作水平的網絡文學作品層出不窮,且逐漸成為網絡文學的主流價值所在。同時,在出版物文學領域,以“2021十大年度國家IP”《三體》為代表的文化價值與商業價值俱佳的文學作品日益增加。
二、有聲文學生態的隱憂:TTS的顛覆
雖然從表層技術形態來看,TTS僅僅是將文字內容轉換為音頻內容,但當TTS技術演進到以“人工智能對人類語音樣本的深度學習”為深層技術邏輯,意味著有聲文學生態真正開始面臨AI智能傳播的深刻影響。“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簡稱AI)作為延伸平臺與技術要領,不斷改變著信息技術傳播的生態環境”[5],有聲文學生態需要直面人工智能帶來的顛覆與機遇。
(一)低水平的有聲文學:被顛覆的部分
“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是對社交媒體時代產品變革的最佳描述,任何一個產業都有可能以極高的頻率迅速迭代甚至是重構,在互聯網技術的賦能下,一種新技術的成熟可以迅速催生相關產業的變革,有聲文學也不例外。無論從商業還是文化邏輯上考量,有聲文學都不應該是簡單的“文字轉語音”,需要傾注播音員和制作人員對藝術的理解與把握。但不可否認的是,當前的有聲文學領域存在著巨量低制作水平的有聲書,這與前述的基于IP觀念的有聲文學產品形成了巨大反差。有聲文學產品從用戶直觀的體驗來看是聽覺產品,基本的藝術與技術門檻應該是存在的,但基于“音頻資產”沉淀的觀念,在成本考量等因素的作用下形成了一批藝術與技術價值較弱的有聲書。對于這部分“有聲音頻”應該理性評估其存在價值,同時應該直視臻于成熟的TTS技術將會對其的替代與顛覆。
TTS技術因其與有聲書在媒介形態的轉換上同樣遵循將文字媒介轉換為音頻媒介的邏輯,自其誕生起就對有聲文學構成了技術隱憂。這種隱憂來自于TTS技術不斷成熟和進步的狀態。早在2018年10月,微軟就發布了“基于深度神經網絡的文本到語音(text-to-speech)分析運行系統”[6],TTS技術在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的加持下,不斷對采樣音頻進行深度學習,最終的技術指向是無限接近于人類的自然語言。在有聲文學領域,最先遭受TTS技術沖擊的就是這種“低水平的有聲文學”,按照目前的技術迭代速度,使用TTS技術轉換的有聲書很快會在用戶聽覺感受上超過低水平的有聲書。這意味著這部分有聲書基于文字版權、音頻錄制、音頻制作、平臺分發所形成的生態將會被顛覆,音頻錄制和音頻制作環節將會被計算機程序所取代,因此而形成成本結構的巨大變化將引起文字版權和平臺分發環節的鏈式反應。
(二)IP化的有聲文學:差異化的機遇
如何看待TTS對于有聲文學生態造成的影響?其對于低水平有聲書的顛覆,反而成為IP理念的有聲文學迅速擴展的催化因素,對于有聲文學生態來說,TTS不是攪局者,而是在發揮“鯰魚效應”。從目前的有聲文學生態來看,雖然業界意識到了持IP理念的有聲文學是破除有聲文學路徑“雙軌化”的重要手段,使有聲文學生態可以良性運轉,但因為“成本—收益”周期較長,符合IP理念的文本作品供給不足,以及網文有聲文學和出版物有聲文學在路徑上的依賴等因素,抑制著IP化的有聲文學的生長。TTS對當前有聲文學生態所形成的實質性影響和可預期的威脅,使有聲文學生態圈的參與者意識到了IP化的有聲文學才是在未來TTS深度入局有聲文學領域之后,可以區別于TTS的唯一路徑。TTS的終極目標是無限接近人類自認語言,當TTS取代了低水平有聲書之后,是否會對有聲文學生態造成深一層次的顛覆?IP化的有聲文學基于商業與文化兼顧的邏輯,是人類在有聲文學方面的理解、情感、態度、智慧等機器無法完全模擬的因素的結晶。這是IP化的有聲文學與TTS技術下有聲書的根本差異,這種差異使前者成為有聲文學生態迭代后的發展路徑。
三、創新與融合:有聲文學生態的重構
有聲文學生態的重構有賴于技術本身的創新,以及在此技術基礎上的新傳播方式,是當前技術時代有聲文學生態的基本走向和發展路徑。
(一)創新:技術賦能的有聲文學生態
作為依存互聯網生態的有聲文學生態,其在技術邏輯上始終無法脫離互聯網“技術賦能”的因素。一是在有聲文學領域,要理性思考與接納TTS技術。TTS技術在媒介形態的轉換上遵循有聲文學從“文字到語音”的相同邏輯,這決定了TTS技術不是局外人,而是這一生態的共同締造者。當前,TTS技術對有聲文學生態良性運轉的參與行為是對低水平有聲書的淘汰,在未來隨著TTS技術的成熟,其在有聲文學中的參與方式會更加多元。二是有聲文學從本質上講是聽覺藝術,無論遵從哪種路徑,用戶的收聽體驗始終是重要考量。在音頻錄制和制作上,對于新技術的應用可以為用戶提供真正意義上的高保真、多聲道的收聽體驗,在傳播載體上“車機”用戶的主流化,也使高保真、多聲道的有聲文學產品具備了廣泛的應用場景。三是社交媒體時代有聲文學傳播平臺在音頻分發上對大數據、人工智能技術的進一步應用,可以使有聲文學產品在平臺分發階段更具有精確性,從而在傳播效果評價維度上進行得到提升。
(二)融合:有聲文學生態新物種的出現
從藝術形態來講,有聲文學是發端于大眾傳媒時代的傳統藝術形式,萬變不離其宗的是從“文本到語音”。一方面,不斷更新的技術環境和網絡文字的閱讀環境,以及有聲文學用戶結構的變化會逐漸促進有聲文學生態的優化。當低水平的有聲書被TTS取代,當IP化的有聲文學成為主流,收聽場景極佳的車機用戶在總體用戶占比中的增長,以及需要“可視化”收聽的移動端用戶的出現,會使有聲文學生態在有聲書、廣播劇、有聲劇之外,利用技術與藝術深度融合所產生的動能,催生出有聲文學生態中的新形式。另一方面,社交媒體時代“大數據”的技術基底為有聲文學面對用戶進行精準傳播提供了可能,使有聲文學生態的“內容產品能夠細分化、滿足細分的受眾需求”[7],這是有聲文學生態向下生長的空間,有聲文學以用戶為傳播目標,利用大數據手段進一步掌握用戶需求,依據細分的用戶需求,對當前以文本類型作為劃分依據的有聲文學進行“類型重構”,以用戶需求而不是文本類型為內容細分標準,使有聲文學生態向下生長出新的類型。
四、結語
之所以要從媒介生態的角度來看待有聲文學,是因為在這一領域中不應存在涇渭分明的割裂和顛撲不破的陳規濫調。有聲文學生態中遵循資本邏輯的路徑與遵循文化邏輯的路徑不應相互排斥,而應加深融合,以IP理念作為破局之道。應該認識到的是,TTS并不是有聲文學生態之外的事物,其本身就是有聲文學生態之中的一環,TTS的參與可以幫助有聲文學生態良性運轉。從媒介生態的角度來看有聲文學,是要從不斷變化的角度看有聲文學。近10年來資本的追逐、技術的賦能、入局者的熱捧,使有聲文學形成了當前的局面。對有聲文學生態危機的破除,對TTS技術隱憂的坦然面對,積極的重構有聲文學生態,是有聲文學的未來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