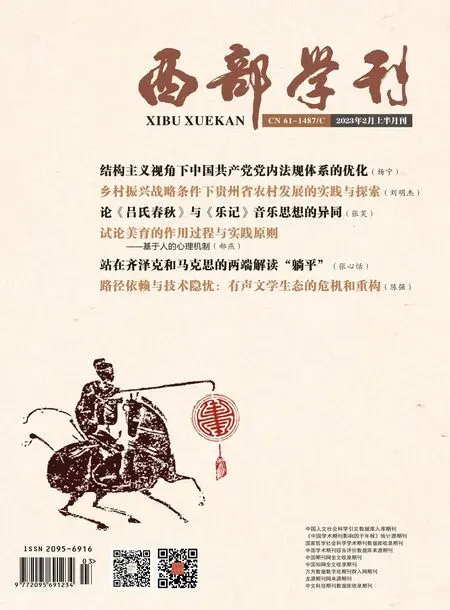論新中國成立以來戰爭題材譯制片的配音藝術
熊 雄
解放前,我國上海等發達地區的電影市場被英美影片所壟斷,解放后,人民不希望再看到資本主義國家的電影,英美影片被全面禁映。“十七年”(1949年至1966年)時期,我國一方面開始著手拍攝自己的電影,另一方面實行拿來主義,大量引進、譯制蘇聯等國的革命電影,以解燃眉之急。戰爭片相較其他類型的影片更具革命性和震撼力,可以很好地起到鼓舞人民的作用,《普通一兵》《團的兒子》等最早一批進入我國的譯制片幾乎全部都是來自蘇聯的戰爭片。可以說,新中國的譯制片事業由戰爭片開始,戰爭也始終是我國譯制片最為經典的主題,戰爭題材譯制片是我國譯制片制作水平的“集大成者”,能較為全面地反映我國譯制片配音的特點與發展。
配音質量是譯制片興衰的根本原因,配音創作是譯制片功能發揮的推動力[1]。藝術家們用聲音締造出無數譯制經典,它們的魅力跨越國界、超越時間。作為代表,戰爭題材譯制片的配音技巧和風格成熟而有影響力,探析其配音藝術的內在規律有助于為后人在譯制片上的二次創作提供借鑒。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程度的加深和綜合國力的增強,越來越多的西方影片進入我國,對我國的本土文化市場造成了一定沖擊。如何通過其配音對譯制片進行“編譯”和“轉碼”,一方面消除兩種文化間的隔閡,完成跨文化交流,另一方面展現漢語言文字的民族性和其獨特魅力,將其為我所用,實現本土化,這一課題或可從新中國成立以來戰爭題材經典譯制片的配音創作實踐中得到啟發。
一、配音腳本的跨文化轉碼
譯制片的配音體現了兩種語言和兩種文化的碰撞與交融。“碰撞與交融”可以理解為兩層含義:一是兩種不同文字語言之間的碰撞與交融,二是兩種有聲語言之間的碰撞與交融[2]。前者集中體現在配音腳本制作中對外國文化的轉碼上,后者則集中體現在配音腳本演繹中對外國文化的轉碼上。
配音腳本的重要性無需多言,它決定了觀眾所聽到的內容,也是配音演員進行創作的基礎,甚至有學者激進地認為,對于譯制片而言,腳本的重要性大于配音,譯制藝術的核心價值主要由翻譯勞動所創造,而非配音[3]。制作配音腳本的過程是一個還原、重構異國文化的過程。由于中國與影片出品國的歷史和文化背景存在著很大差異,原片中有些成語、比喻和典故無法在譯入語中找到完全準確的翻譯,因此腳本是不可能盡善盡美的。但是,新中國的電影工作者們依然對配音腳本精益求精,讓譯本盡量貼合中國人的語言和表達方式,誕生了許多令人拍案叫絕的翻譯。比如,在《普通一兵》中,蘇聯士兵沖鋒時喊的口號是“烏拉”,直譯為中文是“萬歲”,但這顯然不符合我國實際,口型也沒法對上。最終,影片將其譯為“沖啊”,這不僅更加貼近中國的現實,而且口型由開口呼變為與原片口型相同的撮口呼。
腳本既已完成,配音演員欲將譯制片配音腳本形之于聲,要做的依然是對外國文化進行轉碼,這是一個尋找、把握“中間語”的過程。譯配人員運用“陌生化”的藝術手法,在充分尊重和有效傳播外來影片的異國風情與文化特質的基礎上,將聲音呈現出一種獨特的“洋味”,語調多為上揚式,形成獨具特色的“洋調”,創造出了一種中國觀眾最熟悉、最常用,但同時又讓中國觀眾感到驚喜和略有陌生感的特別的語言風格。這種特殊的語言并不妨礙觀眾的理解,也符合影視翻譯中的翻譯原則,夾雜著文化陌生感的表達,往往使得影片中異域情調的喜劇或悲劇效果被強化[4]。比如,《虎口脫險》中指揮家的臺詞:
這個作品要按我個人的理解,/奏得還不夠奔放,還不夠慷慨激昂,要慷慨激昂,邦邦邦……現在,見鬼,膩膩膩……就像溫吞水,/好像不錯其實很糟,/很糟!
配音為了表現指揮家對演奏的不滿,同時也為了口型需要,配音演員故意加快語速,好幾個短句才有一處停頓,并且做了較多的重音處理,展現出指揮家說話時激動的情緒和對藝術執著的追求。這種處理方式巧妙地找到了兩種文化交流形式的“黃金分割點”,觀眾既從配音語言中享受到了異國風情,也得到了對自己民族語言優美形式的認同。
譯制片配音雖然無法擺脫原片文化環境對它的束縛和制約,但譯配人員充分發揮他們的想象力、創造力,在制作和演繹的過程中,對譯制片腳本進行了極為成功的跨文化轉碼,將異域文化本土化,賦予了譯制片配音不同于其他語言藝術的獨特精神氣質,在有限的創作空間里創造出無限的藝術魅力。
二、人物語言的本土化再造
配音演員一般通過控制聲音和氣息對外國影片中的人物進行本土化的人物塑造,并不斷提升技巧、加入新的思考,用語言實現本土化人物再造。回顧新中國成立以來戰爭題材譯制片配音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特點,經過長期的積累,聲音和氣息的運用水平不斷發展,逐步形成了獨特的藝術創作路徑。
在“十七年”中,譯制片配音不是簡單的語言轉換,“而是目的社會中的一種獨特的政治行為、文化行為、文學行為。”[5]這一時期的作品運用一些基本的聲氣變化方式描摹人物特點,努力探索聲音和氣息的運用,進行了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嘗試。東北電影制片廠的《普通一兵》是我國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譯制片,其最鮮明的特點就是全片都用東北話進行配音,其聲音質樸、情感真摯,片中人物就如同我們的東北老鄉一般,完全沒有隔閡之感。而《團的兒子》及其之后的影片配音則有了更多技巧性,比如調整發聲、氣息位置來改變音色、音調等,開拓了我國戰爭題材譯制片塑造多元化人物的創作思路。
“文革”時期,配音演員們開始注重多元形象的塑造與表達,對聲音和氣息的運用有了一定認識,突出不同人物的特點和區別。在南斯拉夫電影《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和《橋》中,戰士們都是地下工作者,與之前蘇聯戰爭片中熱血、激昂的人物形象不同,出于職業的特殊性和斗爭的需要,不會輕易地暴露和展示自己的真實情感。這種角色職業特點的變化也要求配音有所變化,音調和音強不能太高,音色也不能太過富于變化,說話要干凈利落、語氣堅定,更強調配音演員對聲音的控制。不僅如此,這兩部影片可以說是一部“群戲”,沒有過分突出某一人物,幾位主演的戲份和臺詞大致相同,有不少十分出彩的角色,并且人物的情感起伏和思想轉變更為明顯。這種人物形象的多元化要求配音隨之更加多元。
改革開放以來,配音演員的技術水平已臻成熟,在充分理解原片并不改變原意的基礎上加入自己的理解,用多樣化的處理方式再造人物,強化影片的表達效果。在英法兩國合拍的電影《虎口脫險》中,于鼎和尚華配音時口腔一直完全打開用以確保口腔開度和氣流量,用怪誕的聲音、浮夸的情感、夸張的技巧,將人物的特征在每句話中都進行了放大,從而成就了令人捧腹的效果。在美國電影《拯救大兵瑞恩》中,為了展現戰爭的真實與殘酷、還原戰場上的各種慘烈景象,配音時需要“聲嘶力竭”,需要刻意放大一些氣口,但是與《虎口脫險》不同,這里的一切處理要少些藝術色彩,力求真實,讓觀眾仿佛置身戰場之中。美國電影《珍珠港》雖以戰爭為背景,但主線卻是愛情,配音通過說話時對氣息細微的調整,穩中有變,輔以語氣助詞的運用和一些小氣口的處理,突出三角戀情中人物的情感、矛盾和對立。
總的來說,“十七年”時期,戰爭題材譯制片的配音略顯青澀,主要通過對音色、音調等人聲基本屬性的簡單變換來模仿原片的聲音,從而盡量還原人物;“文革”中戰爭題材譯制片的配音擺脫“稚氣”,一步步放開,靈活多變,可以根據人物不同的職業和特點進行多元化處理,嘗試構建人物,對聲音的藝術性進行了更高的追求和探索;改革開放以來戰爭譯制片配音狀態收放自如,方式大膽,聲音表現力強、氣息控制力強,用夸張渲染喜劇效果,用夸張還原戰爭場面,用夸張突出人物情感,完成對原片中角色的重構乃至超越,配音水平臻于成熟。
三、語言的差異化場景展現
戰爭片有著濃厚的時代特點。對聲音、氣息等語言外部表現形式進行控制可以有效地塑造多元人物形象,但無法做到對故事背景的生動展現。配音演員為了在聲音中展現出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時代,積極揣摩影片的文化背景,通過改變語音節奏對語言進行重新建構,展現人物所處具體環境的微觀場景和人物所處國家、所處時代的宏觀場景。
“十七年”的戰爭譯制片配音對差異化場景的展現集中體現在較為微觀的人物活動場景中,逐漸向聲音的宏觀展現進行過渡。在《普通一兵》中,所有人說話的語勢和語音節奏都是比較平緩的,《團的兒子》中人物的說話方式則有些富于變化了。蘇聯影片《列寧在十月》和《列寧在1918》則更進一步,前者中,列寧以一個革命者的姿態出現,此刻的他滿是革命熱情和一腔熱血,勵志推翻反動統治、建立蘇維埃政權,所以,白景晟為其配音時說話節奏比較快,字詞句之間聯系緊密,聽起來血氣方剛,符合這一時期俄國社會群情高漲的革命氛圍;后者中,蘇維埃政權已經建立,但是革命并沒有結束,國家內憂外患,列寧作為一個新生政權的領導者,看到得更多、思考得更多,褪去了一些青澀,多了一絲沉穩,所以為其配音的張伐較之白景晟有所克制,總體而言說話更“慢”、語音節奏更平緩了些,顯得有所收斂,更加成熟。兩位配音演員對語音節奏的不同把握反映了那個革命熱情高漲的崢嶸歲月以及列寧的改變。
“文革”期間戰爭譯制片配音對差異化場景的展現集中體現在文化場景中。《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和《橋》講述的都是南斯拉夫人民反抗德國入侵者的故事。為了展現東歐獨特的異域風情,廣為流行的“譯制腔”就成型于這一時期的作品中,為了有“洋味兒”,人物說話時的語言節奏也產生了變化。比如,在《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中,配音演員將人名“米爾維特瑪雅”中的“米”“爾”“維”和“瑪”字讀作第一聲,“特”和“雅”字讀作輕聲,每個字都是連讀,語勢呈波峰式,“維”字的上揚尤其夸張,模擬外國人說話的獨特韻味。相較之下,《橋》的“洋味兒”稍微弱了一些,片中的地名、人名等特有名詞讀法沒有那么刻意,雖然語勢也是波峰式,但聽起來稍許正常一些。
改革開放以來,戰爭譯制片配音對差異化場景的展現集中體現在宏觀的社會場景中。《虎口脫險》中,一方面,尚華和于鼎模仿法國人說話的語音節奏并加以夸張,說話時抑揚頓挫、宛轉悠揚,總是有種不急不慢的感覺,極具特點的語言風格譯出了浪漫而獨特的法蘭西風情;另一方面,故事發生在全境被德軍占領時的法國,法國人總會不顧個人安危為英國飛行員提供幫助,膽小如油漆匠這般的人物,雖然在分配任務時內心猶豫不決,說話一改平時機靈的模樣,比較拖沓、愛拉長音,但最終總是接受任務,幫助英國飛行員脫險。英國人和法國人因共同的敵人暫時不計前嫌,展現出了難得的“和諧”,這無疑是一種讓人忍俊不禁的喜劇效果,亦是一種對當時歐洲社會風貌的刻畫。《珍珠港》花了不少筆墨描寫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國人對戰爭的態度。士兵們忙著去軍人俱樂部談情說愛、享受生活,幾乎都認為戰爭不會波及美國本土,所以配音十分輕快,輕松、活潑,語音節奏無論是內部還是外部都是松弛的,字里行間中流露著對當前局勢的樂觀,美國社會“隔岸觀火”的態度顯露無疑。
四、重音與停頓:深化故事沖突
故事的沖突是影片最精彩、最關鍵的地方,需要著重展現。配音演員往往通過對重音和停頓的合理調度,讓語言的各個要素由內而外完全為影片效果服務,突出故事矛盾,將影片推向高潮。重音和停頓是譯制片配音乃至所有有聲語言創作中必須掌握的要素,對它的合理應用可以賦予語言極大的信息量,表現、強化人物的各種情感,是語言的高級應用。
有時,人物間早生嫌隙,他們的沖突往往遠非話語表面看起來那么簡單,此時配音要做的就是讀出“內在語”,突出人物間的對立。這需要配音演員將臺詞形之于聲的過程中根據具體情況合理安排重音和停頓,從而營造出沖突的氛圍,讓觀眾聽到的語言表現出其應有的含義,不影響影片原意的表達。
比如《珍珠港》中,大難不死的雷夫從前線回來尋找愛人伊芙琳,卻發現伊芙琳與自己最好的兄弟丹尼有染,二人在酒吧爆發沖突:
丹尼:雷夫,我們談談行嗎?
雷夫:這就是生活。/好,/為我/最好的朋友、最忠實的伙伴丹尼,/為他所做的一切干杯。/你知道嗎,/有人給你敬酒你不喝,/那就說明/你有問題。
丹尼:好吧,雷夫。/既然這樣,/為你干杯。
雷夫的話語比較零碎,所以停頓較多,配音演員一方面模仿醉酒后斷斷續續的說話狀態,另一方面展現雷夫的絕望與失落,難掩內心的沖動。這段話的重音不算太多,但每處重音都十分明顯、有所隱喻,“我”“敬你”“丹尼”預示著當前二人緊張的關系,“這”“一切”“問題”則直指丹尼在自己不在時的所作所為。雷夫借著酒勁兒,半夢半醒之間將內心表露出來,看似平緩的語言下字字帶刺、滿是暗諷,酒館的氣氛瞬間緊張起來,故事的沖突和二人的對立迅速擺到了臺面上,影片迎來了第一個高潮。
很多時候,故事中的矛盾與沖突是顯而易見的,此時配音要做的,就是“火上澆油”“推波助瀾”,將人物激動的情緒放大,進一步推高影片的精彩程度。
比如《列寧在1918》,列寧片頭訓斥波利亞科夫時語速很快,經常連讀好幾個逗號才會有一句停頓,字詞會做較多的重音處理,用以加強列寧對波利亞科夫工作的不滿和對怠工者強硬的態度,展現出列寧恨不得一口氣把所有話說完的激動和對現狀的擔憂。而片末列寧在工廠演講、訓斥資本主義時都是激動,但他的情緒則與前者不同。前者的沖突發生在列寧與波利亞科夫之前,矛盾起因是工作上的問題。波利亞科夫手段軟弱、辦事不力,但至少也是自己的同志,列寧對他頂多是不滿,要求他立刻改正,僅此而已。但這里的沖突,發生在廣大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矛盾是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對列寧而言,資產階級是自己的敵人,更是工人、國家乃至全人類的敵人,是革命的對象,因此對其充滿敵意。配音時為了表現列寧對資產階級剝削的憤怒和領導廣大人民的領袖氣質,配音演員故意放慢語速,模仿偉人演講時的腔調,在相對合適的地方做了較多的停頓和重音處理,語氣逐漸加重、情緒更加飽滿,每個字就如同砸在地上一樣擲地有聲,突出列寧對資產階級那種咬牙切齒的仇恨。
五、結語
我國引進的譯制片中有大量戰爭題材的作品,其中許多經典成為國人永久而美好的記憶。它們的配音隨著時代的變化呈現出不同的特征,形成了跨文化轉碼、多方式塑造多元化人物、展現差異化場景和制造、深化故事沖突四大藝術表現方式,助力外國優秀影片在中國有效傳播,為我們今天的藝術創作提供參考和借鑒。
如今的電影制作越來越商業化,追求利益、講究效率,配音演員們需要在很短的時間內配完一整部影片,如此“高效率”的配音,使得他們沒有老配音演員們慢工出細活的時間和精力。因此,如何讓配音回歸藝術,不失其本心,是譯制片乃至影視劇配音所面臨的一大問題,這不僅需要配音演員們重拾“工匠精神”,尊重藝術、尊重自己的作品,做到對觀眾負責,還需要有關部門對影視市場的資本嚴加監管,更重要的是,需要廣大觀眾充分發揮市場對影片生產的決定性作用,用實打實的票房倒逼影片配音水平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