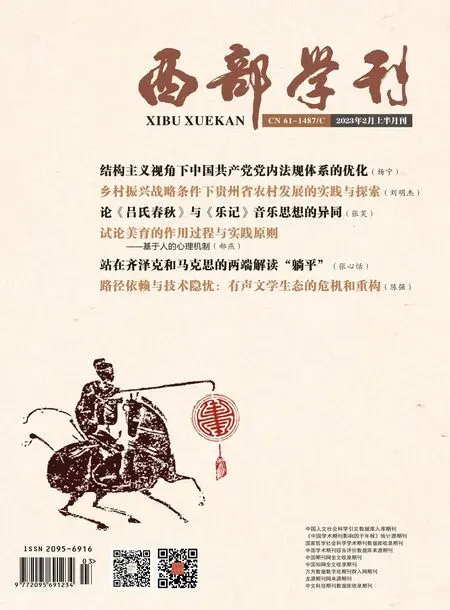在形而上學的基礎上探尋一條超越虛無主義的道路
郭 薇
英國物理學家霍金在他的《大設計》一書中曾提出過這樣的問題,為什么會有一個恰好人類生存的宇宙?這是人類所能提出的最大、最難解的問題,也是歷代哲人和科學家不斷探尋的問題。宇宙是被上帝“設計”出來的嗎?所有這一切從何而來?它需要一個造物主嗎?我們中的多數人在大部分時間里都在為生活瑣事煩擾而無法顧及于此,但是幾乎每個人有時又經常會被這些問題所困擾。因此在筆者看來,人類文明從脫離自然就開始面對著意義問題,人是一種需要意志而存在的生物,人生活在自然中,僅憑本能生存的話不需要思考這個問題,但當人們剪斷與自然鏈接的臍帶脫穎而出的時候,就要靠自己的力量立足于世界上,而人類面對的恰恰是充滿不確定性、充滿危險和黑暗的世界,需要給自己確定安身立命的基礎,或者營造一個精神家園,以此來保證生存下去。所以面對各種不確定的因素,人類所創造的各大文明理念都可以看作是面對空無而建立的價值理念,以此營造一個超感性的理想世界作為現實世界的基礎和根據。因此,對于存在問題、虛無主義、形而上學的討論,在筆者看來更多的是想要尋求某種確定性,給予人在世界上生存的基礎。
一、形而上學之存在
最初,形而上學只是哲學中的一個部分,指本體論,研究世界的本原,康德以及海德格爾時期,他們將形而上學看作是哲學本身,因此形而上學是哲學產生之初就困擾哲學家的一個思想問題。從巴門尼德開始將存在作為研究對象,同時提出作為存在與作為思想是一回事,思想與存在具有同一性。蘇格拉底開始將巴門尼德通過思想把握存在的這種方式具體落實到追問事物的普遍本質上,認為一類事物有一類事物的本質。到柏拉圖就發展成為他的理念論,亞里士多德發展成為他的以實體為核心的范疇體系,這就是形而上學初期的演變過程,再經歷了黑格爾的龐大構建,在某種意義上在尼采這里達到終點。
海德格爾稱尼采是最后的形而上學家,也是形而上學最后的犧牲品,因此對他的思想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尼采認為自己克服了形而上學的虛無主義,而結果卻是恰恰相反,因為他其實和形而上學的思路是一模一樣的,都屬于存在的遺忘,最核心的區別在于形而上學是隱性的,他認為自己研究的是存在,而真正意義上把握的卻是存在者的抽象,并不是存在的存在。尼采認為存在不存在,就是說,歷史上哲學家所致力于構建的超感性世界在他看來是不存在的,現實世界才是真正的存在,公開地拋棄了存在的問題。
存在如此之久的形而上學,為什么在這么久的歷史長河中會一直遺忘存在?海德格爾對于這個問題的思考有一個過程,在形而上學中關于在的遺忘,包括在《存在與時間》中關于此在、生存論的分析,在某種意義上他會認為是因為此在是以一種非本真的、沉淪的方式生存在世,所以最終導致了在的遺忘。但在他思想發生轉折之后,他對于這個問題的思考會更加深入。他認為更重要的是因為存在現身為存在者,而存在本身是隱而不顯的,也就是說存在是以自身缺席的方式存在著的,當它以呈現為存在者的方式讓你去追問存在,但它一旦呈現為存在者人們就看不見存在了,人們關注的就是存在者的抽象。
面對在的遺忘,海德格爾還提出了這樣一種思路,就是回到形而上學之前,去思形而上學未思的存在,因為存在以自身隱匿的方式和存在者一同到達,那么形而上學思的是在者,但在這個思在者的同時一定有它未思的東西。但海德格爾認為形而上學是有其必然性的,我們現在的思想都會認為形而上學錯了,它把在遺忘了,但即使你讓西方文明再來一遍,也還是要這么走的,這就是宿命。從頭開始也是從什么是存在者開始思考,然后激發出存在的思考,這是一個很難扭轉的過程,因此一旦你走上這條道路,就必然對存在熟視無睹。海德格爾嘗試很多方式去思存在,去克服在的遺忘,無論是成功還是失敗,他能夠提出這個問題就非常有意義了。
“存在作為被思考的存在,不再能被叫做存在了,存在之為存在,是一個有別于它本身的東西,它如此確定的是另一個東西,以至于它甚至不存在了。”從海德格爾的這個思路來講,存在與虛無的問題就開始出現了,如果人們思考的存在不存在,很容易就將其等同于虛無,其實這樣是不正確的。海德格爾在《形而上學導論》中討論的最重要的問題就是:“為什么存在者存在,而無反倒不在?”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受到尼采的啟發,他更關注后一半問題。維特根斯坦曾說過:“對于不可說的東西,我們要保持沉默。”但海德格爾卻要千方百計地去研究這個不可說的東西。
因此,經歷一代又一代哲學家的思考,形而上學也沒有把握存在,而思維與存在具有同一性,通過理性認識把握事物本質的方式,就使得存在永遠在他的視野之外。海德格爾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因此他想扭轉方向。
二、虛無主義
當今眾多學者越來越重視虛無主義既有學術方面的原因,又有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首先,虛無主義作為哲學面臨的威脅和挑戰,人們要試圖直面虛無主義問題。其次,在意識形態上,把虛無主義作為自己的立場,主張虛無主義,主張宇宙,人生統統沒有意義,但最后都是要回歸到如何克服虛無主義。
海德格爾曾說過:“存在者之虛無與存在者之存在形影相隨,猶如黑夜之于白晝。倘若沒有黑夜,我們又何曾能看到白晝,何曾能把白晝當作白晝來經驗!因此,一個哲學家是否立即從根本上在存在者之存在中經驗到虛無之切近,這乃是一塊最堅硬、也是最可靠的試金石,可以用來檢驗這位哲學家的思想是否純真,是否有力。誰若經驗不到虛無之切近,他就只能永遠無望地站在哲學門外,不得其門而入。”[1]
現如今大多數人面對虛無主義仍然是束手無策,因此我們相當于都站在哲學門外,而這也是當今哲學面臨的最大問題。
(一)尼采的虛無主義
受叔本華的影響,尼采對這個世界持有悲觀的態度,認為世界是糟糕的,是不值得經受和肯定的。但值得思考的是為什么會有這種悲觀情緒?就像柏拉圖是不會悲觀的,因為他追崇的是“理念”世界,就像虔誠的宗教信徒也是不會悲觀的,因為他認為人世間不過是一場“修行”,人們最終會到達夢想的彼岸世界。在當代社會,每個人都會悲觀,因為在現實世界中是沒有所謂的彼岸世界讓我們去逃離,人生活的世界就是唯一的世界,而這個世界是不能被否定的。但這種世界又是糟糕的,在這種情況下就產生了兩種悲觀主義,弱者的悲觀主義認為一切都是安排好的,我們無能為力;強者的悲觀主義是在看到世界的悲慘后,努力尋找解決辦法。海德格爾認為尼采屬于后者,他看到了哲學的問題,并在積極地尋找出路。尼采在《權力意志》中將悲觀主義稱為“虛無主義的預備形式”,因此悲觀主義是不可避免地向虛無主義發展。
尼采的虛無主義產生的原因就在于目標的缺失,他所處的時代是工業革命后期,野蠻擴張所帶來的環境、生態、資源和人們健康的損壞,使得大部分百姓處于身心疲憊的狀態之下,基督教的價值觀和理論難以維系,人們喪失了目標和依托。所以他理解的虛無主義就等同于“上帝死了”,標志著超感性世界的崩潰,但這恰恰是兩千多年西方哲學一直在構建的工作,去建立一個超感性的世界來作為現實世界的基礎,現在尼采將其摧毀,將所有意義還回現實,由此去克服超感性世界崩塌所帶來的虛無主義。但隨著超感性世界的崩塌,也就表明之前所設定的最高價值已經沉默,對于現實世界來說就只剩下這個世界自身了,而且這個無價值的世界毫無疑問地需要尋求一種新的價值設定,尼采將其稱之為虛無主義。
尼采將其稱之為虛無主義是因為他將超感性世界進行廢除,也就是說最高價值的貶黜,在這個無價值的世界中人們要做的就是重估一切價值,進行一種新的價值設定。尼采在這里試圖將價值作為新的形而上學的基礎,但這個價值的存在方式依舊沒有改變,仍然是在存在者層面上,因而繞了一圈也還是沒有回答存在問題,從這個方面來說依舊是存在的遺忘,同樣也是一種虛無主義。
在尼采的價值哲學中,他其實是將存在作為一種有待規定的價值。因為現在,形而上學不僅不思存在本身,而且這種對存在的不思還被掩蓋在一種假象之中,仿佛它由于把存在評價為價值就以最隆重的方式思考了存在,以至于一切存在之問都變得多余的了[2]。
(二)海德格爾的虛無主義
尼采將上帝死了看作是一種解放,認為自由精神能夠設置和創造新的價值,而海德格爾與此不同,他沒有這么樂觀,他認為將虛無主義看作是人們忘記和背叛自己價值觀的現象,這只是問題的一種方式,上帝死了就是將人們曾經的價值進行抹殺,從而再重新設定新的價值,但這只是核心問題的一個癥狀,虛無主義其實是把人們最深層的關注當作是價值來思考。
海德格爾最關心的并不是人自身的虛無狀態的問題,而是更加寬泛的虛無狀態對于自由的排斥,是一種整體性的虛無主義。他的這些思想預言了虛無時代的到來,人民生活水平飛速提升,但幸福指數卻大大下降,雖然沒有了戰爭殺戮,全球自殺率卻不斷提升,這種現實的虛無已經不是信仰能夠解決的。海德格爾認為,一個物的存在是需要借助一個存在者,虛無是超驗的知識,因此依靠信仰建立的知識體系是不夠牢靠的。
海德格爾稱尼采是最后一個形而上學家,他雖然顛倒了形而上學,但并沒有克服形而上學,因此也就沒有克服虛無主義。形而上學在傳統意義上是關于存在者之為存在者的真理,它包括兩個方面即感性和超感性世界,并且將后者看作是最真實的世界。但隨著超感性世界崩塌,也就代表了形而上學的終結,但這并不意味著歷史的終結反而是另一個新的開端。正如尼采用極端的虛無主義來克服形而上學的虛無主義的方式沒有成功,但他的失敗使得海德格爾要變換思路去開發新的道路。
在海德格爾看來,虛無主義本質就是對虛無的遺忘,就像形而上學是對存在的遺忘,將存在看作存在者加以思考,它是將虛無當作虛無者加以思考,在這個意義上他們二者是相同的,都是對想要研究對象的遺忘。因此,對于虛無主義的克服在任何時代都不是一個容易的事情,要通過經濟、技術、政治這種社會層面來解決哲學問題是不充分的。
雅斯貝爾斯說過:“人類體驗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軟弱,人類在探詢根本性的問題,面對空無,人力求解放和拯救。人在自我的深奧和超然存在的光輝中感受絕對。”
海德格爾認為要想克服虛無主義就要回到最本真、最本己的狀態即此在,他提出過這樣一種思想——向死而生,這個“死”指的是一個過程,就像一個人從出生開始就是在向死亡靠近,他過的每一個小時、每一天、每一年都是走向死亡的過程,但在這個過程中人們確是真正地、強烈地感受著存在感,因此與死亡相比,這個走向死亡的過程更真實、更本真。他用死來激發出人們生的欲望,從這個角度來說,在一定意義上克服著人們內心的虛無主義。在對虛無主義與存在關系討論,到最后更多地是回歸到人類自身的感受上面,回歸到人類如何可以克服自己對于世界、生命、存在、時間的虛無之感。人們在哲學史上對于存在以及價值的探尋,更多是像在尋求某種確定性,打破人生在世的無力感,因此只有不斷地充實自己的心靈感受和精神狀態,勇敢地面對現實世界,才有可能擺脫、克服虛無主義。
三、虛無主義的克服
如果說海德格爾前期寫作的《存在與時間》是為了批判傳統哲學對于存在的遺忘來構建自己的存在哲學,那么他在中后期對于尼采的研究和對于形而上學的思考就是通過一種歷史性的考察來徹底克服形而上學,從而為自己哲學的“思”開辟道路。海德格爾對虛無主義問題的討論,最重要的核心人物就是尼采,他的《尼采》一書是在1936年到1946年之間完成的,這是他開始重新構建《存在與時間》課題的時間,我們可以將這一段時期稱之為他思想道路的轉向。
在普遍意義上,人們通常認為虛無主義是站在形而上學的相反面,但海德格爾認為虛無主義和形而上學其實是同根同源的。換句話說人們必須著眼于形而上學之歷史來理解虛無主義,并且通過克服形而上學來避免陷入虛無主義。海德格爾認為虛無主義的歷史很早就有,它并不是現代才出現的概念,并且在之后也會一直持續下去。因此海德格爾認為,虛無主義的產生與形而上學是同步的[3]。
在海德格爾看來,虛無主義是對虛無自身的遺忘,它將虛無看作是虛無者。從這個角度來說,虛無主義可以等同于形而上學,它們二者都可以被看作是對存在的遺忘。因此,為了克服虛無,海德格爾選擇從“此在”出發,關注存在最本真的狀態。首先他認為人固有一死,每個人都會走向生命的終點,但是這是其他人無法代替的,所以我們應該學會本真的領會死亡,先到死亡中,再領悟死亡,因為在死亡中存在是自己最本真的可能性存在。然后,再發掘良知,這也是人們存在的一種方式,同時也是善性的證據。海德格爾認為只有通過良知,才能找到人們最本真的狀態,找到自我。最后,如何克服“存在”的虛無?在胡塞爾“生活世界”概念的影響之下,海德格爾提出了“共在”的思想,共在的思想就是要讓自我的存在在他人的身上得到確認,在此意義上共在不是社會規范的強制要求,而是我們克服虛無主義的一種方式。
四、結語
海德格爾在其巨著《尼采》和《林中路》中收錄的《尼采的話語:上帝死了》一文中,最重要的話題之一是歐洲虛無主義問題。海德格爾如此熱烈地談論虛無主義,當然不是為了贊揚它,而是為了克服它。正如胡塞爾所說的“歐洲科學危機”,海德格爾將克服虛無主義視為我們時代的“急需”。他之所以關注尼采的思想,正是因為在他看來,尼采是最后也是最有代表性的虛無主義者。從尼采身上可以看出,歐洲虛無主義源于西方形而上學,尼采對歐洲虛無主義的批判是他對整個西方形而上學的批判;由于尼采從虛無主義批判形而上學,從而使自己陷入形而上學,因此成為最后一個形而上學家。海德格爾想以尼采為例,說明他自己的一個創新思路,即通過克服西方形而上學來克服虛無主義。
由此帶來的啟發就是,在現實生活中要勇于接受無意義,生活的意義就在于生活本身,超出生活本身的目的和意義是不存在的,一切都在于生活的過程,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將人生的重心從未來轉移到當下,用現實來對抗虛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