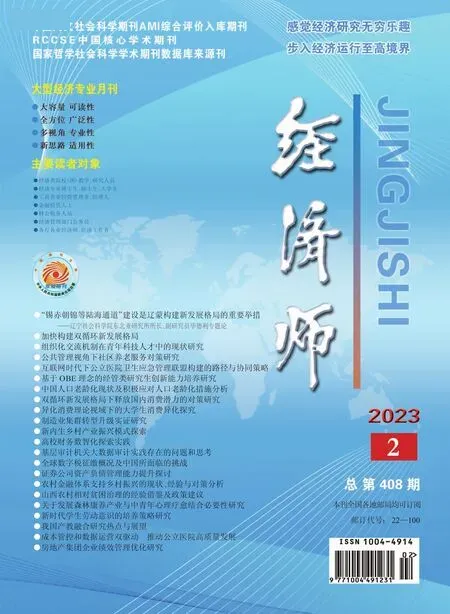區域文化推動基層社會治理研究
——以安徽省蕪湖市為例
●牛艷秋
一、引言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華民族的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蘊含著豐富的哲理與智慧,成為了整個民族的基因和底色,同樣也涵養和滋潤著中國社會善治的土壤。文化對人的影響深遠持久、潛移默化。區域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體系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蘊含著濃厚的地域色彩和文化特質。在歷史進程中,區域文化深刻地引領和培育著當地人們的風俗習慣、思維方式、價值判斷以及生活方式,具有廣泛而強大的影響力。可以說,區域文化的作用會直接影響基層社會治理的效果,深入認識和把握區域文化對于基層社會治理的基礎性作用,是我們打開社會治理現代化的一把鑰匙。
二、區域文化推動基層社會治理的功能分析
(一)培養公共意識
社會的“公共性”特征是在特定的文化基礎之上形成的。在中國,單位制解體過后,公共意識的重塑與再造一直是社會治理的難點。城市化給社會帶來巨大的變革,熟人社會的作用和影響日益衰微,基層面臨著社會碎片化與個體原子化的問題。中國人的交往方式本身缺乏普遍信任[1],尤其在城市社區中,本身都是“陌生人”,所以對參與社會治理存在先天的制約因素,積極性不高。而區域文化則可以作為培養公共意識的粘合劑,以熟悉的文化認同和情感羈絆維系集體的幸福感與群體互助的能力。
(二)維系社會穩定
馬克思指出,“生產關系總合起來就構成所謂社會關系,構成所謂社會。”[2]馬克思認為人的本質就是社會關系的總和,社會關系是以人的聯系為前提形成的各種關系,是社會治理的重要對象。就社會治理而言,離不開現實的社會關系,要形成有效的社會治理,就要促進有利于社會治理的社會關系的局面的形成,使社會中的各種關系達到預期狀態。而文化可以作為協調社會關系、解決社會矛盾的低成本治理方式。一方面,文化可以對社會成員發揮引領、教化、提高人的精神道德境界的作用,成為社會治理的強大助力,使社會關系免去諸多不必要的梗阻;另一方面,在解決群體性事件時,文化可以發揮凝聚共識、擱置爭議的獨特作用,實現價值統一[3],就地化解矛盾的效果。
(三)強化價值引領
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主義、利己主義、拜金主義等不良思想盛行,導致由利益分配失衡而引起的矛盾問題日益增多,使社會治理面臨著復雜嚴峻的挑戰。從古至今,區域文化中沿承下來的優良傳統具有比較穩定的精神指向和價值構建,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影響著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主流意識形態。因此,區域文化的作用不僅僅是簡單地抵消部分不良文化的侵蝕,還可以更深層地培育地方人民的團結意識和責任意識,進一步提高人們的凝聚力、向心力與競爭力。
三、蕪湖區域文化的精神內核
蕪湖歷史文化悠久,是一座古老的城市。《詩經》開篇就寫道“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雎鳩”這個地方就是蕪湖。蕪湖最早見于史籍的地名是“鳩茲”,因鳩鳥云集,湖沼眾多而得名。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有2500多年,漢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鳩茲設縣,始稱蕪湖。一直以來都是兵家和商家必爭之地,農業、手工業、商業比較發達。春秋時期是重要的青銅冶煉中心。南唐時就有“樓臺森列”“煙火萬家”之稱。明朝發展為全國的印染中心,《天工開物》中曾記載“織造尚淞江,漿染尚蕪湖”,蕪湖漿染業在16世紀成為中國之最,領先地位保持三百年之久。清朝時名列全國四大米市之一。
從地理位置和歷史淵源來看,蕪湖市的區域文化凝聚著多元文化的特征[4]。蕪湖居吳頭楚尾,自古享有“吳楚名區”之美譽;資本主義萌芽發端和工商業起步較早,深受徽商文化的浸濡,歷來是著名的商貿中心,是名副其實的“江東名邑”;位于長江中下游地區,又具有鮮明的江南文化的特質。
(一)開放包容的文化特質
蕪湖這座城市在發展歷程中處處盡顯開放的品質,正是不斷地擴大開放才成就了蕪湖今天的繁榮面貌。蕪湖開放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876年的《中英煙臺條約》,當時被辟為全國五大對外通商口岸之一,這讓蕪湖有了睜眼看世界的機會。因貿易往來頻繁的緣故,蕪湖成為長江中下游地區近代工商業的發祥地之一。
得天獨厚的地理區位和便利的交通條件造就了蕪湖區域文化的開放性,使得多元文化與區域文化不斷激蕩交融。改革開放后,安徽省以蕪湖為突破口,走向全國和世界,大力發揮蕪湖文化的開放性優勢。所以,蕪湖區域文化活力的根本所在,就是對各種文化的開放包容和兼收并蓄,不僅如此,也形成了蕪湖民眾海納百川的胸襟和吐故納新的精神。蕪湖的名字是隨著開放而聞名的。也正因為如此,孫中山曾經稱蕪湖為“長江巨埠,皖之中堅”。這種開放包容的特征就是孕育社會治理實踐創新的優良沃土。
(二)誠信務實的文化內核
誠實是一切經濟社會行為需要遵循的基本規范,也是保證社會和諧穩定的關鍵之道。在蕪湖,青弋江穿城而過,連通著徽州的廣大地區,古代蕪湖便因此成為了徽商走向全國的橋梁。徽商文化曾經創造了輝煌的奇跡,商人們通過在這里集結,使得徽商精神中誠信、務實等優良品質在此發揚光大。
當前,蕪湖正處于在更高水平上實現科學發展、率先發展、和諧發展,全面提升城市綜合競爭力的關鍵時期,更加需要從實際出發,講實干、做實事、求實效,搶抓機遇、應對挑戰,切實解決發展中的矛盾和問題,突破發展中的各種障礙。為了更好地解決基層社會治理中面臨的復雜問題,必須大力弘揚誠信務實的精神,樹立社會公德、協調社會關系,增強蕪湖的對內凝聚力和對外吸引力。
(三)改革創新的文化基因
創新是蕪湖區域文化中的靈魂,在每個歷史階段都彰顯著強大的生命力,這種創新思想不僅僅是注重實際行動的落地生根,更是在竭力打造跟跑、并跑到領跑的優勢與特色。蕪湖鐵畫馳名中外,是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承載著蕪湖文化的基因;改革開放后,蕪湖創新文化氛圍愈益濃厚,城市民營經濟改革的邏輯起點正是從蕪湖的“傻子瓜子”起步的;“奇瑞”汽車的誕生與發展是詮釋自立自強、創新創業的一面旗幟;方特歡樂世界是亞洲規模最大的第四代主題公園,它完全由國人自主開發設計,完美交融了時代性與娛樂性,蕪湖也借勢打造成為“東方的奧蘭多”。未來蕪湖要在更高水平上實現科學發展、率先發展、和諧發展,創新總結基層社會治理的機制方法,必須繼續大力弘揚創新理念,不斷推進創新實踐,不斷完善具有蕪湖特色的自主創新模式。
四、區域文化推動基層社會治理的路徑
區域文化作為一種精神內力,可以為社會提供良好地文化氛圍與智力支持,而且與其他要素互相融合、互相促進,推動著生產力的前進。蕪湖的區域文化內涵豐富,特色明顯。從整個社會的層面來說,不僅可以凝聚各界共識,實現價值統一,還可以整合社會資源,保障改善民生水平,降低社會治理成本;從公民個人的層面來說,可以涵養品性,將道德品質內化于心,外化于行,進而提升文明修養,規范個體行為。
(一)以開放包容的文化協調社會階層的關系
當前,我國處于社會矛盾風險的凸顯期,社會分化加劇,利益分配的不合理帶來大量的矛盾與問題。因此,運用好區域文化,就地化解矛盾糾紛,調解人民內部矛盾正是應有之義,也是基層社會治理體制改革的重要途徑。
在開放包容的文化精神的深刻影響下,蕪湖市早在2010年起,就由鏡湖區進行試點,設立了“兩代表一委員”調解工作室。各階層群眾均可以直接與代表委員面對面交流,表達自身利益和真實訴求,解開基層難題的“千千結”。“兩代表一委員”由于參與了每周五一次的調解工作,被當地群眾視為“好朋友,貼心人”。讓群眾遇到困難不著急了,心里踏實了,把溫暖通過基層社會治理的方式傳遞到廣大群眾中去,用文化的力量去促進制度和機制的創新,打通了社會階層之間的梗阻,實現了社會成果的全民共享。如今,“兩代表一委員”的社會治理創新經驗已經在安徽省全省推廣開來。除了線下的矛盾糾紛調節平臺,蕪湖還開發了線上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的新平臺——“解紛蕪優”,在這個小程序中可以調解社會中各種類型的糾紛,特別是全市有近800名調解員主動參與其中,幫助人們解決婚姻家庭、鄰里糾紛、合同糾紛、勞動爭議、土地、拆遷、環境污染、消費、醫療、道路、物業等等問題,涉及到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見,開放包容的文化性格有助于減少基層社會沖突的產生,形成和諧友善、協調相處的社會風氣,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營造良好的社會治理氛圍。
(二)以誠信務實的文化融入“三治融合”的實踐
蕪湖一直以來秉持的誠信務實的優良文化,也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的基本內容,有助于構建符合現代社會標準的道德體系,其中暗含著“三治融合”的本質,是探索基層善治的關鍵[5]。
文化是自治的前提。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堅持和完善“楓橋經驗”,“楓橋經驗”中自治的方法就是在民間文化的自發推動下逐步形成的。比如,楓源村創造的“三上三下”民主決策機制就是源自村內的歷史文化因素。
文化是法治的基礎。薩維尼認為,“在任何地方,法律都是由內部的力量推動的,而不是由立法者的專斷意志推動。”[6]文化對于法治的影響力是不容小覷的,甚至可以說是決定性的。但是,區域文化可能在現實中存在與行政區劃相沖突的問題。這就需要在區域法治建設中避免人為割裂的影響,先厘清文化的隸屬區域,才能充分地發揮區域文化的積極作用。當行政區劃中包含了不同的區域文化時,要更加有針對性地制定法治區域建設的綱領。
文化是德治的動力。在德治過程中,更體現著文化人的作用。一方面可以發掘培育社區領袖和民間能人,最大限度地實現區域社會治理權力網絡的重構。鄉賢在鄉土社會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不僅可以傳承優秀的傳統文化資源,還可以在基層社會治理中用個人的價值取向影響群體的共同價值,積極引領社會成員參與社會活動[7]。蕪湖市灣沚區堅持問題導向,由鄉賢組建了村民道德議事會、紅白理事會、禁賭協會等組織來解決鄉村治理中的難題,在移風易俗和更新孝養理念方面發揮了榜樣的模范帶頭作用,體現了務實的態度和擔當的精神。另一方面,家風家訓是區域文化的具體體現。“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蕪湖區域文化中的家風家訓,其中誠信務實的內核不僅傳承發揚了優良的家庭文化,更成為展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方式,有利于樹立家風家規意識,弘揚傳統美德,促進社會和諧建設。
(三)以改革創新的文化加強黨建引領的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把加強基層黨的建設、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作為貫穿社會治理和基層建設的一條紅線。因此,在基層社會治理中需要積極創新“黨建+”模式,堅持把黨建作為引領發展、推進基層治理的“牛鼻子”,確保黨的全面領導落實到基層工作的方方面面中[8]。在蕪湖市灣沚鎮民主社區的實踐中,不斷創新推進“117N”基層黨建新模式——一個信得過的黨組織、1個標準化的黨建陣地、7個黨支部對應7個網格、N個小區樓道黨建微細胞。充分發揮了基層黨組織的核心引領作用,著力構建“一核多元、合作共治”新型治理機制,實現了在社區黨組織領導下的社區治理和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動。每個社區都有自身獨特的情況和文化,所以在創新“黨建+”模式地實踐中,要因地制宜地把社區中的“陌生人”匯聚成“組織人”,進一步挖掘探索出更多各具特色的黨建品牌。
五、結論
一直以來,我國在基層層面主要是以法治的方式來實現社會治理目標的,但是在現代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基層面臨的問題與挑戰日益復雜多變,所以社會治理的方式也應該逐步走向多元。實際上,文化的嵌入才是更深層次的嵌入,更具有凝聚力和持久力。區域文化的力量深刻地鐫刻在本地民眾身上,體現在當地文化氛圍之中。因此,充分汲取區域文化中的精華,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凝心聚力,有效地拓展基層社會治理的路徑,才能構建起既符合城市特征又兼具區域文化特質的社會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