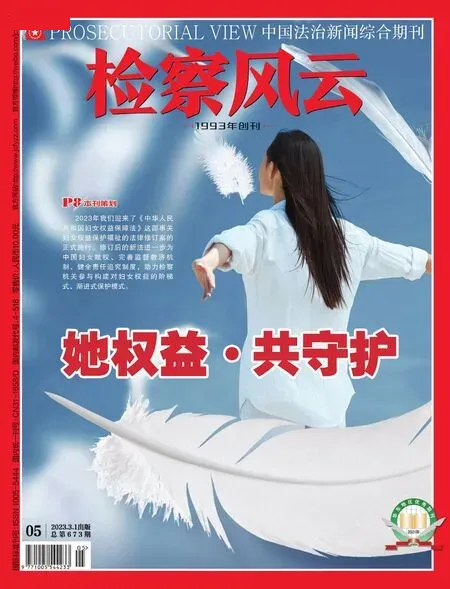多維度夯實婦女權益救濟渠道
文·圖/莊嘉
近年來,我國愈發(fā)重視婦女事業(yè)的發(fā)展,持續(xù)完善婦女權益的法治保障。目前,我國已建立涵蓋100多部法律法規(guī)在內的保障婦女權益的法律體系,先后制定實施3個周期的婦女發(fā)展綱要,性侵、虐待未成年人、拐賣婦女兒童等犯罪行為受到了有力懲處。不過,在執(zhí)法司法實踐中,性別歧視處置、家暴維權、性騷擾處置、被拐婦女救助等領域仍需完善。因此,修訂婦女權益保障法既是回應社會關切的現(xiàn)實需要,也是夯實婦女權益救濟渠道的必然趨勢。
豐富就業(yè)性別歧視的維權路徑
以往,針對就業(yè)性別歧視,當事人通常會借助行政公益訴訟的方式維權,若涉及犯罪,則移送公安處理。假如當事人是單位員工,遭遇性別歧視,還可通過勞動爭議仲裁進行維權。只是,該程序一旦啟動,當事人就可能與用人單位撕破臉,且需要當事人自行取證與舉證,存在一定風險。
令人欣慰的是,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新法”)為婦女員工開辟了新的救濟途徑:一方面,新法明確性別歧視在就業(yè)領域的5種情形,即除國家另有規(guī)定外,用人單位在招錄過程中,“禁止限定為男性或規(guī)定男性優(yōu)先”“除個人基本信息外,禁止進一步詢問或調查女性求職者的婚育情況”“禁止將妊娠測試作為入職體檢項目”“禁止將限制結婚、生育或婚姻、生育狀況作為錄用條件”“禁止其他以性別為由拒絕錄用婦女或差別化地提高對婦女錄用標準的行為”;同時,新法設置了違反上述5種情形的罰則,即:“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責令改正;拒不改正或情節(jié)嚴重的,處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款。”另一方面,新法要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將招聘、錄取、晉職、晉級、評聘專業(yè)技術職稱和職務、培訓、辭退等過程中的性別歧視行為納入勞動保障監(jiān)察范圍。
實然,對于就業(yè)性別歧視,新《上海市婦女權益保障條例》(以下簡稱《條例》)也提供了新的維權路徑,《條例》規(guī)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可以聯(lián)合工會、婦女聯(lián)合會,對就業(yè)性別歧視的用人單位開展約談,并要求限期糾正。
拓展反家暴的外延與聯(lián)管聯(lián)治
從社會危害性角度來看,家庭暴力嚴重危害受害者的身心健康與生命安全,堪稱影響社會穩(wěn)定的隱性毒瘤,而婦女往往是家暴的主要受害者。我國2016年施行的反家庭暴力法將家暴的范圍限定為家庭成員之間,并賦予了家暴受害者報案權、起訴權、反映權、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權等救濟途徑。據(jù)此,家暴受害者的主要救濟途徑包括4種,即縣級以上人民政府開通的婦女權益保護服務熱線、檢察機關的公益訴訟、110報警以及民事訴訟權。其中,人身安全保護令成了不少家暴受害者的護身符。
在最高人民法院發(fā)布的反家暴十大典型案例之一的遼寧省沈陽市皇姑區(qū)人民法院辦理的李某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案中,申請人李某(女)與被申請人宋某系夫妻關系,宋某多次對李某實施捆綁、毆打、謾罵等暴力行為,導致其多次被送醫(yī)救治。皇姑區(qū)人民法院根據(jù)李某的陳述及公安機關記錄材料、醫(yī)院病情介紹單、皇姑區(qū)婦聯(lián)出具的意見等材料,認定李某面臨家庭暴力風險,依照反家庭暴力法規(guī)定,裁定禁止宋某實施家庭暴力,并禁止宋某騷擾、跟蹤、接觸李某及其近親屬。
當然,立法者也注意到,家暴行為已擴展至家庭關系以外的特定關系中。對此,新法加強了婚戀交友關系中的婦女權益保障。戀愛、交友、終止戀愛、離婚后的婦女遭受對方糾纏、騷擾等行為的,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這彰顯了立法者不再以婚姻、家庭或共同生活作為家暴的判斷標準,填補了反家暴保護對象的空白。
值得關注的是,滬上《條例》將反家暴工作納入平安建設,要求健全完善110家暴類警情接處警工作機制,嚴格依法處置家暴類警情。對涉及家暴的報警求助,要求做到快速接處警——該立案的依法立案,認真查處;對情節(jié)較輕的,依法告誡。同時,探索構建公檢法司、婦聯(lián)、共青團、基層社會組織對接聯(lián)動機制,加強對關聯(lián)警情數(shù)據(jù)統(tǒng)計和分析研判,推動反家暴工作齊抓共管。
新法提出,政府及有關部門、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等重點職能部門負有發(fā)現(xiàn)、報告和解救、安置、救助、關愛被拐賣婦女的職責。
進一步健全性騷擾的預防與處置體系
在執(zhí)法司法實踐中,性騷擾警情日趨常見,表現(xiàn)形式主要包括:言語、文字、圖像、肢體行為性騷擾。對此,民法典第1010條賦予了受害人民事維權的途徑。
據(jù)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發(fā)布的《人格權保護審判白皮書》中的案例:沈女士于2021年3月8日入職某公司,工作職位是董事長綜合秘書,主要內容包括為董事長張某安排工作行程、協(xié)助照料張某日常生活等。同年3月31日,公司解除與沈女士的勞動合同和勞動關系。沈女士稱自己在任職期間遭受張某的性騷擾,因未滿足張某的要求而被辭退。沈女士訴至法院要求張某賠禮道歉、賠償精神損失費1元以及律師費。一審、二審法院均認定張某對沈女士的言語具有明顯的性挑逗性質,內容與性有關,且造成沈女士產生抗拒等不良心理反應,構成性騷擾,判令他向沈女士書面賠禮道歉、賠償律師費。民事訴訟儼然成了性騷擾受害者維權的首選,但被性騷擾者往往面臨一定的舉證責任和困難。
對此,新法第23條既賦予了受害婦女民事訴訟權,也規(guī)定了受害婦女可以直接向公安機關報案。在性騷擾接處警中,“隔空性騷擾”屢有發(fā)生,主要是多次通過信件、電話、計算機網(wǎng)絡等途徑傳送淫穢信息,干擾他人正常生活,尚不夠刑事處罰的行為。
在四川省瀘縣公安局辦理的劉某某發(fā)送淫穢信息干擾他人正常生活案中,劉某某利用“跑摩的”的便利,通過微信搜索手機號將女性乘客添加為微信好友,向這些女性乘客發(fā)送大量淫穢視頻、圖片和信息,并發(fā)出邀約,企圖發(fā)生不正當關系。對方屏蔽劉某某微信號后,其又通過手機發(fā)送淫穢短信。根據(jù)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四十二條第(五)項“發(fā)送信息干擾正常生活”,處5日以下拘留或500元以下罰款;情節(jié)較重,處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500元以下罰款。

新法加強了婚戀交友關系中的婦女權益保障
當前,性騷擾案例中,受害者是未成年人的比例正在增加。據(jù)最高人民檢察院(以下簡稱“最高檢”)發(fā)布的未成年人檢察工作報告:近5年來,針對未成年人實施的強奸、強制猥褻、猥褻等性侵犯罪有增加趨勢,網(wǎng)絡“隔空猥褻”侵犯未成年人案件頻發(fā)。針對一些“大灰狼”通過網(wǎng)絡聊天,脅迫女童自拍裸照上傳,嚴重侵害兒童人格尊嚴和身心健康,最高檢發(fā)布指導性案例,確立無身體接觸猥褻行為視同線下犯罪的追訴原則。截至2022年9月,起訴利用網(wǎng)絡“隔空猥褻”未成年人犯罪1130人。
在立法層面,未成年人保護法第54條規(guī)定,禁止對未成年人實施性侵害、性騷擾。教育部頒布的《未成年人學校保護規(guī)定》厘定了學校應當制止教職工及其他進入校園的人員的6類行為,包括:與學生發(fā)生戀愛關系、性關系;撫摸、故意觸碰學生身體特定部位等猥褻行為;向學生作出具有調戲、挑逗或者具有性暗示的言行;向學生展示傳播包含色情、淫穢內容的信息、書刊、影片、音像、圖片或者其他淫穢物品;持有淫穢、色情視聽、圖文資料;其他構成性騷擾、性侵害的違法犯罪行為。
對此,新法對學校、用人單位的合理預防處置措施做了更加細致的列舉。比如,新法第25條規(guī)定了單位的強制義務,如制定禁止性騷擾的規(guī)章制度,開展預防和制止性騷擾的教育培訓活動,支持、協(xié)助受害婦女依法維權,必要時為受害婦女提供心理疏導;更明確提出,“學校應當加強性別平等教育,建立受害學生保護制度與從業(yè)限制制度”。
此外,新法明確規(guī)定行為人和單位應承擔行政責任:一方面,確立了公安機關有批評教育或出具告誡書權,行為人所在單位有處分權。另一方面,學校、用人單位未采取必要措施預防和制止性騷擾,造成女性權益受到侵害或社會影響惡劣,由上級機關或主管部門責令改正;拒不改正或情節(jié)嚴重,依法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給予處分;學校、用人單位在承擔行政責任的同時,還應當向受害人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
探索拐賣婦女的線索發(fā)現(xiàn)與報告機制
拐賣人口犯罪始終是我國高壓嚴打的罪行,拐賣婦女、兒童,情節(jié)特別嚴重的,處死刑。近年來,公安部深入開展“打拐”專項行動,構建“一長三包”責任制,涵蓋了縣市區(qū)公安局長擔任專案組長,全面負責案件偵辦、查找解救被害人、安撫被害人家庭等相關工作。
然而,城郊接合部、鎮(zhèn)村交界地,仍然是該類罪行極易發(fā)生的地域。不法之徒往往為了金錢利益鋌而走險,打著治病、介紹婚姻等幌子拐賣婦女。在江西省龍南市人民法院辦理的羅某某、周某某、王某某等人拐賣婦女案中,犯罪嫌疑人多次以治病、介紹婚姻的名義將被害人騙走,并進行轉賣,從中牟利。經公安機關多次走訪調查,最終成功解救被害人肖某某、李某、賴某某等人。
在公安偵查辦案中,最難的往往是如何快速查找和確認被拐賣者。即便公安部于2009年就建立了全國打拐DNA(脫氧核糖核酸)數(shù)據(jù)庫、制發(fā)了《公安機關處置人員失蹤警情工作規(guī)范》;但單純依托公安機關的力量,尚難以形成嚴密的救助網(wǎng)絡,還需要最大限度發(fā)動社會力量鎖源救人。對此,新法提出,政府及有關部門、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等重點職能部門負有發(fā)現(xiàn)、報告和解救、安置、救助、關愛被拐賣的婦女的職責。如此一來,村委會、居委會等一線網(wǎng)格部門就有了發(fā)現(xiàn)和報告被拐賣婦女的法定職責,司法行政、婦聯(lián)等職能部門也有義務配合救助,這有利于構建被拐賣婦女的快速查找和確認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