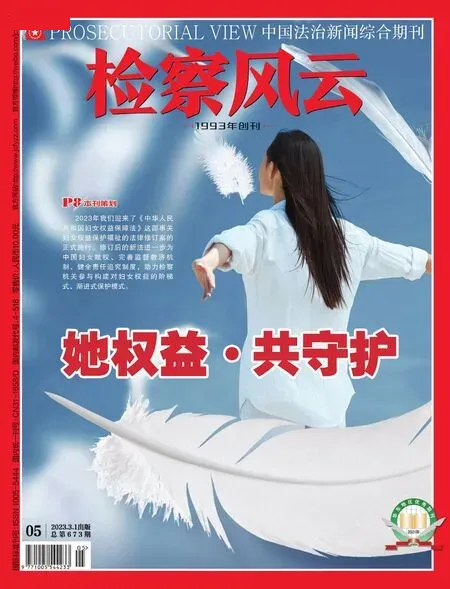法源或陋習:近代中國商業行規爭鳴
文/宋偉哲
古代中國并沒有完善健全的商業法規,商業靠什么來維系健康運轉呢?答案之一便是商業行規。在傳統社會,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的一套規矩,許多規矩在最開始也只是不成文的習慣而已。隨著社會進步,行會開始興起,行規也不斷完善,逐漸演變為具體成文的商業行規。清末民初,中國立法者逐漸認識到了民商事習慣在立法和社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在國家立法中確立了習慣的法源地位。然而在實踐中,商業行規的適用卻并非一帆風順,官方民間為此產生了長時間的爭鳴。重溫這段往事,不但能夠讓人們更加深入地了解當時的中國社會,更能對今天的立法和司法產生深刻的啟迪。
爭議起源
清末法制改革后,清政府開始學習西方編纂近代法律,并進行了大規模的民商事習慣調查。雖然不久之后清廷即宣告覆滅,這些法律并未來得及實施,但是從流傳下來的法律草案來看,還是看到了習慣的重要法源地位。比如《大清民律草案》“總則”第一條規定,“民事,本律所未規定者,依習慣法;無習慣法者,依條理”。民國建立后,政局動蕩,也未曾制定出全新的民商法典。各地的商業行規也依然承擔著補充法律不足,維系商業平穩的職責。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即著手編纂民法典,并確立了“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1929年5月23日,南京國民政府頒布《中華民國民法典》的總則部分,其第一條和第二條規定,“民事,法律所未規定者,依習慣;無習慣者,依法理”“民事所適用之習慣,以不背于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為限”。通過這兩個法律條文,正式確立了習慣的法源地位,在中國法律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民法雖然確立了習慣的法源地位,但是它的適用仍然充滿艱辛,特別是在商業行規領域。上海是近代中國第一大城市,當時上海的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的同業公會,數目之多,門類之廣,今人難以想象。同業公會制定的行規,涉及商業活動的方方面面。翻開《申報》《商業月報》等當時流行的報紙刊物,這方面的新聞報道比比皆是,足見其在商事活動中的重要地位。也正因為此,上海成為這場關于商業行規大爭論的焦點中心。1929年,國民政府頒行《工商同業公會法》,這部法律明確了同業公會的法律性質及組織、運轉規則,肯定了其在商業活動中的積極作用。這本是一件好事,可是在行規和會員方面,這部法律卻留下了漏洞,引發了不少矛盾沖突。

南京炮標勵志社舊址
原來,這部法律并未規定同業者必須強制加入同業公會。這就帶來一個新的問題,凡是沒有加入同業公會的業者,是否需要遵守同業公會制定的行規呢?針對這一問題,社會上產生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第一種意見認為,未入公會者不必遵守行規,中央主管部會及部分不愿意參加同業公會的業者,多持此種意見;第二種意見則與之相反,他們強調未入會者必須遵守行規,同業公會的參與者和地方政府主管機關多持此種意見。1930年6月,上海市商會召開會員大會,許多同業公會向大會提案,要求商會向政府請愿,明確商業行規的法律地位,同時凡經政府核準備案之行規,同業者必須共同遵守。不久,上海市商會遂代表全市公會呈請國民政府,要求規定“未入會同業應一律遵守共同公會呈準立案之行規”。
數月之后,這份呈請卻被中央主管機關工商部駁回,其主要理由如下,“查同業行規并非法律,無強制之可言,而各業所定之行規,又往往含有壟斷性質,或違反善良習慣之處。在主管官廳,對于各業情形,容有不明,雖經予以審核,仍難保其必無流弊。此種不良行規,以法律通例言之,即訴諸法庭,亦難予以保護,何得迫令同業一律遵守。故若不問行規之內容,凡經官廳核準無論已未入會均須遵守,非特于會無濟,反足惹起糾紛,來呈所稱未入會同業均應一律遵守行規等情實有未合”。收到工商部駁文之后,上海同業公會界一片嘩然,表示強烈不滿,準備再次請愿,還向兄弟省市商會提出援助請求。就在這時,全國工商會議即將在南京召開,上海同業公會的主管機關上海市社會局也表達了對同業公會請愿的支持,表示要在全國工商會議上提案,力爭徹底解決這一問題。
會場激辯
1930年11月1日至8日,南京國民政府召開全國工商會議。全國工商界兩百余位代表匯聚一堂,審查討論了四百多個議案。第二年,實業部總務司、商業司出版了《全國工商會議匯編》一書,全書用六百多頁、數十萬字的篇幅,把當時的會議實錄全面公開,使得后人得以完整查閱當時的提案全文以及會場辯論實況。11月6日下午2點至5點,全國工商會議第五次大會在南京炮標勵志社大禮堂舉行,工商部長孔祥熙出席并擔任會議主席。會議開始不久,便進入有關商業行規提案的討論環節。該提案由上海市社會局提出,其主要內容是,“(一)各業擬定之業規須呈經當地主管工商之行政官署核準備案;(二)一經核準備案,則視為同一規章,誓共遵守,無論會員非會員,如有破壞者,得呈請官廳究辦;(三)業規在事實上發生窒礙時,得由官廳增刪”。代表王延松首先發言,他指出這一提案非常重要,特別是來自上海的代表均認為有詳細討論的必要,于是提請大會允許提案人上海社會局局長潘公展就提案向大會做詳細匯報。
潘公展獲準發言后講道:“新商會法的基礎是以同業公會為組織單位,和以前以個人為單位的辦法完全不同……如果同業可以不遵守業規,同業公會是組織不成的,而以同業公會為基礎的商會也一定不能成立。因為同業公會的會員所盡義務非常重要,不但在平時要負維持公會經費的責任,同時還要分攤國家所發行之公債庫券。國家發行一次公債庫券,先由政府向商會分攤,商會就向所屬的同業公會分攤,而同業公會當然要向會中的會員分攤。至于不入會的同業就可以逃避,所以兩相較之入會同業是很吃虧的。”既然吃虧,為什么還有那么多業者要加入同業公會呢?潘公展指出,他們“最大的要求就是同業的業規能夠維持”。為了更形象地說明其中的道理,潘公展連舉金融價格、營業時間、勞方權益等數個例子解釋說明。針對行規壟斷的質疑,潘公展則認為,沒有行規才會造成壟斷。他以杯子生產為例,比如同業行規規定一只杯子賣兩角錢,現在一大資本家售賣一角八分錢,待到別的商家都被壓垮,其就可以任意漲價,這才是真正的壟斷。他還特別強調,行規的價格約束只限于批發,而不涉及零售商,所以行規不會與小商販的利益造成沖突。在潘公展看來,行規是“一件公平折中,根據習慣,迎合潮流的東西”“可以補法律之不足”。潘公展來自行政管理第一線,既代表政府立場,又符合同業之期待,因此他的意見很有分量。
緊接著,時任工商部常務次長的穆湘玥也進行了長篇發言,他主要圍繞之前工商部批駁上海商會呈文進行了詳細解釋。他說部里之所以如此裁決,是“費十二分精神去研究討論的”,并非草率答復。最主要的理由就是“法律與事實不能并行”,既然法律沒有強制同業入會的規定,就沒有道理要求同業一體遵守業規。他還強調,就算工商部批準備案了,其對司法是否有效仍屬未知。將來一旦發生糾紛,司法機關“恐怕還是根據法律”。針對這一點,王延松當即表示反對,他以《中華民國民法典》第一條法律、法理、習慣之適用為論據,舉出上海地方法院經常發函咨詢上海商會商事慣例以備裁判參考的實例,有力反駁了穆湘玥的觀點。這里需要補充說明的是,王延松所舉實證確有其事。由時任上海商會主任秘書嚴諤聲主編并流傳至今的《上海商事慣例》一書,就是當年上海法律工作者向商會咨詢商事習慣的生動記錄。
除了上述幾人,還有許多代表踴躍發言,有人提出要請立法院修法,有人認為應當請司法院進行司法解釋。后人耳熟能詳的出版大家王云五先生,則表態原則通過,請工商部采擇辦理……眾說紛紜,沒有定論。最終,孔祥熙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先以個人名義對此提案“極表贊成”,但是也同時強調,“法律規定如此,我們工商部只能依法辦理”。至于立法院、司法院意見如何,則非工商部所能左右。所以他建議本案原則通過,請工商部酌情采擇辦理,再視情況交立法院修法或司法院解釋,最終大會表決結果也是采用了這一“折中”的方案。
全國工商會議雖然沒有真正解決商業行規的問題,但是畢竟壯大了輿論聲勢,原則性通過提案也證明了多數代表支持遵守行規的提案,增強了同業方面的信心。消息傳到全國各地后,各地商會、同業公會繼續發起大規模請愿,持續給國民政府施壓。重壓之下,工商部于1930年12月5日呈文行政院,表態可以認可上海市社會局提出的三項辦法。12月17日,行政院向上海市政府下令,同意上海市社會局所提提案,同時也對行規的制定提出了一些原則性要求。至此,有關商業行規的論爭終于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