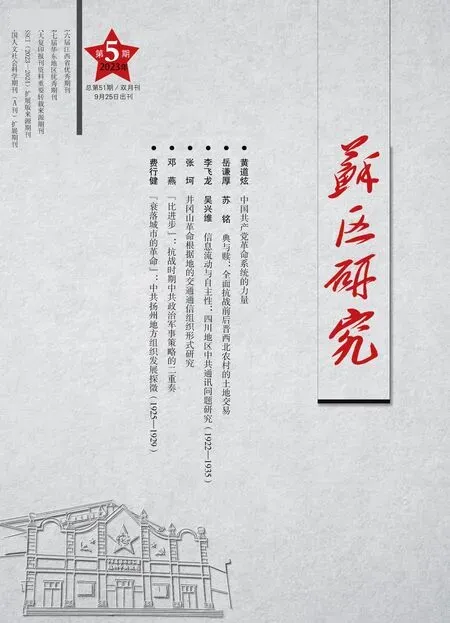中國共產黨革命系統的力量
黃道炫
1945年7月,由美國戰爭信息局撰寫的長篇報告《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起始部分就明確指出:“幾乎所有不帶偏見的觀察者都一致強調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最卓有成效、有最好的政治組織系統與最強的紀律性、最有建設性的隊伍。”(1)Lman P.Van Slyke: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A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War Department,July 194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8.這樣的話,雖然出自美國人之口,卻不失為當年中共陣營的真實寫照。美國人的報告顯示,當年他們已經注意到中共政治組織運作的系統性。系統性的確是中共思想和行為十分重要的特征。
一、系統及中共革命中的系統
系統一詞從希臘語“sys-tema”派生,意為“由部分組成的整體”。一般系統論的創始人貝塔朗菲認為:“一般系統論是關于‘整體’的一般科學,在此之前整體被人們看作是一個不明確的、模糊的和半形而上學的概念。”(2)[美]馮·貝塔朗菲著,林康義、魏宏森等譯:《一般系統論——基礎、發展和應用》,清華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頁。系統是由一些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若干組成部分結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機整體。一個系統至少要由兩個或更多的要素或子系統組成。系統的整體不是各組成要素功能的簡單疊加或拼湊,而是有機地組成一個整體,組成要素及其聯系必須服從系統的整體目標,要以整體最優為原則。系統具有強烈的目的性,系統整體的功能通常超出各個部分的疊加,所謂“整體大于部分之和”。中共革命中常常可以看到的溢出效應就來源于系統的這一特征。
系統追求整體的把握和了解,但系統并不是封閉自足的概念,貝塔朗菲強調開放系統:“每一個生命有機體本質上是一個開放系統。它在連續不斷的流入與流出之中,在其組分的不斷的構成與被壞之中維持自己,只要它是有生命的,它就永遠不會處于化學的和熱力學的平衡狀態,而是維持在與平衡狀態不同的所謂穩態上。這是通常所說的新陳代謝這個基本生命現象的真正本質。”(3)[美]馮·貝塔朗菲著,林康義、魏宏森等譯:《一般系統論——基礎、發展和應用》,第36頁。德內拉·梅多斯則認為,系統運作呈現三個重要的特征:適應力、自組織和層次性。所謂適應力,是指系統內部存在很多相互影響的反饋回路,這些反饋回路傳達信息,作出反饋,使系統迅速調整,保持穩態結構。所謂層次性,是指任何一個大的系統都包含很多子系統,系統和子系統間形成包含和生成關系。一個良好運轉的系統,層次結構可以平衡整體系統和子系統的福利、自由和責任。所謂自組織,是指系統不是靜態的,系統具有學習、運動、多元化、復雜化和進化的能力,在沒有特定外部作用參與時,系統通過信息反饋,可以不斷調整自己的目標和功能,甚至演變出新的結構,發展出全新的行為模式。(4)參見[美]德內拉·梅多斯著,邱昭良譯:《系統之美:決策者的系統思考》,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4—118頁。由此可以看出,現代意義上的系統,既具有很強的規定性,構成行為和思維模式;又具備足夠的彈性,在辯證地生成、進化。所以貝塔朗菲明確表示:“雖然起源不同,但一般系統論的原理和辯證唯物主義相類似則是顯而易見的。”(5)貝塔朗菲:《一般系統論的發展》,龐元正、李建華編:《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經典文獻選編》,求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8頁。
中國傳統思維也有比較明顯的系統特征。李澤厚指出:“正如古代有辯證法的觀念一樣。它們都來自素樸的生活經驗。在中國特定條件下,系統論觀念如同辯證法觀念一樣,它們發展得特別充分。”(6)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頁。不過,李澤厚同時強調,這種系統論由于早熟,也有很多缺陷:“在這種系統論里,似乎把所有經驗都安排妥貼了,似乎一切問題都可以在這系統中求得解決,從而不要求思維離開當下經驗去作超越的反思或思辨的抽象以更深地探求事物的本質。……同時,也是由于注重系統整體,便自覺不自覺地相對輕視、忽略對眾多事物和經驗作各別的單獨的深入觀察和考查,具體事物的分析、剖解、實驗被忽視了。”(7)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第172頁。相對于傳統未經分疏、渾沌、包羅萬象的系統,經過現代科學洗禮的系統是有限的、競爭的(8)關于系統內部的競爭關系,貝塔朗菲認為:“對于一個整體來說,引入組成部分之間競爭的概念,似乎是自相矛盾的。然而,事實上這兩個明顯矛盾的陳述都是系統的本質。任何整體都是以它的要素之間的競爭為基礎的,而且以‘部分之間的斗爭’(羅克斯Roux)為先決條件。部分之間的競爭,是簡單的物理—化學系統以及生命有機體和社會體中的一般組織原理,歸根到底,是實在所呈現的對立物的一致這個命題的一種表達方式。”[美]馮·貝塔朗菲著,林康義、魏宏森等譯:《一般系統論——基礎、發展和應用》,第61頁。、開放的,如貝塔朗菲所說:“現代科學的思想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沒有一個唯一的包羅萬象的‘世界系統’。一切科學構思都只反映了實在的某些方面或某些透視圖。……各種各樣的‘系統理論’同樣也是反映了不同側面的模型。它們不是互斥的,常常可以組合起來應用。”(9)[美]馮·貝塔朗菲著,林康義、魏宏森等譯:《一般系統論——基礎、發展和應用》,第87—88頁。
本文也是在上述規定性和彈性兼備的意義上使用“系統”這一概念。特別需要說明的是,強調中共革命具有系統性運作的特征,作的只是實然判斷,也就是說,這是作者觀察到的一種特征,至于一個政治力量乃至一個社會是不是應該如此,那是應然判斷。其實,如果把系統視為一個開放的、動態運作的彈性概念,那么對系統過分條理化、規范化、固化的擔心,或許可以減少很多。當然,不應回避的是,系統可以帶來解決問題的強大動能,卻也因其條理化、合目的性而易于形成模式化的問題;而且強大的意志加上強大的貫徹系統,有時會造成巨大的慣性,無論對錯都將被放大。以此,信息回饋、異質信息的適量引入,尤其保持系統運作的彈性,開放糾錯機制非常重要,這相當程度決定了系統運作的方向。
就中共革命系統看,這一系統有很多面相,橫看成嶺側成峰。從結構言,意識形態和組織可以說是中共革命系統的核心要素,意識形態(辯證法)和組織分別構成中共系統思維和系統運作的基礎;從功能言,中共的革命系統又可以分成權力系統、貫徹系統、動員系統、培養系統等等,而這些系統間又是相互影響、相互聯系的,并沒有截然分開。事實上,中共革命既在系統之中運作,又在不斷造就、生成系統。系統運作本身就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二、毛澤東的系統觀
抗戰時期,對中共革命理論產生決定性影響的毛澤東,在系統思維和系統運作問題上多有闡發。(10)關于毛澤東的系統思維,1980年代系統論興盛時,國內學界已有注意。較早的論文包括陳軍:《略論毛澤東同志的系統觀》,《學術論壇》1983年第5期;范幼元:《毛澤東的系統觀》,《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1985年第7期,等等。近年還有羅緒春等的《毛澤東系統論思想初探》(一)(二),《系統科學學報》2015年第2期、2016年第2期。早在1927年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毛澤東使用過系統一詞:“中國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種有系統的權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國一省一縣以至一鄉的國家系統(政權),(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長的家族系統(族權),(三)由閻羅天子城隍廟王以至土地的陰間系統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種神怪的神仙系統——總稱之為鬼神系統(神權)。”(11)《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3月28日),[日]竹內實監修:《毛澤東集》第1卷,日本蒼蒼社1982年版,第235—236頁。鑒于文本對考察毛澤東系統概念使用的特殊意義,在此使用蒼蒼社出版的《毛澤東集》。這里,毛澤東是在同類事物組成的整體這一最基礎的意義上使用“系統”這一概念。
1938年,毛澤東寫作《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已經開始在方法論意義上使用“系統”:“我們要系統來講辯證法,就要講講唯物辯證法的許多問題。”毛澤東進一步強調:“實際上具有唯物的與辯證的頭腦之革命者,他們雖從實際中學得了許多辯證法,但是沒有系統化,沒有同已經成就的唯物辯證法那樣的完備性與深刻性,因此必不能洞察運動的遠大前途,不能分析復雜的發展過程,不能抓重要的政治關節,不能處理各方面的革命工作,因此仍有學習辯證法的必要。”(12)《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1938年),《毛澤東集》第6卷,第299、303頁。在毛澤東看來,是不是系統化地理解辯證法,掌握馬克思主義系統思考的方法論,關涉革命者能否洞察政治發展趨勢、掌握革命運動的方向。正因此,毛澤東說:“如果中國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主義的同志,那將是等于打倒一百個日本帝國主義。”(13)《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2—14日),《毛澤東集》第6卷,第260頁。
不過,對當時中共的現實狀況,毛澤東判斷并不樂觀。他認為,中共的“政治工作的研究有第一等的成績,經驗之豐富,新創設之多而且好,全世界除了蘇聯就要算我們了,其中若干特殊的經驗連蘇聯也沒有,但缺點也在于綜合性與系統性之不足”(14)《戰爭和戰略問題》,《黨的政策選集》,晉察冀日報社1946年版,第60頁。。或許正是要解決系統性不足的問題,延安整風期間,毛澤東非常重視系統性的訓練,指出:“像我黨這樣一個大政黨,雖則對于國內國際現狀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績,但對于國內國際的各方面。對于國內國際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們所收集的材料還是零碎的,我們的研究工作還是沒有系統的。二十年來,一般地說,我們并沒有對于上述各方面作過收集材料與著重研究的系統的周密的工作,缺乏調查研究客觀實際狀況的濃厚空氣。”(15)《改造我們的學習》(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集》第7卷,第311—312頁。他將不系統做調查研究的做法稱為主觀主義:“對于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具體情況,不愿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僅僅根據一知半解,根據‘想當然’,就在那里發號施令,這種主觀主義的作風,不是還在許多同志中間存在著嗎?”(16)《改造我們的學習》(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集》第7卷,第314頁。基于此,他“向全黨提出系統地周密地研究周圍環境的任務”(17)《改造我們的學習》(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集》第7卷,第319頁。。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對于主觀主義的批評,對于缺乏調查研究的批評,都得到了當時乃至后世的充分重視,但他在調查研究前面加的定語“系統的”卻往往被忽略。事實上,這一整風期間反復出現的定語,在毛澤東的思想體系中并非可有可無。
在《反對黨八股》中,毛澤東進一步倡導要改變文風。就一個系統而言,文字關系信息傳輸,改變文風,實際就是要改變系統中的信息反饋狀態,提高信息反饋的有效性。所以他提出:
單單按照事物的外部標幟,使用一大堆互相沒有內部聯系的概念,排列成一篇文章、或一個演說,或一個報告,這種辦法,他自己是在做概念的游戲,也會引導人家都做這類游戲,使人不用腦筋想問題,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質,而滿足于甲乙丙丁的現象羅列。……要解決問題,還須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工作與研究工作,這就是分析的過程。提出問題也要用分析,不然,對著模糊雜亂的一大堆事物的現象,你就不能知道問題即矛盾的所在。這里所講的分析過程,是指系統的周密的分析過程。常常問題是提出了,但還不能解決,就是因為還沒有暴露事物的內部聯系,就是因為還沒有經過這種系統的周密的分析過程,因而問題的面貌還不明晰,還不能做綜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決問題。(18)《反對黨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澤東集》第8卷,第100頁。
在論述群眾路線時,毛澤東再一次表現出以系統取代無系統的要求:“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19)《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1943年6月1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頁。
上述引文中反復出現“系統”兩字,當非偶然,顯示毛澤東以系統思維取代片面、直線式思維的雄心。從毛澤東的要求可以看出,他講的系統,是辯證的、開放的、分疏的、競爭的,和現代一般系統論講的系統具有相通性。事實上,如《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所顯示的,毛澤東的系統觀直接源于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這是他提出系統方法的起點;同時,中國傳統樸素的系統論,相信對其也有潛移默化的影響,至少讓毛對系統論的思維方法不會陌生。抗戰時期毛澤東關于系統思維、系統方法的闡述和呼吁,奠定了中共系統認知的基礎,促進著中共思想和工作方法的提升。抗戰行將結束時,毛澤東在中共七大做口頭報告,再一次將革命、理論、馬克思主義和系統放在一起予以概括:“革命要求我們能說明中國的革命運動,說明這個運動的各個方面,說明它的內部聯系,包括軍事、政治、文化、經濟,整個革命工作的各個側面及其內部聯系,并總結經驗,把它提高起來,使之條理化、系統化。什么是理論?就是有系統的知識。馬列主義的理論,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的有系統的知識。”(20)《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政治報告》(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頁。在毛澤東這里,系統可以說是將革命實踐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有效聯結的鏈條。
三、中共革命的系統實踐
系統思維下,中共革命所有的環節都相互聯系:“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種斗爭要互相結合,同時并用,以一種力量為主,以其他力量配合,靈活運用,按照情況變動。”(21)《對敵斗爭與練兵運動》(1944年12月17日),《第一二○師陜甘寧晉綏聯防軍抗日戰爭時期資料叢書》第7卷,第一二○師陜甘寧晉綏聯防軍抗日戰爭史編寫辦公室1994年編印,第391頁。這樣的思維,可從對晉察冀工作的反省中窺察到:
成為我們工作的中心環的開展民主運動,全民動員,鞏固村政權,鞏固人民武裝,開展社會教育,提高民眾政治文化水準,肅清漢奸賣國分子,制裁壞紳壞人,這些工作都沒有到達應有的收獲,與這一中心環緊緊地套起來的第二環是;生產建設(農業生產、合作事業、手工業等),貨幣金融財政稅收,貿易與糧食布匹這一復雜的聯系,這些工作我們也沒有全面的到達必要的收獲。與第二環緊緊套起來的第三環是:合理負擔、減租減息、優待抗屬、救濟災難;解決停滯的勞力與浪費的勞力,這些我們一般做得更差。(22)《邊區政權工作檢討總結》(1939年7月17日),《新長城》第2期(1939年8月31日),第5頁。
上面這段引文,雖然是對工作的自我批評,卻顯示了中共把工作的各個環節相互聯系、層層遞進的思維方式。這樣的思維貫穿所有工作,組織建設也不例外:“黨的組織建設是黨的整個工作的一部分,它必須與黨的整個工作相聯結,才能夠有真正的建設。建黨不是技術工作,如果建黨脫離了黨的整個工作,而孤立起來去進行建設,那就要把它降低到技術工作的地位,就談不到經常與系統,也就沒有真正的建設。”(23)子榮:《論組織建設》(1940年8月),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匯編》第3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18頁。最終的目標就在于:“我們必須把這些寶貴的經驗加以研究,加以整理,使之系統化,使之變成理論的東西,來指導我們政治工作今后的實踐。”(24)《羅瑞卿同志在北方局黨的高級干部會議上的政治工作報告(續完)》,《前線月刊》第7期(1941年1月),第52頁。
中共很注意提升黨員干部的領導藝術,看趨勢,尋規律,找實質,用聯系的觀點把上下、左右、前后打通,建立系統思維。抗戰甫一開始,毛澤東就雄心勃勃地提出:“加強對干部的教育、培養與提拔……使我們的干部不但能治黨,而且能治國,要懂得向全中國與全世界人民講話,并為他們做事,要有遠大的政治眼光與政治家的風度。”(25)《目前抗戰形勢與黨的任務報告提綱》(1937年10月),《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0頁。眼光與風度,特別能顯示系統思維下中國共產黨人對自身的期許。這段話展現的大格局、大胸懷、大目標,既顯示毛澤東及中國共產黨人的雄心壯志,也成為中共塑造干部的標準。
經過中共的教育、灌輸,中共干部已經一定程度上具備系統看問題的能力。八路軍120師干部陳漫遠結合自身實際談到他對領導藝術的理解,從中可以看到系統思維的特征:1.比較的觀點——“各分區有各分區的環境與特點,司令部各科的情形也不相同;每個科長參謀的出身進步,也各不同。要分別看,又要聯系著看,這樣可以得出其共同的地方和它特殊的情形,才能看出工作好壞的原因及提出具體不同的改進方法”。2.時間的觀點——“看一九四三年的工作,要想到四二年是怎樣工作的,看自己的工作也要從過去看到現在,看問題,看部隊,同樣要從歷史發展上去看”。3.聯系的觀點——“從看一個到幾個,從一地到各地,從一個戰斗推到許多戰斗,從一個人一個科推到另一個人另一科,從開始看到末尾,從布置工作,看到完成任務,從這內部的聯系去找出規律,找根源”。(26)陳漫遠:《在整風座談會上的發言》,《晉綏學訊》第4、5期合刊(1943年5月15日),第24頁。比較、發展、聯系,時間上縱深、空間上連貫,如此有意識地開闊視野、系統思維,在當年中國的政治力量中實非尋常。
干部不僅要有系統思維,還要懂得掌握下屬心理,對癥下藥。劉榮只是一個連級指揮員,卻留下了對戰士心理的詳盡分析:
四連戰士反省坦白中,全連一百七十二人,就有八十幾人有離隊想法。他們主要原因都是想家,或是家里想讓回。八路軍是好的,把兒子送來當八路軍,說是義務兵只當三年,為什么到期滿還不回來呢?希望兒子早點回來。另外,一面當了八路軍,又想到自己的美滿家庭,不肯遠離。但沒有離隊的原因由于:一、路遠(300里);二、怕狼吃;三、怕槍斃。所以一個沒有離隊。從這些現象認為帶領農民出身的戰士,掌握其保守性是中心關節,根本在于啟發教育與團結——從感情到理智、私人到政治,有隸屬關系、同志關系,然后再關注以平時的思想與培養其艱苦精神,就沒有帶不了的兵。(27)《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5年1月15日),中國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250頁。
從陳漫遠和劉榮這兩位分別屬于中共陣營中高和中低級干部的總結中,可以清楚看出中共干部的視野、分析力、領導藝術及向下伸展的程度。
中共強調的調查研究事實上也和系統運作相關。系統運作需要高質量和高數量的信息反饋、回流,以保證系統不出偏差。調查正是系統運作不可或缺的一環:“當遇到一個問題時,善于進行系統思考的人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尋找數據,了解系統的歷史情況以及行為隨時間變化的趨勢。”(28)[美]德內拉·梅多斯著,邱昭良譯:《系統之美:決策者的系統思考》,第124頁。
調查、研究、組織、動員,缺一不可。以戰時非常重要的糧食調度為例,當年的報道呈現了各個環節協調展開的案例。由于各地區乃至地區之間駐兵和糧食產出情況不一,根據中共統籌管理政策,需要展開糧食調度。糧食調度耗用大量人力物力,要做好這一工作,調查非常重要:“調查了各地駐軍的性質及其數字,各地糧種及其數字,各地人力與馱口力,決定了糧食流的方向——大方向、小方向,小米流的方向與豆子流的方向,以及運輸的路線。”如此方能做到心中有數。調查之后,再組織運輸,“一級一級算賬,一級一級具體”。組織運輸需要精心設計,報道特別強調,有效的組織中,“‘想’起了很大的作用”,所謂“想”,就是計劃,動腦筋,“有時多捉摸了一下,一個區或一個村一個人就要少運一次,……省下不少人力”。“想”又不是空想,“是根據實際的材料,根據了具體的數字一點一滴來算,根據了農民的特點來想辦法”。比如想到實行包干的辦法,“規定了一村運多少就完了,他就起了勁,爭著先運完了事”。計劃、辦法都有了,最后當然還是要貫徹,“動員與組織干部”予以落實。從調查到算賬到計劃再到落實,一系列組合拳下來,結果就是“為調度糧食所花的勞役,比去年減少三分之二——每一勞力一般在四次至六次之間,各村負擔并很平衡”。(29)向純:《從四專區調糧工作里看到的》,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邊政導報編委會編:《邊政往來》第2卷第8期(1942年12月5日),第24—26頁。
1943年,景曉村聽過中共山東分局書記朱瑞的報告后感嘆:“全篇總結的系統性、連貫性非常緊湊,尤其是朱瑞同志這個總結,即是問題的前后現象,本質與根源,甚至根源的根源,一層深一層的指出來,而不是各個問題分割的,也不是只是許多問題的現象的排列,這說明了對這些問題認識的系統性與透徹性。”(30)北京八路軍山東抗日根據地研究會渤海分會編:《景曉村日記》(1943年5月22日),內部發行,2012年版,第48—49頁。系統、聯系、深入,正是中共一直追求的方向。1949年,竺可楨記下陳毅的一段話:“陳毅市長講一小時,述理論對于革命之重要。謂共產黨之成功,由于知識高于國民黨。”(31)《1949年6月9日日記》,《竺可楨全集》第11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57頁。從知識角度總結國共勝敗,陳毅的確獨具慧眼。這里的“知識”,應該指的是思維方式、思想資源、理論高度,也就是認知和面對世界的方式。在這方面,由于馬克思主義提供的精神資源,中共確實較之其他政治力量高出一籌,而系統性思維帶來的力量,也是中共知識勝過國民黨的重要砝碼。
結語
中共革命就像一個齒輪咬合的巨大機器,環環相扣,一旦運行,全力以赴,效力驚人。大多數時候,觀察者會把這種驚人的效率歸結為組織上的嚴密。這的確是中共革命的關鍵,也是國際共產主義政黨的共性。組織架構的嚴密和馬克思主義賦予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屬性相關,既然承擔著先鋒隊的任務,保證這支隊伍的先進性就十分重要。而要讓一個組織合乎自己的意愿,不可避免需要淘汰、清洗,需要建立保證淘汰、清洗能夠展開的規則,不斷強化這樣的規則成為組織的內在要求。組織的嚴密性就是這樣慢慢形成的。
另外,共產主義運動所處的環境也提出嚴密組織的要求。共產主義運動以完成馬克思主義提出的階級革命目標為使命,這是對現有的統治秩序乃至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秩序的全面顛覆。這樣的任務,不可能在一團和氣中完成,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革命幾乎都在腥風血雨中開展,當非偶然。這樣的成長環境,注定了承擔這一任務的力量會努力嚴密自己的組織,保證這支力量的高度凝聚力。
強大的組織力并非單純依靠組織架構的設計即可實現。1924年改組后的國民黨,組織架構大量引進蘇共模式,組織層級和中共幾無二致。然而,了解國共組織實際運作的人大概都知道,大致相似的組織體系發揮的效能大相徑庭,蔣介石和國民黨人自己也認為國民黨很大程度是敗在組織上。實際上,較之大多數政治力量,國民黨的組織已經堪稱嚴密,只是較之中共瞠乎其后而已。1938年,蔣介石曾通令部下,提示:“每星期必須限令各排班長,分別組設小組會議,公開討論本組本星期經過之缺點與優處,以及各人技能學術勤務成績之優劣,由連長或排長嚴加指導……并準各兵士自我批評”;“軍隊精神,須注重民主化,官長尤要士兵化”。(32)《蔣中正電示陳誠令中央直轄各師長加緊培訓下級干部并注重精神教育》(1938年3月1日),《蔣中正總統檔案》,臺北國史館藏,檔案號:002010300010002。這些措施和中共何其相似,但論到落實,則相距不可以道里計。國共兩黨的比較可以證明,嚴密的組織體系是通向嚴密組織的一部分,但要真正讓嚴密的組織落到實處,中間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組織要運轉,還是需要人,不同的人群對組織力的落實會有相當不同的影響。中共嚴格的紀律是保證組織嚴密不可或缺的環節,但要真正建立嚴格的紀律,不是容易的事。嚴格的紀律下,政治力量的維系需要依靠資源分配、核心理念、團體的向心力、懲戒制度等。中共奪取政權前,可供分配的資源實在有限,保持紀律依靠的主要是后面三者,其中核心理念對于中共這樣的意識形態政黨發揮的作用尤其重大。像中共這樣一個長期處于在野地位、生存艱難的革命黨,沒有理念的支撐,組織的嚴密、紀律的落實,都成無源之水。正因此,干部教育和政治宣傳長期成為中國共產黨工作的重中之重。這里面,有這一政黨內在的邏輯在。
當然,組織、紀律、理念是一個相互作用、互為促進的統一體。歷史的具體進程中,常常很難辨別何者為主、何者為從,更無法截然分開,這是一個相互影響的運作系統。條件成熟后,這套系統就可以形成類似自組織狀態的運行,各種因素互為因果,相須并進,驚人的效率就是這樣煉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