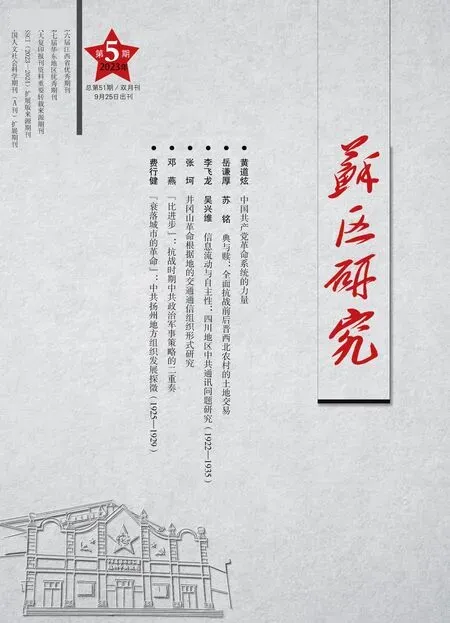“衰落城市的革命”:中共揚州地方組織發展探微(1925—1929)
費行健
國民革命興起后國共兩黨競相發展“黨勢”,中共江蘇地方組織迅猛發展。揚州是清代中葉鹽政、漕運的中心,古時更有“揚一益二”之稱,顯示出古代揚州的重要地位和繁榮景象。然而,隨著近代交通方式的變革以及經濟版圖的重構,近代的揚州城市地位急劇下降,由清中葉的全國性的商業中心,下降到江淮地區區域中心。揚州城市的近代工業較為落后,“很少新興工業”,以手工業為主,“除各縣城和較大市鎮上的電燈廠,很少的碾米廠以外,就只有很少數的手工工廠規模較大”。(1)《揚州特委關于揚州區工作計劃》,中央檔案館、江蘇省檔案館編:《江蘇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4,內部印行,1989年版,第475頁。“揚州很少產業工人,因此小資產階級(尤其是學生)更顯見其重要作用”(2)《江蘇省委致揚州縣委的指示信——對目前揚州工農兵各項工作、宣傳組織工作》(1929年12月2日),《江蘇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8,內部印行,1985年版,第183—184頁。;“農民更無組織”(3)《揚州特委關于揚州區工作計劃》,《江蘇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4,第479頁。,難以發動農民革命。
近年來隨著新革命史的倡導,學界開始將中共革命、地方黨組織與地方社會視為一個整體,將中共革命置于“地方視域”加以考察。王奇生是大陸學者中較早地以組織形態角度研究地方黨組織問題的學者。即從黨組織的內部結構、組織運行以及與不同層級間、黨與群眾間的互動進行一種基于社會學層面的分析。王奇生考察中共廣東黨組織的黨員構成、紀律和支部生活、經費來源和黨內交通、黨組織的內部關系和外部關系等情況發現“廣東的中共地下黨組織松弛渙散,支部有名無實,黨員缺乏訓練,入黨、離異均甚隨便”,而白色恐怖與經濟拮據是地下黨組織面臨的兩大困境。(4)王奇生《黨員、黨組織與鄉村社會——廣東的中共地下黨(1927—1932)》,《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第1—45頁。李里峰考察抗戰時期山東根據地的地方黨組織的黨員群體、干部群體、組織結構和效能、黨員和干部的教育等問題發現“長期戰爭面臨的困局,迫使中共在農民中大量發展新黨員,在意識形態理想和現實斗爭需要之間存在著難以消解的困境”,指出“抗戰時期黨組織的空前發展,很大程度上歸因于當所采取的現實策略和權變之道。”(5)李里峰:《革命政黨與鄉村社會: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形態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92頁。王才友發現舊鄉紳培養起來的青年學生成為國共兩黨在基層社會發軔和競爭及其與舊鄉紳產生代際沖突的重要基礎。在國共之爭的大背景下,舊士紳日趨勢微,但是在浙江平陽縣等地舊鄉紳依舊可憑借代際關系參與到“黨治”與革命之中。(6)王才友:《政黨競爭與代際沖突:反革命視域下的浙南革命(1921—1934)》,《中共黨史研究》2019年第11期,第76—93頁。李里發現1927—1937年間中共在白區的地下機關設置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在1927—1929年的第一階段,中國試圖通過租賃房屋來設置龐大的地下機關體系。在1930—1932年的第二階段,中共試圖通過推行機關群眾化緩解地下機關設置困境。在1933—1937年的第三階段,中共一方面轉移和收縮機關,另一方面突破‘左’傾關門主義,重新將群眾工作放在公開的群眾運動中”。(7)李里:《中國共產黨地下機關設置的調適(1927—1937)》,《歷史研究》2023年第2期,第120—140頁。張仰亮聚焦1927年之前的中共上海地方組織的組織形態和工人動員,指出上海地方組織運轉的成效和不足,稱上海的革命是“中心城市的革命”。(8)張仰亮:《中心城市的革命:中共上海地方組織及工人運動(1920—1927)》,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294頁。對于國共兩黨政治關注度、斗爭激烈程度較低的城市,學界相對較少關注。在這些缺乏革命土壤的地方,黨組織如何落地發展,黨員的社會構成與革命實踐的開展中存在的問題等,都存在進一步考察的空間。筆者以揚州(江都縣)(9)本文所指的江都縣,為民國時期的一等縣,其縣治所位于今揚州城區,并非現今揚州市江都區。本文的描述對象主體為民國時期江都縣轄區內的中共組織活動。一些歷史文獻稱為揚州縣,文中的江都縣與揚州縣為同義詞。文中所涉及的行政區劃范圍以民國時期為準。這一“古代的都市,淮海鹽商的根據地,江淮地主、官紳的集中地”(10)《揚州特委工作報告——關于環境、各種斗爭及黨的工作》(1928年11月1日),《江蘇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4,第457頁。為考察對象,嘗試還原黨組織從“落地”到發展再到革命實踐的歷史過程,進而思考城市衰落與革命的關聯,是否對革命和黨組織的發展產生影響,會對革命產生何種影響。(11)關于近代揚州城市衰落與近代化困境,可參見葉美蘭:《封閉:中國近代城市現代化困境的癥結——以揚州為個案》,《社會科學輯刊》2001年第6期,第116—121頁;葉美蘭:《近代揚州城市現代化緩慢原因分析》,《揚州大學學報》2004年第4期,第91—95頁;葉美蘭:《試析制約揚州城市現代化的主觀因素》,《學海》2006年第1期,第149—155頁。
一、中共揚州地方組織的“落地”與革命的萌芽
1925年5月上旬,中共早期無產階級革命家、青年運動的著名領袖惲代英,以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宣傳部秘書(副部長)的身份來到揚州。惲代英首先來到江蘇省立第五師范發表演說,其演講題目為《師范生與飯碗問題》,內容包括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等。他號召揚州的廣大青年學生投身到國民革命的洪流中去,以改造社會、改造中國為己任,國家和民族才有希望,青年才有希望。此次演講后,惲代英又到省立第八中學演說,進一步擴大動員影響,揚州學生一時間熱血昂揚。(12)中共揚州市委黨史辦公室編:《中國共產黨江蘇省揚州歷史》第1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21年版,第28—29頁。關于惲代英前往揚州的具體時間,似有不同說法。據《惲代英年譜》記載,5月21日,(惲代英)準備赴揚州演說。受到揚州第五師范、第八中學的邀請,已得惲君(惲代英)許可,一候來揚,即行演講。10月7日載“秋季,到揚州,在第五師范、第八中學演講,題為《師范生的飯碗》”。另外曾在第五師范就讀的學生張一萍回憶惲代英的演講在下半年,成貽典回憶是在5月。成貽典當時是高三班的學生,年齡比張一萍要長。筆者個人傾向于惲代英兩次到達揚州,惲代英5月受邀請準備演講內容,說明不久就將演講;如僅僅在10月演講一次則不符合常理,演講通常是演說前準備,提前幾個月準備不符合常理。兩人的回憶內容相近,唯有時間不同,年譜中兩次提及,可能是兩次到揚州演說。參見李良明、鐘德濤主編:《惲代英年譜》,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73、283頁。經惲代英介紹,青年學生李誠、曹起溍、王壽荃、潘錫純等人加入國民黨。惲代英的這次活動不僅發展了一批國民黨黨員,同時也為揚州中共地方組織的建立做了準備。
揚州中共地方組織最早建立于何時,尚無明確定論。1926年底中共江浙區委的一份工作報告稱揚州有6人。(13)關于揚州建黨的時間,揚州官方黨史部門認定的建黨時間是1927年,但認為在此之前就已有黨員活動。(《中國共產黨江蘇省揚州歷史》第1卷,第31頁。)江蘇省委1927年10月報告稱:揚州今年“上半年有同志17人,現有六七人,已指定王壽荃同志成立獨支。”(14)《中共江蘇省委關于各縣黨的組織及工作概況》,《江蘇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內部印行,1984年版,第198頁。揚州的中共早期黨員曹起蘅、羅青、陳洪進、顧寶艮等人回憶:1925年秋,曹起溍在省立第八中學建立黨支部,這是揚州的第一個中共組織。(15)《中國共產黨揚州史》第1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頁。但揚州的團組織建立時間有確切時間記載:1926年6月下旬,揚州有團員4人,下半年發展至6人,建有共青團特別支部,隸屬于共青團江浙區委。(16)《團江浙區委最近三個月工作情況報告》(1926年6月25日和12月31日),轉引自《中國共產黨江蘇省揚州歷史》第1卷,第31頁。
國共合作期間,揚州的中共黨員以國民黨江都縣黨部執行委員的身份進行公開活動,秘密身份是中共黨員。故揚州的中共地方組織前身是惲代英所動員并創建的國民黨地下組織,共產黨員以國民黨黨員的身份活動,公開身份則大多數為在校學生。學生、學校和黨組織成為相互關聯的整體,學校既是學生學習的場所,也成為了地下黨組織的活動載體。
1927年4月,國民黨厲行“清黨”,江蘇省黨部負責人、共產黨人侯紹裘被殺害,國民黨江都縣黨部的青年黨員們隨之產生分化。原國民黨江都縣黨部常委李誠選擇脫離中國共產黨,加入右派實控的國民黨江都縣黨部。(17)據李誠于1950年向上海軍管會的交代材料。絕大部分青年學生或升學或就業,還有些人選擇返鄉躲避,以防在國民黨清黨時被認定為共產黨人。王壽荃、曹起溍兩人沒有選擇升學或就業,而是選擇不畏艱險繼續進行革命活動,成為職業革命者。1927年8、9月間,王壽荃在上海與原國民黨江蘇省黨部特派員、中共黨員陳勃取得聯系,經陳勃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8)關于王壽荃返回揚州的時間及揚州中共組織成立時間有不同說法。據江蘇省檔案館、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江蘇黨史大事記(1919—1949)》,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65頁;王壽荃于1927年8月被派往揚州,9月成立揚州獨立支部。(《中國共產黨揚州史》第1卷,第36頁);9月中共江蘇省委批準成立揚州獨立支部,指定王為書記。王壽荃本人回憶,8、9月間在上海聯系到陳勃。王認為:“揚州的中共黨組織成立時間應當晚于八七會議之后,有人認為1927年之前揚州就有黨組織,是把國民黨的左派組織誤認為是共產黨的地下組織了。”(中共江都縣委黨史辦公室編:《江都縣革命史料》,內部印行1985年版,第141頁。)王壽荃回到揚州后,即與曹起溍聯系,建立中共揚州縣獨立支部,有黨員7人。12月改為中共揚州縣特別支部,下轄揚州中學、耀揚火柴廠兩個支部,共計11名黨員。1928年,王壽荃離開揚州,由曹起溍代理書記。
梳理上述史實不難看出,中共揚州地方組織的“落地”是以國民黨組織的名義完成的。國共合作時期,國共兩黨競相發展黨勢,皆派員回鄉,發展黨員,建立黨組織。(19)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修訂增補本)》,華文出版社2010年版。揚州的國民黨組織既沒有黃埔軍校學生回鄉動員,也非本邑人士創建,更不是同盟會時期的黨員所建。同樣,揚州中共地方組織創建也沒有本邑人士的因素。這一點與江蘇省內絕大多數地方有所不同。(20)江蘇省地方志編撰委員會編:《江蘇省志·國民黨志》,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江蘇省地方志編撰委員會編:《江蘇省志·中共志》,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中共江蘇省委黨史辦公室編:《中共江蘇地方史》第1卷,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等。那么,揚州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一般而言,革命的產生需要一定的社會要素,人口過度增長、資源分配不均、自然災害、宗教沖突、土客之爭等都有可能催生革命。而上述因素在近代的揚州均不顯著,內生革命的可能性較小,多表現為工人加薪、農民減租這一類低烈度的社會運動,無法成為高烈度的暴力革命。揚州近代政黨最早產生的具體時間無從考訂,但可以確定在民國初年揚州已誕生近代政黨組織——中國社會黨揚州支部。(21)陳沛:《中國社會黨揚州支部始末》,《揚州文史資料》第4輯,內部印行,1985年版,第138—140頁。同時民初政黨政治確實曇花一現,很快失敗。迨國民革命興起,揚州一直無人參與建立地方黨組織的工作,直到惲代英到來,國民黨組織才得以建立,而中共揚州地方組織則是由國民革命期間的國民黨組織裂變而成,一部分黨員成為國民黨右派,大部分升學,王壽荃、曹起溍繼續堅持,揚州中共地方組織始得以建立。故筆者認為,揚州建黨沒有本邑人士因素屬于偶然現象,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近代揚州城市地位下降,成為政治版圖中“被遺忘的城市”。
二、主要黨員、黨員社會構成與黨組織工作的主陣地
揚州中共地方組織創建和發展的主要參與者是學生,包括揚州當地在校學生和揚州在外地求學的學生。揚州最初的一批共產黨員王壽荃、曹起溍、陳洪進、曹如福、羅青、胡耐秋、成貽典、張一萍等人均是在校學生。(22)王壽荃:《我在揚州參加中共揚州地下黨早期活動的情況》,《江都縣革命史料》,第141頁。以上所列的揚州早期中共黨員的身份,筆者以當事人本人的回憶材料為準。揚州中共地方組織的發展過程并非一帆風順的,黨員數量和社會影響力相對有限。據1928年7月的報告,“當時城內六個支部、八個小組,計:1.揚中支部二組11人(學生八,工人三);2.耀揚支部二組20人(女工4,男工16);3.香業支部3人(二人系工人領袖);4.黃包車夫3人;5.舊城支部4人(學生1,自由職業2,職工1);6.新城支部4人(學生2,自由職業2)。總計45人,工人30,學生11,自由職業4。另外,揚州特支還有四個農村支部,共計21人。”(23)《揚州特支(1928年)七月十五日的工作報告》,《揚州革命史料選》第1輯,內部印行,1984年版,第17—30頁。另見《江蘇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4,第425—426頁。
1928年7、8月間揚州特支的負責人有:書記 王壽荃(1927.9—1928.5)、曹起溍(代理,1928.5—1928.7);干事會 曹起溍(1927.9—1928.8)、蔡興(1928.7—1928.8)、郭成昌(1928.7—1928.8)。(24)《中國共產黨揚州史》,第403頁。蔡興是校印刷廠的工人,1931年被捕,叛變投敵;郭成昌原是旅法華工,由中共江蘇省委派至江都縣搞黨的工作,1929年2月被捕,判處一年零二月的有期徒刑,后情況不詳。(25)《第一、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共江都縣黨組織歷史發展簡況》,《江都縣革命史料》,第74頁。就揚州特支黨員的職業(成分)而言,此時的工人黨員占66.7%,學生僅占24.4%,另有自由職業者(知識分子)、佃農、雇農、自耕農、青幫成員等。通過《揚州特委工作報告——各種斗爭及黨的工作》(1928年11月1日)》中的《活動分子調查表》,可以更加清晰直觀的看出揚州縣委主要黨員的個人履歷,并分析其社會構成。(具體見表1)

表1 活動分子調查(1928年11月1日)
從表1可知,揚州特委下屬的揚州縣委和相鄰幾個縣的縣委共有活動分子20人。在性別上,男性19人,女性1人,男女黨員比列相差懸殊。這意味著婦女工作人手嚴重不足,工作難有建樹。年齡分布上,有年齡統計的黨員中,全部是30歲(含)以下的青年人,且大部分為25歲以下的青年人,青年群體聚合的社會特征尤為明顯。籍貫方面,除郭成昌為上級黨組織指派;耀揚火柴廠支部李新康是淮安清江浦人,劉志滄是鎮江人在儀征工作,非本地人;其余黨員絕大多數是本邑人士,這一點是有利于黨組織發展的。黨員本地化可以充分利用社會關系網絡,從熟人入手,壯大組織規模。職業分布上,小知識分子、農民、工人都包含;其中,學生2人,占10%。教員4人,占20%。工人7人,占35%。農民2人,占10%。失業店員2人,占10%。另有醫生1人、專職黨務1人、幫會分子1人,各占5%。學生、教員、醫生屬于小知識分子,合計7人,占35%。,加上失業店員2人,合計9人,占45%。(26)2位失業店員的學歷無從查證,但這一年齡段的加入中共地下組織的城市青年,一般均接受過教育,不太可能是文盲,也可以劃分為小知識分子。即此時揚州特委的活動分子中,小知識分子和工人占據大多數,且負責人郭成昌是工人出身,“工人黨”的特征顯著。且失業工人、佃農等有津貼或生活費補助,而學生黨員卻沒有。
就1928年全國范圍內的中共組織黨員構成而言,這一點似乎并不意外。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于莫斯科召開。在會上,共產國際過分強調“領導干部成分工人化”的組織原則,工人出身的向忠發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主席。隨之,許多中共省委及下屬黨組織主要負責人同樣由工人黨員擔任。知識分子出身的李富春也不再適合擔任江蘇省委書記,遂改組江蘇省委。10月17日,根據中共中央通過的一份江蘇省委名單,正式常委有7人,分別是羅登賢、曾山、何孟雄、馬玉夫、徐炳根、徐錫根、王克全,除曾山和何孟雄外,其余均是工人出身。(27)曹英:《中共選擇了毛澤東》,華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311頁。江蘇省委就南通、揚州組織的發展也指出:“近北各縣自指<導>機關一直到支部及群眾工作人員,尚未提拔工農分子,仍是知識分子包辦,堅決勇敢分子屢遭損失,新起的工農未提升而接不上來,正值近北群眾斗爭已到劇烈的開始,至整個黨表現動搖。固然另有原因,上級的指導不能下去,未建立密切的關系,不過原因之一;而主要原因,仍是未發動群眾的斗爭,提拔勇敢工農知識分子,實為這區工作的危機。”(28)《江蘇省委關于南通和揚州區的決議案》(1928年),《江蘇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4,第343頁。
1928年7月中共江蘇省委決定組織淞浦、滬寧、南通、淮鹽、徐海、揚州等6個特委,其中揚州特委領導揚州、泰州、高郵、寶應、東臺、興化、六合等縣。(29)《江蘇農民秋收斗爭決議案》(1928年7月),《江蘇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3,內部印行,1985年版,第609頁。1928年9月,中共揚州特委正式建立,但僅有書記夏采曦(30)夏采曦(1906—1939),江蘇嘉定(今屬上海)人。1919年入上海民立中學,任校學生會評議部長。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后歷任揚州特委書記、南京市委書記、江蘇省委宣傳部長等職。1939年在蘇聯因“肅反”擴大化而犧牲。(化名李斐)一人。1929年,又增加一名負責人李濟平(31)李濟平(1908—1930),江蘇江陰人。1924年畢業于勵實中學,后到天章綢緞店當學徒。1927年參加中國共產黨,任中共江陰縣委委員。同年赴蘇聯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1929年1月擔任中共揚州特委委員,為特委負責人之一,9月任中共江都縣委書記,12月調任中共江蘇省委巡視員。(化名趙亞)。中共揚州特委建立后,把有計劃地發展全區各地的黨組織作為中心任務。(32)《中國共產黨江蘇省揚州歷史》第1卷,第40頁。經過揚州特委的整頓、改進,并派員在轄區內新建了一些黨組織,揚州特委下屬各個縣基本建立了中共基層支部,發展了一批黨員。
夏采曦名義上為揚州特委負責人,但實際上只有組織,沒有干部,他認為“特委本身太可憐了,什么都是我一個人”。(33)《揚州特委最近工作報告——關于組織、職運、農村、青年及今后工作問題》(1929年2月12日),《揚州革命史料選》第1輯,第38頁。工作推進困難重重,甚至需要花錢雇傭助手,處理黨組織日常事務。“曾找到一個技術工人,但這是一個死要錢的書呆子,最近他已不高興做工作,到農整會當干事去了,(三十元一個月),要另找人非常困難,而且大概非要給生活費不可。因為同志們都窮的要死,找職業。”揚州特委雖然建立,但缺乏得力的干部,此時的夏采曦雖是揚州特委負責人,但實際作用卻相當于江蘇省委和下屬縣委間的聯絡人與縣委工作仲裁人。根本無法統籌下屬各個縣的組織工作,甚至離開揚州都很難,因為揚州縣委工作無法正常運轉。李濟平到揚州后,情況稍有好轉,“特委以前是我一人,一個多月前才派了李濟平同志到揚工作,增加了一個負責,當然應付工作起來比較強多了”。但“濟平同志沒有參加什么實際工作,方從莫京回來,對于中國革命情形也不很熟悉,因此,他布置工作也不怎樣得力。我們商量工作問題,他很少有意見發表,或竟沒有,而且特委只二人,當然還是很弱”。(34)《揚州特委最近工作報告——關于組織、職運、農村、青年及今后工作問題》(1929年2月12日),《揚州革命史料選》第1輯,第38頁。《江蘇革命歷史文件匯集》標記時間為1930年2月12日,似乎有誤,按內容李濟平剛剛返回,李濟平返回的時間是1929年1月。(中共揚州市委組織部編:《中國共產黨江蘇省揚州市組織史資料(1926—1987)》,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6頁。)揚州特委的工作還是夏采曦一人處置,揚州特委干部力量依舊空虛。
中共揚州縣委最早的兩位負責人是王壽荃和曹起溍。曹起溍,1906年出生在一個職員家庭。1922年,曹起溍進入江蘇省立第八中學讀書,在進步教師的影響和指導下,他開始閱讀一些進步書籍,受到很大的觸動和影響,萌生了革命的意識。1925年秋,經惲代英介紹,曹起溍等人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暑假,曹起溍考入上海南洋公學,因家庭無力資助他上大學,揚州一時又難以找到合適的職業,曹起溍決心留在家鄉干革命。同年,在國民黨江都縣黨部的選舉和分工中,曹起溍任組織部部長兼執行委員。國共合作破裂后,1927年9月,曹起溍與王壽荃建立起中共揚州特別支部。1929年8月16日,曹起溍不幸被捕。1931年2月24日,曹起溍犧牲于鎮江北固山,年僅25歲。
王壽荃,1907年出生于安徽,1919年隨父兄來到揚州定居。王壽荃與曹起溍是第八中學的同學,王壽荃成績優異,在同學中很有號召力。國共合作時期,在國民黨江都縣黨部中擔任宣傳部部長和執行委員,后任中共揚州縣委書記。王壽荃在揚州城內發展了一批青年黨員,和曹起溍一道前往農村開展工作。1928年五六月間,王壽荃因為個人生活方面原因離開揚州,一是因為家庭負擔,自己沒有固定職業,二是因為他父親對他逼婚,使他想離開揚州。王壽荃離開揚州后,先到江陰參與指導農民運動,因身體羸弱,得過幾次重病,心灰意冷,于1930年脫黨加入國民黨。1949年在新疆參與策劃起義活動,1950年由香港返回北京,重新參加革命工作。1972年于北京逝世,享年65歲。(35)《江都縣革命史料》,內有關于曹起溍、王壽荃生平情況的介紹,上述兩段以相關人員憶述資料為依據。王壽荃在國共內戰時期曾是張治中部下,為新疆和平解放作出一定貢獻。曹起溍和王壽荃兩人的經歷也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白區地下黨員的艱難,職業革命者對于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巨大差距,選擇了不同的道路,進而走向不同的人生軌跡,卻又最終歸于同路。當然,客觀而論兩人都不是出色的縣委領導者,這一時期揚州特委書記夏采曦才是實際領導者。
中共揚州特委建立后不久即決定解散揚州縣委,由揚州特委兼揚州縣委。(36)按《中國共產黨揚州史》《中國共產黨江蘇省揚州市組織史資料(1926—1987)》《揚州市志》等文獻的記載,“中共揚州特委建立后不久即決定解散揚州縣委,由揚州特委兼揚州縣委”。筆者閱讀原始檔案文件發現,1928年9月至10月間揚州特委與揚州縣委有過短暫的共存時期。筆者推斷兩個黨組織共存期間,類似于當今的兩塊牌子、合署辦公。同時對揚州城區區委和揚州西鄉區委進行整頓改組,決定由曹起溍和郭成昌分別擔任兩個區的區委書記,由揚州特委直接領導。夏采曦批評稱:“縣委=0,所以我把他解散,以后由特委兼任”。(37)《揚州特委工作報告》(1928年11月1日),《江都縣革命史料》,第9頁。“城區原有支部5個,人數44人,區委1個,5個人,新找到未成立支部的零星同志4人,西鄉原有支部5個……這次我下鄉去調查,大概那里同志不過三十余人,所謂支部、區委的組織全是虛的,他們連會都沒開過一次。成分:城區11個知識分子,余皆工人、店員等。西鄉有五六個流氓頭兒,四個自耕農,其余皆佃雇農,但都是流氓的徒弟。城區區委改組,書記曹,常委蔡興(校工)、林棲(知識分子)……西鄉區委書記郭成昌、委員張德旺(青幫流氓)、顧××(學生,新派下鄉)、孫玉喜(系雇農,很好)、胡文德(佃農)。(38)《揚州特委工作報告》(1928年11月1日),《江都縣革命史料》,第8—9頁。揚州特委指出:“揚州城廂和西北鄉是從前唯一的工作區域是比較很健全的。城廂組織也有新的發展……這里是我們工作的中心,同志約在八十人以上。揚州西北鄉同志從前有50至60人。但因負責工作同志的錯誤,同志不認識黨,以為黨是出錢收買黨員的。流氓成分是絕對的,同志幾乎全是兩個流氓頭兒的徒子徒孫。三個月前曾有一度捕人的謠言以后,同志幾乎全體脫離關系,只剩十幾個想向黨要錢的人,膽小非常。最近曾幾度派人去,但錢和工作他們總沒有正確觀念,而流氓又向黨要挾,現在尚無辦法。”(39)《揚州特委最近工作報告及今后工作計劃》(1929年2月12日),《江蘇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4,第623、624頁。
同時夏采曦對于曹起溍和郭成昌兩人的工作狀況很是不滿,對于二人的評價相當負面,認為“縣委、區委都開不成會,事實上縣委是曹起溍一人負責,他鬧戀愛,什么事都敷衍。”(40)《揚州特委工作報告》(1928年11月1日)》,《江蘇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4,第463頁。夏指出城區工作“非常紊亂”。至于郭成昌更是毫不留情,認為“他膽子太小”,“公安局曾派一次便衣偵探去,他就不敢下鄉去,他不下鄉去,那邊又無從接收”。“農民同志一部分散了,到各地做工去了。后來他下鄉,卻又瞞著我住在城內,又私到儀征去玩。”(41)《揚州特委夏采曦給省委的工作報告(十一月)——關于組織情形》(1928年12月12日),《江蘇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4,第490頁。夏采曦只得另派一個同志和他一同下鄉,恢復工作,“一方面監視他,一方面接收工作。”(42)《揚州特委夏采曦給省委的工作報告(十一月)——關于組織情形》(1928年12月12日),《江蘇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4,第491頁。在夏采曦看來,曹起溍空有革命信仰,工作經驗和能力嚴重不足;郭成昌更是不稱職,甚至需要“監視”工作。這一細節顯現出揚州縣委缺乏能力出眾的領導者,進而言之,國統區的中共地下組織普遍缺乏得力的干部,導致工作開展艱難,層層折扣,革命的工作計劃與革命實踐相背離。
揚州縣委工作的主陣地集中在揚州城區和揚州的西北鄉一帶。城區的黨員主要是青年學生以及由青年學生所動員加入黨組織的工人,主陣地是揚州中學和耀揚火柴廠。(43)1927年6月,江蘇省立第五師范學校和省立第八中學合并,成立江蘇省立揚州中學。耀揚火柴廠是揚州的一家私營企業,內有300多名工人,其中男工60多人,女工200多人,童工50多人,一直是揚州工人運動的中心。西北鄉一帶的黨員多為幫會成員(農民),對于黨組織還缺乏理性認識,僅僅是通過幫會內的師徒關系或者傳統社會里最常見的團體聚合模式即血緣、地緣關系進行聯系。黨的觀念很薄弱,鄉村社會的傳統關系在很大程度上取代黨的意志。鄉村工作進展困難,“農民膽小(比較青年和兒童),難接近。難存身,因生人一到,農民就疑惑是盜匪”。(44)《七月十五日至八月十五日的工作報告》,《江蘇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4,第433頁。近代以來的中國社會,農民、會黨與農村,學生、工人與城市,城鄉人口二元化傾向愈發明顯。對于城市的產業工人而言,隨著產業規模的擴大,近代新型業緣組織的地位與作用也日益凸顯。與城市相反,農村則完全是通過傳統的“熟人社會”進行聯系,以實現人與人的聚合。
揚州近代工業并不發達,產業工人與近代工廠較之于滬寧地區的上海、無錫等發達地區仍是數量有限且規模較小的。“江都的工人,只有振揚電燈廠,火柴工會(火柴廠),是機器工人,其余全是手工業者,和家庭工業者。”(45)《七月十五日至八月十五日的工作報告》(1928年7月19日),《江蘇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4,第429頁。故而揚州城區雖建有較為完備的黨組織,但就其對學生和產業工人的動員效果而言,顯然遠未達到上級黨組織設想的要求。雖然對于城市的產業工人而言,隨著產業規模的擴大,近代新型業緣組織的地位與作用也日益凸顯。但是由于揚州的近代工業并不發達,產業的集聚度很低,揚州特委對此也深感棘手:“流氓非常成問題。火柴廠罷工每次受流氓的阻礙。我們已克服了一部分流氓,但同志都是青幫,同志的老頭子搗蛋——爭斗時受廠方囑托來說情,非常難對付”。(46)《揚州特委最近工作報告——關于組織、職運、農村、青年及今后工作問題》(1929年2月12日),《揚州革命史料選》第1輯,第38頁。耀揚火柴廠內的男工多數為幫會成員,對于黨組織還缺乏認識與理解,僅僅是通過幫會內的師徒關系或者說是傳統社會里最常見的團體聚合模式,即血緣、地緣關系為紐帶進行聯系。即使是產業工人和工人黨員也無法脫離傳統“熟人社會”的桎梏。江蘇省委對于耀揚火柴廠的組織問題特別提出:“(一)群眾的組織問題毫未提及,是個很大的缺點。(二)支部的工作最重要的必須使每個同志能做工作……(三)支部工作主要的是要全體同志到群眾中起作用。(四)目前整頓支部健全支部工作,……舊的同志如果不是有大不了的錯誤,不必機械的不要他們,同時還要注意發展新的同志,并要發展女工同志。”(47)《江蘇省委復揚州縣委信》(1929年11月8日),《江都縣革命史料》,第33—34頁。另見《江蘇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8,內部印行,1985年版,第40、41頁。由此可見,耀揚火柴廠內的工人黨員一則是數量較少;二則大多仍是以地緣、血緣為紐帶的幫會成員為主體;三則耀揚火柴廠是一個以女工為主體的工廠,但女性黨員的數量還是遠遠不足,不能充分在女性工人中宣傳黨的勞工政策,進而有效組織女工斗爭。
三、革命實踐:黨員與黨組織視角
革命由口號到實踐、由紙面到落地的過程,黨組織無疑是關鍵性的因素,而黨組織又是由無數的黨員個體所構成的。黨員、黨組織與革命實踐三者密不可分,三者所扮演的角色各不相同,整體上相互之間又有緊密的關聯,共同構成革命的三大結構性要素。那么在青年黨員記憶中的革命和黨組織文件中的革命設計,有何異同之處?黨員是否能夠達成黨組織的要求呢?
王壽荃作為揚州縣委書記,在白色恐怖的環境下發展黨員、壯大黨組織力量,保證生存是一切的前提。王壽荃回憶在城區發展黨員的情況:“發展黨員主要是在揚州城區,對象有城市平民以及失學青年和無業小市民。方法主要是通過舊的社會關系。……一些黨的文件大都放在曹起溍家,開會和碰頭則在林棲家。活動的主要內容是搞發展黨員的工作。也曾想搞工人運動,但沒有搞起來。我們與國民黨的關系也沒有完全斷絕……”(48)王壽荃:《我在揚州參加中共揚州地下黨早期活動的情況》,《江都縣革命史料》,第137—145頁。揚州黨組織曾發動過耀揚火柴廠的工人罷工,最早發生在1928年9月,此時王壽荃已經離開揚州,自然無從知曉。可以看出,作為青年學生的王壽荃和曹起溍沒有太多有效的辦法和途徑發展黨組織。一方面作為學生所擁有的社會關系單一,實際能依靠的只有傳統的血緣、地緣關系,連學緣關系都很難利用。另一方面,兩人所在的家庭都是普通家庭,經濟基礎和社會關系網絡的局限,使得作為職業革命者的兩人,基本生存尚不能有效保障,遑論進行社會動員。
王壽荃回憶與江蘇省委的聯系工作,他曾到上海與江蘇省委聯系過三次,第一次接關系,第二次匯報工作,最后一次是離開揚州前。(49)王壽荃:《我在揚州參加中共揚州地下黨早期活動的情況》,《江都縣革命史料》,第144頁。王壽荃稱:“(第二次)在上海我還領了一百元活動費,并通過省委機關的幫助,以四十五元購買了一支勃朗寧手槍和一百粒子彈。”(50)王壽荃:《我在揚州參加中共揚州地下黨早期活動的情況》,《江都縣革命史料》,第145頁。并回憶了將手槍和子彈帶回揚州的經過。關于秘密工作和技術工作,揚州特委認為:“江都的同志都不留心秘密技術,所以特制秘密工作須知。技術工作倘能做得好,都會運用”。(51)《最近工作情況給省委的報告》(1928年7月15日),《江蘇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4,第428頁。
王壽荃回憶揚州黨組織與省委的聯系方式包括:1.通信聯系。信件用的是密寫法,計有兩種寫法:一種是先寫好一封普通信函,然后再用米汁在空白處寫上要寫的內容;另一種是特制的藥水密寫。顯現密寫字跡也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將信紙放在煤油燈罩上烤一下,字跡就顯現出來;另一種是碘酒顯現。省委機關大多是利用某些商號或洋行。為了避免國民黨特務檢查,通訊地點還常常更換。2.通過省委機關派來的地下交通進行聯系。3.通過特派員陳勃進行聯系。那時陳勃經常來往于上海和他工作的鹽城、阜寧之間,路過揚州時就托他帶向省委反映一些工作上的情況和問題,他也有時為我們帶來省委的指示和文件。(52)王壽荃:《我在揚州參加中共揚州地下黨早期活動的情況》,《江都縣革命史料》,第146—147頁。
從王壽荃的描述可見,揚州縣委與上級黨組織的聯系并不便利。空間上,揚州距離上海不算遠,且為平原地帶,以交通條件論,江浙地區的地方組織似乎與上級組織的聯系不應如此周折。即使如此,揚州縣委與江蘇省委尚無直接聯絡的渠道(如電報),而是通過江蘇省委蘇北特派員進行間接聯系。信息的傳遞相對滯后,也反映出揚州特委和下屬縣委在江蘇全省工作中的地位,沒有重要且迫切的信息需要傳達。缺乏省委指導的地方黨組織在更多的時候,只能是根據自身情況自主發展組織。
1927年11月中共揚州耀揚火柴廠支部建立后,隨即秘密組建工會,5名工會委員中有4名是共產黨員,在工人中有較高的威信。工會向資方提出為工會活動提供場所和活動津貼,資方起先答應工會要求。但經過核算后,資方認為工會要求過高,不能滿足勞方的要求。對此,黨支部通過工會號召工人每天少工作兩小時,以此對抗。資方甚感恐慌,遂與工會談判,表示每月撥給經費16元,其余條件也一概答應。經過這次斗爭,工會的影響力進一步提高,促進了之后工人運動的開展。(53)《中國共產黨江蘇省揚州歷史》第1卷,第45頁。
在1928年7、8月間有一次小的斗爭風波,“起因是一資本家的走狗,私給一女工手帕子,引起我們同志的反對,而釀成罷工風潮。結果資方傳出黨調停將手帕撕去,但那天罷工工資、尚未發出,而該工會代表鄧某(非同志)有右傾的危險,資本家更加緊進攻,取消工友包飯制……男女待遇不平等,離間工人勢力,收買女工賊,偵查女工行動和任意的侮辱女工等,都是資方壓迫的表示”。(54)《最近工作情況給省委的報告》(1928年7月15日),《江蘇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4,第430頁。針對這一情況,揚州特別支部決議:(1)迅速發展黨的組織,每工作間至少要有一同志。(2)嚴密組織,結弟兄,拜姊妹。(3)女工全體加入工會,要求改組,工會正付(副)要男女各一。(4)在開大會時,同志預先推當選人,屆時公開講演,對于下屆當選人,提出下列口號的要求:A反對取消包飯制,維持客幫失業工友生活。B反對男女待遇不平,主持公道。C反對搜查出廠女工身體,保全女工面子。D要求補發無故停工工資。E驅逐女工賊出廠,并要求廠方切實負責,聲明以后不再有此非法行為!(5)組織健全,即行斗爭。(55)《最近工作情況給省委的報告》(1928年7月15日),《江蘇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4,第430—431頁。然而這一次斗爭風波結果卻是不了了之,未取得預期結果。
從黨組織的工作計劃看,農民運動始終是這一時期中共各級組織關注的重點。1928年夏,曹起溍、駱孟開等人到揚州東鄉進行農村調查,選定江都、泰州、泰興三縣交界的高漢莊、李家橋、孫家墩開展工作,組織“窮人會”,提出“欠債不還錢,欠租不還租”“窮人要吃飯,窮人要翻身”等口號。同時,他在三地分別創建黨支部,發展共產黨員四五十人。在曹起溍等人的領導下,黨支部發動了3000多個農戶參加的抗租抗債斗爭,迫使地主減租減息。(56)《中國共產黨江蘇省揚州歷史》第1卷,第49頁。
曹起溍等醞釀發動年關斗爭時,恰逢國民黨江都縣大橋區黨部委員李維亭到高漢莊探親,見到張貼的革命標語,十分驚恐,便命楊灣鄉鄉長史建候、地主馬敬仁暗地里查明情況向上密報。不久,縣政府和縣公安局接到密報后,隨即派出武裝偵緝隊會同地方武裝自衛隊于1929年2月9日(農歷臘月三十日)包圍高漢莊、李家橋、孫家墩,搜捕“共產分子”。逮捕了共產黨員景子英、張永千、王淦等三人,曹起溍在當地群眾的掩護下,藏身在一個農民家的夾墻內,得以脫險。景子英等押至大橋區公安分駐所后,在刑訊逼供下,景子英供出揚州黨組織領導機關和聯絡站所在地揚州板橋二十九號和交通員周長庚。農歷正月初一清晨,偵緝隊逮捕周長庚,以及與周同住的西北區委書記郭成昌。郭、周二人經不起刑訊,供出一些基層黨組織的負責人及其住址。從正月初三起又陸續逮捕黨團員多人,包括共青團特支負責人駱家騮,學生江世侯(即江上青)、耀揚火柴廠支部書記李前康、香業支部書記張學義、舊城支部書記林曦、邵伯特支成員許開甲等十二人。后經江蘇省高等法院判決,均被判半年以上徒刑。列入搜捕名單的揚州特委書記夏采曦、揚州縣委書記李濟平、曹起溍、蔡興等中共揚州黨組織的主要負責人,全部外出避難,中共揚州地下組織有四、五個月完全停止活動,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因該事件發生在農歷正月初,故稱為“正月事變”。(57)《第一、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共江都縣黨組織歷史發展簡況》,《江都縣革命史料》,第79—80頁。
“正月事變”幾乎波及到揚州黨組織的所有骨干黨員,這次事變后“黨在揚州,事實上已瓦解。”(58)《第一、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共江都縣黨組織歷史發展簡況》,《江都縣革命史料》,第80頁。客觀地說,“正月事變”的發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高漢莊等地本是預備作為農民抗租抗稅運動的策源地,揚州縣委在此地顯然有一定的群眾基礎;不想原本應在大橋區辦公的國民黨大橋區黨部委員李維亭到此地探親,看到宣傳標語,由此引起一連串的連鎖反應。主觀上因為曹起溍搞動員工作經驗不足,提前泄露行動計劃(標語);客觀原因則是因為揚州處于南京政府統治區域的核心區域國共力量對比懸殊,同時中共地下的區域過于狹小,毫無回旋余地。從國民黨方面看,“正月事變”固然有些“歪打正著”,同時也體現出李維亭作為基層黨務人員的高度警覺性;國民黨方面的處置迅速且隱蔽,反映出有關人員工作經驗的豐富,這一點自然是學生出身的曹起溍等人所不及的。同時,由于揚州的地下黨組織沒有采取單線聯系的方式,造成一人被捕招供,立刻多人被捕的被動局面。黨組織與革命事業遭到相當的損失,此后再次重建的揚州縣委雖然恢復了部分支部并動員了一批黨員,但始終處于“白色恐怖”的高壓之下,屢遭破壞。且因為高層政策愈加激進,揚州縣委因而作出如“雙十”斗爭等不切實際的冒險行動,損失更甚。至1933年底,中共在揚州的黨、團組織基本被摧毀殆盡,停止活動。(59)《中國共產黨江蘇省揚州歷史》第1卷,第57頁。
結語
回顧揚州中共地方組織的創建、發展和革命實踐的歷史過程,可以看出:首先,中共揚州地方組織的“落地”是以國民黨組織的名義完成的。建立者是惲代英,而非派員回鄉創建,屬于“輸入革命”,這一點與江蘇省內絕大多數地方有所不同。中共揚州地方組織最初的一批黨員主要是學生、小學教師、醫生等小知識分子。文化程度、交流習慣、認識能力的趨同使得他們很快接受中共的基本理論完成作為基層黨員的基本訓練,形成群體的聚合,進而完成地方黨組織的“落地”。
黨員構成方面,由學生群體為主體到工人群體的大量吸納,完成上級黨組織的要求,即“堅決的改造和堅強黨的組織”,“不僅是形式上來‘提拔工農分子’及‘民權化’,<而>是在實質上來怎樣改造組織的形式,改換工作的方法,改換新的工作的習慣。”(60)《江蘇省委最近工作決議案》(1928年9月),《江蘇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4,第72—73頁。學生從黨員構成的主體,成為相對的配角,黨組織完成從學生到工人的黨員構成的演進過程,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共革命逐漸工農化的縮影。作為近代工業落后、產業聚集較差的邊緣化的城市,揚州缺乏動員革命所需的一些因素。同時白色恐怖使得暴力革命不但難以施行,相反客觀上暴力革命加速了地下組織的暴露,國統區國共兩黨武力的懸殊,無疑使得暴力革命成為中共單方面的訴求,革命需求和革命供給兩端嚴重不平衡。
近代以來城鄉二元對立愈發顯現,革命在城市和鄉村亦呈現出不同的狀態。就揚州言,城市地位的下降、近代工業的落后、產業工人數量嚴重不足等原因,使得以產業工業人為中心的城市革命無從談起。作為革命生力軍的學生,不得不離開城市前往鄉村,開展以農民為中心的鄉村革命。農民的文化水平、生活慣習與學生存在巨大差異,“窮人會”等民間會社成為鄉村動員的有效路徑,但空間范圍相對局限于揚州東鄉因“東鄉農民最苦”(61)《揚州特委工作報告——關于環境、各種斗爭及黨的工作》(1928年11月1日),《江蘇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4,第458頁。,其他區域農民生活并不十分困苦,黨組織在縣域范圍尚不能完全覆蓋。由此可以看出,揚州城區缺乏革命的場域;鄉村因自耕農、佃農較多土地矛盾不突出,農民缺乏暴力革命的訴求。筆者以為:近代揚州城市的衰落對于中共發動工農革命相對是不利的。既缺乏革命要素和革命訴求,加之上級組織缺乏重視、缺乏得力干部等原因,“衰落城市的革命”自然難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