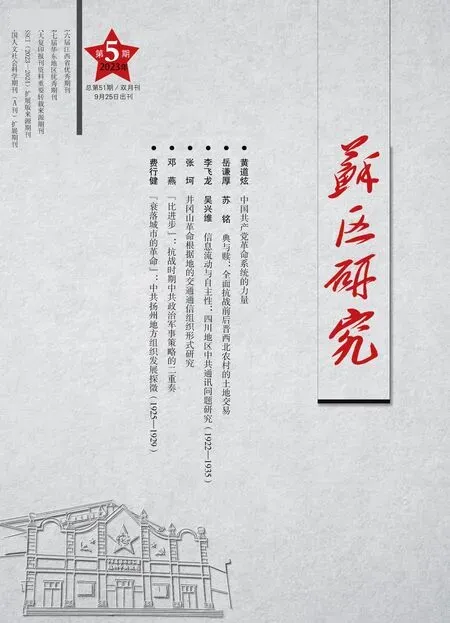信息流動(dòng)與自主性:四川地區(qū)中共通訊問題研究(1922—1935)
李飛龍 吳興維
保有順暢的溝通渠道、建立穩(wěn)定的通訊聯(lián)系之于中共發(fā)展壯大而言,至關(guān)重要。1925年4月,在中共四大后不久,中共中央就發(fā)布了《關(guān)于建立和健全黨內(nèi)交通問題》的指示,強(qiáng)調(diào)通訊工作在組織上的重要性,“等于人身上的血脈,血脈之流滯,影響于人的生死”。(1)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chǎn)黨組織史資料(1921.7—1949.9)》第8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頁。不過,四川地處中國西南邊陲,周圍崇山峻嶺,地形封閉,與外界的信息交流極為不便,有蜀道難難于上青天之說。加之護(hù)國戰(zhàn)爭后,川內(nèi)軍閥割據(jù)、各自為政,嚴(yán)防中共通訊往來,故自1922年四川共產(chǎn)組織成立伊始,通訊工作就困難重重。面對(duì)地理環(huán)境和政治形勢的不利因素,四川地區(qū)中共組織先是借助郵政寄遞、人員往來等外在方式,后又設(shè)立了專門的內(nèi)部交通機(jī)構(gòu),一定程度上保證了信息、人員和物資的往來,展示了中共在夾縫中生存的能力和極強(qiáng)的韌性。
對(duì)于黨內(nèi)通訊,學(xué)界已有涉及,如王奇生在討論大革命失敗后廣東中共地下黨時(shí)注意到了黨內(nèi)交通和情報(bào)傳遞問題(2)王奇生:《黨員、黨組織與鄉(xiāng)村社會(huì):廣東的中共地下黨(1927—1932年)》,《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第24—36頁。,王士花考察了抗戰(zhàn)時(shí)期中共在山東的交通網(wǎng)絡(luò)(3)王士花:《抗戰(zhàn)時(shí)期中共在山東的交通工作》,《史學(xué)月刊》2018年第12期,第57—63頁。,周俊還專門指出了黨內(nèi)交通研究的不足及改進(jìn)之處。(4)周俊:《組織的血脈:黨內(nèi)交通研究的再檢視》,《中共黨史研究》2021年第6期,第45—50頁。上述討論無疑深化了黨內(nèi)通訊制度研究。但是,對(duì)于中共中央聯(lián)系較弱、自主性較強(qiáng)的邊緣地區(qū),還少有關(guān)注。基于此,本文擬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為基礎(chǔ)資料,嘗試回答四川地區(qū)中共早期組織通訊工作的具體運(yùn)轉(zhuǎn)、所遇困境以及制度生成等問題,進(jìn)而理解中國共產(chǎn)黨的自主意識(shí)及其價(jià)值。
一、四川地區(qū)中共組織的外部通訊手段
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初期,四川地區(qū)共產(chǎn)主義組織是以一種網(wǎng)絡(luò)狀方式成長起來的,屬于多中心的網(wǎng)絡(luò)狀、扁平型發(fā)展模式,如最早建立的成都、重慶、瀘州等黨團(tuán)組織,多并行不悖、多水分流地自行生長。這一時(shí)期,四川內(nèi)部各地方黨組織間雖然交集不多,但均與中央保持不定期的通訊聯(lián)系。
郵政寄遞是四川地區(qū)早期中共組織與上級(jí)保持聯(lián)系的重要方式。在四川中共組織創(chuàng)建初期,組織成員較少,規(guī)模也不大,加之革命環(huán)境相對(duì)寬松,使得依靠郵政寄遞進(jìn)行信息溝通、指示傳達(dá)、經(jīng)費(fèi)輸送等革命活動(dòng)成為可能。從1922年10月,自成都、重慶、瀘縣等地方團(tuán)組織相繼成立開始,主要負(fù)責(zé)人便通過郵局,向中共中央寫信報(bào)告各地籌建情況,并隨信附列了各地通訊處,以便與中央加強(qiáng)聯(lián)系。四川地區(qū)中共的各類宣傳品、各筆運(yùn)作經(jīng)費(fèi),也是通過郵局傳遞的。1926年1月,重慶團(tuán)地委先后兩次向中央報(bào)告,分別查收了由中央寄來的98—102號(hào)通告(5)《團(tuán)重慶地委致團(tuán)中央報(bào)告(第3號(hào))——關(guān)于通訊地址和收到刊物的說明》(1926年1月2日),中央檔案館、四川省檔案館編:《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9,內(nèi)部發(fā)行,1987年版,第3頁。,以及100份《青工運(yùn)動(dòng)》(6)《團(tuán)重慶地委給團(tuán)中央的信——查收刊物、款項(xiàng)事》(1926年1月29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9,第39頁。。同年3月,重慶團(tuán)地委還陸續(xù)收到團(tuán)中央?yún)R寄的30元和20元款項(xiàng),以此作為團(tuán)組織開展工作的活動(dòng)經(jīng)費(fèi)。(7)童庸生:《童庸生向中央的報(bào)告——重慶黨、團(tuán)地委組織分工情況》(1926年3月5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9,第73頁。顯然,在四川中共組織建立的早期,黨內(nèi)信件、各類宣傳品以及活動(dòng)經(jīng)費(fèi),均能通過郵政傳遞。這些文件、報(bào)刊、經(jīng)費(fèi)成為四川黨團(tuán)組織發(fā)展的行動(dòng)指導(dǎo)和物質(zhì)基礎(chǔ)。
大革命失敗以后,四川中共組織在困境中得到發(fā)展,此時(shí)郵政傳遞仍是地方黨組織之間、組織與上級(jí)溝通的主要渠道。1927年11月,四川臨時(shí)省委整理和統(tǒng)計(jì)了10月份的收發(fā)信件情況,其中收入信件總數(shù)為144件,內(nèi)含報(bào)告70件、聞?dòng)?1件、請(qǐng)示34件、其他29件;發(fā)出信件總數(shù)為103件,內(nèi)含交給機(jī)關(guān)65件,交給同志38件。(8)《四川臨時(shí)省委致中央的報(bào)告——關(guān)于十月份政治及校務(wù)工作概況》(1927年11月),《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內(nèi)部發(fā)行,1984年版,第332頁。其中不乏郵政傳遞的信件。1929年4月,臨時(shí)省委表示,盡管重慶當(dāng)局嚴(yán)格檢查密信,臨時(shí)省委的第一號(hào)報(bào)告仍可通過郵寄送達(dá)中央。(9)《四川臨時(shí)省委致中央報(bào)告——四川政治經(jīng)濟(jì)形勢與最近黨的工作》(1929年4月28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4,內(nèi)部發(fā)行,1985年版,第3頁。1933年初,四川省軍委書記程秉淵抵達(dá)上海向中共中央?yún)R報(bào)工作,隨后中央便郵寄來一封指示四川黨目前任務(wù)的信件。同年3月,團(tuán)四川省委亦提及一月前的工作報(bào)告已由交通員寄來。(10)《團(tuán)四川省委致團(tuán)中央報(bào)告(新編第4號(hào))——各級(jí)團(tuán)部及省委近一月來工作情形》(1933年3月28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0,內(nèi)部發(fā)行,1987年版,第238頁。由此可見,即便大革命失敗后,郵政寄遞的信息溝通、指示傳達(dá)、經(jīng)費(fèi)輸送方式,一直為四川中共組織所使用。
然而,頻繁的郵政通信和傳輸物資,以及四川地區(qū)中共組織力量的增強(qiáng),也引來了四川軍閥的警覺。為阻斷四川地區(qū)中共組織的信息往來,遏制川內(nèi)中共組織的發(fā)展壯大,四川各派軍閥對(duì)郵政往來之信件進(jìn)行了嚴(yán)格檢查。1925年3月,涪陵團(tuán)支部發(fā)現(xiàn),其通訊處收件人“李用三”之名已被覺察,收到的18號(hào)通告“信封全開”。(11)《團(tuán)涪陵支部給團(tuán)中央的報(bào)告(第6號(hào))——關(guān)于通訊問題》(1925年3月22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內(nèi)部發(fā)行,1986年版,第226頁。1926年1月,重慶團(tuán)地委覺察到,團(tuán)中央不僅突然變更了通訊地址,收到的封信和包裹也已被人拆閱。(12)《團(tuán)重慶地委致團(tuán)中央報(bào)告(第3號(hào))——關(guān)于通訊地址和收到刊物的說明》(1926年1月2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9,第3—4頁。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國民黨更加大了對(duì)郵件的檢查力度,同年7月,在南京戒嚴(yán)司令部下特設(shè)了郵政檢查委員會(huì),檢查往來一切郵件,尤其嚴(yán)格檢查“關(guān)于共產(chǎn)黨及帝國主義者宣傳之件”。(13)《南京戒嚴(yán)司令部檢查郵政委員會(huì)抄報(bào)〈檢查郵政暫行條例〉致中央宣傳部函》(1927年7月27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1編文化(1),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57—158頁。1931年,四川軍閥劉湘組織的“清共委員會(huì)”,其核心任務(wù)之一,就是“檢查郵件,尋跡查號(hào),追蹤緝捕”。(14)蔣維彥:《軍閥對(duì)中共合川地下黨的破壞》,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huì)議四川省合川縣委員會(huì)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huì)編:《合川文史資料選輯》第6輯,內(nèi)部發(fā)行,1989年版,第16頁。四川軍閥嚴(yán)查郵政寄遞,無疑給處于成長期的四川中共黨組織以巨大壓力和嚴(yán)峻挑戰(zhàn)。
為了躲避四川軍閥對(duì)郵政通信的追查,四川中共組織開始啟用秘密通信方法,1927年10月,四川臨時(shí)省委發(fā)布通告,決定按周發(fā)行《政治通訊》,并用米湯印寫以便遞寄,各地收到后需用碘酒擦出,方能閱讀。(15)《四川臨時(shí)省委通告(第23號(hào))——發(fā)行〈政治通訊〉加強(qiáng)政治學(xué)習(xí)事》(1927年10月7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第178頁。1928年5月,臨時(shí)省委常委劉堅(jiān)予上報(bào)中共中央,建議中央此后寄發(fā)通告,以秘密方法書寫。借助于郵政寄遞的秘密通信方法,曾短暫地掩護(hù)了中共組織間的信息溝通、指示傳達(dá)與經(jīng)費(fèi)輸送。直到1929年4月,因重慶軍閥檢查密信,四川中共組織與中央約定的秘寫法“已為敵人所發(fā)覺”,省委“不敢再用前秘寫法做報(bào)告給中央”,秘密通信方法遂暫時(shí)中斷。(16)《四川臨時(shí)省委致中央報(bào)告——四川政治經(jīng)濟(jì)形勢與最近黨的工作》(1929年4月28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4,第3頁。事實(shí)上,在當(dāng)時(shí)的技術(shù)條件下,破解這種秘密通信方法并非難事,1927年9月,四川臨時(shí)省委就曾向中央報(bào)告,“聞郵(17)郵,即郵局用水浸火烤及涂海碘酒三法檢查”來往信件,經(jīng)嘗試用黃碘酒即可擦出,故建議中央“另約其它藥水”。(18)《四川臨時(shí)省委致中央報(bào)告——最近政治組織狀況和省委的工作》(1927年9月1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第73—74頁。由此觀之,四川中共組織與四川軍閥在秘密戰(zhàn)線上的博弈和斗爭,從未停止。
除郵政寄遞外,四川黨組織內(nèi)部、四川地方與中共中央之間的信息溝通、指示傳達(dá)、經(jīng)費(fèi)輸送,還可通過人員往來實(shí)現(xiàn)循環(huán)流動(dòng)。即一方面通過巡視工作的推進(jìn),依靠巡視員傳達(dá)上級(jí)指示或向上級(jí)匯報(bào)執(zhí)行情況,另一方面依靠黨組織的人員流動(dòng),由組織成員順道攜帶消息、文件、經(jīng)費(fèi)等。
巡視工作的開展,可以有效傳達(dá)上級(jí)指示,指導(dǎo)地方工作,促進(jìn)信息流通。1931年6月,在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固定巡視員的通知中,強(qiáng)調(diào)“要根本轉(zhuǎn)變過去公文形式的指導(dǎo)而成為實(shí)際有效的活的指導(dǎo)”。在中共中央看來,作為“活的領(lǐng)導(dǎo)”的巡視員制度,可以實(shí)現(xiàn)面對(duì)面指導(dǎo),破除官僚主義。同時(shí),由于“采用活的領(lǐng)導(dǎo),極力減少文件的來往”,客觀上也造成了以巡視替代文件實(shí)現(xiàn)信息互通。(19)《中國共產(chǎn)黨組織史資料(1921.7—1949.9)》第8卷,第408頁。四川地區(qū)巡視工作最早是在團(tuán)組織中開展的,1926年3月,重慶團(tuán)地委書記童庸生向團(tuán)中央報(bào)告了瀘州、江津、榮昌團(tuán)組織建設(shè)的巡視情況,其中瀘州團(tuán)組織將近30人,江津已成立團(tuán)組織(共13人),榮昌團(tuán)組織未能建立。(20)童庸生:《童庸生向團(tuán)中央的報(bào)告——巡視瀘州團(tuán)及江津、榮昌團(tuán)情況》(1926年3月10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9,第75—76頁。此后,無論是四川團(tuán)組織還是黨組織,派遣巡視員成為常態(tài)。1928年5月,為加強(qiáng)對(duì)川東的領(lǐng)導(dǎo),四川臨時(shí)省委派遣劉堅(jiān)予至川東巡視。1929年8—9月,四川省委由成都遷回重慶后,又派遣劉堅(jiān)予巡視下川南,程秉淵巡視上川南,陳惠巡視川西。1931年5月,團(tuán)四川省委還計(jì)劃固定兩名省委巡視員,輪流外出巡視,從7月起巡視中心縣。同時(shí),四川地方黨組織還接受中共中央的巡視,1931年10月,中共中央派小元到四川巡視并改組省委,1934年1月,中央巡視員徐平抵達(dá)成都,指導(dǎo)四川省委開展反右傾機(jī)會(huì)主義的斗爭。(21)《中國共產(chǎn)黨四川省組織史資料(1921—1949)》,第56、4頁。四川中共組織的內(nèi)部巡視和中央對(duì)四川黨組織的外部巡視,共同支撐了四川黨組織內(nèi)部、四川地方組織與中共中央之間的信息互通。
但是,巡視制度以及巡視制度所附加的信息互通不甚理想。1929—1930年,四川省委委員李寬懷巡視川東時(shí),因未能完成巡視任務(wù),“應(yīng)去巡視的不去巡視”,導(dǎo)致四川省委上報(bào)中央,要求對(duì)其處分。(22)《四川省委致中央報(bào)告——請(qǐng)示對(duì)李寬懷錯(cuò)誤的處分》(1930年4月24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5,內(nèi)部發(fā)行,1985年版,第82頁。1932年,四川省委發(fā)現(xiàn),巡視員訓(xùn)練培養(yǎng)不夠,不能很好完成巡視任務(wù),只能“走馬觀花”解決零碎問題。(23)《四川省委致中央報(bào)告——7月到“九·一八”工作情況)》(1932年9月25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6,內(nèi)部發(fā)行,1985年版,第106頁。無可否認(rèn),巡視力度不夠、覆蓋面有限,固然有巡視員能力的問題,但僅將此歸因于巡視員自身的工作態(tài)度和自身能力,顯然是不準(zhǔn)確的,甚至是片面的。嚴(yán)峻且極為危險(xiǎn)的外部環(huán)境、巡視制度初建時(shí)期的不成熟、地方黨組織發(fā)展經(jīng)費(fèi)的匱乏以及人員數(shù)量的緊缺,都是巡視制度實(shí)踐成效打了折扣的重要原因。以經(jīng)費(fèi)和人員為例,1927年,四川臨時(shí)省委曾感慨,“省委經(jīng)費(fèi)困難到了極點(diǎn)!來源既少,需要支出之處則甚多,是以各種工作均感到極大困難”。(24)《四川臨時(shí)省委通告(第31號(hào))——節(jié)約經(jīng)費(fèi)增加收入辦法》(1927年10月25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第239頁。1929年,四川臨時(shí)省委在強(qiáng)調(diào)巡視工作重要性的同時(shí),認(rèn)為是“經(jīng)費(fèi)及人力的關(guān)系”,才使巡視工作“做得很少,而且沒有什么成績”。(25)劉方澈:《四川臨時(shí)省委劉方澈給中央的報(bào)告——關(guān)于組織工作情況》(1929年1月15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3,內(nèi)部發(fā)行,1984年版,第325頁。1933年,四川中共組織在總結(jié)全川巡視情況時(shí),亦抱怨巡視人員匱乏,“兩年以來培養(yǎng)出來的新巡視員不上五個(gè)”。(26)《四川省委關(guān)于全川黨的組織工作決議》(1933年8月16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6,第455頁。四川中共組織的感慨和抱怨,都直接說明巡視制度實(shí)踐的困境。
另一種依靠人員流動(dòng)來實(shí)現(xiàn)信息互通的方式,是組織成員順道攜帶消息、文件和經(jīng)費(fèi)。1922年7月,為尋求團(tuán)中央的指導(dǎo)與幫助,四川共產(chǎn)主義運(yùn)動(dòng)的發(fā)起者王右木離蓉抵滬,10月返回四川,并隨身攜帶團(tuán)章和團(tuán)中央第一次代表大會(huì)文件。1924年5月,楊闇公抵達(dá)重慶,與童庸生接頭并討論團(tuán)組織發(fā)展后,于6月初乘輪船東下,該月中旬抵達(dá)上海,并與中央取得聯(lián)系。(27)中共四川省委黨史研究室:《四川黨史人物傳》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5頁。1928年4月,四川省委派遣劉堅(jiān)予前往上海匯報(bào)四川中共組織在“三九”事變中遭到的破壞,并委托劉堅(jiān)予攜帶省委二月擴(kuò)大會(huì)議的多項(xiàng)議案,請(qǐng)求中央指示。(28)《四川省委向中央的報(bào)告——四川政治經(jīng)濟(jì)形勢及省委各項(xiàng)工作的現(xiàn)狀與計(jì)劃》(1928年8月20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3,第243頁。1929年2月,考慮到郵政寄遞的潛在風(fēng)險(xiǎn),決定由臨時(shí)省委委員劉遠(yuǎn)翔順道攜帶上報(bào)中央的第二號(hào)文件。(29)《中國共產(chǎn)黨四川省組織史資料(1921—1949)》,第55頁;《四川臨時(shí)省委致中央報(bào)告——四川政治經(jīng)濟(jì)形勢與最近黨的工作》(1929年4月28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4,第3頁。
不過,依靠組織成員順道攜帶消息、文件和經(jīng)費(fèi),必然會(huì)受到人員流動(dòng)頻率的影響,譬如四川黨組織派人去中央時(shí),多是主動(dòng)尋求上級(jí)指導(dǎo)、參加黨代會(huì)或組織遭到破壞的匯報(bào),這種人員流動(dòng)的頻率并不高。加之“蜀道難”的地理?xiàng)l件,也決定了人員往來并非易事,1924年7月底,楊闇公由滬返渝,在歸途中,楊闇公深感“吾川旅行之不便,真是匪言可喻”(30)楊紹中、周永林、李暢培編輯整理:《楊闇公日記》,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9頁。,尤其在入川的地界,船行的異常緩慢,日走三四百里,常有盜匪出沒。(31)《楊闇公日記》,第146頁。楊闇公此次返渝,歷時(shí)半月之久。
應(yīng)該說,郵政寄遞、人員往來是四川中共組織內(nèi)部以及四川地方組織與中共中央之間信息溝通、指示傳達(dá)、經(jīng)費(fèi)輸送的主要渠道,但同時(shí),還有一些輔助方式。其一,是無線電報(bào)。中共使用專門無線電作為信息互通,時(shí)間較晚,直到1929年秋,才在上海大西路復(fù)康里9號(hào)租了一棟三層樓,安裝了第一部秘密電臺(tái)。1930年1月,中共中央與中共南方局試行了第一次無線電密碼通訊,是為無線電技術(shù)使用的開端。由此判斷,在此前后,四川地方黨組織不太可能擁有獨(dú)立的無線電設(shè)備。不過,沒有獨(dú)立的無線電設(shè)備,中共地方黨組織仍可借用軍事機(jī)關(guān)或者民用電報(bào)。1929年2月,四川臨時(shí)省委曾向中央提出使用軍用無線電傳遞重要消息,并告知自己的收電地址在成都,需黨中央在上海或者南京找到軍事機(jī)關(guān)收電和發(fā)電。依據(jù)軍用電臺(tái)、收電地址等關(guān)鍵信息,可以推測,這是四川地下黨打入軍閥內(nèi)部,獲得了使用軍事無線電設(shè)備的便利。同時(shí),四川中共組織還可使用民用電報(bào),“三三一”慘案后,中共中央曾指派傅烈、周貢植等五人組成臨時(shí)省委,由武漢到重慶并重建四川地區(qū)中共組織,在武漢至重慶途中,傅烈等人曾給武漢發(fā)去“兩信一電”,不過因武漢方面地址變更未能收到。(32)《中國共產(chǎn)黨四川省組織史資料(1921—1949)》,第51頁;《四川臨時(shí)省委致中央報(bào)告——最近政治組織狀況和省委的工作》(1927年9月1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第73頁。這“兩信一電”中的“一電”,極有可能是通過民用電報(bào)所發(fā)。需要強(qiáng)調(diào)的是,在白色恐怖之下,無論是通過軍事機(jī)關(guān)還是民用電報(bào),都十分危險(xiǎn),前者由于高度機(jī)密,消息很容易被破獲,后者因?yàn)闆]有加密,消息極可能泄露,因此使用頻率極低。
其二,是根據(jù)報(bào)紙刊物以及民間傳聞。這種情況多出現(xiàn)在組織徹底失聯(lián)的情況下。1929年7月,四川省委指責(zé)第七混成旅在兵變工作中行事匆忙,不待省委回信指示便擅自行動(dòng),發(fā)動(dòng)后也不給省委匯報(bào),因此省委只能在報(bào)紙和傳聞中得到部分消息。(33)《四川省委通訊第5號(hào)——關(guān)于第七混成旅兵變中錯(cuò)誤的批評(píng)及今后工作的指示》(1929年7月10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4,第111頁。當(dāng)然,由于戰(zhàn)時(shí)緊迫,無法及時(shí)匯報(bào),也是兵變和暴動(dòng)中的常態(tài),在這種緊急情況下,四川省委要獲取消息,進(jìn)而判斷形勢,唯有根據(jù)報(bào)紙刊物以及民間傳聞了。
總的來說,在四川中共組織成立初期,郵政寄遞、人員往來是四川中共組織內(nèi)部以及四川地方與中共中央之間信息溝通、指示傳達(dá)、經(jīng)費(fèi)輸送的主要渠道,無線電報(bào)、報(bào)刊和民間傳聞是輔助手段,它們共同構(gòu)成了四川地區(qū)中共通訊的多維渠道。不過,這些渠道都是借助于近代以來搭建的通訊技術(shù)體系,抑或人員往來的攜帶,具有明顯的外部性和臨時(shí)性特征。更重要的是,這種通訊體系極易暴露,因此建立中共領(lǐng)導(dǎo)下的專門的通訊網(wǎng)絡(luò),就顯得尤為關(guān)鍵。
二、四川地區(qū)中共黨內(nèi)通訊機(jī)構(gòu)與路線
從1922年四川中共組織建立開始,直至1927年大革命失敗為止,四川中共組織都沒有創(chuàng)建自己的通訊機(jī)構(gòu),這主要是因?yàn)猷]政寄遞、人員往來尚能勉強(qiáng)支撐中共的信息溝通、指示傳達(dá)以及經(jīng)費(fèi)輸送。當(dāng)然,這并不是說郵政寄遞、人員往來沒有問題,實(shí)際上由于郵件延誤以致信息傳遞不能及時(shí)之事常有發(fā)生。1925年3月,涪陵團(tuán)支部就報(bào)稱,每回接得中央之各種紀(jì)念運(yùn)動(dòng)指示,如“二·七”“三·八”等紀(jì)念運(yùn)動(dòng),常是指示信到達(dá)時(shí),運(yùn)動(dòng)時(shí)間已過。(34)《團(tuán)涪陵支部給團(tuán)中央的報(bào)告(第6號(hào))——關(guān)于通訊問題》(1925年3月22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226頁。同年12月23日,瀘州地方團(tuán)組織在報(bào)告中也提到,因川內(nèi)郵傳太慢,曾多次接到中央“某事變之通告而某事變?nèi)掌谝堰^”,例如投考黃埔軍校事宜。(35)《瀘州地方團(tuán)向團(tuán)中央的報(bào)告——最近校務(wù)情形》(1925年12月23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348頁。顯然,此類問題的出現(xiàn),主要是由于四川地域廣袤、山高路遠(yuǎn),交通工具落后所致。簡言之,此時(shí)四川中共組織雖偶發(fā)郵政文件遭到拆封之事,但自然地理、交通工具,應(yīng)是郵政寄遞、人員往來所致信息滯后的主要原因。
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后,白色恐怖籠罩中國大地,大量中共黨員慘遭逮捕和殺害,利用傳統(tǒng)郵政寄遞、人員往來實(shí)現(xiàn)信息溝通、指示傳達(dá)、經(jīng)費(fèi)輸送,不論是文件暴露和人員危險(xiǎn)程度,還是信息傳遞和擴(kuò)散速度,都面臨著極大的考驗(yàn)。為此,1927年8月21日,在《中央通告第三號(hào)》中,中共中央明確提出必須建立單獨(dú)的黨內(nèi)交通機(jī)關(guān)和交通網(wǎng),要求:“八七緊急會(huì)議議決中央建立通達(dá)各省的交通,各省委建立通達(dá)各縣的交通,各縣委建立通達(dá)各鄉(xiāng)的交通——構(gòu)成一個(gè)黨的全國交通網(wǎng)”(36)《中共中央通告(第3號(hào))——關(guān)于建立黨內(nèi)交通網(wǎng)》(1927年8月21日),江西省郵電管理局編:《華東戰(zhàn)時(shí)交通通信史料匯編(中央蘇區(qū)卷)》,人民郵電出版社1995年版,第35頁。。同時(shí),第三號(hào)通告還對(duì)全國交通網(wǎng)的職責(zé)、組織構(gòu)成、交通員工作注意事項(xiàng)等作了詳細(xì)部署。至此,全國性統(tǒng)一的交通網(wǎng)絡(luò)逐漸在各地建立起來。
在《中央通告第三號(hào)》的要求和中共中央的指導(dǎo)下,也是在岌岌可危的斗爭形勢下,為了分擔(dān)信息、文件的傳遞壓力,四川省委著手建立黨內(nèi)交通機(jī)關(guān)。1927年8月,早在四川臨時(shí)省委成立之初,就在省委秘書處之下設(shè)置了兩名交通員,其中一人負(fù)責(zé)接洽各地組織并作談話記錄及收取信件,另一人負(fù)責(zé)川內(nèi)各地的交通聯(lián)絡(luò)及發(fā)出信件。交通員每日上下午須到各通信處、接洽處收取文件兩次,寄發(fā)在秘書處領(lǐng)取的應(yīng)發(fā)文件,緊急文件要做到隨收隨送,不拘定時(shí)間。(37)《四川臨時(shí)省委秘書處組織及辦事細(xì)則》(1927年),《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第381—383頁。此時(shí)交通員的職責(zé)主要為書信和文件的收發(fā),并未涉及專門的信息網(wǎng)絡(luò)和人員通道。
1927年9月,在四川臨時(shí)省委組織部的計(jì)劃中,決定正式“設(shè)立秘密的交通處,傳遞各種文件及消息”。(38)《四川臨時(shí)省委組織部工作計(jì)劃》(1927年9月),《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第129—130頁。到11月,四川臨時(shí)省委進(jìn)一步明確了省內(nèi)交通路線,決定將四川劃分為兩個(gè)區(qū)域,共設(shè)置兩名省內(nèi)交通員,一人由合川從川北往成都,沿岷江至敘府、自井、瀘州、合江、江津、返重慶,另一人沿?fù)P子江下經(jīng)長壽、涪陵、豐都至萬縣,再由宣漢、大竹、鄰水返回重慶。(39)《四川臨時(shí)省委致中央的報(bào)告——關(guān)于十月份政治及校務(wù)工作概況》(1927年11月),《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第337頁。通訊機(jī)構(gòu)的設(shè)置和交通線路的規(guī)劃,可視為四川地區(qū)中共專門交通網(wǎng)的開端。隨著中共黨內(nèi)通訊機(jī)構(gòu)和交通線路的建立,四川省內(nèi)文件、信息、人員和物資的流動(dòng)有了很大改善,至1929年底,四川省委已感受到黨內(nèi)交通的便利,“巡視制度與全省交通網(wǎng),已經(jīng)開始建立,上下級(jí)關(guān)系比較從前親密得多”。(40)《四川省委第二次全體會(huì)議文件》(1929年11月),《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4,第288頁。不過,需要說明的是,無論是交通員數(shù)量還是交通路線規(guī)劃,此時(shí)四川中共的交通網(wǎng)仍處于初創(chuàng)階段。
1930年3—5月,四川地區(qū)中共組織內(nèi)部接連出現(xiàn)叛徒告密事件(41)《中國共產(chǎn)黨四川省組織史資料(1921—1949)》,第57頁。,不僅使四川省委遭受重大破壞,叛徒還“每日在郵局檢查來往信件”,以致傳統(tǒng)依靠郵政寄遞的方式無法存續(xù)。基于外部斗爭環(huán)境的變化,1930年12月,四川省委開始升級(jí)黨內(nèi)通訊機(jī)構(gòu),成立了省交通總處,并征調(diào)候補(bǔ)交通員3人在渝備用,計(jì)劃建立三條干線交通,同時(shí)省交通總處還幫助川東、川西、川南、川北建立了各區(qū)交通線。到1931年2月,川西已走過一次,因潼川交通機(jī)關(guān)被破壞,不能到達(dá)成都;川南(由渝至榮昌再至自井)走過4次,均到榮昌站,因“榮昌縣挪用交通費(fèi)致未達(dá)自井”;川東線(渝—萬)走過2次,其中一次因萬縣機(jī)關(guān)被破壞未能接頭;渝順線亦派遣交通員前往,可直達(dá)順慶。(42)《四川省委致長江局報(bào)告——四川政治經(jīng)濟(jì)形勢及黨的工作情況》(1931年2月14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5,第426—432頁。到1931年12月,四川地區(qū)的中共交通網(wǎng)已實(shí)現(xiàn)覆蓋并順利運(yùn)行,據(jù)省委統(tǒng)計(jì),自該年8月以來,川南自貢、瀘州交通已來回5次,川北順慶4次,川東重慶5次,川西南路2次,下東梁山1次。(43)《四川省委致中央報(bào)告——政治路線和工作作風(fēng)的轉(zhuǎn)變》(1931年12月1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5,第550—551頁。此時(shí),四川中共的黨內(nèi)交通線已不再是1927年底規(guī)劃的兩條路線,而是分別可抵達(dá)川南、川北、川東、川西各地,雖行走之路極為艱辛,但1931年底的黨內(nèi)交通線路顯然更加密集且合理。
同時(shí),四川中共組織依靠黨內(nèi)交通與中共中央保持聯(lián)系。1927年11月,四川臨時(shí)省委向中央報(bào)告,收到交通員賀學(xué)禮帶回的中央通訊、蜀字公函及8—11月經(jīng)費(fèi),之后省委又依靠交通員將四川臨時(shí)省委的各類報(bào)告、通告、計(jì)劃書、宣傳冊(cè)等文件送抵中央。(44)《四川臨時(shí)省委給中央的信——關(guān)于干部、經(jīng)費(fèi)、宣傳與軍訓(xùn)材料的要求》(1927年11月7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第349—350頁。不過,1928年10月,四川中共組織因地方軍閥的大舉搜捕,以及團(tuán)省委內(nèi)部叛變告密,四川黨團(tuán)省委機(jī)關(guān)均遭嚴(yán)重破壞,黨內(nèi)交通機(jī)關(guān)亦無法正常運(yùn)行。為保持與中央的通訊往來,四川省委計(jì)劃以湖北宜昌交通處為樞紐站,請(qǐng)求中央將匯款及文件暫交宜昌交通處,再由省委派人取回。(45)劉堅(jiān)予:《劉堅(jiān)予給中央的報(bào)告——黨團(tuán)省委被破壞情形及恢復(fù)工作》(1928年10月23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3,第295頁。該年11月,四川臨時(shí)省委派宣傳部主任劉榮簡赴中央報(bào)告工作,并正式在鄂西宜昌建立交通機(jī)關(guān)。(46)《四川臨時(shí)省委給中央的報(bào)告——臨時(shí)省委的組建與川戰(zhàn)爆發(fā)情況》(1929年1月17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3,第359頁。從此,宜昌交通處一度成為四川與中央保持通訊、輸送物資的中轉(zhuǎn)站。
需要強(qiáng)調(diào)的是,隨著1933年2月川陜蘇區(qū)的創(chuàng)建,四川省委與川陜蘇區(qū)的秘密交通線也得以建立并逐步完善,并成為中共中央聯(lián)絡(luò)川陜蘇區(qū)的中轉(zhuǎn)站。1933年4月,三臺(tái)中心縣委書記文俊,將搜集到的軍閥田頌堯29軍的作戰(zhàn)計(jì)劃、軍事地圖等情報(bào),轉(zhuǎn)送到鹽亭聯(lián)絡(luò)站,再由交通員經(jīng)南部縣最終送達(dá)川陜蘇區(qū)。(47)唐宏毅、楊重華:《配合紅軍創(chuàng)建川陜蘇區(qū)的斗爭》,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huì)議四川省三臺(tái)縣委員會(huì)文史資料征集委員會(huì)編:《三臺(tái)文史資料選輯》第5輯,內(nèi)部發(fā)行,1986年版,第7頁。同年8月,中央特派員廖承志、交通員楊德安與四川省委書記羅世文奉調(diào)赴川陜蘇區(qū)工作,三人從成都出發(fā)到三臺(tái),后經(jīng)鹽亭、南部、閬中、蒼溪交通站,在各地交通員護(hù)送下,于10月成功抵達(dá)川陜蘇區(qū)。(48)唐宏毅:《廖承志赴川陜蘇區(qū)》,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huì)議四川省綿陽市委員會(huì)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huì)編:《綿陽文史資料選刊》第12輯,內(nèi)部發(fā)行,1994年版,第36—42頁。1934年3月,四川省委還準(zhǔn)備派遣兩名地下黨(其中一人當(dāng)過兵,另一人是交通員),護(hù)送一名郵政局長前往川陜蘇區(qū),并計(jì)劃輸送一批失業(yè)工人、文化工作人員以及專業(yè)人才去蘇區(qū)。(49)《四川省委給中央的報(bào)告——省委最近工作及中江、邛大黨的狀況》(1934年3月14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7,內(nèi)部發(fā)行,1986年版,第185—186頁。經(jīng)由交通線的大規(guī)模人員流動(dòng),說明了四川省委與川陜蘇區(qū)之間秘密交通線的重要性。至1934年,四川省委與川陜蘇區(qū)之間已建立了三條秘密交通線,第一條由成都經(jīng)三臺(tái)、鹽亭、南部、閬中、蒼溪,渡東河到達(dá)川陜蘇區(qū),負(fù)責(zé)人員輸送;第二條由成都過三臺(tái)(柳池)、鹽亭、富村驛、南部(建興)、閬中、蒼溪,渡東河到達(dá)川陜蘇區(qū),負(fù)責(zé)情報(bào)傳遞;第三條由成都途徑三臺(tái)(瀘溪)、柳池、鹽亭、蒼溪,最后渡東河抵達(dá)川陜蘇區(qū),負(fù)責(zé)白區(qū)失業(yè)工農(nóng)群眾的運(yùn)送。(50)何薇、尚恩怡:《對(duì)1933年由成都進(jìn)入川陜蘇區(qū)秘密交通線的辨析》,《蘇區(qū)研究》2019年第6期,第76頁。三條交通線均有專人負(fù)責(zé)且分工明確,足見四川省委與川陜蘇區(qū)之間聯(lián)系的頻繁程度。
黨內(nèi)交通的創(chuàng)建和擴(kuò)展,自然意味著交通經(jīng)費(fèi)投入的增加。1927年9月,四川臨時(shí)省委向中央報(bào)告了8月份的經(jīng)費(fèi)預(yù)算,其中交通費(fèi)為100元,約占總經(jīng)費(fèi)的15%。(51)《四川臨時(shí)省委致中央報(bào)告——最近政治組織狀況和省委的工作》(1927年9月1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第85—86頁。不久,省委又上報(bào)了該年11月至1928年1月的預(yù)算,其中川漢交通費(fèi)每月130元,省內(nèi)交通費(fèi)每月80元,并強(qiáng)調(diào)省內(nèi)交通員只能“取步行或坐船,若全坐轎,此款當(dāng)不足”。(52)《四川臨時(shí)省委致中央的報(bào)告——關(guān)于十月份政治及校務(wù)工作概況》(1927年11月),《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第336—337頁。而實(shí)際上1927年8至11月中共四川省委接收中央下?lián)艿慕煌ㄙM(fèi)總額為260元,12月交通費(fèi)100元。顯然,中央下?lián)艿慕煌ㄙM(fèi)用并不能滿足實(shí)際所需,特別是隨著川漢交通線路投入運(yùn)作,四川中共組織呈報(bào)的交通費(fèi)預(yù)算也水漲船高,增加至230元,約為總預(yù)算的24%。(53)劉堅(jiān)予:《四川省委劉堅(jiān)予向中央的報(bào)告——關(guān)于四川政治經(jīng)濟(jì)形勢及黨務(wù)狀況》(1928年5月4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3,第236、239頁。但到1931年,由于四川中共組織工作內(nèi)容增加,新添了巡視、工運(yùn)、兵運(yùn)等,擠壓了交通費(fèi)支出,故在省委提交的8月份預(yù)算中,交通費(fèi)降為120元,約占總預(yù)算的15%,較1928年有明顯下降。(54)《四川省委致中央報(bào)告——政治路線和工作作風(fēng)的轉(zhuǎn)變》(1931年12月1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5,第553頁。
不過,經(jīng)費(fèi)不足的問題始終存在。1927年12月,四川臨時(shí)省委上報(bào)中央,“經(jīng)費(fèi)一錢沒有,終日只是借債度日,工作幾乎要無形停頓起來”,不僅無法遞送省內(nèi)的消息和文件,連給中央的“十一月報(bào)告,無錢派交通送上”。(55)《四川臨時(shí)省委給中央的報(bào)告——請(qǐng)解決軍事人才、黨團(tuán)省委關(guān)系、學(xué)習(xí)材料、經(jīng)費(fèi)等問題》(1927年12月24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第379—380頁。1928年5月,劉堅(jiān)予感嘆:“全靠省委工作同志到處東挪西借,勉強(qiáng)維持,無日不在籌款,無事不受經(jīng)費(fèi)之牽制(如前次派交通到中央,因無輪費(fèi),報(bào)告做好后,耽擱一月多不能動(dòng)身)。”(56)劉堅(jiān)予:《四川省委劉堅(jiān)予向中央的報(bào)告——關(guān)于四川政治經(jīng)濟(jì)形勢及黨務(wù)狀況》(1928年5月4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3,第236頁。沒有交通經(jīng)費(fèi),不能坐船出川向中央?yún)R報(bào),足見四川地區(qū)中共黨內(nèi)交通建設(shè)的窘迫。盡管多次呈報(bào)中央,四川省委的財(cái)政困境并未因此得到有效解決,1931年7月,省委再次直言已欠債約1500元,但各地工作又不能中斷,尤其是交通和印刷工作。(57)《四川省委給中央的信——關(guān)于經(jīng)費(fèi)、干部、器材等的要求》(1931年7月21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5,第501頁。1934年3月,省委報(bào)告中央:“川委目前工作展開,特別健全交通、巡視和訓(xùn)練工作,經(jīng)費(fèi)上感覺十分困難。”(58)《四川省委給中央的報(bào)告——省委最近工作及中江、邛大黨的狀況》(1934年3月14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7,第188頁。長期以來的經(jīng)費(fèi)匱乏,不僅導(dǎo)致黨內(nèi)交通工作難以保障,其他日常活動(dòng)也被嚴(yán)重影響。
此外,在動(dòng)蕩的時(shí)局下,黨內(nèi)交通還會(huì)出現(xiàn)信件丟失和貪污行為。1933年12月,為了指導(dǎo)遂安暴動(dòng),交通員需往來于四川省委和遂安縣委兩地,便出現(xiàn)了交通員丟失省委指示信的情況,無疑增加了暴動(dòng)被破壞的可能性。1934年7月,俞兒(交通員,后叛變)在負(fù)責(zé)四川地區(qū)中共交通工作時(shí),曾從上海獲取80元法幣的活動(dòng)經(jīng)費(fèi),到成都后需兌換成川洋(四川本地貨幣),約為90元,但他卻僅給交通人員川洋80元,多余款項(xiàng)未交付組織,若他“自己失掉一元錢又要黨補(bǔ)他”。(59)《四川省委向中央的報(bào)告——省委遭受破壞的教訓(xùn)》(1934年7月24日常委會(huì)通過),《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7,第330頁。更有甚者,還出現(xiàn)了交通員卷款潛逃之事,1930年底至1931年初,在川西交通線的開辟中,就出現(xiàn)過兩次交通員的卷款潛逃。(60)《四川省委致長江局報(bào)告——四川政治經(jīng)濟(jì)形勢及黨的工作情況》(1931年2月14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5,第432頁。當(dāng)然,信件丟失非主觀意愿,拿走余款屬貪污行為,卷款潛逃是見利起意,并不應(yīng)歸因于黨內(nèi)交通制度本身。
綜上,從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為了保障川內(nèi)以及四川與中央之間文件、信息、人員以及物資流動(dòng)的暢通,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四川地區(qū)中共組織逐漸建立了多條黨內(nèi)秘密交通線,此舉無疑緩解了信息溝通、指示傳達(dá)、經(jīng)費(fèi)輸送的壓力,有利于四川中共組織研判內(nèi)外環(huán)境、整合多方資源,維系了川內(nèi)中共革命力量的生存和發(fā)展。不過,受困于人員和經(jīng)費(fèi)的掣肘,文件、信息、人員以及物資常常無法準(zhǔn)時(shí)送達(dá),影響了黨內(nèi)交通的順暢互動(dòng),以致仍需外部郵政寄遞和人員往來作為補(bǔ)充。四川地區(qū)中共組織的這種通訊形勢,一方面隔離和斷裂了四川地區(qū)中共組織的聯(lián)系,影響了上下級(jí)之間的信息溝通、指示傳達(dá)、經(jīng)費(fèi)輸送,但正如一枚硬幣的兩個(gè)面向一樣,這種隔離和斷裂,也保留了地方黨組織發(fā)展的自主性,使其可在四川軍閥的嚴(yán)厲政策下艱難成長。
三、通訊與地方黨組織的自主性
在中共革命早期,四川地區(qū)的中共組織并不處于革命版圖中的核心位置,也不像貴州地區(qū)一樣,是在與上級(jí)失聯(lián),處于斷線狀態(tài)中自主發(fā)展起來的,而是在惡劣的自然和政治環(huán)境下,無法實(shí)現(xiàn)與中共中央的正常聯(lián)系(也包括中共四川省委和基層黨部之間),屬于時(shí)聯(lián)時(shí)斷的情況。那么,在上級(jí)機(jī)關(guān)鞭長莫及,無法提供實(shí)際指導(dǎo)之下,就產(chǎn)生了上級(jí)指示與地方黨組織實(shí)際運(yùn)作之間一種微妙的“落差”,以及這種“落差”所逐漸衍生的自主性。
那么,我們不禁要問,上文所討論的四川地區(qū)中共通訊與地方黨組織的自主性之間到底什么關(guān)系?為了回答這一問題,茲舉幾例以示說明,內(nèi)容分別涉及農(nóng)民暴動(dòng)、軍隊(duì)兵變以及建立蘇區(qū)之爭。
關(guān)于第七混成旅兵變。江防第七混成旅屬軍閥鄧錫侯江防軍黃逸民部,1928年秋中共便在該軍隊(duì)建立了黨組織,1929年初曾領(lǐng)導(dǎo)過廣安觀音閣和遂寧罷操索餉,以及士兵代表團(tuán)驅(qū)逐反動(dòng)官兵的斗爭。然而,兩次斗爭也給黨組織的生存帶來了隱患。為清除中共在軍隊(duì)中的影響,師長李其相開始拖延甚至斷絕該部隊(duì)的給養(yǎng),以至部隊(duì)一日三餐都成問題。鑒于此,同年5月,怡生特委(即江防第七混成旅旅委)一面派人趕赴合川縣委,說明“軍支所在部隊(duì)有立刻被黃隱、李其相解決的危險(xiǎn)”,請(qǐng)求合川縣委給予援助。(61)《川東特委軍委通告(行字第1號(hào))——關(guān)于第七混成旅兵變的軍事工作任務(wù)》(1929年5月14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8,內(nèi)部發(fā)行,1986年版,第20頁。同時(shí),又直接上報(bào)至四川臨時(shí)省委,決定舉行兵變。但是,四川臨時(shí)省委并不認(rèn)可兵變的請(qǐng)求,認(rèn)為兵變條件尚不成熟,要求怡生特委盡可能延遲一段時(shí)間。(62)《四川臨時(shí)省委通訊第274號(hào),維字第4號(hào)——關(guān)于第七混成旅兵變策略和組織問題的指示》(1929年5月16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4,第56—57頁。6月,怡生特委又請(qǐng)求批準(zhǔn)起義,四川臨時(shí)省委再次要求其不能輕舉妄動(dòng),應(yīng)該“盡量運(yùn)用策略延緩一個(gè)時(shí)期,增加準(zhǔn)備方面的工作”。(63)《四川省委通訊偉字第1號(hào),覺字第1號(hào)——關(guān)于加強(qiáng)第七混成旅兵變準(zhǔn)備工作的指示》(1929年6月),《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4,第86—87頁。同月28日,針對(duì)怡生特委再次送來的請(qǐng)示報(bào)告,四川省軍委開始作出讓步,強(qiáng)調(diào)理解特委的艱難處境,但仍希望其“積極加緊準(zhǔn)備工作,發(fā)動(dòng)群眾起來,盡可能使這一工作有充分把握”,并指示怡生特委一旦發(fā)動(dòng)兵變,應(yīng)先去遂寧鄉(xiāng)打游擊戰(zhàn),且必須旗幟鮮明反對(duì)軍閥等。(64)《四川省軍委通訊偉字第1號(hào),覺字第2號(hào)——關(guān)于第七混成旅兵變策略總路線的指示》(1929年6月28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4,第92—108頁。但該指示信還未送達(dá)旅委,29日午后1時(shí),旅長曠繼勛就以革命委員會(huì)代表身份通告支隊(duì),宣布成立工農(nóng)革命委員會(huì),舉行兵變。午后8時(shí),即帶領(lǐng)軍隊(duì),兵分兩路向蓬溪進(jìn)發(fā)。至7月30日,部隊(duì)在梁山貓兒寨寡不敵眾,起義最終失敗。(65)《怡生特委書記周三元給省委的報(bào)告——關(guān)于第七混成旅兵變經(jīng)過》(1929年7月),《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8,第63—68頁。審視第七混成旅兵變的整個(gè)過程,怡生特委與四川省委的通訊可謂頻繁,但雙方對(duì)兵變的認(rèn)知完全相反,無法達(dá)成一致意見。當(dāng)然,四川省軍委的28日回信確實(shí)沒有及時(shí)送達(dá)旅委,以致省委在兵變的經(jīng)驗(yàn)總結(jié)中也批評(píng)怡生特委行事匆忙,連“省委的回信都沒有接著就拖起跑了,發(fā)動(dòng)后也不給省委的報(bào)告”。(66)《四川省委通訊第5號(hào)——關(guān)于第七混成旅兵變中錯(cuò)誤的批評(píng)及今后工作的指示》(1929年7月10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4,第111頁。但28日回信僅是四川省軍委的妥協(xié)和指示兵變后的行軍路線及策略,對(duì)兵變能否成功、革命能否堅(jiān)持至關(guān)重要嗎?這也許是個(gè)問題。但可以明確的是,通訊的滯后并不是曠繼勛發(fā)動(dòng)兵變的主要原因,第七混成旅所處的生存環(huán)境和革命訴求,才是地方黨組織長成的關(guān)鍵因素,而非通訊這一技術(shù)手段。
關(guān)于下東蘇區(qū)的爭論。1932年2月,中共四川省委接到中共中央要求創(chuàng)建蘇區(qū)的指示后,梁山中心縣委即在虎城區(qū)發(fā)動(dòng)游擊戰(zhàn)爭。同年4月,四川省委再次明確了梁山中心縣委的任務(wù),是實(shí)地“學(xué)習(xí)游擊戰(zhàn)爭”,“奪取敵人武裝”,“創(chuàng)造川東蘇維埃政權(quán)”。(67)《四川省委致梁山中心縣委信——關(guān)于組織工作的指示》(1932年4月28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6,第40頁。不過,圍繞創(chuàng)建全川東蘇區(qū)還是下東蘇區(qū),四川中共組織內(nèi)部卻產(chǎn)生了分歧。部分四川省委成員認(rèn)為,虎南赤區(qū)“雖是二個(gè)偏僻小場,但已跨著梁開二縣,它的周圍又有過去一、二、三路紅軍的影響”,故“成立蘇維埃的一天就應(yīng)是川東蘇維埃”。同時(shí),團(tuán)四川省委和另一部分省委成員卻認(rèn)為,虎南赤區(qū)雖有60多名黨員,1000名左右農(nóng)協(xié)會(huì)員,2000余人的青農(nóng)成員,但“黨的工作不健全,差不多全是英雄領(lǐng)導(dǎo)”,故建議“在下東創(chuàng)造蘇區(qū)而不是就建立川東蘇維埃,由創(chuàng)造個(gè)別蘇區(qū)而發(fā)展成為全川東蘇維埃”。雙方觀點(diǎn)明確且互不相讓。在相持不下后,中共四川省委寫信上報(bào)中共中央,請(qǐng)求最終裁決。(68)《四川省委致中央報(bào)告——關(guān)于創(chuàng)造下東蘇區(qū)問題》(1932年5月),《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6,第59—62頁。圍繞創(chuàng)建全川東蘇區(qū)還是下東蘇區(qū)的爭論,本質(zhì)是如何執(zhí)行中共中央廣泛建立游擊區(qū)和蘇維埃的問題,僅從中共中央戰(zhàn)略意圖看,“畢其功于一役”的全川東蘇區(qū)顯然更能表現(xiàn)立場堅(jiān)定。不過,這種立場正確并未得到四川中共組織的廣泛支持,甚至可以說,反對(duì)聲音還要更高一些,不僅是四川省委的部分人員,還包括團(tuán)四川省委的全部,甚至上報(bào)中央文件的起草者,也明確支持先在下東建立蘇區(qū)。當(dāng)然,在四川中共組織等來中央指示之前,梁山中心縣委領(lǐng)導(dǎo)下的虎城區(qū)農(nóng)民組織就遭到破壞,下東蘇區(qū)最終失敗。下東蘇維埃的失敗,主要原因仍是自身力量薄弱,敵對(duì)勢力強(qiáng)大,通訊在上級(jí)與下級(jí)關(guān)系中所起的作用,雖然存在,但卻不是決定性的。
關(guān)于遂安農(nóng)民暴動(dòng)。1933年夏秋之際,遂寧、安岳一帶由于夏季苦旱、入秋苦雨,大季主要作物紅苕的產(chǎn)量,僅為1932年的三分之一,“且在地內(nèi)爛了些”。不過,地租并未減少,“捐稅急如星火,借貸無門”,以致兩縣農(nóng)民的生存遇到巨大挑戰(zhàn)。恰在此時(shí),川陜紅軍進(jìn)入鼎盛時(shí)期,加之軍閥留守于遂寧、安岳部隊(duì)甚少。基于此,中共遂安縣委認(rèn)為,此地“組織迸(69)迸,即奔。騰發(fā)展,群眾武裝斗爭情緒如狂潮一般”,暴動(dòng)時(shí)機(jī)已經(jīng)成熟,“不即干,真是無產(chǎn)階級(jí)的罪人”,并決定于農(nóng)歷11月9日領(lǐng)導(dǎo)通賢場、涼風(fēng)店、龍臺(tái)三區(qū)的農(nóng)民暴動(dòng)。(70)《四川省委關(guān)于遂安暴動(dòng)問題向中央的報(bào)告——省委、省巡視員、遂安縣委往來信件摘錄》(1933年12月24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6,第539—563頁。不過,由于出現(xiàn)消息泄露,引發(fā)當(dāng)?shù)匚溲b抓捕,遂安縣委不得不將暴動(dòng)時(shí)間提到農(nóng)歷11月6日,但暴動(dòng)不久即被鎮(zhèn)壓。縱觀遂安暴動(dòng)的經(jīng)過,從省委收到遂安縣委第一封請(qǐng)求暴動(dòng)的信件開始,便回信不同意其立即組織暴動(dòng),但交通員不慎將此信件丟失,之后遂安縣委又多次向省委提出舉行暴動(dòng),省委隨之去信,亦力求“制止他們的冒險(xiǎn)盲動(dòng)”。(71)《四川省委關(guān)于遂安暴動(dòng)問題向中央的報(bào)告——省委、省巡視員、遂安縣委往來信件摘錄》(1933年12月24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6,第539—563頁。關(guān)于遂安暴動(dòng)是否應(yīng)該發(fā)動(dòng),或者說,是中共四川省委的日常斗爭正確,還是遂安縣委的暴動(dòng)更符合實(shí)際情況,這里很難給予是非的判斷。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即便交通員沒有丟失指示信件,或者指示信件準(zhǔn)時(shí)到達(dá),遂安農(nóng)民暴動(dòng)是否還會(huì)如約而至,恐怕就要涉及上下層級(jí)關(guān)系以及遂安政治軍事生態(tài)等復(fù)雜面向了。
無論是第七混成旅的兵變,還是下東蘇區(qū)之爭論,抑或是遂安農(nóng)民暴動(dòng),都屬于通訊阻塞或中斷后引發(fā)的地方黨組織自主行為,是基層黨組織根據(jù)客觀環(huán)境作出的一種形勢判斷。由此看,四川地區(qū)中共組織的通訊與自主性之間并非簡單的因果關(guān)系,通訊受阻或許一定程度上導(dǎo)致了地方黨的自主性,但四川黨組織所作的判斷與行動(dòng),更多的是源于其所處的客觀環(huán)境,而非通訊是否暢通。質(zhì)言之,在外有強(qiáng)敵的情況下,地方黨組織能否生存與發(fā)展是其自主性強(qiáng)弱的核心因素。
實(shí)際上,除通訊本身外,非中共革命版圖中心的地位、組織架構(gòu)的多層級(jí)性,以及“蜀道難”的地理?xiàng)l件,都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共地方黨組織的自主性。
首先,在中共革命早期版圖中,四川地區(qū)既不屬于核心位置,又不屬于邊緣地帶,客觀上決定了四川地方黨組織在集中與自主之間的游離。一方面,四川素來就有革命的歷史傳統(tǒng),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yùn)動(dòng),再到中共組織的創(chuàng)建,四川一直走向全國的前列,很早便產(chǎn)生了諸如社會(huì)主義青年團(tuán)、中國青年共產(chǎn)黨等進(jìn)步團(tuán)體。因此,四川中共革命的早期,基本是由四川本地骨干主導(dǎo)的,如王右木、楊闇公、吳玉章、廖劃平、童庸生等。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力量有限,其精力主要集中于東部,對(duì)四川力有不逮,無法給予人員和經(jīng)費(fèi)的全力支持。1931年4月,團(tuán)四川省委在上報(bào)團(tuán)中央的信件中,直指“去年自十月以后即未得中央?yún)R一款來”,向中央提交的幾次報(bào)告和通信,也未見中央答復(fù)。(72)《團(tuán)四川省委致團(tuán)中央報(bào)告——省委補(bǔ)選與各部工作》(1931年4月),《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9,第208頁。1933年11月,四川省委在上報(bào)中共中央的信件中,也強(qiáng)調(diào)中央對(duì)“川委工作的指導(dǎo)太忽視,自從有黨以來,只小隅巡視過一次,來不過兩天就走”,中央給四川的指示信也“遲得太厲害”,交通員“在滬等了兩月余”,中央才把指示信寫完,而省委“所要的中央通信處,一年余不發(fā)”,“要的游戰(zhàn)小冊(cè)、兵運(yùn)指導(dǎo)信,不但不拿來,數(shù)次信都不回”。(73)《四川省委昆致中央的報(bào)告——關(guān)于四川經(jīng)濟(jì)政治狀況、黨的組織和黨領(lǐng)導(dǎo)下的群眾工作》(1933年11月11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6,第528頁。中共中央對(duì)四川中共組織的行為,也許是對(duì)全國革命形勢研判下的反映,也許是客觀偶發(fā)因素或個(gè)人工作方式所致,很難給予貼近真實(shí)的歷史還原,但這種行為,毫無疑問會(huì)激起四川地區(qū)中共組織的怨言,這種不滿或許就是引發(fā)“自作主張”的原因之一。
其次,是中共組織架構(gòu)的多層級(jí)性。需要強(qiáng)調(diào)的是,信息垂直傳遞并不必然導(dǎo)致弱化效應(yīng),在一定的制度環(huán)境下,還可能出現(xiàn)強(qiáng)化效應(yīng),如“層層加碼”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這取決于上下層級(jí)的數(shù)量和歸屬關(guān)系的強(qiáng)弱。不過,在中共革命的早期,尤其在白區(qū)工作中,這種信息垂直傳遞的弱化效應(yīng)是明顯的。在四川共產(chǎn)主義組織創(chuàng)建早期,各地黨團(tuán)組織基本上直屬黨團(tuán)中央領(lǐng)導(dǎo),直到1926年中共重慶地委成立,成為中共在四川建立的第一個(gè)最高機(jī)關(guān),領(lǐng)導(dǎo)全省黨組織。1927年8月,四川臨時(shí)省委建立后,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以及中共五大黨章規(guī)定,各地黨組織名稱都需依據(jù)當(dāng)時(shí)行政區(qū)劃更改,黨組織層級(jí)也由原來的四級(jí)變動(dòng)為“中央—省委—市縣委—區(qū)委—支部”五級(jí)。除此之外,自四川臨時(shí)省委成立后,還在川西、川東和川南等地建立特委或中心縣委,如1927年11月,臨時(shí)省委在重慶建立后,為便于指揮川西地區(qū)的政治軍事,領(lǐng)導(dǎo)川西地區(qū)的黨組織,于成都建立了川西特委。伴隨著中共組織系統(tǒng)的完善和發(fā)展,在惡劣的政治環(huán)境中,消息與文件傳遞的壓力也隨之增加,而信息垂直傳遞的弱化效應(yīng),又是地方黨組織自主性的土壤。對(duì)此,四川省委感慨道:“省委與各地方關(guān)系本就太不親密,各地沒有詳細(xì)的報(bào)告,省委又缺乏巡視工作,中間還隔一層特委,中央的和省委的指示經(jīng)過幾道折扣,傳達(dá)到支部,簡直不成一個(gè)樣子了。”(74)《四川省委兩月工作總報(bào)告——從6月15日新省委成立到8月20日移回重慶》(1929年10月9日),《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4,第234頁。
最后,四川地區(qū)特殊的地理?xiàng)l件和革命環(huán)境,也增加了中共地方黨組織自主性的可能。四川地處上江上游,其核心地區(qū)屬于典型的盆地地形,盆地四周圍繞著海拔1000—3000米的山地或高原,盆地內(nèi)部地勢北高南低、南部為長江干流所經(jīng),北部各支流分別穿經(jīng)盆地中北部南流入江,形成一個(gè)相對(duì)獨(dú)立的地理單元。四川經(jīng)濟(jì)文化的內(nèi)外交流常因“其間山峽崎嶇,灘流沖突,水陸轉(zhuǎn)運(yùn),皆有節(jié)節(jié)阻滯之虞”。(75)宓汝成編:《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1863—1911)》第3冊(cè),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1058頁。在這樣的地理環(huán)境之下,文件、信息、人員、物資的流動(dòng),常常滯后于革命形勢的變化和需要,迫使地方黨組織不得不自行選擇行動(dòng)策略。同時(shí),四川極為復(fù)雜的政治軍事格局也極大阻礙了地方黨組織的革命活動(dòng)。自袁世凱去世后,各地軍閥相互混戰(zhàn)、割據(jù)稱雄,在四川地區(qū),各軍閥還實(shí)行“防區(qū)制”抵制其他軍閥,保證自身地盤和軍事實(shí)力。四川中共組織成立以后,川內(nèi)各派系軍閥勢力此消彼長、分分合合,但對(duì)中共的打擊卻一直持續(xù)。因此,四川黨團(tuán)組織幾乎一直處于地下活動(dòng)狀態(tài),獲取內(nèi)外消息極為不易,在信息真空的環(huán)境中,地方黨組織的自主性自然容易得到萌發(fā)。
當(dāng)然,在考察四川地區(qū)中共組織自主性的同時(shí),也不能忽視列寧主義政黨集中的力量。從1922年成都、重慶、瀘縣等地方團(tuán)組織的建立開始,一直持續(xù)到1935年,中共在四川地區(qū)的發(fā)展幾經(jīng)波折,中間還經(jīng)歷了“三三一”慘案,但生命力極強(qiáng),總體上呈現(xiàn)出上升趨勢。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點(diǎn),就是中共中央的指導(dǎo)和幫助,無論是發(fā)展方向的把握,還是經(jīng)費(fèi)人員的支持,抑或是多次重建四川省委,如果沒有中共中央的統(tǒng)籌與協(xié)助,僅靠四川地區(qū)中共組織的自身力量,恐怕多會(huì)出現(xiàn)貴州中共組織一樣的結(jié)局,在遭到地方軍閥破壞以后,即一蹶不振。四川中共組織1935—1936年的沉寂,亦可作為“央地”關(guān)系的佐證。由于叛徒的出賣,1935年6月,四川省委遭到地方軍閥破壞,省內(nèi)黨組織元?dú)獯髠?次年2月,僅存的自貢中心市委也遭破壞,四川境內(nèi)中共組織至此消失殆盡。但為什么之前四川黨組織在遭到破壞后,可以重建,而此次就難以為繼呢?顯然,這與此時(shí)中共中央在西北剛剛落腳,還無暇顧及四川地方的黨組織有關(guān)。或者說,在中央發(fā)展限于困境時(shí),也就無力從人員經(jīng)費(fèi)以及方針政策上予以幫助。
結(jié)語
在四川中共組織建立和發(fā)展的早期,借助于傳統(tǒng)通訊技術(shù)體系以及人員往來攜帶等方式,四川地區(qū)中共實(shí)現(xiàn)了組織內(nèi)必須的信息溝通、指示傳達(dá)和經(jīng)費(fèi)輸送,這種通訊方式具有明顯的外部性和臨時(shí)性特征。不過,從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受限于外部政治環(huán)境的變化,郵政寄遞和人員往來很難實(shí)現(xiàn)常態(tài)化和制度化,故從“八七”會(huì)議之后,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四川地區(qū)的中共組織逐漸建立了多條黨內(nèi)秘密交通線,此舉無疑緩解了信息溝通、指示傳達(dá)、經(jīng)費(fèi)輸送的壓力,維系了川內(nèi)中共革命力量的生存和發(fā)展。
但是,非中共革命版圖中心的地位、組織架構(gòu)的多層級(jí)性,以及“蜀道難”的地理?xiàng)l件,都使得四川中共組織具有明顯的隔離特征。正因?yàn)榇?川內(nèi)中共組織才保留相當(dāng)大的自主性,可以在四川軍閥的嚴(yán)厲政策下艱難成長。論者認(rèn)為,在土地革命時(shí)期,中央屢犯“左”傾錯(cuò)誤,而中央與各蘇區(qū)相去甚遠(yuǎn),正是在此交通通訊不便的情況下,毛澤東創(chuàng)建中央蘇區(qū)和中央紅軍的過程中較少受到錯(cuò)誤干擾,成功開辟了由“地方軍事化”到“軍事地方化”的獨(dú)特發(fā)展道路。(76)應(yīng)星:《軍事發(fā)包制》,《社會(huì)》2020年第5期,第6頁。與毛澤東的“軍事地方化”成功不同,同樣的交通通訊不便,并沒有給四川地區(qū)中共組織帶來成功,相反的是,四川中共革命在1935年后陷入了長時(shí)間的低谷。但是,我們并不能因?yàn)樗拇ǖ貐^(qū)中共革命的挫折,就否認(rèn)一定的自主性所帶來的活力和靈動(dòng),尤其是政治壓力和軍事打擊嚴(yán)厲之時(shí),這種自主性就顯得更加彌足珍貴。更進(jìn)一步講,正是由于屢次自主性的試錯(cuò),才換來尤為珍貴的成功,而這種成功又可以被復(fù)制,并引導(dǎo)中共革命走向勝利。
歷史研究的一個(gè)重要任務(wù),就是挖掘和揭示各種“關(guān)系”的互動(dòng)性、豐富性和復(fù)雜性。(77)李金錚:《抗日根據(jù)地的“關(guān)系”史研究》,《抗日戰(zhàn)爭研究》2016年第2期,第10頁。就中共地下黨而言,這種“關(guān)系”可以是隱性的,表現(xiàn)為組織成員之間疏離與矛盾、思想的碰撞與沖突,也可以是顯性的,表現(xiàn)為組織之間信息、文件、物資的流動(dòng)。對(duì)于后世的研究者來說,隱性關(guān)系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即便根據(jù)歷史人物的日記,也較難判斷其對(duì)事態(tài)發(fā)展的影響。相反,依據(jù)遺留之文獻(xiàn),通過信息、文件、物資流動(dòng)的頻率和內(nèi)容,或一定程度上可以考察出中央與地方以及地方各組織之間的親密關(guān)系,這是顯性關(guān)系的優(yōu)勢。文本所討論的,無論是郵政寄遞、人員往來,還是黨內(nèi)交通機(jī)構(gòu)、交通網(wǎng)絡(luò),均可視為“央地”關(guān)系的顯性樣態(tài)。由此看,對(duì)中共通訊工作的研究,無疑就是對(duì)挖掘和揭示“關(guān)系”的一種推動(dò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