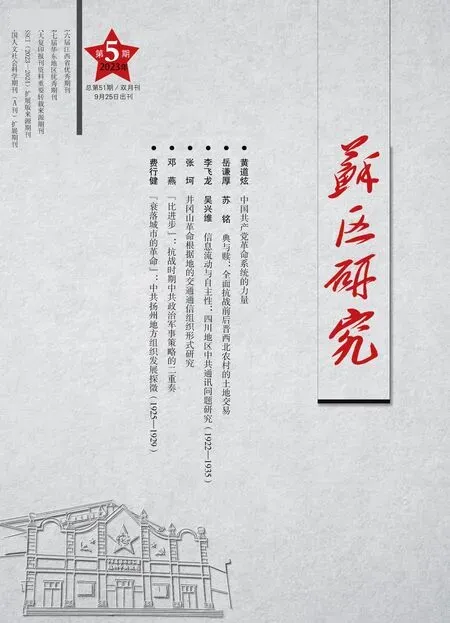覺醒與重塑:中國早期共產主義者革命觀的馬克思主義轉向
李超群
近代中國內憂外患、禮崩樂壞的困頓時局使得無數知識精英急欲尋求治國救民的革命觀念和思想來求解舊中國積貧積弱的問題根源。最終,在眾多流派思潮的相互激蕩中,馬克思主義以其豐富的科學性、實踐性、斗爭性脫穎而出,成為眾多進步知識精英的堅定選擇。然而,值得一提的是,這些脫胎于舊社會的知識精英進行自我思想清算以選擇和接受馬克思主義來重塑自身革命觀并非一蹴而就、一舉頓悟的過程,其中有諸多歷史邏輯和細節值得深入考察和分析。當前,學界關于中國共產黨早期革命觀的研究,大多著眼于對某一革命先驅的革命思想研究或中國共產黨早期革命思想中某一方面的研究(1)關于某一早期共產主義者的革命思想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張艷國:《李大釗、瞿秋白對俄國道路的認識》,《中國社會科學》2016年第10期;劉輝:《惲代英與中國共產黨階級分析的興起》,《人文雜志》2018年第6期;楊奎松:《淺談中共建黨前后的列寧主義接受史——以1920年前后毛澤東的思想轉變及列寧主義化的經過為例》,《史學月刊》2021年第7期;侯慶斌:《旅法期間蔡和森革命觀的形塑與表達》,《中共黨史研究》2023年第2期;楊泰龍:《多向度的“革命”:中共成立前陳獨秀革命思想演變探究》,《蘇區研究》2023年第3期。關于中國共產黨早期革命思想的某一方面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周家彬:《早期中國共產黨對無產階級領導權理論的探索》,《馬克思主義研究》2020年第12期;周利生、劉堅:《早期中共黨人對“反帝”的認識(1921—1927)——兼論國共黨內合作》,《黨史研究與教學》2021年第3期;楊泰龍:《革命與農民:中共對農民革命的認知演進與理論建構》,《黨史研究與教學》2021年第4期;歐陽哲生:《從五四時期的“主義”建構到中共初創的行動綱領——一條思想史線索的考察》,《中共黨史研究》2021年第6期。,尚缺乏對早期共產主義者革命觀的整體性觀照與深入闡釋,更鮮有對早期共產主義者在選擇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過程中其革命觀轉變前后的比較研究以及對其革命觀轉向的歷史緣由的深入探究。鑒于此,在當前結論預設、宏大敘事的理論背景下,將目光聚焦于“歷史的個體”和“個體的歷史”,著眼于歷史洪流中個體革命意識醞釀與覺醒的心路歷程,選取以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蔡和森等為代表的中國早期共產主義者革命觀轉變這一視角來透視和回溯他們是如何選擇馬克思主義、選擇無產階級革命道路等一系列問題。同時,從中窺探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思想運動的整體性歷史圖景,并為學界已有相關研究成果作一補充和完善。
一、早期共產主義者革命觀轉向的內容考察
近代中國復雜的社會歷史情境造就和影響了眾多進步知識分子的思想前史和觀念轉向。20世紀20年代前后,由于國際國內一系列事件與因素的影響,早期共產主義者在各種主義思潮的眾聲喧嘩中不僅實現了自身理想信仰的堅定,其革命觀也在此過程中展現出向馬克思主義轉向的思想演變軌跡。
(一)革命主體:從“民眾的大聯合”到“注重農人工人的勢力”
能否準確劃定革命主體是中國革命勝利與否的前提條件,這事關革命領導者對于革命潛在力量的挖掘、組織與動員。具體而言,受制于中國傳統思想中圣賢觀、民本主義等影響,一些進步知識分子雖然或多或少認識到中國革命離不開平民大眾的支持和呼應。但是,他們認為平民大眾不可能自發自覺地產生革命性,而需要依靠社會賢達、知識分子對他們開蒙啟智。早在1912年6月,青年毛澤東在《商鞅徙木立信論》中就把國家困頓淪落的根源歸于民眾受傳統封建文化之禁錮而愚不能知,“吾讀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嘆吾國國民之愚也,而嘆執政者之煞費苦心也,而嘆數千年來民智之不開、國幾蹈于淪亡之慘也。”(2)《商鞅徙木立信論》(1912年6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頁。對于這樣一種社會境況,“齏其躬而有益于國與群,仁人君子所欲為也。”(3)《致友人信》(1915年7月),《毛澤東早期文稿》,第12頁。即是說他將救世啟智的希望寄托于仁人圣賢。惲代英在青年時期也一度持類似的觀點。(4)1919年6月19日,惲代英在起草武漢學生聯合會對于全國學生聯合會的宣言書中,認為學生聯合會的宗旨之一在于“注意下級平民的通俗教育”,如果方法施行得當,則“下級平民藉此固能得多少覺悟,一改其今日昏迷不醒之狀態”。可見,惲代英當時也持民智未開的觀點,并提倡知識分子對平民大眾進行開蒙啟智。參見《武漢學生聯合會提出對于全國學生聯合會意見書》(1919年6月19日),《惲代英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9頁。客觀而言,這一認識在當時具有一定的進步性,但依舊沒有擺脫傳統封建文化中上智下愚式的思想枷鎖。
“五四”時期,無政府主義的廣泛傳播促使平民主義、勞動主義思潮流行開來。受此影響,知識分子將革命目光轉移到平民大眾身上,平民大眾在他們的視野中不再以漠視國事的“草野愚民”(5)參見《安徽愛國會演說》(1903年5月26日),《陳獨秀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頁。的形象出現,而是作為組織化的革命火種被寄予厚望。1919年7月,毛澤東在《湘江評論》的創刊宣言中寫道:“世界什么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么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6)《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1頁。他主張采取民眾大聯合的方法來推翻強權,爭取自由。并認為,蘇俄十月革命“以民眾的大聯合,和貴族的大聯合資本家的大聯合相抗,收了‘社會改革’的勝利”(7)《民眾的大聯合(一)》(1919年7月21日),《毛澤東早期文稿》,第313頁。。據此,他號召:“刻不容緩的民眾大聯合,我們應該積極進行!”(8)《民眾的大聯合(三)》(1919年8月4日),《毛澤東早期文稿》,第356頁。此時的毛澤東尚處于由激進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過程中,他雖然認識到民眾中所蘊藏的革命潛力,但是激進而又籠統地認為中國革命主體是泛指在封建軍閥統治下的一切受壓迫者群體。1919年11月,陳獨秀在《實行民治的基礎》一文中分析中國革命應采取民治主義和民治政治時亦認為,“人民直接的實際的自治與聯合”(9)《實行民治的基礎》(1919年11月2日),《陳獨秀文集》第1卷,第499頁。是實行民治的真正基礎。中國實行民治主義的形式是成立地方自治和同業聯合兩種組織。可見,他們已經意識到中國革命需要廣大民眾參與其中并主動聯合起來同強權勢力作斗爭。但是,客觀而言,民眾大聯合這一觀點,主要還是基于平民主義思潮的影響以及從革命主體數量層面來考察所得出的政治主張,而尚未考量到不同階級力量的革命性和斗爭性。
20世紀20年代,隨著馬列主義著作的廣泛傳播以及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相結合,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和階級分析方法成為早期共產主義者考量革命主體力量的重要依據和方法,工農大眾作為最富有反叛意識的革命群體成為他們考量中國革命主體的新關注點。1923年12月,陳獨秀在《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一文中認為在半殖民地社會,農民階級因人口眾多,自然是“國民革命之偉大的勢力,中國之國民革命若不得農民之加入,終不能成功一個大的民眾革命”。但是,他又指出農民階級由于散漫且封建保守,必須有“強大的無產階級為主力軍,才能夠實現此種革命的爭斗并擁護此種革命的勢力建設此種革命的事業”。工人階級“一旦感覺得這種革命于自身亦有利益時,往往成為急進的先鋒”。(10)《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1923年12月1日),《陳獨秀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97—498頁。可見,陳獨秀認為農民作為革命的重要力量,必須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之下,才能形成組織化的革命力量。1924年4月,惲代英在《中國革命的基本勢力》一文中亦認為,中國革命不能依賴士商紳吏、兵匪游民等階級。“我們所應當倚賴的,必須是真正的生產者——農人,工人。”(11)《中國革命的基本勢力》(1924年4月20日),《惲代英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56頁。他們已經初步意識到革命民眾是劃分階級的,并就工農聯盟是革命主體力量這一認識達成基本共識。但是,受制于認識的局限性、革命實踐的缺乏以及俄國革命經驗的影響,他們對于農民這一革命力量的考量,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數量與規模優勢以及隨之產生的“人多力量大”的簡單邏輯認識,而尚未充分認識到中國農民在“壓迫—反抗”的革命邏輯下所天然富有革命性和斗爭性,沒有著眼于農民革命主體性意識的喚醒。這一認識在大革命失敗后,隨著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運動的開展以及毛澤東對于農民革命性問題的不斷認識中得到轉變和深化。
(二)革命對象:從“反對強權”到推翻“三座大山”
準確劃分革命對象是革命斗爭開展的基本前提。正如毛澤東所言:“中國過去一切革命斗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12)《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頁。在這一問題上,早期共產主義者歷經了從感性到理性、從籠統到清晰、從片面到科學的認識理路。具體而言,五四運動以前,一些進步知識分子對于帝國主義大都是基于其侵略罪行和強盜行為所產生的激憤中來認識的,尚處于排外主義的感性認識階段,尚未認清帝國主義的性質和侵略本質。例如,1914年11月,陳獨秀在一戰爆發不久后就指出:“夫帝國主義,人權自由主義之仇敵也,人道之洪水猛獸也。”(13)《愛國心與自覺心》(1914年11月10日),《陳獨秀文集》第1卷,第84頁。但是,對于一戰后協約國的勝利,陳獨秀卻認為這是“公理戰勝強權”(14)參見《隨感錄》(1919年2月9日),《陳獨秀文集》第1卷,第390頁。的勝利,并幻想協約國一方能夠取消列強對華的一切不平等條約。這種矛盾認識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當時知識分子對于帝國主義的片面認知。
20世紀20年代前后,由于國內外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影響,一些進步知識分子開始認識到帝國主義的本質以及其與本國封建軍閥之間的勾連。“我們歷來對外的信條,總是‘以夷制夷’;對內的信條,總是‘依重特殊勢力’。這都是根本的大錯。”(15)《秘密外交與強盜世界》(1919年5月18日),《李大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58頁。李大釗一語道破民國政府對外妥協于列強,對內依賴于封建軍閥勢力的政治軟弱性。他在1919年發表的《秘密外交與強盜世界》《再論新亞細亞主義》等文章中揭露了帝國主義的腐朽性和垂死性,并強調要“反抗侵略主義,反抗強盜世界的強盜行為”(16)《秘密外交與強盜世界》(1919年5月18日),《李大釗全集》第2卷,第457頁。。惲代英在1924年6月發表的《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一文中亦指出通過革命來推翻軍閥和反抗帝國主義這兩項任務“必須同時的同樣的加以注意”(17)《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1924年6月14日),《惲代英全集》第6卷,第402頁。。他們已經認識到必須把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一并作為首當其沖的革命對象。
政治上層建筑建立在一定社會經濟基礎之上是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早期共產主義者依據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來觀察和分析封建軍閥賴以生存的經濟與社會基礎,進一步認識到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統治的關鍵所在。1923年6月,瞿秋白在起草黨的三大黨綱草案時就指出:“中國舊時的經濟生活極其散漫,并沒有成為一個集中的經濟區域,這些散漫的半獨立的區域,到處都能夠將財閥的經濟力去供給軍事長官或土匪,使他們都有所憑借;因此就造成了軍閥統治的政治形勢。”(18)《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1923年6月),《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3頁。他敏銳地認識到中國分散且封閉的封建地主經濟是滋養封建軍閥統治根基的根源。周恩來在分析廣東革命形勢后亦有類似認識:“買辦、大地主、逆黨、土豪、民團、土匪、貪官污吏沒有一種不是舊社會遺存的半封建勢力,沒有一種勢力不是與革命為敵的。”(19)周恩來:《現時廣東的政治斗爭》(1926年12月17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520頁。中國革命在反帝反軍閥的同時,也要“與一切半封建勢力作政治斗爭”(20)周恩來:《現時廣東的政治斗爭》(1926年12月17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3冊,第521頁。。但是,“半封建勢力”的成分較為復雜,指向籠統且不清晰,難以從中精準劃定革命對象的主次。1926年9月,毛澤東在充分考察中國社會各階級狀況及政治態度的基礎上認為,農村封建地主階級“乃其國內統治階級國外帝國主義之唯一堅實的基礎,不動搖這個基礎,便萬萬不能動搖這個基礎的上層建筑物”(21)參見《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農民問題叢刊〉序》(1926年9月1日),《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頁。。由此,毛澤東充分認識到并明確反封建任務的關鍵對象之一是消滅農村地主階級。
近代資產階級由于深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內外雙重壓迫,其內部畸形分化為不同的階級成分。因此,對于資產階級不能一概而論,而應區分出其中所應聯合的成分和打擊對象。對此,1923年4月,陳獨秀在發表的《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一文中認為,在中國特殊社會性質下,資產階級內部分化為革命的、反革命的、中立的資產階級三部分。其中,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即官僚資產階級始終是“靠帝國主義的列強及國內的軍閥而生存,他們始終是阻撓革命運動”(22)《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1923年4月25日),《陳獨秀文集》第2卷,第352頁。,因此,“絕對不可和他們妥協。”(23)《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1923年4月25日),《陳獨秀文集》第2卷,第352頁。瞿秋白亦認為,官僚式資本主義是“軍閥制度的政治及帝國主義的經濟之副產品。——凡此等份子當然成為賣國派、專制派”(24)《政治運動與智識階級》(1923年1月27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2卷,第2頁。。1925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對不同資產階級的革命性進行了準確分析。他認為官僚、買辦階級是革命的敵人,小資產階級是革命團結對象,民族資產階級的右翼是革命敵人,左翼是革命團結的對象。(25)參見《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9頁。由此,他們就打擊和反抗官僚資本主義達成基本共識。
(三)革命道路:從“根本和平之解決”到“走俄國人的路”
“選擇什么樣的革命道路”是革命運動開展的核心關鍵。這一問題涉及到革命的性質、目標、手段、方式等內容的考量與選擇。在這一問題上,受小資產階級空想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相當一部分人普遍認為中國革命和社會改造應該走和平、溫和的改良道路,實行無血革命。1919年7月,毛澤東在觀察世界革命運動后認為:“實行‘呼聲革命’——面包的呼聲,自由的呼聲,平等的呼聲——‘無血革命’。不至張起大擾亂。”(26)《〈湘江評論〉創刊宣言》(1919年7月14日),《毛澤東早期文稿》,第271頁。此時的毛澤東雖對于馬克思主義革命觀有所了解,但相比之下,小資產階級溫和改良道路更得到他的青睞。陳獨秀在評價蘇俄革命時,亦片面認為他們“只限于局部的行動,不能聯絡成統一的政府”(27)《國外大事述評·俄羅斯之混沌狀態》,《每周評論》第3號(1919年1月5日),第1版。。并反對十月革命中“用平民壓制中等社會,殘殺貴族及反對者”(28)《國外大事述評·俄國包圍過激派之運動》,《每周評論》第4號(1919年1月12日),第1版。的過激行為。他認為,現階段中國“要想政象清寧,當首先排斥武力政治”(29)《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1918年7月15日),《陳獨秀文集》第1卷,第306頁。。可見,此時的他們雖然認識到中國社會問題需要根本改造和根本解決。但是,又幻想這種解決是通過走和平改良道路來實現。對此,有學者指出:“這種觀念正是‘改良的革命’的觀念。因為所求在于‘根本’,不是‘皮相’、‘枝節’,不是簡單的政府更替,因此未嘗不算‘革命’;因為‘解決’立足于平和。‘互助’、‘調和’、‘漸進’和‘忍耐’,因而又實實在在只是改良。”(30)楊奎松:《社會主義從改良到革命——十月革命對中國社會思想的影響》,《學術界》1987年第5期,第23頁。這一觀點較為準確地反映出他們對于革命與改良二者抉擇的矛盾心理。
然而隨著小資產階級理想主義幻想的破滅,進步知識分子對于溫和改良道路的狂熱性逐漸褪去,俄國十月革命道路的成功樣板自然而然成為他們考察中國革命出路的重要參照系。1918年7月到11月,李大釗深入觀察和分析俄國革命后,先后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等文章,稱贊十月革命是“和平之曙光”(31)《法俄革命之比較觀》(1918年7月1日),《李大釗全集》第2卷,第330頁。,“二十世紀中世界革命的先聲”。(32)《庶民的勝利》(1918年11月),《李大釗全集》第2卷,第359頁。并指出中國對于這一世界革命新潮流“只能迎,不可拒”(33)《庶民的勝利》(1918年11月),《李大釗全集》第2卷,第359頁。。這也是他成為一名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社會革命論者的重要標志。旅歐進步知識分子蔡和森赴法后,在對各種主義思潮和世界革命形勢有所了解的基礎上,革命觀念得到極大轉變。1920年8月,他在寫給毛澤東的書信中談道:“社會主義真為改造現世界對癥之方,中國也不能外此。”(34)《蔡林彬給毛澤東》(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文集》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6頁。他認為中國不但會有自己的“二月革命”,還會有“十月革命”的發生,并希望毛澤東積極參與到中國自己的“十月革命”中去。(35)參見《蔡林彬給毛澤東》(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文集》上,第57—58頁。對此,毛澤東在復信中明確表示“贊成馬克思式的革命”(36)《毛澤東給蕭旭東蔡林彬并在法諸會友》(1920年12月1日),《蔡和森文集》上,第60頁。,鮮明地表示出徹底的革命立場。這意味著,“走俄國人的路”成為他們的普遍共識。他們據此開始重新思索和設計“中國式的十月革命”的道路并為之不懈奮斗乃至獻身。
(四)革命手段:從“枝枝節節以圖改良”到“大刀闊斧地來主張共產革命”
革命手段是革命道路在具體走向過程中的實踐展現。革命和改良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歷史過程和歷史現象。選擇不同的革命道路,必然導致革命的手段、斗爭的路徑上的差異。
在近代社會,凡是具有某些進步因素和可利用成分的學說思潮幾乎都被進步知識分子拿來作為指導中國革命和社會改造的理論依據。這其中除卻馬克思列寧主義之外,還包括空想社會主義、新村主義、工讀互助主義等各種小資產階級社會思潮。早期共產主義者受到這些社會思潮的影響,由此提出一系列具有改良主義性質的救國主張。1916年,周恩來在受到教育救國學說影響后認為,中國落后挨打的主要原因在于“大道淪喪,人失其格,固無品斷之價值也”,“然追原禍始,罪安歸乎?是不得不歸過于教育也”。(37)《讀孟祿教育宗旨注重人格感言》(1916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南開大學編:《周恩來早期文集(1912年10月—1924年6月)》上,中央文獻出版社、南開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82頁。此時他主張教育救國以喚醒國格,提升國民素養。李達在青年時期一度萌生教育救國的理想,而在辛亥革命后,他又主張實業救國。(38)參見周可、汪信硯:《李達年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頁。1920年9月,毛澤東在受地方自治思潮以及改良主義的影響后認為,解決中國問題“不能由總處下手,只能由分處下手”(39)《打破沒有基礎的大中國建設許多的中國從湖南做起》(1920年9月5日),《毛澤東早期文稿》,第457頁。。在確立聯省自治這一革命主張后,毛澤東認為這是“達到根本改造的一種手段,是對付‘目前環境’最經濟最有效的一種手段”(40)《“驅張”和“自治”不是我們的根本主張》(1920年11月),《毛澤東早期文稿》,第514頁。。惲代英在最初理解社會主義時,便將個人主義的社會主義分為新村運動和階級革命兩種。1920年11月,他在《論社會主義》一文中指出:“我信人類的共存,社會的聯帶,本是無上真實的事。那便與其提倡爭存的道理,不如提倡互助的道理。”(41)《論社會主義》(1920年11月15日),《惲代英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66—267頁。他認為社會互助優于階級斗爭,中國革命的出路在于通過互助協作來組織和建立新村,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會。
20世紀20年代左右,在中國馬克思主義思想運動的蓬勃興起中,各種所謂的朦朧的“社會主義”美好想象最終偃旗息鼓。早期共產主義者開始認識到舊社會崩潰和新社會興起的根源在于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動。枝節改造、漸進改革等改良主義方法并不能根本解決中國積貧積弱的問題。1919年8月,李大釗在《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中運用唯物史觀科學分析了中國革命問題的實質并肯定階級斗爭的作用。他認為:“經濟組織一有變動,他們都跟著變動。換一句話說,就是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解決”,“階級競爭說,了不注意,絲毫不去用這個學理作工具,為工人聯合的實際運動,那經濟的革命,恐怕永遠不能實現。”(42)《再論問題與主義》(1919年8月17日),《李大釗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5頁。在第二次赴京深入接觸了解社會主義后,毛澤東轉而選擇和信奉馬克思主義革命學說。1921年1月,他在與新民學會長沙會友討論社會問題時講道:“社會政策,是補苴罅漏的政策,不成辦法……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采用。”(43)《在新民學會長沙會員大會上的發言》(1921年1月1日、2日),《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2頁。由此,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和暴力革命學說最終脫穎而出,成為早期共產主義者所信奉和遵循的終身革命信條。
(五)革命前途:從“誠心鞏固共和國體”到“建立勞動者的國家”
革命的前途是一切革命活動開展的終點,也是近代以來眾多標榜救國救世的主義思潮所共同著眼的價值歸宿。具體而言,辛亥革命后,進步知識分子普遍認為中國革命出路在于建立以主權在民和三權分立學說為原則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政體。對此,1917年6月,陳獨秀在發表的時局隨感中談及到:“愚固迷信共和,以為政治之極則。政治之有共和,學術之有科學,乃近代文明之二大鴻寶也。”(44)《時局雜感》(1917年6月1日),《陳獨秀文集》第1卷,第244頁。他認為資產階級民主共和政體具有不可替代的進步性,之所以出現種種社會問題,主要是由于封建舊思想文化的束縛和阻礙導致共和政體在中國落地時出現“舊瓶裝新酒”的制度失靈現象。從這層意義上而言,這一時期他們所提出的教育救國、實業救國、科學救國等主張也是在維護民主共和政體前提下的一些實質為枝節改造、補苴罅漏的改良手段。這也從側面說明,當時他們普遍認為民主共和政體在中國行得通。中國社會政治問題的出現是由于政體運行與中國經濟社會低水平發展之間的矛盾張力所致,與資產階級共和政體本身的優劣以及是否適合中國實際等問題無關。
1919年,五四運動的爆發“以活生生的事實向人們表明,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統治下,不僅國家的獨立富強不能實現,人民的生存權利也根本無法保障”(45)丁守和、殷敘彝:《從五四啟蒙運動到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社1979年版,第130頁。。國內共和政治的殘酷現實驅使他們必須拋棄對資產階級反動政府以及民主共和制度的幻想。對此,1920年11月,陳獨秀在發表的《國慶紀念底價值》一文中揭露道:“全國底教育、輿論、選舉,都操在少數的資本家手里,表面上是共和政治,實際上是金力政治,所以共和底自由幸福多數人是沒有分的。”(46)《國慶紀念底價值》(1920年11月11日),《陳獨秀文集》第2卷,第57頁。此時他已經意識到資產階級共和政體在中國走不通,并在封建軍閥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下已經畸形走樣。毛澤東更是一語中的地揭露道:“中國名為共和,實則專制,愈弄愈糟。”(47)澤東:《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湘江評論》創刊號(1919年7月14日),第3版。正是基于對反動舊政府和民主共和政體的厭棄,在這一思想徘徊時期,早期共產主義者主張并開展的新村運動、工讀互助運動、地方自治運動等政治改良革命可以視為他們在未完全理解和接受馬克思主義革命觀以及蘇俄社會主義革命道路前夕的一些具有革命自救性質的試驗和插曲。
進入20世紀20年代,隨著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以及國家觀的廣泛傳播和接受,他們在領導開展共產主義運動中對中國革命前途產生了新認識。1920年9月,陳獨秀在分析國內各派別的政治態度時指出:“我承認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即生產階級)的國家,創造那禁止對內對外一切掠奪的政治法律,為現代社會第一需要。”(48)《談政治》(1920年9月1日),《陳獨秀文集》第2卷,第39—40頁。李達也持相同的觀點:“無產階級的革命,在顛覆有產階級的權勢,建立勞動者的國家,實行無產階級專政。”(49)李達:《馬克思還原》(1920年12月26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502頁。此外,他們還對無產階級政黨和革命后的政權形式進行展望。例如,在革命領導力量方面,1922年4月,李達在發表的《評第四國際》一文中認為:“無產階級要實行革命,必有一個共產黨從中指導,才有勝利之可言。”(50)《評第四國際》(1922年4月22日),《李達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3頁。在國家政權形式方面,瞿秋白指出,無產階級斗爭目的在于“建立無產階級獨裁制,創造世界的蘇維埃共和國,以進于無產階級的共產社會”(51)《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1923年6月),《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2卷,第116頁。。此時的早期共產主義者已經普遍認識到中國革命的前途在于徹底打碎資產階級舊國家機器,通過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的階級斗爭和暴力革命來建設無產階級專政政權。
二、早期共產主義者革命觀轉向的歷史緣由
早期共產主義者由最初思想主張的混沌無序狀態到選擇和運用馬克思主義來觀察和分析中國革命問題的這段心路歷程中有諸多疑問和歷史細節值得深入思考。例如,是什么原因促使馬克思主義脫穎而出?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們放棄曾經一度信奉的小資產階級主義思潮而選擇將馬克思主義確立為開展革命的思想指南?等等。“人的思想發展,是一個復雜的動態過程,具體而微地分析何時實現思想轉變,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52)李良明等:《惲代英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1頁。如果過于注重從宏觀層面的標志性事件、時間節點以及所謂的分水嶺上來簡單判定和刻意對應早期共產主義者的思想轉向,得到的結論難以服眾。因此,對于早期共產主義者思想發展史的研究,應以宏觀分析為主,輔之以微觀考量,重點考察和綜合他們所處的時代背景、開展的革命實踐、自身成長和社會經歷、國內外社會政治事件等等因素,從而初步透視到他們進行自我思想清算以及思想轉向的歷史緣由。
(一)革命實踐失敗的反復驗證
任何一種理論只有在實踐中反復驗證才能證明其是否具有實踐性和科學性。近代特殊社會背景下,中國儼然成為各種主義思潮的試驗場,知識精英急欲抓住一切進步思想和理論用于指導革命實踐的開展來驗證其是否能夠為中國革命和社會改造服務。受無政府主義和地方自治思潮影響的青年毛澤東在領導湖南自治運動失敗后,對以往所信奉的主義思潮進行反思,他意識到“理論上說得通,事實上做不到”(53)《致蔡和森等》(1920年12月1日),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4頁。的主義從來不能救國救世。由此,他將革命目光轉向俄國革命道路。1920年12月,他同蔡和森講道:“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采,單要采這個恐怖的方法。”(54)《致蔡和森等》(1920年12月1日),《毛澤東書信選集》,第4頁。毛澤東從思想混沌的狀態中開始脫離出來,其一經選擇接受馬克思主義和俄國革命道路便再無更改。
在意識到自身曾經所堅定信奉并付諸于試驗的政治理想不現實后轉而選擇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并非只有毛澤東一人。在當時社會背景下,進步知識分子對于社會主義的認識尚處于朦朧狀態。在他們看來,互助、平等、協作是各種“社會主義”思潮的核心要義,中國革命和社會改造應該“以‘互助’、‘協作’、‘友誼’、‘人道’、‘改造人類精神’來作為改造社會組織的互補劑和雙行道”(55)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54頁。。據此,他們組織發起以“工讀互助團”為代表的一系列烏托邦式的社會改良試驗。受之影響,社會上各種無政府主義社團隨即競相涌現。例如,1919年底,惲代英就曾效仿北京工讀互助團在武漢組織發起了武昌工讀互助團(56)參見李良明等:《惲代英思想研究》,第138—139頁。;毛澤東在參觀北京工讀互助團之后,亦有在岳麓山建立新村的想法(57)參見《學生之工作》(1919年12月1日),《毛澤東早期文稿》,第406頁。。然而,以工讀互助團為代表的烏托邦式的社會改良方案脫離中國國情實際,最終失敗解散。對此,1920年12月,陳獨秀在發表的《關于社會主義的討論》一文中就講道:“在全社會底一種經濟組織、生產制度未推翻以前,一個人或一團體決沒有單獨改造底余地,試問福利耶以來的新村運動,像北京工讀互助團及惲君的《未來之夢》等類,是否真是癡人說夢?”(58)《關于社會主義的討論》(1920年12月1日),《陳獨秀文集》第2卷,第90頁。施存統也據此總結道:“一、要改造社會,須從根本上謀全體之改造,枝枝節節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會沒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試驗新生活;不論工讀互助團和新村。”(59)存統:《“工讀互助團”底實驗和教訓》(1920年5月1日),《星期評論》第48號·勞動紀念號,第7張。由此,他們開始檢視以往所信奉的各種所謂的“社會主義”思潮對于中國革命和社會改造是否具有可行性和有效性,并最終得出中國革命必須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和暴力革命理論來指導推翻舊政權舊制度才能夠勝利的基本共識。
(二)社會思潮論爭掃清馬克思主義傳播的思想障礙
列寧曾指出:“馬克思的學說直接為教育和組織現代社會的先進階級服務,指出這一階級的任務,并且證明現代制度由于經濟的發展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這一學說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經過戰斗,也就不足為奇了。”(60)《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1908年4月3日以前),《列寧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頁。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無產階級打碎舊世界、建設新世界的先進理論,其在近代帝國主義、封建軍閥以及資產階級反動勢力的勾結和壓迫下傳播,必然會遇到敵視和阻撓。“五四”時期,圍繞解決中國問題這一核心論點,李大釗、陳獨秀、蔡和森、李達等人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相繼展開了三次思想論戰。三次論戰的實質是圍繞中國要不要馬克思主義之爭、要不要實行徹底的民主革命之爭以及中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社會主義道路之爭。早期共產主義者在這場論戰之中,撰寫和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有力回應和駁斥了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進攻。例如,在關于“問題與主義”的思潮論戰過程中,李大釗于1919年8月到1920年1月之間先后撰寫和發表了《再論問題與主義》《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由經濟上解釋近代中國思想變動的原因》等文章,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從邏輯上有力駁斥了胡適的錯誤論調,明確指出中國革命應走階級斗爭和暴力革命道路。1920年11月到1921年4月,李達針對張東蓀、梁啟超等人主張階級調和,反對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謬論,相繼通過報刊發表了《張東蓀現原形》《社會革命底商榷》《討論社會主義并質梁任公》等文章,批判了張、梁歪曲中國社會階級關系和反對社會革命的論調,揭露了他們偽社會主義的面目。
此外,除卻在進步報刊上發表理論文章進行公開論戰駁斥之外,這些論戰也在進步團體中得到開展。1921年1月,新民學會長沙會友曾就“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方法進行過激烈討論,并就中國革命采取何種主義進行了意見交換。(61)1921年1月2日,新民學會會員就學會的目的、達到目的的方法等問題進行集會討論。最終確定學會的目的在于“改造中國與世界”。在就達到這一目的該采取何種方法時,學會會員之間進行了發言和討論,大體形成了“過激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三種主張,并最終進行投票表決。參見《新民學會會務報告(第2號)》(1921年1月2日),中國革命博物館、湖南省博物館編:《新民學會資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26頁。總之,在思潮論戰的交鋒中,早期共產主義者廓清了社會思潮迷霧和自身的思想混沌狀態。同時,也在無形之中為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掃清了思想障礙,為馬克思主義的最終脫穎而出提供了輿論先機。
(三)馬克思主義著作與觀點譯介的有力推動
對于早期共產主義者思想接受史的研究,離不開對于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史的考量和關照。二者統一于求解中國革命出路這一重大政治現實問題之中。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以前,馬克思主義的早期傳播大多以有選擇性地對相關觀點的籠統介紹和只言片語的內容節譯為主,譯介主體主要是在華傳教士、資產階級改良派、革命派和無政府主義者,譯介版本大都是直接轉譯日本學者的著述。而資產階級“由于他們的立場和政治需要,并不能準確地介紹它,甚至加以歪曲和批評,因此很難把這些一鱗半爪看作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62)彭明:《五四運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8頁。但是,對于當時各種小資產階級思潮占據主流地位的近代社會而言,這些零碎的新思想的傳播在一定意義上為早期共產主義者初步接觸和了解馬克思主義提供了原初語境。
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爆發,開啟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新局面。早期共產主義者作為馬克思主義傳播的生力軍,開始系統全面地譯介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和基本理論。在經典著作譯介方面,李達在留日期間,全力鉆研馬克思主義,翻譯出《唯物史觀解說》《社會問題總覽》《馬克思經濟學說》等書,并在國內出版。李漢俊在回國后專心從事馬克思主義的翻譯和寫作工作,他翻譯的《馬格斯資本論入門》《婦女之過去與將來》等也相繼出版發行。此外,還有惲代英翻譯的《階級爭斗》、瞿秋白翻譯的《唯物論》、蔡和森翻譯的《國家與革命》等譯作,均大體在1919年至1922年前后出版發行。(63)對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初期傳播的譯作書目,田子渝教授等人已在相關著作中整理列出。參見田子渝等:《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初期傳播史(1918—1922)》,學習出版社2012年版,第400—504頁。這些馬克思主義著述的譯介和出版對進步知識分子理解、選擇和接受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起到巨大推動作用。例如,毛澤東在回憶青年時期讀過的《階級斗爭》《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史》等中譯本后,就曾講到這些譯本對于自己思想轉向的重要意義:“我才知道人類自有史以來就有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我只取了它四個字:‘階級斗爭’,老老實實地來開始研究實際的階級斗爭。”(64)《關于農村調查》(1941年9月13日),《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頁。此外,早期共產主義者還著重于馬克思主義某些觀點的研究并撰寫相關文章進行闡釋。例如,《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馬克思唯物史觀要旨》等文章對唯物史觀進行了重點解讀和宣傳;《馬克思學說》《馬克思主義淺說》等文章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進行了介紹和詮釋,等等。總之,這些譯介工作無疑有力地深化了馬克思主義傳播的廣度和深度,為早期共產主義者探索和分析中國革命規律和革命形勢、重塑革命觀提供了理論武器和思想準備。
(四)巴黎和會外交失敗與蘇俄發表對華宣言鮮明對比的客觀促進
巴黎和會上外交失敗的殘酷現實打碎了國人對于帝國主義列強的幻想和憧憬。早期共產主義者更是對這一強盜行徑進行強烈譴責。1918年12月,陳獨秀在一戰結束后大呼協約國的勝利是“公理戰勝強權”,并稱贊美國總統威爾遜為“世界上第一個好人”(65)參見《〈每周評論〉發刊詞》(1918年12月22日),《陳獨秀文集》第1卷,第343頁。。而巴黎和會外交失敗后,他在1919年5月發表的隨感中寫道:“我看這兩個分贓會議,與世界永久和平人類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萬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來直接解決不可。”(66)《隨感錄》(1919年5月4日),《陳獨秀文集》第1卷,第461頁。瞿秋白在五四運動爆發后更是疾呼:“中國人要是不想生存在世界上,也就罷了。要是想生存在世界上,那就不能不趕快覺悟——真正的覺悟——去改造現在的社會,重建現在的國家。”(67)《歐洲大戰與國民自解》(1919年11月1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頁。可見,巴黎和會外交失敗打破了他們先前對于西方列強重建國際新秩序的幻想以及對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和政治文明的憧憬。他們在批判以西方列強為主宰的舊世界的同時,也表達出對于尋找救國救民的革命新思想新道路的渴求。
“對巴黎和會幻想開始破滅的時候,也正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開始傳播的時候。”(68)彭明:《五四運動史》,第262頁。恰在此時,1919年7月25日,蘇俄發表了“第一次對華宣言”(以下簡稱《宣言》)。《宣言》宣布單方面廢除沙俄時代對華的一切不平等秘密條約,表示把沙皇政府“獨自從中國人民那里掠奪的或與日本人、協約國共同掠奪的一切交還中國人民”(69)薛銜天等編:《中蘇國家關系資料匯編(1917—1924)》,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58頁。。《宣言》中文譯本全部刊出后,在飽受列強欺辱的中國人民中間產生空前的轟動。“擁有事實的理論一定是能夠征服人心的理論。”(70)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版,第377頁。在巴黎和會外交失敗與蘇俄對華宣言的鮮明對比中以及共產國際代表維金斯基來華宣傳十月革命和蘇俄對外政策的背景下,進步知識分子毅然地將目光轉向蘇俄十月革命道路和馬克思主義。1920年8月,毛澤東在《宣言》于國內發表幾個月后,就在《大公報》上講道:“俄國精神學術之不可不研究。”(71)《發起留俄勤工儉學》,(1920年8月22日),《新民學會資料》,第351頁。他號召青年赴俄留學,并決定成立俄羅斯研究會以“研究俄羅斯一切事情為宗旨”(72)《俄羅斯研究會成立》(1920年8月23日),《新民學會資料》,第354頁。。陳獨秀得知《宣言》發表后,于1920年的五一勞動節在《新青年》上將《宣言》全文刊出。在4個月后發表的《談政治》一文中,他明確主張通過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來推翻資產階級統治。此外,張國燾晚年回憶起這段歷史時也談及:“當時蘇俄政府對中國的宣言發生了甚大的影響,也是促成馬克思主義運動在中國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當時從南到北,不少人都在摸索俄國革命成功的途徑。”(73)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版,第83—84頁。這也印證了蘇俄對華宣言在進步知識分子的思想轉變中所產生的巨大轟動。
(五)個人主觀條件的綜合影響
影響個人思想轉變的因素包括客觀與主觀兩方面。其中,客觀因素影響著思想轉向的大體方向和總體條件,主觀因素則影響著思想轉向的具體方式、過程和特點等方面。考察早期共產主義者所具備的主觀條件優勢可以發現,他們大都具備留學經歷或出國訪問背景,視野開闊,且具有語言優勢,主觀上易于接受和理解馬克思主義以改造自身世界觀。
具體而言,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渠道大體包括日本渠道、歐洲渠道以及蘇俄渠道。其中,日本作為近代社會主義運動勃興的重要陣地,李大釗、陳獨秀、李漢俊、李達等人都曾有留日經歷且精通日語。在留日期間,他們與日本的社會主義者建立起師徒、好友等親密聯系,并通過多種途徑直接接觸到馬克思主義學說和馬克思主義著述。例如,李大釗就曾是日本社會主義學者安部磯雄的學生,并受過日本學者河上肇、幸德秋水的影響而深入接觸馬克思主義。據《李大釗傳》中記載,留日求學期間,“大釗同志并已開始研究關于介紹馬克思主義的著作。特別是讀了日本早期工人運動著名領袖幸德秋水的一些著作,曾經給了他較大的影響。”(74)《李大釗傳》編寫組編:《李大釗傳》,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頁。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中,他就特意說明引用的馬克思主義著作的譯文部分來自河上肇博士。(75)李大釗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中,對于《哲學的貧困》《共產者宣言》《經濟學批評》的序文部分的引用特意注明:“以上的譯語,從河上肇博士”。參見《我的馬克思主義觀》(1919年9月、11月),《李大釗全集》第3卷,第14頁。李漢俊同樣作為留日學生,是“日本帝國大學畢業,他是河上肇的得意門生,他對于書本上的馬克思主義有些研究,對蘇俄十月革命以后的材料也看得較多”(76)包惠僧:《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前后的回憶》(1953年8、9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選編:《“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7頁。。此外,蔡和森、周恩來、趙世炎、李維漢等人在旅歐期間,利用語言優勢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成立中共旅歐支部,并逐步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蔡和森在留法期間,“猛看猛譯”馬克思主義原著促使其思想發生激烈轉變。據蕭三晚年回憶:“蔡和森很用功,看法文報紙,一個一個字查字典,不久他就能看《共產黨宣言》法文本了,他是我們中接受馬克思主義最早的一個。”(77)蕭三:《回憶赴法勤工儉學和旅歐支部》(1957年4月),《“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二)》,第513—514頁。周恩來在反復對比各種思潮之后,認為“社會主義已成為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并“最終確定了共產主義信仰”。(78)參見:《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52頁。瞿秋白在1920年10月以特派記者的身份趕赴蘇俄進行直接采訪和報道。他“來俄不到一年,經過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地的考察,已經逐步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革命思想,接受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并且用來指導考察、寫作以及剖析和改造自己的思想”(79)陳鐵健:《瞿秋白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3頁。。因此,這也就不難理解他們能夠率先接觸到新思想新思潮,并在譯介和撰寫有關馬克思主義理論文章的同時,深入理解和領悟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
三、早期共產主義者革命觀轉向的歷史影響
考察革命觀轉向的內容和歷史緣由,充分彰顯了馬克思主義所具有的實踐性、革命性和科學性,深刻詮釋了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救中國這一科學真理。中國早期共產主義者在反復比較中,在艱辛探索中,在實踐檢驗中選擇和接受馬克思主義并運用其來改造自身革命觀的過程,具有不可忽視的歷史影響與歷史價值。
(一)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形成提供了基本的認知先導
開展革命行動以打碎舊世界、建立新世界,是探求中國革命出路、整體改造中國社會的必然選擇。對此,“中國先進分子歷經千辛萬苦,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嘗試過種種改造中國社會的方案。這些探索和斗爭,雖然每一次都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推動了中國歷史的進步,但卻都未能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和中國人民的悲慘命運。”(80)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 第1卷(1921—1949)》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8頁。歷史和實踐證明,在中國這種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雙重壓迫且面臨極其深重的生存危機的歷史境遇之下,改良主義與和平改造救不了中國,資產階級政治力量領導和推動的舊民主主義革命亦無法真正實現國家統一與主權獨立。唯有在紛亂復雜的社會思潮中重新比較、審定和選擇能夠解決中國現實問題的救世方案,為新民主主義革命行動提供科學理論準備和思想武器,從而接續完成舊民主主義革命未竟的革命任務以實現新舊革命的歷史嬗遞,才是順應近現代中國歷史主題并找到一條嶄新革命道路的必然選擇。對此,“馬克思主義以其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與極富斗爭性的階級革命理論最終成為激進學者與青年的最終選擇。”(81)陳宇翔、薛光遠:《中國早期共產主義者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過程述論》,《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4年第5期,第100頁。早期共產主義者最終選擇并信奉馬克思主義,將其作為全面清算和改造自身世界觀的有力思想武器,并完成了由“舊民主主義者”向“新民主主義者”的身份與認知層面的馬克思主義化。
在這一思想轉向過程中,針對革命主體、革命對象、革命道路、革命手段以及革命前途等關鍵問題,早期共產主義者對各自以往所秉持的舊革命觀進行徹底地理論反思和思想清算,提出一系列新論斷新主張。其中,對于中國革命的主體力量,他們已經認識到工人階級和廣大農民所結成的工農聯盟是進行無產階級革命所必須依靠的最基本最穩固的革命力量;對于革命對象,他們歷經由反抗帝國主義到反抗帝國主義以及與其相勾結的本國封建軍閥勢力、由反帝反軍閥到反抗維護封建軍閥統治背后的封建地主階級勢力、由將資產階級作為革命聯合對象到劃分出反抗官僚資本主義的認知演進;對于革命道路走向,他們從主張并信奉走資產階級政治改良道路到就“走俄國人的路”(82)《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71頁。達成一致共識;對于革命手段,他們從主張枝節改造、地方自治、社會互助等政治改良主義并歷經改造試驗失敗后,轉向徹底選擇和接受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斗爭和暴力革命的理論學說;對于中國革命前途,他們從推崇和擁護資產階級民主共和政體轉向通過革命徹底打碎資產階級舊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
由此可見,早期共產主義者在初步選擇和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理論后,他們對于中國革命問題的思考也在總體上脫離出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桎梏,超越了舊民主主義革命理論中僅將反帝反封建作為革命對象、將無產階級作為革命追隨者尚不能獨立領導革命、將資產階級不加分析地統一看待為革命力量、將建立民主共和政體作為中國革命的必然前途以及漠視農民階級革命力量的局限性,從而實現中國革命理論的創新性建構,并初步呈現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鮮明特點,由此跨入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思想領域。可以說,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政治綱領以及統一戰線策略都能夠在早期共產主義革命觀中找到思想源頭。這無疑為中國共產黨開創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和思想先導。隨著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蓬勃開展,早期共產主義者的革命觀念和主張也得到不斷深化和拓展。
(二)為探索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提供了馬克思主義方法論指導
恩格斯曾指出:“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83)《恩格斯致韋爾納·桑巴特》(1895年3月11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4頁。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理論作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領導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總結無產階級革命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所創造的科學理論體系,對于指導落后國家和落后民族獨立自主開展革命運動以走向新的社會發展階段具有重要啟示意義。但是,囿于歷史和時代的局限性、各個民族國家具體革命實際的適用性以及歷史文化傳統的差異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雖然對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形式、策略、手段、目標等內容進行了一般性規定和總體性指導,但他們尚未對落后國家尤其是中國革命問題的特殊性作出具體分析。因此,選定馬克思主義作為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不能僅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無產階級革命理論中去搬用、套用現成的結論和觀點,關鍵在于領會和運用馬克思主義來破解馬克思主義的普遍性與中國革命問題的特殊性之間的關系問題,從而為中國革命開展提供科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指導。
對于上述認知,1926年5月,李大釗在《馬克思的中國民族革命觀》一文中開宗明義地指出:“我們現在要想根據馬克思主義就中國現在的民族革命運動尋求一個顯明的分析,最好是一讀馬克思當時關于中國革命的論文。從此我們不僅可以得到他的公式,我們更可以看出他怎樣的應用他的研究的方法,以解剖那赤裸裸的歷史事實,整理那粗生的材料,最后我們便可以得到一個明確的結果。”(84)《馬克思的中國民族革命觀》(1926年5月),《李大釗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5頁。1921年1月,毛澤東在答復蔡和森關于中國共產黨哲學基礎問題的看法時更是深刻指出:“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這是事實,不像唯理觀之不能證實而容易被人搖動。”(85)《致蔡和森》(1921年1月21日),《毛澤東書信選集》,第11頁。這表明,在思想轉向過程中,早期共產主義者不僅對自身所存在的非馬克思主義因素進行清算與反思,同時,他們已經開始初步領悟和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科學分析中國革命問題和社會現實問題。
具體而言,早期共產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和階級分析方法尤為青睞。他們運用階級分析方法來分析和批判帝國主義侵略本質以及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對革命所持有的不同態度,從而劃清革命“敵我”。對此,李大釗就曾明確指出:“階級競爭說恰如一條金線,把這三大原理從根本上聯絡起來。”(86)《我的馬克思主義觀》(1919年9月、11月),《李大釗全集》第3卷,第5頁。同時,他們也已初步運用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關系的理論來分析支撐封建軍閥勢力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經濟與社會基礎,從而創造性地提出反抗封建地主階級勢力的革命任務。除此之外,早期共產主義者還運用群眾史觀的理論觀點進一步分析和明晰中國革命的主體力量。他們摒棄了以往所秉持的“圣賢救世”的英雄史觀以及揚棄“民眾大聯合”的革命民主主義觀念,逐步意識到中國革命“除了中國勞動者聯合起來組織革命團體,改變生產制度,是無法挽救的”(87)《關于社會主義的討論》(1920年12月1日),《陳獨秀文集》第2卷,第88頁。,必須領導和組織工農聯盟以進行暴力革命才能夠取得勝利。這些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為其后新民主主義革命推進過程中所提出和創造的諸如黨的群眾路線、統一戰線政策、土地革命政策以及“人民戰爭”思想等革命戰略與策略提供了根本方法論自覺,并在革命實踐中得到不斷地深化、豐富和完善,從而最終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哲學。
(三)有力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
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外來異域學說傳入中國,觀點主張的介紹、經典著作的譯介以及出版發行、思潮論爭的交鋒以及與之相關的媒介準備是其得以廣泛傳播并開啟馬克思主義“化”中國歷史進程的基本前提。對此,有學者指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雖然具有歷史的必然性,但它不單是一個客觀的自然歷史過程,更是一個自覺的社會歷史過程,是歷史必然性同主體能動性的辯證統一。”(88)金民卿:《青年毛澤東的思想轉變之路:毛澤東是怎樣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353頁。早期共產主義者在選擇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轉向過程中所進行的譯介工作、出版發行工作以及相關觀點主張的研究與闡釋工作,為開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先導和實踐準備。
具體而言,在著作譯介工作方面,早期共產主義者通過翻譯和介紹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理論學說以及撰寫相關文章來闡釋和發表,不斷擴大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廣度和深度。對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早期譯介工作,僅在1921年,早期共產主義者創辦的中國第一個出版發行機構——人民出版社,已經出版和準備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達15種,已經出版和將要出版的列寧系列書目達17種。(89)參見彭明主編:《從空想到科學——中國社會主義思想發展的歷史考察》,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335、343頁。在出版發行方面,早期共產主義者通過創辦進步報刊來作為馬克思主義傳播的輿論宣傳陣地。“據不完全統計,五四運動后的半年內,一定程度上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進步報刊達到200多種。”(90)李軍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及其話語體系的初步建構》,學習出版社2013年版,第47頁。《新青年》在五四運動后開辟“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欄目,開始轉向對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每周評論》《星期評論》《勞動界》《湘江評論》《共產黨》等報刊在此期間陸續在各地創辦。這些刊物作為刊載介紹和解讀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文章以及新舊思潮論戰的宣傳陣地,有力拓寬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受眾面。在理論傳播方面,早期共產主義者充分利用自身職業優勢和工作便利條件以及成立相關研究社團和機構來暢通和構建馬克思主義傳播的媒介渠道。任何一種外來理論的本土傳播,必然需要一定的媒介工具作為橋梁和中介。對此,考察早期共產主義者的身份職業可以發現,他們是集學者、媒體人、社團負責人、革命者等職業于一身的知識精英群體。例如,李大釗、陳獨秀是《每周評論》《新青年》的主要創辦人和撰稿人;李達是人民出版社的主要負責人和《共產黨》月刊的創辦人;惲代英是《中國青年》的第一任主編和主要撰稿人,等等。又如,1918年到1921年期間,毛澤東在湖南相繼發起的新民學會、文化書社、俄羅斯研究會、湖南自修大學等(91)對于毛澤東發起成立的文化書社和俄羅斯研究會,有學者在研究后認為:“不論從文化書社的創辦初衷,還是從文化書社日后的發展來看,它都不是一個一般性的文化書店,而是一個思想導向明確、以傳播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為核心任務的陣地。”“俄羅斯研究會的成立,是毛澤東宣傳介紹俄國十月革命,擴大馬克思列寧主義影響力的實踐活動,也是他把個人信仰上升為現實實踐的重要嘗試。”參見吳璇:《青年毛澤東世界觀轉變歷程再考察——兼評1920年“夏天說”“冬天說”和“過程說”》,《毛澤東研究》2022年第5期,第74—75頁。對于在湖南乃至全國范圍內傳播馬克思主義、樹立馬克思主義旗幟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對此,有學者總結道:“這批啟蒙者、革命者通過新聞、出版等傳媒,打開了科學社會主義的閘門,使馬克思主義的洪流浩浩蕩蕩不可遏制地洶涌九州大地。”(92)田子渝等:《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初期傳播史(1918—1922)》,第35頁。由此推動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共產黨救國救民、立黨立國的有力思想武器。
余論
個體的思想轉變是一個極其復雜的過程。以歷史的眼光來考察和追溯這段思想轉向的心路歷程不能脫離早期共產主義者所處的社會歷史情境。列寧曾指出:“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93)《論民族自決權》(1914年2—5月),《列寧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32頁。在近代中國所面臨的黑暗境遇以及仁人志士艱難求索的時代背景之下,“當時人對現狀的失望與反感以及對未來的熱望使他們非常關心如何由沉重的現實通向理想的未來的途徑。”(94)張灝著、任鋒編校:《轉型時代與幽暗意識——張灝自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61頁。因此,任何外來思潮學說都具有不可忽視的進步意義,都可以視為進步知識分子基于對新社會的熱望以及革命失敗的殘酷現實而產生的對于新思想武器的渴求。然而,“思想的先進性和思想的影響并不是相等的。”(95)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第422頁。任何一種外來思想的落地生根,必須考量這一思想對本國實際的適用性、與本土文化的契合性、思想傳播的廣度與深度以及接受程度,并需要在實踐中去加以檢驗和發展。近代中國的社會歷史情境內在要求革命觀念和思想必須具有切實的實踐性和有效性,必須適合于國情實際并指引救國救世道路的開辟。早期共產主義者選擇并接受馬克思主義,推動馬克思主義在眾多主義思潮之中脫穎而出,實現自身世界觀、革命觀的新陳代謝,這是比較和選擇的結果,也是歷史和時代的造就。但是,在回溯這段心路歷程時,我們不能單純地抱有一種“事后認知”的片面心理去過分誤讀甚至苛責前人所曾經信奉和付諸實踐過的一些非馬克思主義思潮,甚至因此看輕他們在革命洪流中以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的努力和建樹。我們不能割裂他們思想轉向前后的邏輯因果關系,沒有轉向前的質疑、驗證和批判,就沒有轉向后對于馬克思主義的選擇、接受和運用。歷史浪潮中沒有“如果”,真實的歷史演進沒有假設。作為時代今人回望這段歷史,我們雖然不能以一種“存在即合理”的唯心主義心態對他們曾經信奉過的這些主義思潮進行維護甚至辯護。但是,持有客觀理性的尊重之心來審視歷史洪流中這段苦心孤詣的心路歷程應該是無可非議的。而這也是對待黨的歷史所應有的正確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