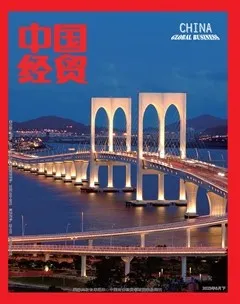共同富裕視域下的農村集體經濟治理體系研究
鄧蓉 梁景智 羅明東

摘 要: 發展集體經濟既是鄉村振興背景下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徑,也是鄉村治理的經濟基礎。盡管共同富裕目標的“終點線”一致,但城市與農村的“起跑線”差距甚大。村集體經濟作為實現其組織成員共同富裕的一種經濟形式,以集體經濟為主體,以公共產權為基礎,構成了要素流動和利益分配模式的農村經濟治理秩序。本文基于524個村(社區)調查視角,探討包括農村集體經濟治理領導機制、載體機制、運行機制、制衡機制、經營機制等在內的法人治理結構體系,試圖充分挖掘與發揮集體經濟組織在組織動員和示范帶動方面的巨大潛力,以期對激發鄉村振興共同富裕工作有所裨益。
關鍵詞:共同富裕? 農村集體經濟? 治理機制體制
一、共同富裕視角下農村集體經濟治理邏輯及研究綜述
共同富裕理論起源于馬克思主義,由中國共產黨持續進行豐富與創新。馬克思、恩格斯分別從經濟基礎和制度保障兩個層次對財富分配的公正和共享的內涵及其實現途徑進行了闡述,成為中國共產黨引領全體人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理論來源。在伴隨中國共產黨走過的一百多年歷程中,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政權建立和人民解放為共同富裕理論發展奠定了制度基礎和政治前提[1];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生產力發展和生產關系變革為共同富裕理論提供了思想基礎和理論框架[2];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先富共富論”、“以人為本發展”等為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論支撐和實踐依據;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期,實現共同富裕既是社會主義的根本要求,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一個鮮明特征,并顯現出強烈的人民性內涵和多維度實現路徑。
農村集體經濟起源于我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3],并衍生出由農民個體組成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土地改革后,農村集體經濟載體呈現出“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遞進式發展,農業逐步進入社會主義發展軌道。但絕對平均分配思路減弱了成員生產積極性,農業現代化道路受阻[4]。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確立后,個體經營活力得以釋放,但雙層經營體制以“分”為主,農村集體經濟日漸“空心化”[5]。新時代“三權分置”確立后,“統分結合”聚焦于實現高水平統一,實現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壯大[6]。
因此,脫貧攻堅—全面小康—共同富裕”貫穿于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的艱苦奮斗歷程,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連續性和階段性的統一。馬克思和恩格斯(1848)曾指出,“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而未來社會“生產將以所有人的富裕為目的”,可見共同富裕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目標[7],而發展集體經濟成為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證[8]。
二、524個村(社區)視角下的集體經濟治理困惑
根據對524個村(社區)樣本進行透析后發現,當前農村集體資產已成規模、負債率較低,但集體收入整體滯后、支出結構單一等混合矛盾特征,由此形成治理困頓。
(一)統計嵌入寬口性導致盲點隱患,形成研判風險。
樣本顯示目前集體經濟組織建設覆蓋率高,但載體形式混亂。經濟(股份)合作社作為集體經濟組織的法定載體,在相關部門“登記賦碼”實際操作中,仍有相當比例的其他組織形式代替經濟組織。各地報送口徑不一致,造成寬口誤差。統計數據是各級政府了解集體經濟發展、制定發展戰略的基礎,統計口徑不一致可能為后續集體經濟發展帶來政策研判上的盲點,易導致政策失靈。剖析這一現象的原因,一是對集體經濟組織載體形式認知模糊。數據顯示有53.2%的占比將村委會等同于集體經濟組織,28.4%認為“專業合作社就等于集體經濟組織”,甚至將業主公司、家庭農場、種養殖大戶等產值都算在集體經濟組織收益中。二是對“全體經濟組織成員”概念認知模糊,一部分股份(經濟)合作社成立于2017年前,按照一般農民專業合作社要求,在無法保證全體經濟組織成員參與的前提下,卻行使了集體經濟組織權益;另一部分股份(經濟)合作社為了對外擴展經營成立了公司,卻未以全民股份(經濟)合作社特別法人發起,而是以村兩委干部自然人的形式發起,又未解決代持股問題,形成個人公司代替經濟組織的局面。以上情況都可能會成為未來村級治理成本高、風險大的隱患,給下一步發展集體經濟帶來政策研判誤區。
(二)法人架構缺失導致財務隱患,形成審計風險。
經濟組織的法人架構體系,兼容決策、管理、財務等機構體制以及動議、分配、監督等制衡機制,但在524個村(社區)成立的各類集體經濟組織中,卻有88.4%未搭建法人架構,由此可能導致兩類隱患:一是難以明確集體資產管理權的歸屬。每逢村組換屆則極易導致集體資產流失;二是集體經濟組織內部建設存在風險。數據分析發現,在調查樣本的各類集體經濟組織中,單獨建立基本賬戶的平均建賬率占83.75%,沒有按集體經濟組織會計核算體系記賬的卻高達87.6%,雖然獨立建賬,但核算體系仍然是預算會計。預算會計與集體經濟組織會計核算方式的差異,在同一項目的賬戶認定中會形成不同的結論,例如預算會計沒有激勵經費項目,但集體經濟組織會計可按年收入2%—5%提取獎勵基金。因此,無論是“一肩挑”帶來的制衡機制缺陷還是兩大會計核算項目差異,都易引發巡察審計風險,給基層實際操作帶來不確定性。
(三)意愿彈性不張導致信任危機,形成滯后風險。
在集體所有的產權架構下,以資源盤活經濟為主要模式的集體經濟發展,是一個確定的話題。但在調查數據統計梳理和走訪過程中對于是否要發展集體經濟,呈現出各占50%的“勢均力敵”膠著狀態,具體表現為四個層面:一是職能部門片面理解“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存分去統”關系,認定多年來農民自己發展小農經濟取得成效,應該給以鼓勵,因而不愿支持集體經濟發展;二是鄉鎮(街道)對發展集體經濟有畏懼負面情緒,前些年受各種因素疊加影響,出現村辦企業因為經營不善導致破產倒閉,背上債務,農民上訪等情況,使部分基層領導干部“怕”字當頭,求太平、穩著落的心理較重,因而不愿引導;三是村(社區)干部特別是黨組織書記覺得,即使有了一定的集體財產與收益,怕說不清楚,怕群眾不相信,盡量少惹麻煩,因而不愿帶頭;四是農民集體意識比較淡薄,覺得集體經濟是留給干部的,對群眾沒有任何益處,不如守住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來得實在,因而不愿參與。多層面認知辨識的模糊和缺乏發展集體經濟的決心和信心,因而無法形成合力,致使集體經濟發展步履緩慢。
(四)人力資源匱乏導致市場隱患,形成經營風險。
經濟組織要走向外部市場循環,其基本條件既需要專業經營管理人力支撐,又有遵循市場相應邏輯與游戲規則。調查顯示,高達74.6%的村(社區)有發展集體經濟專項財政資金,其中32.7%的集體收入最大來源是財政撥款,產業收入僅占25%。524個調查樣本顯示可通過生產經營創造收益的平均有效經營率僅占32.64%,即一些集體經濟組織包括股份(經濟)合作社、公司可能都是空殼空轉的。
綜上所述,當前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取得了長足進步,集體經濟發展帶來的治理成效已顯現,但從面上看,集體經濟在組織架構、實現形式、制衡機制、分配途徑以及財務管理等方面也還存在著一些問題,給鄉村治理帶來諸多不確定性。需要從農村集體經濟治理體系視角來研究探討農村集體所有制有效實現形式,創新農村集體經濟運行機制,保護農民集體資產權益等理論與實踐問題。
三、探討共同富裕視域下構建農村集體經濟治理體系的思路
2016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指出:探索農村集體所有制有效實現形式,盤活農村集體資產,構建集體經濟治理體系,對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增強集體經濟發展活力,引領農民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具有深遠歷史意義。而構建農村集體經濟治理體系就是構建黨領導下的管理農村集體經濟的制度體系,確保“治理有效”將成為新時期農村集體經濟制度體系健全和完善的重要目標[14]。
(一)探索“村黨組織書記承擔法人代表”的集體經濟治理領導機制
創新黨對農村經濟組織的領導方式,提高執政水平,探索建立“村黨組織書記承擔法人代表”的集體經濟發展的領導機制是構建農村集體經濟治理體系的核心。
一是落實黨組織在集體經濟組織的法定地位。按照2019年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農村組織工作條例》要求,村黨組織書記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中的領導職務應按法定程序進行。通過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代表的合法身份,把村黨組織內嵌到經濟組織治理結構之中,把黨的領導融入經濟組織治理各環節。
二是創新黨組織在集體經濟組織中的領導方式。基層黨組織要因地制宜,促進集體經濟發展,領導和支持集體經濟組織管理集體資產,協調利益關系,組織生產服務和集體資源合理開發,確保集體資產保值增值,確保農民受益[15]。因此要把黨的基層領導與經濟發展規律、現代市場規律結合起來,創新農村治理體系中的領導形式與執政方式。
三是選好黨組織在集體經濟組織中領導班子。黨組織的領導與意圖是通過“人”來實現的,配強村“兩委”干部,特別是黨組織書記,起到“領頭羊”作用。因此,探索“村黨組織書記承擔法人代表”集體經濟發展的領導機制,關鍵是選好人,一方面要把那些既有“公心”與奉獻精神、又有能力帶領群眾致富的人培養成為村黨組織書記;另一方面還要注重村后備干部的發掘培育,注重從農村致富帶頭人、退伍軍人、大學生返鄉創業、外出務工經商人員中選拔村干部,使村級黨組織干部隊伍有活水源頭。
(二)探索以“農村經濟(股份)合作社為主干”的集體經濟治理載體多元機制
農村“三級”經濟組織載體的混亂是集體經濟治理的頑疾,要選擇好集體經濟組織載體,保障財政資金安全,適應市場需求,壯大集體經濟。因此,創新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實現形式,探索以“農村經濟(股份)合作社為主干”的集體經濟治理載體多元機制是構建農村集體經濟治理體系的基礎。
一是以經濟(股份)合作社為主要載體。按照《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集體資產管理的主體,是特殊的經濟組織,可以稱為經濟合作社,也可以稱為股份經濟合作社。因此經濟(股份)合作社是目前集體經濟組織的法定載體和主要實現形式,典型特點為經營的是村(組)公共資源,主要是土地,并由全體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參與。
二是以有限責任公司為重要載體。由于合作社不是一個完全的市場主體,從實踐來看,以公司代替集體經濟組織,可以解決股份(經濟)合作社作為集體經濟組織法定形式的兩個缺陷,其一不能出具正式發票特別是增值稅專業發票,其二很難向金融機構融資。因此,公司作為集體經濟組織的一種載體出現,既有利于集體經濟受《公司法》的調整與保護,也方便集體經濟引入法人治理結構內部的制衡與管理手段,從而更好地與市場打交道[16]。
三是以混合合作社或公司為補充載體。為了創新集體經濟組織多種實現形式,聚合更多資源、資金、人脈,不斷壯大集體經濟,可以探索包括集體經濟組織與農民個人、其他專業合作社以及各類公司相互入股、參股、控股等方式成立的合伙專業合作社、合伙公司來共同經營,形成集體經濟組織“大樹”的“主葉”。
(三)探索“政府引導、財政幫扶、農民參與、獨立經營”的農村集體經濟治理運行機制
農村集體經濟的不完全市場主體性以及獨特的組織性,在較長時效內都會有政府、企業、業主等主體參與發展的空間。因此,正確處理政府、集體、業主、農民的關系,劃分發展集體經濟的參與者、利益相關者的權責范圍,探索“政府引導、財政幫扶、農民參與、獨立經營”的農村集體經濟治理運行機制是構建農村集體經濟治理體系的關鍵。
一是將政府“主導”向“引導”角色轉變。目前有大量財政專項資金扶持集體經濟,但集體經濟組織自身法人架構體系不完善,產業經營人才缺口,市場適應能力弱性,各地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的實踐中,仍然是以政府“主導”為主。一方面是保障財政資金的安全,另一方面是便于推動產業發展。但這種角色定位只適用于集體經濟產業初級發展階段,政府在完成相關組織工作后,應及時“抽身”,轉向“幕后”。
二是將財政短期集中幫扶向長效幫扶機制轉變。發展集體經濟是長期、常態的過程,要破除地方政府“短期政治任務”、“短期成果成效”的政績觀,將目前各級財政大量、密集、無差別投入扶持集體經濟資金的方式轉為均衡、合理分布、差異化的科學長效幫扶機制。其一要建立長效幫扶的篩選機制,不能把一個地方所有的村(社區)集體經濟拉平,要根據區位、地理自然條件、發展基礎、干部能力以及農村人才回流狀況等綜合指標篩選重點村組,進行重點幫扶,形成示范輻射效應;其二要建立長效幫扶均衡機制。政府要制定財政扶持集體經濟發展所需的基礎設施建設、產業發展等中長期資金投入規劃。
三是將國有平臺公司扶持經營向集體經濟組織獨立經營轉變。目前,已形成規模和品牌的集體產業,其背后的經營主導仍然是地方各類國有平臺公司,但農村資源、資產、資本的權益屬性,是需要確保其集體經濟組織自身的核心地位。
參考文獻:
[1]侯曉東,朱巧玲,萬春芳.百年共同富裕:演進歷程、理論創新與路徑選擇[J].經濟問題,2022(02):1-8.DOI:10.16011/j.cnki.jjwt.2022.02.001.
[2]方寧.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共同富裕思想的發展與實踐研究[J].南京審計大學學報,2022,19(01):8-17.
[3]陸雷,趙黎.從特殊到一般:中國農村集體經濟現代化的省思與前瞻[J].中國農村經濟,2021(12):2-21.
[4]劉冠軍,惠建國.中國農村集體經濟的實現形式與創新發展[J].甘肅社會科學,2021(03):189-196.DOI:10.15891/j.cnki.cn62-1093/c.2021.03.026.
[5]謝宗藩,肖媚,王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嬗變:嵌入性視角下發展動力機制變遷[J].農業經濟問題,2021(12):92-103.
[6]李志平,田小坤.中國特色農村現代化未來演變趨勢與對策思考[J].統計與決策,2022,38(11):5-10.DOI:10.13546/j.cnki.tjyjc.2022.11.001.
[7]張賢明.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推進之道[J].理論導報,2021(09):59-60.
[8]習近平.因地制宜發揮優勢? 走自己發展的路子[J].領導科學,1992(03):3-4.
[9]史耀疆,任保平,王生龍,J.J.Kennedy.選舉提名方式與土地管理體制:村民對村領導行為及其績效的評價[J].經濟研究,2004(09):110-117.
[10].Ran Tao, Ping Qin.How Has Rural Tax Reform Affected Farmers and Local Governance in China?[J].China & World Economy,2007,(03):19-32.
[11]郭曉鳴.全面完善集體經濟組織管理制度,發揮鄉村能人帶動作用[J].農村工作通訊,2019(16):47.
[12]王偉. 農村社區數字治理問題研究[D].貴州師范大學,2016.
[13]鄧蓉.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進程中的集體經濟組織主體地位重塑[J].農村經濟,2017(03):43-48.
[14]崔超.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村集體經濟的百年探索與啟示[J].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學報,2021,14(05):64-73.DOI:10.16223/j.cnki.cn61-1456/c.2021.05.002.
[15]鄧蓉.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后的村級治理結構建設初探——以都江堰市農村產權制度改革試點為例[J].成都行政學院學報,2009(01):62-65.
[16]鄧蓉.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進程中的集體經濟組織主體地位重塑[J].農村經濟,2017(03):43-48.
(作者單位:鄧蓉 中共都江堰市委黨校、梁景智 中共都江堰市委黨校、羅明東 中共都江堰市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