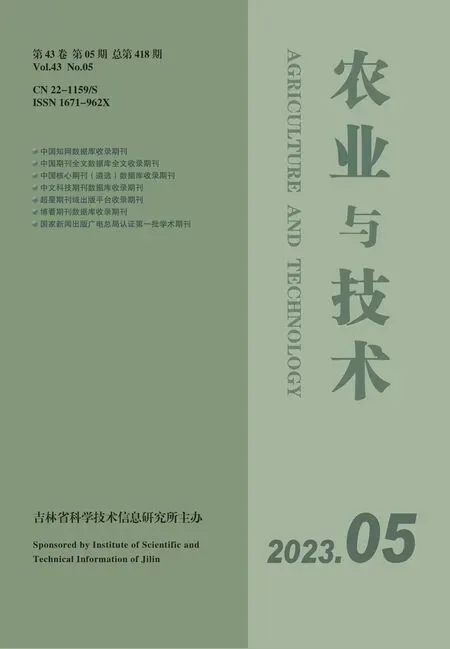鄉村振興戰略下耕地流轉資源配置問題研究
段明亮 朱敏
(上海應用技術大學人文學院,上海 201418)
改革開放以來,農業農村經濟發展取得一定成效,相較于快速發展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農業農村發展仍比較緩慢,城市與農村收入差距懸殊,導致城鄉二元經濟體系矛盾日益明顯。解決農村經濟體制問題,需高度重視“三農”問題,“三農”問題與農村土地存在密切聯系。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和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城市化發展過程中,需嚴格管控耕地和糧食種植面積減少問題,耕地與糧食種植面積的降低,必將影響我國糧食安全問題[1]。因此,解決農村耕地問題對我國農業農村、鄉村振興發展至關重要。《新土地管理法》對農村土地問題作出了明文規定:“堅持農用地農用”,遏制耕地“非農化”,防止耕地“非糧化”。遠郊作為上海市副食品工業生產基地,以種植農產品為主,在國家鄉村振興和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背景下,遠郊將作為上海市政府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主戰場,上海市政府積極響應國家號召,積極推行了農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積極推動了農民耕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管理,以促進農業農村的適度規模經營,促進了農業規模化、產業化,積極整合了上海市遠郊土地的落荒、閑置。因此,如何高效整合耕地流轉資源配置,對推進遠郊農業現代化發展,實現城市和遠郊統籌融合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1 上海市耕地流轉現狀調查
上海市作為國際化大都市,城鄉一體化的發展導致上海市土地資源矛盾日益突出,2013—2016年,上海市耕地面積從188000hm2發展到190753hm2,呈遞增趨勢增長;2017年在上海市總耕地面積中,永久基本農田數量達169333hm2,總糧食種植面積118667hm2。奉賢區作為上海市最大農業區,可耕地面積21933hm2。其中,農戶家庭承包耕地面積1447hm2,奉賢區已轉出的農用地面積16387hm2,農戶委托村集體經濟組織轉出面積13093hm2。
2008年上海市政府提出組建“農村土地流轉服務中心”;至2016年,已建成74家鄉鎮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管理服務中心;“農村土地流轉服務中心”建設的核心點:農戶將自己手中的承包地委托于村集體進行流轉,村鎮委和土地流轉服務中心應對土地流轉簽約的合同、土地流轉的價格及時監管,規范整個土地流轉行為;“農村土地流轉服務中心”成立后,農戶自發土地流轉比例逐漸下降,委托流轉比例不斷上升;2013年,上海市遠郊農戶耕地承包面積120333hm2,已委托流轉面積為79200hm2,占耕地承包流轉比例的65.8%;2014年,上海市政府加大社會治理力度,強力推行委托流轉;至2016年底,在總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中,委托流轉率達到95%以上[2]。
2 上海市耕地流轉資源配置的效應分析
上海市鄉村振興“十四五”規劃:發揮超大城市鄉村功能,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使上海鄉村振興戰略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更加完善,并在全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省份中優先基本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形成城鄉融合發展新格局[3]。現階段全國開啟鄉村振興改革熱潮,各省政府部門意識到解決農業農村土地問題不僅直接關系農村經濟發展的速度,同時也對進一步縮小城鄉經濟發展帶來直接影響。土地流轉后的規模化經營將會為農村經濟發展引進更多的先進技術,促進農村農業活動的科學化與規范化的開展和管理,先進的科學技術也為農業種植活動帶來更高的工作效率,為提高農產品的產值和農產品的收益,解決農業經濟奠定基礎。
2.1 耕地流轉率遠超全國水平
上海市作為大都市,遠郊耕地流轉方式的多元化為發展新型經營主體和多樣化經營方式的繁榮發展提供條件。在城市化和城鄉融合發展背景下,上海市遠郊勞動力大量轉移,對土地流轉以及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具有正向影響。2016年,上海市耕地流轉率達75%左右;2018年,在出租、轉包等傳統土地流轉方式基礎上,上海市政府提出土地流轉的新模式——農民拿經營權入股村集體,加大對農業補貼力度,促使上海市遠郊農業規模化經營、家庭農場迅速發展起來。在用地管理制度的領域,上海市遠郊已具有成熟的方案與實踐,如松江區家庭農場,奉賢區農村宅基地集約利用新模式,在全國發揮了先行先試的示范效應[4]。
2.2 農業現代化水平優勢明顯
農業現代化基礎設施建設和改善,對提高農業種植生產率具有積極效應,為上海市政府發展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提供保障。遠郊隸屬上海管轄,因此遠郊農業發展有著天然的優勢,受都市地理位置的影響,遠郊路線較密集且路況相比欠發達地區農業區也較發達,為農產品運輸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奠定基礎;鄉村振興、城鄉融合與農業現代化的發展,政府高度重視遠郊地區的農業發展,近年來上海市政府投入大量資金用于遠郊農業機械、農業大棚、農村道路等農業基礎設施的建設,使上海市遠郊地區農業發展比傳統農業區農業發展基礎設施條件更完善[5]。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應加大農業機械化投入,上海市遠郊耕地存在地塊小,較分散等特征,使得上海市遠郊農業機械供給尚存在不足。
3 上海市耕地流轉資源配置存在的問題
3.1 耕地流轉簽約合同時間短
土地流轉簽約的合同周期以短中期為主,以1a為主,少部分是3a。土地作為維持農民最基本的物質保障,土地一旦流轉出去,便意味著農民最基本的物質保障將直接換成金錢來衡量,上海市城鄉居民養老金費用存在懸殊。當農地流轉之后,對以土地為主要收入的農戶來講,家庭收入可能在較短時期內出現家庭積蓄暫時不能夠維持基本生活的過渡期,就會引發嚴重的社會矛盾。同時,由于農民對于土地流轉出去的遠期收益保障不太清楚,因此導致部分年齡較大的農民不愿意將土地承包流轉出去。
3.2 農業勞動力缺口大
上海市作為一線城市、金融城市、國際化大都市,賦予上海市擁有大量就業機會,吸引大量遠郊青年勞動力加入城市二三產業就職,農村青年勞動力大量轉移、農業人口老齡化趨勢增長,使得遠郊農業勞動力面臨著后備主體的潛在缺失。農業種植需要消耗大量的體力與精力,家庭農業青年勞動力的轉移,部分老年農戶也逐漸退出農產品種植。
3.3 耕地連片流轉率低
上海市遠郊土地存在地塊小且分散,高低錯落不平,相對集中連片土地較少[6],導致部分村鎮耕地連片流轉率占流轉總面積的份額相對較小,不利于正規農業合作社、家庭農場的建設,在沒有進行“三塊地”改革之前,遠郊部分農戶多以低于2hm2的耕地進行承包經營,參與流轉的耕地也更多以散戶經營為主,其中又以非本市戶籍的居多。
3.4 耕地流轉非糧化嚴重
近年來,上海耕地逐漸傾向于非糧化、非農化。2017年,水稻等糧食播種面積為13.31萬hm2,占46.6%;經濟作物播種面積為15.28萬hm2,占53.4%。2018年,水稻等糧食播種面積為12.99萬hm2,占45.5%;經濟作物播種面積為15.54萬hm2,占54.5%。2019年,水稻等糧食播種面積為11.74萬hm2,占44.4%;經濟作物播種面積為14.69萬hm2,占55.6%。2020年,水稻等糧食播種面積為11.43萬hm2,占44.3%;經濟作物播種面積為14.35萬hm2,占55.7%。種植經濟作物獲取收益大于種植糧食作物收入,使得土地流轉后的承包商將土地進行經濟作物種植,勢必會導致糧食產量明顯下降。糧食種植面積不斷下降,必將會對糧食生產產生一定的影響,導致糧食數量出現安全危機。
4 上海市耕地流轉的優化路徑選擇
4.1 建立健全耕地流轉管理機制
政府有關部門人員應該明確在土地流轉管理過程中的職責,加強對土地流轉后的土地用途進行監管,做出及時的指導檢查監督,嚴格懲處非農化現象。對所要交易流轉的土地也要及時進行公開,確保農民的知情權;公開交易的信息也必須在上海市農業要素交易所網絡平臺和村務公開欄進行公示,接受社會各群體的監督。土地管理機構也應該對土地流轉經營資格進行認真核實,嚴格執行農村土地流轉備案制度,以確保土地流轉工作的正常運行。
4.2 規范耕地流轉費用行為
積極宣傳土地管理法規,提高農戶對土地政策的了解度,指導督促各村鎮委員加強流轉合同的規范簽訂,加強對土地流轉費用收支監管,避免出現村與村土地流轉費用差距懸殊過大;積極做好村務公開工作,嚴禁出現土地流轉違規現象,如土地流轉費收支不入賬、虛假流轉、虛報自家土地面積等手段套取補貼資金等行為,一旦出現,凡經核查屬實,政府管理人員有權取消農戶補貼資格,依法追回補貼資金。
4.3 探索多元化耕地流轉模式
上海現有流轉方式以委托、入股為主,上海市政府應該根據區域特色,嘗試開發多元化的土地流轉經營方式,提高土地連片流轉,促進土地規模化經營水平和農田基礎設施水平。積極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提高農產品的產值率,探索加大土地經營權流轉效益收入等手段來吸引農民參與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從而實現土地流轉方式新的突破。
4.4 完善土地“三權分置”
政府應落實集體所有權,穩定農村土地承包關系,平等保護經營權,注重大力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促進農地資源優化配置,提高農業生產效率[7]。同時,區政府應組建仲裁者或者組成專門的隊伍,形成“民間協商、鎮村調解、區縣仲裁、司法保障”的工作體系,分層次調解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糾紛的問題[8]。
5 結束語
自改革開放40年以來,我國城市化率由18%上升到60%左右,城鎮化進程的發展,使土地變得異常的珍貴,許多區域政府為了解決城鎮化所帶來的土地空間的緊張,以土地征收與土地流轉緩解城鎮化建設用地緊張的矛盾。本研究通過走訪調研和數據統計,發現上海市耕地流轉資源配置存在耕地流轉簽約合同時間短、農業勞動力缺口大、耕地流轉連片率低、耕地流轉非糧化嚴重的問題。在國家號召鄉村振興戰略和城鄉融合發展背景下,上海市政府提出,到2025年,上海鄉村振興戰略實施效果將領先全國的宏圖。現階段,上海市遠郊處于城市與非城市交叉的位置,其既有城市特征,又有農村特征,上海市政府以有序推進郊區農用地承包流轉,做好土地征收流轉承包的補償制度,農業生產的規模化、集中化經營來促進城鄉融合、城鄉經濟一體化發展。
耕地流轉是實現鄉村振興和農業現代化發展的重要抓手,是規模化種植的前提。集中土地,成片規模化種植,是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的一個重要方法,隨著科技的進步,傳統的農業種植生產方式逐漸被機械化、專業化、產業化、現代化的高科技機器所代替。因此,如何提高耕地流轉需要綜合考慮。上海作為一線城市,本研究基于上海市耕地流轉存在的問題提出改良上海市耕地流轉資源配置的建議措施,是否同樣適用于其他地區,仍有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