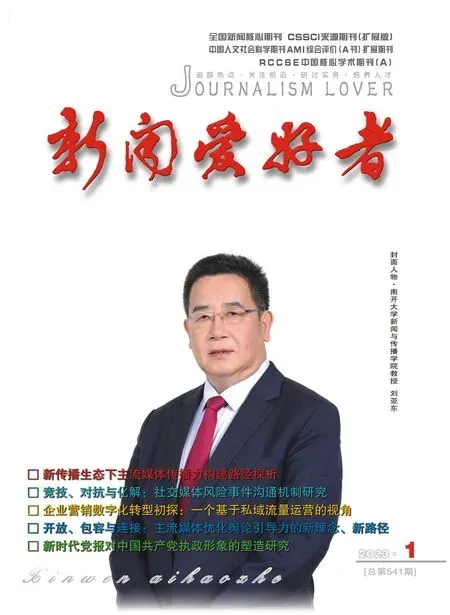移動社交圈群中的青少年道德風險探究
□錢婷婷 卞佳樂 馮蓓蓓
媒介技術的強力驅動與日新月異的社交方式正在廣大青少年中勾勒出“圈群化生活”的社會圖譜。這類社群體現出的排他性、群體認知非理性、輿論極化等特點,加劇了他們對道德規訓內容的情感排斥,引發道德信仰生成培育的困境。只有充分利用網絡圈群的優勢屬性,掌握網絡環境中青少年道德風險的生成規律,才能建立起培育和踐行道德信仰的長效機制,幫助青少年筑牢馬克思主義信仰的根基。
一、迷失的“自我”:行為異化與移動社交圈群交往風險
(一)錯位的“語言抗爭”
隨著媒介主義對人們日常生活的全面滲透,人們追求精神生產的日常實踐活動正在被媒介所掌控,這種影響在青少年身上的敘事效果尤為顯著。作為主流文化之外的亞文化形態在網絡技術的更迭中,被青少年群體不斷重構并賦予新的內涵。“圈群文化”作為一種網絡亞文化,它對青少年的道德認知和行為產生了一定影響并引發道德風險。
話語是文化的載體,而“飯圈文化”通過一定的儀式,對“新入者”和“違規者”進行行為規范(如花錢打榜、買專輯、應援等),并對“違規者”以特有的話語行為進行懲戒。這種現象已經在圈群中不斷彌散,甚至成為約定俗成的“規則”。在“話題”制造的場域中,青少年因為共同的“精神偶像”而在網絡空間上變成一系列“符號”存在。市場利益的驅使讓“組織者”通過設定一定意義的“話題場域”來建構矛盾,不斷造成“圈群成員”的觀點對立,“互撕”可以讓處于不同價值立場的粉絲保持對偶像的持續經濟投入,這種交往方式打破了傳統交往在時間、空間以及身份地位上的普遍性和穩定性,不斷消解傳統主流文化的規制功能。粉絲的“語言抗爭”通過自媒體傳播加速了圈群內部的群體認同,并演變為青少年網絡日常交往的“口頭禪”,影響了他們對于網絡交往道德認知的邊界。
話語的力量并不僅僅是言語,更在于它是社會交往的存在方式,是在社會生活中進行的道德實踐。典型的“臟話”最終會投射在圈群青少年的道德生態中,成為青少年道德冷漠風險的來源。正是由于網絡道德認知的矛盾與偏差,才導致青少年的網絡交往道德意識被弱化,模糊了作為一個“社會人”的基本道德觀念。從本質上說,“飯圈”中青少年“臟話”是精神生產的資本化和群體亞文化規訓相互作用的結果,網絡交往主體的異化說明完善主體道德人格的重要性。
(二)隱匿的“游戲心態”
在技術主義的宏大語境中,傳統的以祖先崇拜為中心的文化生產模式被解構,一種以市場為導向的娛樂消費主義生產方式取而代之。它將不同領域或者地域的特質文化相互整合,并通過新媒體快速傳播,逐漸成為青少年的精神寄托并影響著青少年的價值觀。高度市場化伴隨著快速崛起的媒介傳播技術,讓文化生產轉向娛樂化、商業化甚至是低俗化。互聯網技術的快速發展也讓具有“懷疑權威”“反傳統”的解構主義思潮以各種新的形式呈現在青少年面前,而這種思潮所帶來的個性化、多元化色彩滿足了青少年的普遍心理需求。因此,面對虛擬社會和現實世界高度融合的普遍事實,“文化的批量化生產”和后現代“解構主義”思潮的快速傳播為青少年泛娛樂化價值觀的形成提供了廣闊空間。“泛娛樂化”在道德領域中表現為:青少年為了個人利益在網絡交往過程中所呈現的“游戲”心態,這是一種對社會道德評價秉持無所謂對錯、無所謂高尚卑劣,甚至是觸碰法律底線的價值觀。網絡交往環境的虛擬化、交往方式的符號化、交往角色的隱匿化使得“網絡圈群”的道德約束機制弱化,青少年道德責任感正逐步被資本構建的“虛擬偶像”所消解。
(三)割裂的“心理補償”
隨著移動傳播技術的發展,帶來了消費主義思潮對青少年的全面滲透,青少年對于感官刺激、新奇事物等帶有熱衷偏好。這種消費景觀,影響青少年的不僅僅是價值觀,更是一種道德風險,而背后反映出的是青少年對于道德價值的冷漠。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在《啟蒙的辯證法》中寫道:“在通往現代科學的道路上,人們放棄了任何對意義的探求。他們用公式替代概念,用規則和概率替代原因和動機。”[1]在數字化生活中,作為交往主體的青少年在網絡空間上變成了“物欲符號”,即人的形象、身份、性格等通過“數字景觀”重構為一種物質欲望的心理崇拜和心理補償,這種交往方式打破了傳統交往在時間、空間以及身份地位上的普遍性和穩定性,不斷消解主流文化的規制功能,“網絡低俗文化”在虛擬與現實相互融合而共同構成的日常敘事中演變為青少年的網絡 “日常”,其背后隱藏的功利主義價值觀,會影響青少年培育正確、理性的道德認知。
二、真實抑或虛無:移動社交圈群中青少年交往道德風險的形成邏輯
(一)媒介時代的存在方式
網絡時代,個體存在方式的變化讓青少年失去平衡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之間的動力,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青少年存在方式的媒介化。從橫向看,人與人之間是一種媒介化的交流聯系;從縱向看,每個人只是整個網絡媒介生產和生活環節中的虛擬“節點”。自媒體時代,熱衷于接受媒介傳播信息的青少年往往只關心自己感興趣的話題,對于社會公共議題的關注不夠,削弱了青少年公共生活的共識基礎、價值導向和道德底線,青少年主流價值認知面臨被邊緣化的風險。二是青少年存在方式的物質化。在消費主義文化與西方物欲主義消費觀相互作用的宏觀敘事中,“飯圈”青少年為了追求所喜歡的偶像的排名,產生了超前的消費行為,消費主義文化正潛移默化地改變著青少年的網絡行為方式,這些都會對青少年信仰功利化、泛娛樂化和庸俗化帶來直接影響。三是青少年存在方式的虛擬化。無論網絡技術如何更迭,網絡社會與個體生存之間的現實關系是建立在網絡主體感性基礎上的。這種建立在絕對快感上的網絡沉溺個體,在“對象”和“主體”兩個世界喪失了感性活動的真實性,青少年在此過程中如果產生不正確的網絡認知,易造成網絡交往的主體性風險。
(二)擬態環境中的娛樂生活
麥克斯韋爾·麥庫姆斯在《議程設置》中指出:輿論可以 “制造危機”“媒介構造并呈現給公眾一個擬態環境,而這個擬態環境極大塑造了公眾看待世界的方式”。[2]圈群傳播所誘發的道德風險是當下互聯網媒介倫理缺失的一種表現,媒介技術的發展引發了社會道德認知的“斷裂”。自媒體時代所彌漫的道德風險形成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網絡圈群的群體性存在。媒介帶給人“交往世界”的同時也在建構人的“精神世界”。虛擬社會中任何媒介所傳播的信息都是人建構的結果。因此,技術主義所建構的虛擬場景讓青少年有了足夠的興趣體驗,并通過網絡媒介形成特定圈群。第二,虛擬敘事結構與媒介倫理道德的矛盾。媒介市場化改革的邏輯本身也在于建構媒介對信息傳播的認知過程。“場景效應”和“眼球經濟”共同推動著青少年網絡交往的族群化形態,以追求小眾新奇、娛樂戲謔和共同興趣為“點擊率”的圈群敘事成為青少年網絡亞文化生活的新形式。基于網絡圈群亞文化與主流文化的張力所導致的價值失衡,會影響青少年對社會道德的消解認知,由此引發各類道德風險的產生。第三,圈群交往主體與圈層現象。無論是“游戲沉溺”還是“COSPLAY”圈群扮演,網絡興趣群的青少年行為所引發的討論和行為都產生了較大的社會爭議。需強調的是,擺脫圈群的過度市場化運作,對作為社會監督和信息傳播窗口的媒介及其新聞工作者來說,正是規避青少年網絡交往道德風險的重要前提。
(三)景觀消費中的行為過程
在網絡直播這種沉浸體驗中,以價值認知、道德倫理和法律規范為主要風險表征形式,與其期待構成了“意義的對裂”,這不僅降低了青少年健康成長的正能量指數,而且對其未來發展也將產生消極影響。第一,價值認知的歪曲。在青少年網絡直播消費中,他們不僅僅購買自己需要的商品,更需要在購物的同時滿足對主播的“凝視”,網絡直播中的帶貨主播需要按照粉絲個性化需要形成“行為規訓”。第二,流量經濟助推不良之風。“實時”意味著網絡直播可以將現實生活世界的各種場景輕易地“復制”進入虛擬世界,較快吸引用戶形成個性化體驗。與此同時,互聯網企業或者主播為了增強用戶“黏性”,通過實時“身體—場景”所提供的話語、動作和觀念觸碰社會道德底線,隨著“流量”的增加,也必然會消解社會道德倫理對青少年的價值形塑。第三,網絡直播消費的群落共享。通過參與網絡直播所提供的真實消費過程,青少年群體能夠獲得現實生活中難以獲得的各種情感體驗和認同。因此,網絡直播行業中的種種違法違規亂象的產生,其背后是網絡主播通過圈群青少年群體的價值共享,獲得對其直播場景中的錯誤觀點或行為的集體消費,從而加強了圈群成員對直播以及成員間彼此的認同感。
三、重塑理性:移動社交圈群中青少年道德風險的治理路徑
(一)議程設置,增強青少年網絡道德教育的實效性
青少年網絡交往道德失范行為的發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網絡社會的工具理性導致精神向度異質和個性化,從而在此過程中產生缺乏道德自覺和自律意識的現象。網絡是連接社會與個體的關鍵環節,其即時性、互動性的特征也為議程設置的擴展提供了實踐的空間。因此,調適青少年網絡交往行為的關鍵就在于通過議程設置提升青少年“從我做起”的網絡道德自覺意識,樹立正確的網絡道德價值觀。
青少年在使用網絡的過程中,并不具有 “獨占性”,而是從屬于不同性質的社群。經某一社群達成共識的議程隨著成員的流動會不斷流向其他社群,這就引起了社群間的互動。互聯網平臺應加強對議程中“核心價值”的把控,尋找最佳的議程設置點,這樣在群體的深化中才能重塑青少年的理性行為,端正符合道德規范的網絡交往行為。
(二)加強對話,完善精細化常態化的監管與治理
對話,并非你一言我一語的回復,究其本質是平等精神的體現。在對話中,要將青少年置于與“我”的平等位置中,在“眾聲喧嘩”中實現價值的引領。在建立網絡圈群青少年交往的道德風險應對機制中,一方面,既要加強網絡相關法律條文的制定和完善,發揮網絡文化治理的制度優勢,加大對網絡違法行為的打擊力度,切斷網絡圈群輿情生成的利益輸送鏈,引導建立積極向上的網絡文化氛圍;另一方面,在滿足訴求之余也要重塑“圈群”成員的社交規則,有效建立符合青少年自身利益的網絡規范。實施社交軟件實名制。各大移動社交軟件應當實施實名制,在用戶注冊前需對其進行身份驗證,并對用戶進行年齡限制,根據不同年齡段對青少年軟件的使用時間進行限制,最大限度地保護其身心健康。加大監管力度,設立專門監管機構,大力抵制“非法集資”“刷數據”“拉踩、引戰”等行為的發生,監督藝人及其粉絲的言論,凈化網絡空間,營造良好的輿論環境。
(三)價值引領,構建青少年文化建設長效機制
百年來,中國共產黨總是把青少年特別是青年看作是推動社會歷史發展和前行的重要力量,因此,對青少年的引領培養,應彰顯時代責任。第一,青少年首先要不負對政治立場的期許,其次才是不負發展理念的期許。網絡媒體作為社會的守望者,應與學校、家庭、共青團等發揮合力育人的作用和價值,加強輿論的引導與監督功能。第二,落實網絡陣地建設,打造育人平臺。學校德育工作者要主動利用網絡新媒體,主動擁抱網絡圈群的民間話語體系,加強對新媒體技術的學習以及駕馭使用能力。借助全媒體時代的豐富形式,學習新知識、掌握新話語、駕馭新技術,在潛移默化中對青少年進行道德熏陶,同時增強網絡道德教育的吸引力、說服力和實效性。第三,建立青少年文化建設長效機制。特別是注重將優秀傳統文化教育與德育教育等相結合,共同推進與弘揚青少年文化主旋律,不斷加強優質青少年文化建設。
四、結語
網絡“圈群化”改變了原有的傳播生態,讓“意義”在關系的聯結中不斷流動,而與之相伴的道德風險也成為當下亟待解決的難題。亞文化儀式中的“語言抗爭”、扭曲的消費主義讓青少年的網絡行為逐漸失范,因此,加強青少年自身的行為調適、建立常態化的監管機制,都是現實而又合理的選擇。如此,才能構建起風清氣正的網絡環境,推進優質青少年文化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