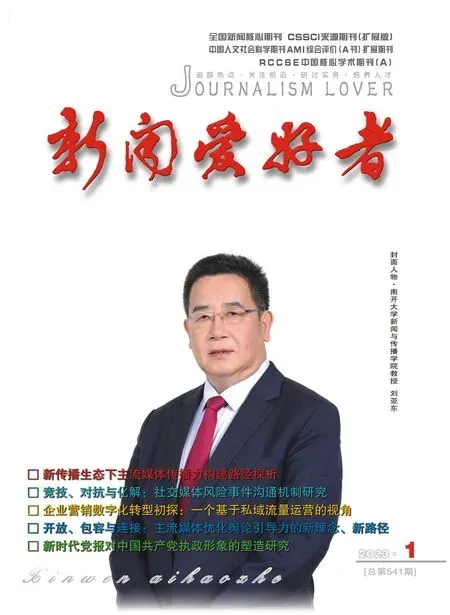中西文化藝術碰撞與融合
——評《西方美術文化發(fā)展史》
當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同一場域共同言說時,相互之間產生碰撞、進行融合在所難免,但這也是不同文化共同發(fā)展的必經之路。在世紀之交,由美術史論研究者、美術教育學者李蒲星著、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西方美術文化發(fā)展史》一書,通過八章,系統(tǒng)描摹了西方美術文化的“基本狀態(tài)”“自然時代”“和諧時代”“壓迫時代”“覺醒時代”“理性時代”“解放時代”和“自由時代”,并且結合對同時期的藝術思潮、藝術家及藝術品的品評,緩緩揭開西方美術文化的神秘面紗。該書作為一本碰撞之書、交流之書、融合之書,呈現(xiàn)出以下鮮明特點。
一、形:模擬外觀,比中對西
該書外在師法西方一般藝術史論,以歷史斷代為架構線索,而在成書行文時,作者有意對照中西美術在同時期的“共同事件”,在詳盡論述西方美術狀況的同時,對中國美術在同一時段的發(fā)展情況稍加描繪,著力創(chuàng)造交流場域,不懼碰撞,反而以此占領受眾的“對比心智”,使受眾對“中西美術發(fā)展從源頭即開始產生不同”這一史實一目了然。在第一章中,作者從分類、語言、材料和傳統(tǒng)四個方面對西方美術文化發(fā)展史做了宏觀論述,為自己的研究方法和邏輯架構設計做出說明,更開門見山地表明立場:“本書分類方法和材料來源于西方,而語言和著述傳統(tǒng)卻在進行‘東方試驗’,這也是導師高爾泰先生的鼓勵:中國學者寫的西方的美術史,要介紹西方的發(fā)展,更要有中國的樣子”;除此之外,作者在每一章最后一節(jié)均設“結語”,對本章內容進行總結、概括,再次強化中西美術發(fā)展對比的同時,尊重中國美術教育發(fā)展現(xiàn)狀,雖形肖西方,內核仍是“中國的樣子”:尊重規(guī)律,格物致知。
二、神:中國史觀,西學方法
作為一部藝術史,該書重中之重在史料的發(fā)現(xiàn)、整理、說明和運用。該書中,作者充分考察了史料,又不局限于“故紙堆”,在史料運用上,作者并非采用以往西方史論類專著常見的 “材料—說明—闡釋或立論—得出結論”的方法,而是將史料用作“描寫”和“增加實感”,同時大量使用關于美術作品出現(xiàn)背景和社會現(xiàn)實的材料:例如,在論述“前衛(wèi)主義”時,作者大量引用了歷史材料,其用意并非以材料推導出某種“前衛(wèi)主義”結論,而是用以描繪當時的歷史環(huán)境和人民生活,以便受眾在閱讀本書的過程中體會當時的歷史背景,進而在后續(xù)學習時更容易理解某種美術思潮或代表人物在某一時間節(jié)點出現(xiàn)的必然性。這是中國唯物主義史觀“歷史為人民造就”的集中應用,完全區(qū)別于西方的“歷史是由天才和偉人創(chuàng)造”的“英雄史觀”——兩者的區(qū)別,在前文所述的“共同事件法”的行文模式下,形成鮮明對比。這種由理論切入,以史料作描寫而非專為理論服務,力求讓受眾建立直觀感受和了解必然性的理論史觀與著述方法,使本書將西方美術發(fā)展理論與中國國情完全相容,也與傳統(tǒng)文化中“潤物無聲”的德育、美育觀念不謀而合,在一定程度上也為我國當代的美術教育提供了中國化的思路和理念。
三、魂:中西融合,美美與共
如果說上述兩個特點尚顯“中”“西”涇渭之分,激發(fā)了中西文化碰撞,該書的寫作風格,則是“中西融合”的完美體現(xiàn)。作者在高度理論化的同時,憑借自己的“第一感受”“第一印象”,用極為緩和、優(yōu)美的語言對西方美術作品或美術思潮進行 “印象式品評”。而這種由著名文學評論家李健吾先生首創(chuàng)并發(fā)揚于中國的“印象式品評”,彰顯了西方美術中的“印象主義”思潮對中國文藝批評所產生的深遠影響,也是作者著力將“西方美術文化發(fā)展史”這一舶來理論以自己的學識與行文進行融合加工、使之更加“本土化”的有力佐證。同時,該書將對西方美術發(fā)展的考察置于歷史與文化的大背景下,以西方邏輯框架與中國理論史觀進行融合闡述,體現(xiàn)了作者對中西文化藝術碰撞融合的問題意識和深刻思索。
綜上所述,《西方美術文化發(fā)展史》一書,凸顯了藝術在發(fā)展過程中的文化價值,并且致力于開啟一種中國話語體系下的西方藝術文化研究范式,幫助讀者看到文化和藝術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中國與西方之間的交會與碰撞的同時,也引發(fā)更多關于我國當代藝術文化發(fā)展的探索與深思。同時,該書利用文學化、“印象式”的方法論作為成書、行文的指導原則,使西方“印象派”風格完全為我所用,造就了該書既是一本美術學、文藝學理論專著,也是一本美文文集的“融合身份”,為相關領域的研究者樹立了學術榜樣,也為文化和藝術領域的初學者與普通愛好者打開了藝術鑒賞與文化理解的新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