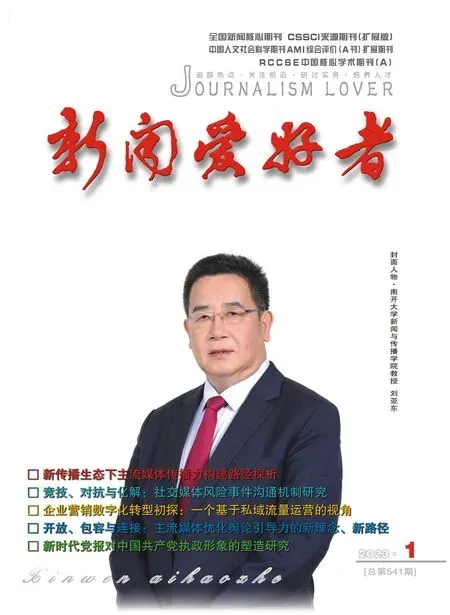中西新聞比較視角下“全球新聞”的生產及思考
——以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葬禮的系列報道為例
□符逸帆
20世紀末開始,世界以“全球”為單位,產生了一個獨特的話語空間。本地文化和世界文化交融,傳統的民族身份認同變得模糊。一個國家的決策、一種文化產品的流行、一項新科技的產生,都會在全世界不同地區產生影響。新聞領域也不例外。媒體的全球化意味著新聞內容正變得更加非地域化,這讓新聞業發展出了一種不同于傳統的生態。因此,傳播學和新聞學研究者們開始探索新的角度來挖掘新聞的意義和表現方式。在21世紀初期,許多學者提出了“全球新聞”(global journalism)的概念。[1]全球新聞學研究屬于國際傳播和跨國傳播領域,主要通過政治經濟和全球化兩方面分析新聞媒體和全球化的關系。[2]
Peter Berglez(2008)于研究中表示,被全球化趨勢影響的當下,“全球新聞”可以看作一個有別于傳統國內/國際新聞框架的概念。[3]傳統的國際新聞往往以特定的空間、政治或文化背景下發生的事情為基礎來進行報道。在全球觀視角下,它旨在體現某個事件的背后關于世界經濟、政治和社會的相互影響、相互牽制。換言之,如果全球化意味著人、文化、區域、經濟等各領域之間越發復雜的關系,那么全球化新聞則是指重點整合并報道這些關系。Ulrich Beck曾于2006年提出:大多數新聞媒體仍舊過于拘泥于國家的視角。他認為,新聞報道需要突破以某個單一國家為主,將新聞事件置于更廣泛的跨國背景下并探討不同角色的關聯性——若將新聞事件與全球化環境相結合,能夠呈現出一個更全面、更深刻的新聞面貌。[4]由此,在日益全球化的時代,許多學者將全球新聞視為當代新聞內容和新聞學教育理想的發展方向。然而,“全球新聞”仍作為一個較新的概念,該領域存在的關鍵性問題在于經驗性研究的缺乏。即便從概念和理論角度而言,“全球新聞學”有建設性十足的觀點支撐,但實際上它作為一種新的新聞風格,至今并未明確與其他類型的跨國新聞區分,特別是國際新聞報道。在過去的20年間,雖然有部分研究通過對比多國新聞報道,證明了一些媒體以全球化角度撰寫新聞報道的趨勢,但也有不少學者對“全球新聞”的實際存在持懷疑態度。[5]
本文以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葬禮這一事件為切入點,選取了四份中英新聞報道,從文本內容展開論述,探討中英媒體對這一事件的報道是否涉足“全球新聞”所必備的要素、在何種程度上體現了“全球新聞”,以及新聞媒體中所反映的全球化現狀。
一、研究方法與樣本概述
本文選取內容分析為主要研究方法。此方法常用于剖析文本中存在的某些詞語、主題或概念的存在、意義和關系。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中,往往用其分析傳播信息內容。因此,當分析對象為新聞報道時,內容分析可以用來挖掘偏見或偏向性。探尋一篇報道背后的內容價值、文化環境、社會認知等信息。關于對“全球新聞”的實證檢驗,本文利用了Peter Berglez 分別于2008年和2013年提出的概念模型——“Complex relations of space,power and identity in global journalism”。[6]該模型建議通過分析新聞文本片段來探討其對全球化視角下復雜關系的呈現。全球化語境下的空間、權力和身份作為“全球新聞”的基本構件三要素——可以用來判斷新聞媒體是如何將多種復雜關系納入報道之中的。
本文以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葬禮事件為背景,Google News 和百度新聞兩大搜索引擎為來源,選取了四篇中英新聞報道作為樣本進行分析。兩篇中文報道分別是來自《中國報道》的《英國女王葬禮今日舉行,她任命的特拉斯能成為新的“鐵娘子”嗎?》和《直新聞》的《從英女王葬禮看英國外交》。前者聚焦英國當前所面臨的民生、經濟和外交等問題,通過回顧首相競選過程,對其今后的政治舉措提出了疑問。后者從英國國葬出發,針對因受邀賓客、座位安排、行程待遇等方面所引發的議論作出了報道,指出了此次英方在女王葬禮前后在外交上的不足之處。
兩篇英文報道,《每日電訊報》的Queen Elizabeth II laid to rest amid an outpouring of love重點刻畫家庭成員的個人情感與英國王室職責角色的矛盾點,將伊麗莎白二世時代的終結與查爾斯身份的更替相結合。[7]《衛報》 的Queen Elizabeth II:from public pomp to a private family farewell展示了世紀葬禮儀式感、沿路民眾的熱烈反應等,同時記錄了英國王室葬禮溫情的一面。[8]
二、研究分析
(一)空間關系
在本文所選取的四個樣本中,多元的地理環境在不同程度上得以體現。《中國報道》從英國面臨的外交問題入手,將英國與歐洲、美國、中國、俄羅斯、烏克蘭等國家和地區的外交現狀進行了總結和分析,指出英國女王去世等英國大事件將會對世界其他地區造成影響。同時,以中方角度針對世界格局進行了理解和預測。如此,突破了這一新聞事件在地域性上的局限,將單一事件延伸到對國際政治局勢的探討。《從英女王葬禮看英國外交》更是將全球化視角下的空間關系體現得淋漓盡致,將英方對各國代表的安排和互動態度延伸到與各地區、國家的關系。沒有把具體的某一個地方作為重心,而是分別以英國外交為出發點討論其與世界各地的相互影響。
相較于中國媒體的報道,兩篇英文報道中體現的空間感稍顯單一,主要還是以“國內新聞”的方式呈現事件。《每日電訊報》多以“the world”一詞表現事件和世界的聯系。比如,用“the watching world”將事件與全世界的目光相結合。《衛報》也使用了同樣的單詞用來體現全球視角:“all round the nation,Commonwealth and world”。英國王室、英聯邦、全世界皆于此刻共情,構建出一種跨越國境的緊密情感連接。
(二)權力關系
“全球新聞”里的權力關系,是指新聞事件的主題如何展現了國內、國外和全球三種層面的權力關系。當跨國和全球性的權力被納入新聞報道中時,全球新聞風格就得以誕生。
《中國報道》通過列舉英國內部的問題,展示了其國內層面的權力關系,也報道了英國與其他國家、地區的外交平衡、立場選擇,展現了第二層的權力關系。在展現全球權力關系方面,文章不但以宏觀角度對比了英國對歐洲、對中國的外交態度,也貫穿融合了三層權力關系視野,將其國內的政府內部派別權力關系延伸到對外的關系處理,以及在國際上的角色定位。由此可見,此樣本對國內和國外因素進行了比較和分析組合,展現了全球新聞在權力關系方面的關鍵性元素。
《直新聞》的報道雖然在一些方面展現了國際層面的權力關系——英國的舉動所造成的與不同國家的外交危機,導致英國人民在未來可能會面臨的民生、經濟問題——不過,該篇報道所體現的權力關系比較單一,只展現了地方、議會與他國的權力結構,不夠多面和多層次。
英國媒體的報道更傾向于保留傳統的國內新聞報道視角,即便略微提及了不同國家角色的政治力量,但無論從篇幅還是內容上來看,都不太滿足“全球新聞”模型所要求展現的權力元素。比如,《每日電訊報》展示了以英國為中心的聯邦權力結構。《衛報》則是將重點放在了突出議會和王室的統治力量,展示了英國獨特的君主立憲政治體系,而并未展現全球化視角的權力關系。
(三)身份關系
本文選取的中文報道均未體現全球新聞必備的跨國的、世界性的身份象征。所謂身份的全球性,指的是需要突破被國籍所定義的政治認同,繼而突破國境邊界形成一種超越國家文化、超越民族歸屬的世界性身份。《直新聞》進行了以國為政治身份的對比,使用了“英方邀請”“俄方官員”“伊朗方面”等清晰界定國家身份的詞語。《中國報道》則是以中方視角看待英國問題,同樣強調了以國家為單位的身份不同。而對全球新聞而言,它所傳達的身份本質是一種普遍的身份象征,突破被國境邊界所定義的身份認知。因此,在這個層面上,這兩篇樣本都并未表達出一種存在于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共同身份。
英國媒體的報道表現出了脫離基于國家的政治身份認同的傾向。《衛報》 的報道在刻畫民眾時用“the crowds”“the world”對所有關注這件事的人們作為統稱。不管是在英民眾,還是在世界各地觀看直播的觀眾,都在同樣的時間,跨越空間、跨越國界,成為一個擁有共同身份標簽的集體,即歷史見證者。類似的用詞也頻繁在《每日電訊報》里出現。女王葬禮儀式的關注者們不分國籍、不分種族、不論政治背景,只因此事件共享一個身份:作為參與者、見證者。此外,全文以一種尤其溫情的語調,突出了“家”的概念——“home”和“family”高頻率出現,以此降低階級感、疏離感,在情感上塑造出一種集體感和歸屬感的同時,打破固化的階級、政治定位,用一種普遍性的、容易被所有人代入的身份認知貫穿全文。
三、總結和討論
(一)全球新聞的具體體現
全球新聞作為全球化時代所需要的新聞形式,它與當今世界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日益無邊界化、融合化、復雜化密切相關。本文分析結果發現,樣本均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全球新聞的必備要素。通過對國際局勢、國際關系、國際觀眾展開延伸,這些報道大多以一種國內/國外新聞加上全球性視角的混合方式,展現了全球觀。
在空間和權力關系上,中國媒體的報道通過將英國與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進行聯系和對比,呈現出了更豐富的全球性。英國報道更大程度上保留了國內新聞的報道模式,將權力方面的核心重點放在本國的政治結構上。在身份關系上,英國媒體的報道則體現出了豐富性,試圖消除國籍對身份認知的約束,從而體現出一種廣泛適用的無國界性質的身份。因此,全球新聞在一定程度上有存在的跡象。以一個全球事件為中心和對報道的事件延伸為對全球的展望,模糊了本國與他國的界線,打造出一個世界性的社會現實,以此產生一種新興的報道風格。不過,對于這個領域而言,仍然需要更多長期縱向研究來進行不斷的填充,建立更牢固的實證用以支持這一概念。
(二)全球化和民族國家
值得注意的是,針對新聞事件中復雜全球關系的呈現仍處于比較淺顯的層面。就本文所選取的樣本而言,在許多情況下,對于空間、權力、身份關系的涉及和表達,往往限于簡單提及一個全球行為或問題,而沒有充分探索或闡述所有涉及的復雜關系。由此看來,新聞的框架仍然是基于所屬國家的視角。新聞媒體既是保障民族凝結的重要角色,也是意識形態擴散的重要場所——這不由得令人深思,處于全球化浪潮中心的它,在客觀新聞價值標準和全球性視野的“中立性”外衣下,實質究竟是促使了全球化的發展,還是讓民族主義更加根深蒂固了?即便四則樣本都力圖在內容和語言表達上呈現一種全面的、全球化的視角,但可以看出,當今的新聞媒體不可避免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國內環境、社會價值觀、文化背景等多方面的影響。比如,中國媒體對國家身份的強調、對文化差異的關注,以此區分本國和他國的差異性。英國媒體即便在身份認知上呈現了一定的統一性,但也反復提及了“家”一詞。以此維護國家的優先權、完整性以及民族利益。在全球化的外表下,新聞媒體非但沒有消除民族國家的功能,而且仍舊在不斷地產生和加強某些社會共享的價值和觀念。因此,新聞媒體在全球化語境中存在的矛盾對立點也不言而喻:在打造無國界性質的同時,需要捍衛家國文化。現下新聞媒體的這一矛盾,其實也反映出全球化的現狀。
世界經濟、文化、社會、環境、政治的關系發展至今,全球關系網仍處于一個緊密結合的狀態,維持并延續著全球化的表象,但當代全球化社會也正處在轉型期。在足夠適應世界的完整性、依存性、關聯性之后,接下來的方向,似乎便是轉而逐漸瓦解這個全球關系網內部的連接性力量。家國民族的特殊性、基于國家的權力關系,本國、本地文化儼然已重新被當作重點捍衛對象。作為文化、思想、價值的載體,傳播媒體在這個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通過對重大事件的報道,在挖掘其國際性、全球性元素的同時,也隱含著強調本國特殊性的大量信息。由此看來,在這個全球化時代,宣揚各國自身的文化特性或許才是傳播的本質。這不僅宣告著家國思想對塑造當代全球化的重要性回歸,也不斷提醒著人們關于民族國家在如今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