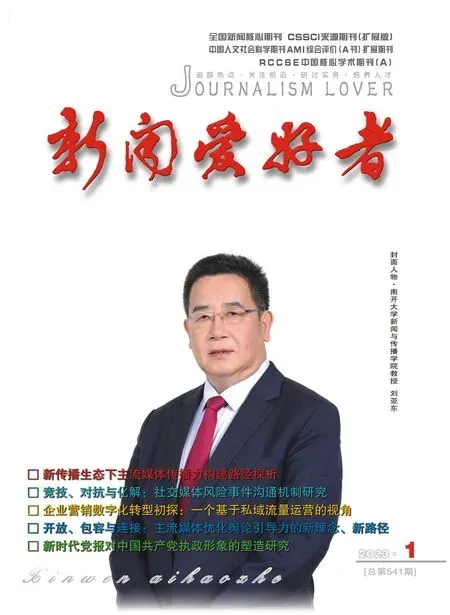論媒介傳播對話劇生產的促進
——從現代海派話劇的繁盛談起
□尹 詩
抗戰時期是上海話劇史上特殊的黃金時代,政治的弱化和商業性的凸顯,將海派話劇推向了高潮。本文指的海派話劇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在上海產生的帶有商業性的、以市民觀念為主的通俗劇。此時期話劇的繁榮須臾離不開報刊媒介的推動,劇評便是話劇和媒介互動關系的呈現,構成了戲劇活動重要的組成部分。隨著國內越來越多的新都會的崛起,究竟怎樣才能重新激活話劇的活力?新中國成立前上海話劇的繁榮,是足以給人啟發的。尤其是在當今資訊時代,充分發揮媒介的作用,聆聽觀眾心聲,圍繞“觀演互動”做好文章,才是話劇真正深入大眾,走向繁榮發展的有效途徑。
一、媒介參與海派話劇生產的繁盛圖景
出版業的興起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上海大眾文化發達的表征,作為大眾傳媒的報紙雜志與文學藝術的傳播共生共榮。話劇自1907年傳入中國,其發展幾經曲折且成熟較晚,在1940年代終于呈現了繁榮景象。在話劇史上這段特殊時段,媒介密切參與話劇生產且對話劇的興盛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近代中國,任何社會思想的傳播和各種政治運動的進行,都需要通過報紙來廣泛吸引和爭取民眾。在從封閉走向開放、從傳統走向現代的轉型過程中,“各種價值發生碰撞,曾被視為‘小道’的戲劇與正統詩文試圖一決高下,報刊的傳播特質使它成為輿論的陣地,有效提升了戲劇的地位”。[1]
話劇評論通過媒體影響著觀眾,也影響作用于劇團和劇目生產,能夠還原特定歷史語境下話劇的藝術傳播方式與形貌。當時刊登話劇信息的現代報刊多達100 余種,既有專業刊物《戲劇雜志》《劇藝》《話劇界》《舞臺藝術》等;也有具有影響力的報刊如《申報》《萬象》《半月影劇》《大眾影訊》《良友》《雜志》《天下》等;還包括都市小報,如《社會日報》《力報》《海報》《大上海報》《平報》《中國藝壇日報》《娛樂》《鐵報》等報的各種正刊及副刊。不少評劇者既是話劇愛好者,也是報刊編輯,或是話劇活動的實踐者等。多重身份使得他們的藝術主張和創作實踐融入媒介傳播活動,隨之產生了新聞報道、演出手記、座談會紀要等各種形式的劇評文章,再現了話劇在現代報刊媒介中的實際刊載和在讀者群中的傳播情況。報刊劇評作為雅俗共賞的大眾文體,極大地促進了話劇的生產傳播。而當時發達的商業娛樂休閑形式如京劇、話劇、彈詞、灘簧、電影,則無一例外離不開報刊媒介的傳播。大眾傳媒和各種娛樂形式一道,共同促進了大眾文化的繁盛。
二、對河南本土話劇市場發展的思考
話劇的發展繁榮離不開報刊媒介的推動。可是反觀今天的話劇,我們不得不承認在傳媒技術高度發展的時代,媒介在促進話劇的發展方面尚有較大的空間。話劇在創作和演出中是如何滿足人們審美和娛樂各方面的需求的?大眾媒介又是如何參與建構話劇審美藝術的演變與革新?相信經由媒介的研究視角,能夠展開別開生面的探討。而在話劇生產—觀眾接受—媒介傳播等互動的系統中觀照話劇,或許能夠開啟研究現代話劇的新面向,呈現出多樣化的戲劇生態。
(一)設立“劇評”欄目,實現“觀演互動”
以海派話劇為例,各種立場、不同角度的海派話劇評論極大程度地呈現了話劇的繁復多面。劇團變幻、劇目出爐及花落誰家、主打戲的定奪以及劇人境遇等面向的劇評,呈現了劇團、劇人、劇目、演出之間互動的網狀圖景。如對于黃佐臨領導的苦干劇團,劇評稱“與上海藝術劇團合作后,又與藝光劇團合作,苦了華藝劇團被踢”。[2]對于李健吾頻繁變換劇團,報道稱:“李健吾在華藝劇團客串演出后,即加入上海藝術劇團,不料合作三日又告脫離。及后加入藝光,最近又加入聯誼劇團。”劇評亦能完整呈現話劇的舞臺藝術,以舞臺布景、服裝道具、音樂、演員演技等領域的評論使得“劇本”與“演出”并重。如評論看出《浮生六記》 以電影化手法增強視覺沖擊力的特征:“蕓娘說完臨終的話‘春天不遠了’,病榻后面的綠幔掀起,露出窗外暮春三月的景象。”[3]還有劇評贊揚使用西歐曲調配樂的《香妃》,為中國新歌劇奠定了基石。而像石揮、孫景路等話劇明星撰寫的“演出手記”,彰顯出個性化的演劇風格,也是考察話劇藝術的重要維度。
結合河南目前的話劇市場,引入新媒體以加強話劇傳播、評論勢在必行。新媒體戲劇評論是隨著互聯網技術的出現而誕生的。觀察當下的新媒體戲劇評論我們發現,微博、微信公眾號、豆瓣網已經成為最為重要的三個媒介平臺。而話劇評論與話劇演出一般都是同步發展的。北京等一線城市最早出現新媒體話劇評論,直到現在還有“北小京看話劇”“安妮看戲”等依然發揮影響力的公眾號。從話劇在河南劇場演出的次數來看,遠不及其他一些一線城市的多,出演的話劇種類和數量也比不過一線城市。河南話劇演出場所整體不多,鄭州的大劇場僅有河南藝術中心一家,除此之外是象劇場、開心簡史先鋒劇場、鄭州丹尼斯大衛城劇場等小劇場。在新媒體盛行的當下,完全可以凸顯媒體的責任,在宣傳、互動等方面加強話劇的傳播流布。在上演的劇目甚至場所不能被多數人獲悉的今天,新媒體具有天然的優勢來充當作品展播的載體,只有傳播量和關注度上升,才能有相應的話劇評論的發達。
首先,話劇演出機構不妨在開設公眾號的基礎上,設立“劇評”欄目,在促進生產和消費的連接方面充分發揮功效,讓受眾的觀劇感受有途徑發表。現有的劇院公眾號介紹劇作內容的多,但是未見有 “劇評”欄目,這樣話劇的觀眾接受情形便無從把握,這對于從市場的角度去促進話劇發展顯然不利。當前是新媒體戲劇評論的“多元主體時代”。“就評論主體來說,有三個明顯的變化:一是由于傳統紙媒積極開通新媒體平臺,一些專業研究者、學者開始介入新媒體戲劇評論,他們的聲音被更多的讀者觀眾所接受;二是文化機構、企業和媒體工作者更為積極地利用新媒體平臺,傳播業內演出信息,進行戲劇推廣;三是評論主體的多元化格局已然初步形成:出現了更多的專業人士以及自媒體戲劇評論人主持的微信公眾號”。[4]河南話劇評論的發展亦需提到日程上來。可以從劇評中了解觀眾的興趣點,把握不同的形式如悲劇、喜劇、歷史劇、現代劇、翻譯劇對于觀眾的吸引程度,而且通過大數據展開分析研究,不同性別、年齡人的觀劇需求也都能得到呈現。在劇評的媒介平臺中,也要注意引入“學院派”批評,以深刻專業的內涵、客觀公正的立場,清新端正的文風引領學術前沿,培育提升讀者觀眾的審美力。
(二)媒介與話劇的市場化發展
話劇在告別“舉國體制”之后,從“封閉到開放,從單一到豐富,從探索到成熟,從‘等、靠、要’到自己闖市場。話劇內容的百花齊放也呼喚話劇評論的繁復多姿。報刊及新媒體在話劇發展中擔負著不可推卸的重任。高揚劇評對于話劇的影響,是遵循話劇市場發展的規律,培育話劇市場健康發展的重要途徑。可以說,中國話劇的每一個變化都連接著我們觀念的變化,都連接著這個時代的變化”。[5]越來越多的私人投資按照市場化運作形式生產的小劇場出現,數量、票房、觀眾標志著戲劇在市場運作方面的成功。近年來,隨著鄭州人對文化生活多樣性的需求增強,許多商業綜合體、書店、文藝創意園區搭建起了小劇場舞臺,不過,“朝氣滿滿的小劇場話劇市場,并不能掩蓋處于起步階段的現實。戲劇人才缺乏、觀眾基礎仍需培育、市場化運作經驗不足等問題尚未解決”。[6]近年,國家對舞臺藝術加大了資助力度,河南省推出的話劇《紅旗渠》,以及舞劇《風中少林》《精忠報國》都曾入選中宣部“五個一工程”或“國家舞臺藝術精品工程”。但是話劇市場的活力也需要民營團體的崛起,他們也要和國家資助的精品之作一道為繁榮話劇文化市場作貢獻。影響話劇市場化運營的原因很多, 但媒介傳播對現代話劇的影響尚未較好地展現。話劇要進一步深入人心,話劇市場的擴大都需要加大媒體的宣傳力度。
上海話劇商業市場在1940年代達到繁榮,媒體在其中發揮的重要作用提供了足以為今日話劇市場借鑒的經驗教訓。首先,“明星制”“流行風”“潮流化”的形成,皆是媒體促進話劇市場化的典型體現。公眾輿論在明星文化的發展流傳上,擔當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媒體評論還引領了話劇的“流行風”“潮流化”。媒介劇評成為話劇市場發展的風向標,自然地形成流行風和潮流化。如1942年上半年“伶人戲”走紅滬上、1944年的鬧劇流行。媒體評論還能有效引導話劇市場的健康發展。一方面,劇評看到了商業化對于話劇擴張觀眾市場,促進演劇職業化等方面的重要性,同時又以精英思想的話語引領劇壇,能有效避免話劇誤入商業化的泥淖。另一方面,劇評對都市商業機制引發海派話劇內部發生變化的現象,如噱頭、生意眼等加以批評。商業競爭固然能促進劇團發展,但不可避免也會帶來負面影響。媒體劇評提出“為了生意眼而向著低級趣味而努力總不是正路,恐怕還有覆沒的危險”[7]等,自然會對劇壇商業化起到糾偏、制衡的作用。還有“反映現實的程度和是否有利于改進人生理應成為評價作品藝術的標準”[8]等言論,對于防止話劇湮沒于低俗化都有著積極意義。
積極探究話劇發展的路徑符合黨為廣大人民謀幸福而提出的中國夢的宏觀規劃。同時,文化生活的豐富亦是當代都市軟實力的重要表征,關系著人們精神生活的豐富和幸福生活理想的實現。當下,市民階層的興起已經為話劇接受群體的形成提供了前提。媒介作為話劇和市民大眾之間的橋梁,與話劇、市民大眾組成互為建構的話劇生產場域。劇評雖然只是作者的觀劇感受和理論評說,但在報刊印刷媒介的推動下,卻成了建構話劇生產與演出的重要因素,必然帶來話劇現代意義和審美藝術的演變與革新,促使人們在創作與接受、媒介與話劇的多元關系中探討話劇生存與演進的軌跡。
(三)媒介與話劇審美藝術的演變與革新
話劇審美藝術的演變與革新往往最先通過媒介展現出來。劇評作為話劇與人民大眾關系的生動反映,能夠促進對于中國話劇大眾化和民族化的探索趨向深入。1940年代,因抗戰話劇不能深入民眾而展開的話劇“民族形式”論爭中,借鑒戲曲的問題已成為戲劇界的共識。從評論可以看出,話劇以加唱京戲等戲曲呈現趨于民間化、民族化的風貌。如《秋海棠》上演時,劇評清一色地對《秋海棠》京戲戲分加以好評,便是看到了京戲為話劇增加觀眾的功勞,對于1941年的劇壇《秦淮月》《錦繡天》等“伶人戲”的流行,評論直言應歸功于“京戲”的滲透。由于話劇是舶來品,不太適應長期浸淫于戲曲的國民欣賞需求,但是加入京戲后的話劇卻滿足了觀眾的欣賞需求。“伶人戲”的熱潮證明了民族化的道路才是話劇發展的正途,媒介在話劇民族化的發展中起到了推動作用。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話劇民族化的先行者焦菊隱先生創作了《虎符》《蔡文姬》《茶館》等具有民族風格、民族氣派的中國話劇。而從20世紀中國話劇的走向展望21世紀中國話劇的發展,可以肯定創造具有民族特色的話劇仍然是21世紀中國話劇發展的主要目標。田漢、曹禺等人的話劇創作正因其滲透著戲曲的藝術審美或是以戲曲的美學精神去融解西方話劇藝術而顯示出濃郁的民族特色。今天話劇舞臺上的《立秋》《戲臺》《驚夢》無不是妙用民族戲曲以增強話劇藝術感染力的典范。河南作為戲劇大省,具有深厚的戲劇傳統,產生過《程嬰救孤》《清風亭》《朱安女士》等膾炙人口的作品。相對于“戲劇大省”到“戲劇強省”的進軍,河南話劇的發展卻顯得滯后。傳統民族戲劇如何發揮自身的優勢助力話劇發展,使得話劇市場得以拓展,這將是今后編劇者努力的方向。而充分利用媒介傳播的力量,積極搭橋穿線,以作品研討會、戲劇節、作品演出等形式多頭并進拉動話劇產業,進而實現話劇和民族地方藝術的融合也是必然趨勢。以媒介劇評聚焦民族傳統和現代藝術的融合方式,擴展且創新話劇民族化的審美批評,將會極大地豐富戲劇的藝術表現、激活戲劇的藝術潛力,給中國話劇的發展帶來無限生機。
三、結語
媒介帶來的變化不僅是信息傳播領域的變化,同時折射出政治思想、社會文化和文學的變革。以媒介視角觀照話劇,關注劇評對于話劇的影響,是從政治生態環境的制約、都市大眾文化的影響以及藝術與商業的博弈等綜合考察話劇發展。而話劇市場的繁榮健康發展,以及話劇生產和審美藝術的豐富呈現,必然離不開媒體的巨大推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