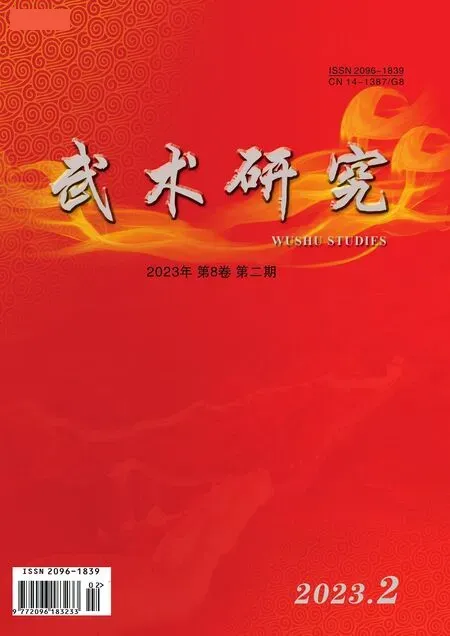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永春白鶴拳塑造新型鄉村的田野調查
張隆寧 陳云云 鄭崇德
福建師范大學體育科學學院,福建 福州 350117
1 問題提出
社會經濟大轉變時期,大多數年輕人入城打工,留在鄉村的大部分是中、老年人,思想落后,文化水平低,導致鄉村文化建設滯后,制約鄉村農民主體能動性的發揮,各鄰居之間更趨向于陌生化。[1]鄉村人心渙散,村民生活方式傾向于個性化發展,村落的傳統秩序、禮治逐漸淡化,傳統村落轉型這一問題需要長時間規劃,并切實深入去觀察村落(趙旭東,2016)。[2]2018年,國務院頒發《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提出:“鄉村興則國家興,鄉村衰則國家衰,鄉村振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鄉村發展處于大變革、大轉型時期,鄉村產業變化亟需轉型”。[3]
2 永春白鶴拳對鄉村振興建構事件闡述
2.1 集結精英:鄉村生產結構轉型
大多數村民依靠雙手自給自足,村落生產力低,更多的年輕人涌向城市,傳統文化繼承出現“斷裂”現象。[4]整個永春縣中最大的永春白鶴拳村落并不是大羽村,大羽村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不出名,鄉村很落后,大多數年輕人到外地打工,村里留下的只有老人和小孩為避免給研究對象帶來影響,在涉及地名、人名時均采用化名。該時期,大羽村發展相對落后,勞動力全面流失,村落的發展缺乏內驅動力,出現“空巢”老人、“空巢”學生現象,導致白鶴拳在傳承過程中出現斷層。1956年起,一大批出生在大羽村的海外華僑向家鄉投入資金,修建小學、大羽村公路等,大羽村的經濟發展迅速,村民的物質生活和思想觀念發生很大的改變,生活質量逐漸提升。
大羽村緊隨國家政策,將村落實際情況與國家頒布的文件《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相結合,使大羽村在2007年建立永春白鶴拳史館,2008年成為國家級非遺,吸引大量游客。部分村民由農民轉為武館經營者,由農民轉為個體戶等,使自身身份發生變化。武館經營者主要是以夏、冬令營為主;個體戶主要經營工藝品店、農家樂和土特產店等。鄉村結構轉型使村落成員又重新凝聚為一個利益共同體,以白鶴拳為核心的認同感和歸屬感產生。大羽村的生產結構未完全轉型,但不可否認,大羽村的生態環境和生活水平提高是因為永春白鶴拳史館的建立使白鶴拳獲得更多村民的支持,讓更多人練習白鶴拳。由此可見,民俗體育文化儼然成為具有交換價值的商品。
2.2 建立團體:“以武養武”手段為生
《宋記》記載:“河北州縣近山谷處,民間各有弓箭社及獵射人……”,[5]弓箭社的含義是指民間的組織,進入社的每人都有弓箭一個,箭射三十只,相當于被砍一刀,民間組織的影響力大于精英個人的力量。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需要民間組織,集體的力量大于個人的力量。周氏家族與鄭氏家族傳承者各自組建武館“以拳為生”,在傳承傳統文化的基礎上獲取利潤,由此不僅保留了文化資本還獲得經濟資本。村里大部分年輕人都出去了,留下一部分中年人和老年人,想著不能丟掉老一輩留下來的東西,所以我就想利用村里的永春白鶴拳史館為中心,村里的幾位拳師組織的團隊,并收一些徒弟,不僅可以將拳繼續傳承,還可應付日常開銷。在國家資助下,大羽村環境變化較大,不僅吸引喜愛白鶴拳的習練者還吸引大量的游客,村民利用自身所長為村落做貢獻,推動白鶴拳走出大羽村、走出永春、走入世界,通過大家共同努力,打造不知名小村落成為全國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區)。
2.3 演武活動:凝聚村民集體記憶
民俗活動是傳統文化的載體之一,滲透著個體對歷史的表達,也是人們所表現的一種符號化的形式,符號始終貫穿著人們的生活,德國哲學家卡西勒在《論人》中寫到“對于人類文化生活形式的豐富性和多樣性來說,文化形式都是符號的形式”。[6]每個人都經歷文化和社會化的過程,努力朝著符合社會發展的方向而發展。祭拜方七娘活動在大羽村舉辦,是文化的象征,是永春白鶴拳傳人充滿象征的交流體系。20世紀90年代,我們就有祭祀活動,但那時候祭祀活動大家還未聚集在一起,沒這么大的場地容納我們,都是在自家門口進行,現在大羽村建演武場,每年農歷六月二十四日聚集一起祭祀方七娘,并舉辦演武活動。
演武活動期間,常年在外的拳師、海外習練永春白鶴拳的友人以及福州鶴拳拳師(福州鶴拳是永春白鶴拳演化的拳種)等都參加方七娘祭祀活動。他們的回歸不是個人的回歸,代表著永春白鶴拳的文化從大羽村出發向城市輻射,再從城市到達村落尋根的返祖過程。不同群體的演武表演代表不同時空的拳師在同一時空下的交錯,喚醒村民集體記憶,通過祭祀方七娘誕生的演武活動,塑造以永春白鶴拳為紐帶的共同存在,強化村民和拳師之間的集體認同感,凝聚村民之間的感情。
2.4 產品開發:文化資源成為品牌
武術文化是我國獨具特色的文化資源,不同地域的環境滋養出不同的武術拳種,所以有“南拳北腿”之分。永春白鶴拳作為福建七大拳種之一的南拳,獨具特色的拳種風格受到廣大群眾的喜愛。大羽村支部成員對國家頒布的政策能夠快速精準找到定位,抓準時機,以白鶴拳為中心先后建立中國永春白鶴拳史館、演武場等,將大羽村建設成美麗鄉村,得到習總書記的認可。習近平總書記來信說道:“今年你們帶領村民們發揮資源優勢,發展特色產業,大羽村成為遠近聞名的美麗宜居村莊,我們由衷的為你們感到高興”。2008年,白鶴拳成為省級非遺后,鶴拳拳師參加國家武術節,又在2009年舉辦首屆“海峽論壇·兩岸傳統武術交流大賽”,并拍攝專題片、電影等,推動體育產業供給側改革,助力大羽村產業振興。
3 永春白鶴拳塑造新農村的鄉村振興建構啟示
3.1 多元主體參與:不同資本獲取
在參與過程中,多元主體參與具有不同職能,彼此既要競爭,又要合作,通過相互沖突和協調達成一致的目標,實現鄉村振興。[7]鄉村振興不僅需要政府的強有力支持,也需要社會各群眾團體的積極響應。2007年ZJS回歸大羽村擔任村支部書記,對政策敏銳的ZJS針對2005年第十六屆五中全會首次提出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相關文件進行解讀,認為構建新農村精神文明建設離不開政府、市場、精英和民間組織各方參與,在支部書記帶領下吸引各方人士,使大羽村成為全國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區)。ZJS擔任“領頭雁”職位,擁有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ZJY是村民公認的“熱心人”,主動宣傳鄉村振興建設,擁有一定的社會資本;ZQY是武術館館主,擁有文化資本。在他們的合力下,大羽村團隊建立成功,共分為周氏和鄭氏兩隊。大羽村的村民擁有文化資本,永春白鶴拳史館團隊抓準時機,增加新項目,獲取了社會資本和經濟資本,使自身的文化資本轉變為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吸引更多消費者,消費者通過自身感受,留下長久記憶,學習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通過文化對消費者的熏陶,展現中華文化。
3.2 強化社會規范:制定村規、家訓維護良好秩序
現代化社會沖擊,城鎮化擴張,維護鄉土社會的道德、禮俗、倫理等因素逐漸消失,村落社會秩序不斷解構,村民之間的關系淡化。[8]梁漱溟先生表示,要實現鄉村社會秩序的相對穩定,必須通過道德約束人們交往的行為,維系鄉村秩序的良序進行。[9]大羽村村頭掛著村規民約、鄭氏家訓、周氏家訓的牌匾,時刻提醒村民將武德、武訓牢記在心里。雖然鄭氏武館與周氏武館分開授徒,但村規進行約束,雙方不得侵犯對方利益,逐漸形成道德規范,在鄉村營造文明風氣。鄉村通過政府的支持,修建中華永春白鶴拳史館、美化鄉村環境,通過環境導致個人思想也發生變化。大羽村通過傳統文化為紐帶形成根基最為深厚的共同體,鄉村風氣的熏陶,道德精神內化為個體道德,村民之間的關系親近,村民的參與意識、責任感和集體感提升,村民之間團結,凝聚力增強,從而實現大羽村振興。
3.3 喚醒集體意識:儀式展演活動重構
集體意識是個人意識通過活動方式傳播,引導其他個體的行為取向。[10]秩序的生活依賴于社會成員的某種情感,人們的行為又被這種情感所控制,所以儀式在社會中就顯現得非常重要,并且這種情感一代又一代地傳承下去。大羽村未修建史館前,永春白鶴拳弟子聚集少、接觸少,鄉鄰之間趨于陌生化。史館修建后,每年6月24日在大羽村舉辦“方七娘祭祀”活動。永春白鶴拳弟子的歷史記憶通過物質載體、集體實踐和儀式操演等,在社會實踐中傳承,通過他們的觀念和行動影響下一代。儀式展演活動主要參與:儀式組織者、儀式參與者以及儀式觀看者。儀式的神秘感、民俗活動都是“他者”所關注的焦點,在村民眼中,祭拜方七娘被當作一種文化符號受到社會關注,從而更加認可村落的歷史文化,對村落文化更加自信,將文化資本轉化為文化資源,讓大羽村頗負盛名,吸引更多游客。
3.4 經濟結構轉型:構建合作型經濟共同體
村民基于個體的生存與發展,建構以白鶴拳為主的“民俗經濟”,[11]大羽村以白鶴拳驅動經濟結構轉型和民俗發展,利用大羽村的地形、氣候,打造自然生態旅游環境。大羽村由生存型鄉村轉變為景區型鄉村、白鶴拳習練者從單純的傳授者轉變為表演者、村民由勞作者轉變為個體戶,村民之間建立合作型經濟共同體,利用文化資本吸引更多文化資源,鄉村文化資源增加、知名度提升,利用傳統文化吸引游客,調整產業結構,村民發揮自身能力和智慧,將文化資源形成經濟共同體。村民主動將閑置的房屋改裝成旅社、小型超市等實體經濟以及路邊小攤,村民互相幫襯合作,使大羽村形成合作型鄉村,大羽村以白鶴拳為主開發精品功夫系列旅游路線——“學白鶴拳、嘗功夫小吃、住功夫客棧、品功夫茶道、采功夫農果”,讓游客體驗白鶴拳文化特色鄉村的魅力,在此基礎上全面推動鄉村振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