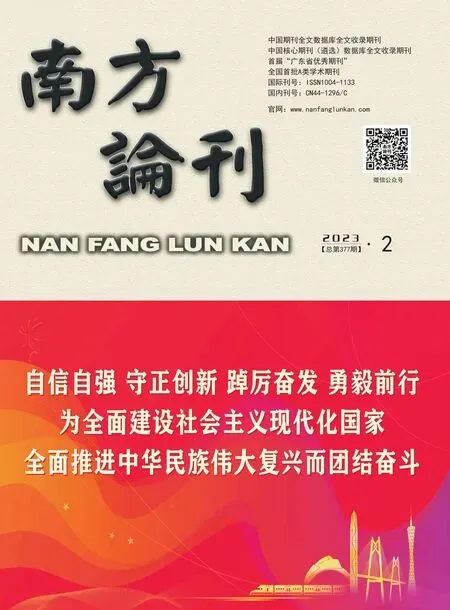農(nóng)業(yè)社會主義改造中的群眾動員:緣起、策略及啟示
汪淇
(中南民族大學(xué) 湖北武漢 430074)
農(nóng)業(yè)社會主義改造是新中國初期繼土地改革之后國家政權(quán)對農(nóng)村社會的又一次重大介入,客觀上講,農(nóng)業(yè)社會主義改造和土地改革一樣“都干得很好”[1],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共對農(nóng)民進行了深入廣泛的群眾動員,使農(nóng)業(yè)社會主義改造獲得了廣大農(nóng)民的認同和支持。
一、農(nóng)業(yè)社會主義改造中群眾動員的緣起
(一)農(nóng)業(yè)社會主義改造中群眾動員的必然性
土地改革結(jié)束后不久,隨著黨和國家中心工作的轉(zhuǎn)移,農(nóng)村又掀起了農(nóng)業(yè)社會主義改造。農(nóng)業(yè)社會主義改造的目標(biāo)是要建立蘇聯(lián)式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合作社,對于沉浸在土地改革后剛剛獲得土地自由經(jīng)營權(quán)的農(nóng)民來說,就是要將他們尚未“捂熱”的土地上交集體所有,因而,許多農(nóng)民對待農(nóng)業(yè)合作化的態(tài)度是十分排斥抵觸的。首先,農(nóng)民普遍具有根深蒂固的土地私有觀念。民以食為天,“食”以土地為源,對于農(nóng)民而言,土地是獲取生命安全和發(fā)家致富的資本,是退路和底線,他們對于土地飽含無限熱愛和眷念。其次,土地改革后農(nóng)民大多存在單干思想,總體來看,主要出于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有些農(nóng)民自家牲畜齊全,勞動力充足,雇上一個幫工便能展開生產(chǎn),所以覺得沒有入社必要。二是有些農(nóng)民認為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是各家各戶自己的事情,農(nóng)業(yè)合作化把眾人聚集在一起勞動,“樹大分叉、人多分家”,人心不齊不僅難以搞好生產(chǎn),可能還會有吵不完的架。而且他們早已習(xí)慣了自給自足、分散經(jīng)營的生產(chǎn)模式,對于入社后各方面都要受到組織的安排限制感到十分累贅。三是部分農(nóng)民認為自己土地多、土地肥,和別人的貧地、瘦地一起生產(chǎn)會吃虧,因此“懷里揣著不如手里拿著”。四是部分農(nóng)民擔(dān)心入了社,政府就知道了自家有多少畝田地、收成了多少谷子,會將剩余的糧食征收,因而害怕入社。再次,受小農(nóng)思想的影響,許多農(nóng)民目光狹窄、思想保守,對于農(nóng)業(yè)合作化的生產(chǎn)模式充滿了顧慮和懷疑。不可否認,中國幾千年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在養(yǎng)成農(nóng)民自給自足的生產(chǎn)習(xí)慣的同時也造成了他們以自己的半畝方田為中心,以收成尚能飽腹為期翼,缺乏多余的生產(chǎn)熱情和動力。他們只關(guān)注眼前利益,看不到事物的長足發(fā)展。如若做某一件事情無法立刻帶來收益,便覺得這件事情是無用的。在生產(chǎn)方式上,小農(nóng)經(jīng)濟的脆弱性造成了農(nóng)民嚴(yán)重的求穩(wěn)怕變心理,他們不敢、不愿、不輕易嘗試新的種植品種、新的耕作方式。對于他們而言,試驗并不意味著嘗試,而是巨大的冒險,一旦失敗將帶來致命的打擊。正如馬克思所述:“對小農(nóng)民來說,只要死一頭母牛,他就不能按原有的規(guī)模來重新開始他的再生產(chǎn)。”[2]最后,土地改革以后農(nóng)村生產(chǎn)開始出現(xiàn)資本主義化苗頭。列寧曾警示:“小生產(chǎn)是經(jīng)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fā)地和大批地產(chǎn)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chǎn)階級的。”[3]農(nóng)民生產(chǎn)過程中自發(fā)勢力的滋生、資本主義性質(zhì)雇傭行為的出現(xiàn)、勞動剝削、投機倒把等現(xiàn)象的錯亂叢生若不及時引導(dǎo)和制止,這些思想慢慢浸染其他成員無疑會帶來極大的社會危害。
農(nóng)民是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主體,農(nóng)民的立場和態(tài)度事關(guān)農(nóng)業(yè)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的成敗。中共中央明確指出:“全黨必須知道:沒有農(nóng)民的社會主義覺悟的增長,沒有他們的自覺的積極的參加,就不能夠有真正的農(nóng)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4]因此,推動農(nóng)業(yè)社會主義改造,充分調(diào)動農(nóng)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是現(xiàn)實的必然要求。
(二)農(nóng)業(yè)社會主義改造中群眾動員的可行性
在封建政權(quán)統(tǒng)治中,“王權(quán)止于縣政”,士紳階層充當(dāng)國家政權(quán)和底層社會的黏合劑,封建君主政權(quán)從未真正觸及底層社會,農(nóng)村處于“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的高度分散狀態(tài)。鴉片戰(zhàn)爭以后,中國開始學(xué)習(xí)西方的政治制度,開啟了現(xiàn)代國家政權(quán)的建設(shè)道路,國家政權(quán)逐漸下移。但從清末到整個民國,國家政權(quán)對于整個基層社會的控制集中于無休止的壓迫,不但未能構(gòu)建起深入完備的農(nóng)村基層政權(quán)體系,反而使農(nóng)村秩序陷入混亂。新中國成立后,農(nóng)村基層政權(quán)組織體系逐步建立,國家權(quán)力縱向統(tǒng)一于黨中央、橫向統(tǒng)一于黨組織,形成了國家政權(quán)對農(nóng)村社會的全面植入,實現(xiàn)了國家對個體農(nóng)民的直接管理。土地是農(nóng)民最關(guān)切、最直接的利益需求。土地改革的完成不僅將土地利益重新分配,而且對個體農(nóng)民進行了階級的劃分和政治身份的甄別,使其直接納入國家階級結(jié)構(gòu)的體系中,內(nèi)在地依附于國家政權(quán)和政黨意志,國家對個體農(nóng)民的直接管理進一步深入。1953年“統(tǒng)購統(tǒng)銷政策”的出臺和實施形成了國家對農(nóng)產(chǎn)品的全面壟斷和集中分配,割裂了農(nóng)民和市場的自由流通,間接控制了農(nóng)村的土地流轉(zhuǎn)、人口遷移,個體農(nóng)民對國家政權(quán)更加緊密依附。緊隨而來的人民公社化時代則將這種直接管理和控制推向頂峰。盡管這一時期國家權(quán)力對個體農(nóng)民逐步強勢的管理和控制給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的發(fā)展帶來一定弊端,但就群眾動員而言,形成了黨和國家空前的動員能力。
二、農(nóng)業(yè)社會主義改造中的群眾動員策略
要實現(xiàn)群眾動員的目標(biāo),恰當(dāng)?shù)膭訂T策略是成功的關(guān)鍵。在推進農(nóng)業(yè)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中國共產(chǎn)黨汲取土地改革的成功經(jīng)驗,在充分掌握農(nóng)民心理的基礎(chǔ)上結(jié)合具體的改革任務(wù)通過思想教育、利益關(guān)照、情感說服、政治施壓等手段有效調(diào)動了農(nóng)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一)思想教育
思想教育是中國共產(chǎn)黨始終貫徹執(zhí)行的動員形式,并且深諳此道。根據(jù)具體的建設(shè)要求和農(nóng)民的現(xiàn)實心理,黨和國家在農(nóng)業(yè)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對農(nóng)民群眾進行了以下幾個方面的思想教育。首先,新舊兩條道路的教育。土地革命完成以后,農(nóng)民中存在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資本主義道路的選擇。受自身文化水平的限制以及封建小農(nóng)思想的桎梏,農(nóng)民對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沒有清晰的了解,無法作出有利于農(nóng)業(yè)長久發(fā)展的正確選擇。為此黨中央發(fā)布文件強調(diào):“鄉(xiāng)村黨的組織在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合作社的工作,必須善于聯(lián)系社員的實際生活,不斷地在社員中進行關(guān)于社會主義(沒有人剝削人、而使大家都富裕起來)和資本主義(最少數(shù)人剝削最大多數(shù)人、而使大多數(shù)人貧窮、只有很少的人富裕)兩條新舊不同道路的教育”[5],旨在通過思想引導(dǎo)使群眾認清資本主義剝削的本質(zhì)以及社會主義道路的光明平坦。其次,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合作化的優(yōu)越性的教育。農(nóng)民具有保守重利的特點,農(nóng)業(yè)合作化是對中國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的一次巨大變革,也是對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方式和農(nóng)民生產(chǎn)觀念的極大顛覆。為此,對農(nóng)業(yè)合作化的相關(guān)政策及其優(yōu)越性進行宣傳教育,使農(nóng)民群眾了解什么是農(nóng)業(yè)合作化、怎樣進行合作化、走農(nóng)業(yè)合作化道路能夠為他們帶來怎樣的利益十分必要。中共吉林省委書記張士英曾指出:“農(nóng)村黨支部必須反復(fù)向農(nóng)民宣傳組織起來的好處,可以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廣的方法,使農(nóng)民認識到組織起來比單干能多打糧,集體經(jīng)濟優(yōu)于個體經(jīng)濟。”[6]為了獲得農(nóng)民群眾的信任,一方面,黨和國家對蘇聯(lián)集體農(nóng)莊的幸福生活和成功經(jīng)驗廣泛宣傳,生動描繪農(nóng)業(yè)集體化道路的美好遠景;另一方面,就國內(nèi)農(nóng)業(yè)集體化已經(jīng)取得的成果進行總結(jié)和報道。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農(nóng)業(yè)部發(fā)布文件介紹全國各地農(nóng)業(yè)合作社的發(fā)展數(shù)字變化以及“組織起來”后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取得的跨越式進步,以切實的成績論證了農(nóng)業(yè)合作化的巨大優(yōu)越性。此外,針對農(nóng)業(yè)社會主義改造推進過程中農(nóng)民存在的私利心理、利己主義、個人主義等錯誤價值觀,各地區(qū)集中開展了勞動光榮教育、集體主義教育、愛國主義教育糾正農(nóng)民的錯誤思想,為農(nóng)業(yè)合作化的發(fā)展奠定了思想基礎(chǔ)。
(二)利益關(guān)照
馬克思主義強調(diào),在分析社會發(fā)展的原因時不僅要考察人們的思想動機,還要看到思想動機背后的物質(zhì)動因和經(jīng)濟根源。在經(jīng)濟層面上,“小農(nóng)具有崇富、實利、保守、節(jié)儉等特點……他們一般都無追求意識形態(tài)的理想和沖動,而只追求實際的物質(zhì)利益。他們往往根據(jù)能否得到實際利益來決定自己的行為取舍”。[7]因此,對農(nóng)民的動員工作若是僅僅停留于思想層面的教育引導(dǎo)將收效甚微。
對于農(nóng)民而言,經(jīng)濟利益是最實際的利益滿足。1950年,東北局宣布貧雇農(nóng)加入互助合作組織可以享受農(nóng)貸、農(nóng)具、農(nóng)業(yè)優(yōu)良品種等扶助政策;1952年,農(nóng)業(yè)部及中國人民銀行于當(dāng)年的農(nóng)貸指示中明確指出農(nóng)貸主要以互助合作組織為對象,對于優(yōu)先組織起來者給予優(yōu)先扶助和利息優(yōu)待。這樣的優(yōu)惠政策在基層的政策實施中同樣向互助合作組織傾斜,如昆山縣一次性發(fā)放26億貸款扶持貧苦農(nóng)民加入互助合作組織;虹橋的高級社不僅享受貸款優(yōu)惠,還享有生產(chǎn)資料方面的諸多幫扶。對于社員而言,除了政策上的優(yōu)惠,在生活資源方面也受到了極大的利益關(guān)照,凡持有互助合作組織證明文件的農(nóng)民在買賣農(nóng)副產(chǎn)品時一定程度上受到供銷社的照顧。
政治利益是對經(jīng)濟利益的有力補充。在“政治掛帥”的社會氛圍下,貧富農(nóng)政治身份的劃分、入社順序的先后排列,家庭及個人的先進與落后都是社會動員的利益激勵方式。這種激勵方式不僅是對農(nóng)民政治身份的認可,對于農(nóng)民獲取經(jīng)濟利益也具有十分顯著的效果。例如,國家在發(fā)放農(nóng)業(yè)貸款、征集公糧、提供農(nóng)作物種子時,先進的家庭會受到特殊照顧,落后的家庭則相反。
對于農(nóng)民而言,加入農(nóng)業(yè)合作社最本質(zhì)的原因在于有利可圖,因而黨和國家對其經(jīng)濟利益和政治利益的雙重滿足起到了顯著的動員效果,“這是一種在交換基礎(chǔ)上的行為選擇,即規(guī)范的提供者以各種渠道和方式給予受動對象所需要的利益和需求,受動對象則以相應(yīng)的行動回報規(guī)范的提供者的期待和愿望”[8]。
(三)情感說服
情感說服旨在通過情感誘導(dǎo)達到動員群眾的目的。在初級社的動員工作中,建社干部和骨干下鄉(xiāng)以后先對農(nóng)民的思想狀況進行摸底,在了解群眾的現(xiàn)實心理以后針對具體問題同群眾進行說明解釋,初步打消他們的擔(dān)憂和顧慮,而后以家庭為單位召開農(nóng)民會議,引導(dǎo)農(nóng)民總結(jié)互助合作的成績,指出小農(nóng)經(jīng)濟的脆弱性和未來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方向,使其明白農(nóng)業(yè)合作的優(yōu)越性和必然性。在高級社的群眾動員工作中,許多地區(qū)汲取土地改革的經(jīng)驗,采取“三同”“個別發(fā)動”“組織串聯(lián)”“會議發(fā)動”相結(jié)合的方法組織動員,各地建社干部和骨干扛著米糧、被子、衣物住到農(nóng)民家里與他們同吃同住同勞動,和他們建立深厚的干群情誼。
貧農(nóng)生活艱苦、生產(chǎn)資料匱乏,因而大多能夠積極響應(yīng)黨和國家號召,總體上都比較擁護和支持農(nóng)業(yè)合作化。中農(nóng)占據(jù)農(nóng)民人口的絕大多數(shù),但由于生產(chǎn)資料尚且充足,具有強烈的私有觀念和自發(fā)傾向,對待入社始終顧慮重重、猶豫不決。針對他們的情況,各地區(qū)采取協(xié)商的形式進行組織動員。如昌黎縣在轉(zhuǎn)辦高級社時向當(dāng)?shù)刂修r(nóng)商量道:“你們?nèi)缭溉肷纾€是先吸收你們?yōu)楹茫绮辉敢猓€要等你們。”[9]面對干部們的誠懇解釋、耐心引導(dǎo),許多群眾為之動容,深切表示不入社對不起黨,對不起毛主席。
(四)政治施壓
在農(nóng)業(yè)合作化的初始階段,為了安定農(nóng)民的情緒、緩和兩條道路的矛盾,各地區(qū)基本遵循“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指導(dǎo)原則。到了中后期,隨著農(nóng)業(yè)合作化運動的迅猛發(fā)展,面對富農(nóng)以及一部分持續(xù)消極被動、頑固抵抗甚至暗中破壞的落后分子,各地區(qū)開始采取政治施壓手段,通過施壓造成農(nóng)民巨大的心理壓力,以達到個體農(nóng)民服從國家農(nóng)業(yè)發(fā)展戰(zhàn)略的目的。
從施壓的手段來看,主要有以下幾種形式。一是口頭施壓。口頭施壓是最常用的施壓手段,主要是就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和階級成分方面進行施壓,如有些地區(qū)的干部常常對單干戶口頭施壓,不入社就讓他們的地里長青草,就要提升階級成分。單干戶要求單干的本質(zhì)原因就在于他們認為單干能夠獲得更多的收成,如今單干不僅要承擔(dān)顆粒無收的風(fēng)險,還將面臨階級成分的提升,在政治掛帥的時代背景下,這樣的口頭施壓無疑擊中了單干戶的思想命脈。二是精神施壓。在動員群眾加入合作社的過程中,有些地區(qū)采取“開會熬鷹”的形式對農(nóng)民進行施壓。“熬鷹”起源于哈薩克族的一個傳統(tǒng)習(xí)俗,是訓(xùn)練獵鷹的傳統(tǒng)方式,通過不給鷹吃喝,不讓其睡覺,使其困餓,從而達到消磨其意志的目的。“開會熬鷹”就是把那些不愿意入社的消極分子集聚在一起開會,不入社就不散會。對于習(xí)慣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nóng)民而言,這種施壓方式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三是施加待遇差。在糧食統(tǒng)購統(tǒng)銷工作中,入社農(nóng)民受到黨和組織的諸多照顧,不入社的農(nóng)民在統(tǒng)購中被要求更多地派購,在統(tǒng)銷中限制供應(yīng);在農(nóng)貸、信貸中,入社的農(nóng)民享受優(yōu)惠政策,未入社的農(nóng)民受到限制和歧視。農(nóng)民的生產(chǎn)生活同國家政策緊密相關(guān),待遇的落差不僅意味著直接利益的流失,更給農(nóng)民的生產(chǎn)生活帶來諸多限制,由此造成的得不償失與許多要求單干的農(nóng)民的初衷嚴(yán)重違背,入社顯然成為了更好的選擇。
三、農(nóng)業(yè)社會主義改造中群眾動員的現(xiàn)實啟示
群眾動員工作是黨的一項極其重要的工作,是黨貫徹群眾路線、同人民群眾建立密切聯(lián)系的重要渠道。農(nóng)業(yè)社會主義改造中中國共產(chǎn)黨群眾動員的成功經(jīng)驗是黨和人民的重要財富,對于新時代做好黨的群眾動員工作,充分發(fā)揮黨的組織動員力具有重要啟示。
(一)黨的集中統(tǒng)一領(lǐng)導(dǎo)是根本
“辦好中國的事情,關(guān)鍵在黨。”[10]農(nóng)業(yè)社會主義改造是中國共產(chǎn)黨帶領(lǐng)中國農(nóng)民進行的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黨的集中統(tǒng)一領(lǐng)導(dǎo)是根本保證。一方面,黨發(fā)揮著決策和掌舵作用。針對不少地區(qū)出現(xiàn)的宣傳工作散漫、宣傳能力薄弱以及錯誤宣傳的狀況,黨中央及時充實黨的宣傳隊伍,完善黨的基層宣傳機構(gòu),要求各級黨委將宣傳工作納入黨委會議議程,與此同時,大力興辦宣傳培訓(xùn)班,培養(yǎng)宣傳干部和宣傳員的業(yè)務(wù)能力,提高他們的宣傳本領(lǐng)。另一方面,黨發(fā)揮著示范引領(lǐng)作用。農(nóng)業(yè)社會主義改造中的群眾動員以黨員干部為中心層層發(fā)動,首先打通黨員干部的思想,而后發(fā)揮他們的帶頭引領(lǐng)作用影響群眾。在對宣傳工具的領(lǐng)導(dǎo)上,黨不僅完善和鞏固了國家宣傳網(wǎng),還實現(xiàn)了對非黨宣傳網(wǎng)的全面領(lǐng)導(dǎo)。
新時代黨的組織動員工作面臨更高更嚴(yán)格的要求,更加需要堅持黨的集中統(tǒng)一領(lǐng)導(dǎo),充分發(fā)揮各級黨委總攬全局、協(xié)調(diào)各方的作用,為實現(xiàn)民族興、國家強、人民富提供強有力的政治保證。
(二)長期持續(xù)的思想教育是前提
農(nóng)民的思想具有反復(fù)性的特點,對農(nóng)民進行思想教育是一項長期持續(xù)的工程。自農(nóng)業(yè)社會主義改造伊始,針對農(nóng)民對于農(nóng)業(yè)集體化道路觀望和懷疑的態(tài)度,黨和國家對農(nóng)民新舊兩條道路的教育、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合作化的優(yōu)越性的教育從未松懈止歇;就農(nóng)業(yè)集體化不同階段農(nóng)民表現(xiàn)出的私利心理、利己主義、個人主義等錯誤思想,各地宣傳部門及時開展勞動光榮教育、集體主義教育、愛國主義教育宣傳活動。長期持續(xù)的教育繃緊了農(nóng)民心中的弦,為調(diào)動農(nóng)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奠定了思想基礎(chǔ)。
思想是行動的理性前提,做好黨的組織動員工作要充分發(fā)揮思想教育的育人功能,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地轉(zhuǎn)變?nèi)嗣袢罕姷乃枷耄鰪娙嗣袢罕姷恼螀⑴c意識,幫助他們認清自身的主人翁地位,提高他們參與國家和社會治理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三)注重心理引導(dǎo)是重點
農(nóng)民思想保守、內(nèi)心封閉,在宣傳動員農(nóng)民的過程中,掌握農(nóng)民的心理,注重對農(nóng)民進行心理引導(dǎo)尤為重要。疾風(fēng)驟雨似的行政命令能夠起到快速動員的目的,但并不能觸及農(nóng)民的深層心理,無法達到真正意義上的認識統(tǒng)一、行動統(tǒng)一。相反,春風(fēng)化雨似的引導(dǎo)說服對于農(nóng)民來說更加容易接受。農(nóng)業(yè)社會主義改造中,黨和國家推行的農(nóng)業(yè)集體化道路同農(nóng)民的土地私有心理相違背,并不為農(nóng)民主動接受。為了改造農(nóng)民的意識,獲得農(nóng)民的支持和認可,各地宣傳部門根據(jù)農(nóng)民的特點對農(nóng)民進行了一次次深入耐心的心理引導(dǎo)。由于農(nóng)民依靠經(jīng)驗生產(chǎn)生活,具有“向后看”的思維特點,習(xí)慣于在同過去的比較中尋找未來發(fā)展的方向,為此,“憶苦思甜”成為農(nóng)業(yè)社會主義改造中動員群眾的一項重要活動。通過引導(dǎo)農(nóng)民群眾回憶過去生產(chǎn)條件下艱難困苦的生活和感受當(dāng)下幸福有盼頭的生活,使其明白農(nóng)業(yè)合作化道路是農(nóng)業(yè)發(fā)展的光明前途,具有無比的優(yōu)越性;黨的決策和工作是為了農(nóng)民好,是為了帶領(lǐng)農(nóng)民走向更美好幸福的未來,因此,要感恩黨,信任黨,跟黨走。
毋庸置疑,任何一項方針政策在推行的過程中難免出現(xiàn)不同的聲音,面對那些排斥的、不堅定、不信任、不配合的聲音,在組織群眾、動員群眾的過程中,黨員干部應(yīng)當(dāng)注重對群眾進行心理引導(dǎo),了解他們的擔(dān)憂和顧慮,真心實意為他們排憂解難,以此獲得他們的理解、認同和支持。
(四)維護和保障群眾的利益是關(guān)鍵
“每一既定社會的經(jīng)濟關(guān)系首先表現(xiàn)為利益。”[11]宣傳動員工作是做人的思想工作,每一個人都是理性經(jīng)濟人,離開利益談動員只會陷入教條主義,難以取得滿意的效果。農(nóng)民具有崇富、實利的特點,他們習(xí)慣于根據(jù)事物能否獲得利益決定自己的行為取舍。農(nóng)業(yè)社會主義改造中的群眾動員能夠取得良好的成效離不開黨和國家對農(nóng)民的利益關(guān)照,不論是通過對農(nóng)業(yè)合作社進行資金、技術(shù)、生產(chǎn)資料的幫扶,對困難農(nóng)民設(shè)立貧農(nóng)貸款基金,對入社農(nóng)民實施農(nóng)業(yè)貸款、糧食統(tǒng)購統(tǒng)銷優(yōu)惠等措施直接滿足農(nóng)民群眾的現(xiàn)實利益;還是通過劃分農(nóng)民的政治身份間接滿足農(nóng)民群眾的現(xiàn)實利益,“國家的幫助”充分保障和滿足了農(nóng)民的利益需求。
人民是國家和社會治理的主體,調(diào)動人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要了解人民群眾的需求,減輕人民的負擔(dān),拓寬人民的視野,增加人民的收入,“任何時候都必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實現(xiàn)好、維護好、發(fā)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12]。
(五)滿足群眾的美好生活需求是內(nèi)在動力
對美好生活的需求是一個人的內(nèi)在驅(qū)動力。新中國初期,久經(jīng)戰(zhàn)爭磨難、飽受貧困之苦的農(nóng)民迫切要求解決溫飽問題,糧食產(chǎn)量的增長、種類的豐富是農(nóng)民深切的盼望。國內(nèi)對蘇聯(lián)集體農(nóng)莊幸福美好生活的生動描繪不時沖擊農(nóng)民的內(nèi)心,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農(nóng)業(yè)部發(fā)布文件介紹全國各地農(nóng)業(yè)合作社的發(fā)展數(shù)字變化以及“組織起來”后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上取得的跨越式進步更是令廣大農(nóng)民群眾歡欣鼓舞,許多農(nóng)民由衷感嘆,看著現(xiàn)在,想著將來,心里高興,干活有勁兒。
十九大報告指出,當(dāng)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jīng)轉(zhuǎn)化為人們?nèi)找嬖鲩L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fā)展之間的矛盾。農(nóng)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已經(jīng)由求溫飽轉(zhuǎn)變?yōu)榍蠊健⑶蟀l(fā)展、求富裕,求安身樂業(yè)、求生態(tài)良好、求政通人和。充分滿足新時代下人民群眾新的更高層次的內(nèi)在需求,是有效動員人民群眾的重要驅(qū)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