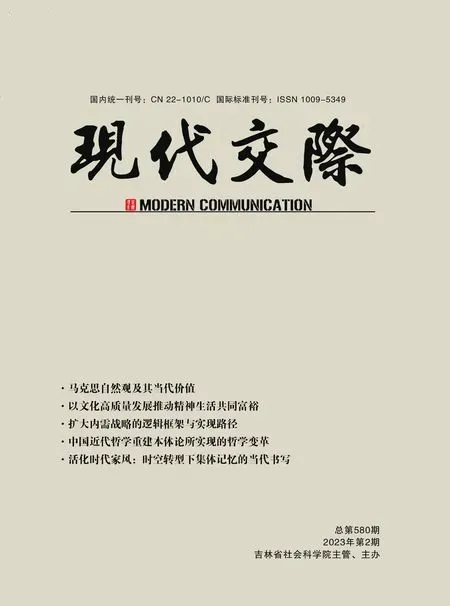中國近代哲學重建本體論所實現的哲學變革
□王友琛 杜恒義
(1.山東師范大學 山東 濟南 250358;2.中共滕州市委黨校 山東 棗莊 277500)
中國近代哲學重建本體論所實現的哲學變革問題,值得給予高度重視。中國哲學本體論雖有“天人相分”的觀點,但主流觀點是“天人合一”。明末清初至五四運動這段時期,中國哲學史進入近代哲學時期,并正式拉開了哲學變革的帷幕。其中,王船山提出的“能所”思想,標志著中國近代哲學本體論正式自覺地向類似主客二分式過渡,形成了中國近代哲學本體論的一個轉折點,正式開啟了向西方近代哲學召喚主體性原則的時期。本文在現實的維度上對中國近代哲學重建本體論所實現的哲學變革進行歷史反思,力圖證明中國近代哲學本體論向主客二分式轉變并沒有拋棄“天人合一”思想,恰恰是對“天人合一”思想的辯證超越。中國近代哲學以主客二分式重建本體論,實現了對人之主體生存的本體論觀照。同時,將本體論與認識論相結合,通過對主客二分式的認識論的吸納與轉化,實現人的主體性回歸。中國近代哲學批判繼承“天人合一”思想,借鑒西方近代的主客二分式,開辟了一條吸納并超越西方近代主客二分式的哲學變革之路。
一、中國近代哲學以主客二分式重建本體論,實現了對人之主體生存的本體論關照
本體問題,就是“人生在世”的結構,即人與世界萬物的關系,是中國哲學的基礎和核心。中國近代哲學是對先秦哲學、秦漢至明清之際哲學的繼承和超越,其所實現的哲學變革是本體論的根本變革。這種變革不是全盤移植西方近代哲學本體論,而是以中國哲學本體論為“體”,以西方近代哲學本體論為“用”,使本體去蔽于主體改造客體的現實實踐之中。哲學使現實的人在感性活動中自覺澄明生存本質精神,是現實的人生存本質的形而上學表達。因此,哲學本體論必然體現著人的主體邏輯,必須自洽于人的現實感性生活。然而,中國哲學在近代之前卻試圖用“天”壓人,不可避免地將脫離人的主體性的抽象“天人合一”為本體,忽視了主體本身在客體改造中的作用。中國古代哲學在明清之前停滯于“前主客體關系的天人合一”,構建的是全面壓制人的絕對命令,因而限制了人的認識活動和實踐活動。中國近代哲學就是要批判傳統的“天人合一”思想,推翻“天”對人的統治,破除對抽象之“天”的盲目崇拜,從而確立人在感性世界中的現實生存方式。可以說,中國的“天人合一”思想雖具有不可忽視的先進性,但也具有不容掩蓋的缺陷。倘若不對此進行批判,必然會忽視對人之主體生存的本體論觀照。
嚴格意義上來講,西方近代哲學的主客二分式思想發端于柏拉圖的“理念論”。明確地將哲學主導原則導向主客二分式,則是西方近代哲學的創始人笛卡兒。當然,笛卡兒的哲學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沒有進入主客二分式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因素,將“神”作為世界萬物的共同本根。黑格爾提出的“絕對精神”使主客體實現了最高階段的統一,是西方近代哲學主客二分式的集大成者,但他的“絕對精神”也上升到了世界萬物之最終本根的高度,體現了人與世界相通這一人類精神的最高形態。總而言之,從笛卡兒到黑格爾,西方近代哲學雖時有體現沒有進入主客二分式的“天人合一”思想,但其根本原則仍是主客二分式。中國近代哲學的變革同樣表現為“主體性哲學”轉向,但與西方早期自然哲學的轉向又有著本質的差別。相較于西方早期自然哲學主體性轉向的內生性,中國近代哲學則是借助于外在力量,在吸納西方近代哲學主客二分式的現實過程中生成了“存在者之為存在者”的人本邏輯,實現了向人之現實生存的回歸。在先秦哲學時期和秦漢至明清之際的哲學時期,中國哲學各派一般不關注主體和客體以及思維和存在何者是第一性、何者是第二性的問題,完全混淆了主體和客體之間的區別,否定了主體與“天”這個存在的本體論關聯,因而世界之本體是與人無涉的超感性存在。先秦哲學和秦漢至明清之際的哲學雖肯定主體和客體之間的同一性,卻忽視了兩者之間的差異性,導致主客不分,造成本體論與認識論的嚴重脫節。可以說,只有揭示主客體之間的對立,才能從中轉向本體論的主體邏輯。如果對主客體之間的對立沒有清晰而全面的認識,必難以轉向本體論的主題邏輯。在進入中國近代哲學發展時期之前,中國哲學較為缺乏本體論的主體邏輯,某種意義上對中國哲學發展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阻礙。中國近代哲學在國內外環境發生明顯變化的情況下,對中國哲學幾千年來的舊哲學傳統進行了歷史性變革,在現實的外在推動下引進西方的主體性、個體性和科學精神,打通了哲學變革的基礎性環節,產生了極為深刻而長遠的影響。
然而,主體性的引進并非本體論變革的完成,借鑒西方近代哲學主客二分式僅是中國近代哲學本體論變革的開始,絕不是中國近代哲學本體論變革的結束。中國近代思想家不是在抽象主客體關系的超感性范疇實現哲學變革的,而是在破立并舉中逐步實現哲學變革的。如果中國近代思想家沒有在破立并舉中逐步實現哲學變革,中國近代哲學的重建本體論之路就會有走“彎路”的危險和可能。對于這一點,我們不能有錯誤認識。因此,我們既要肯定主體的能動地位,又要看到其發揮作用的社會歷史性,以及物質條件、政治條件和精神條件等對其的影響。主體活動的現實性和具體性歸根到底是由社會生產關系所決定的,這也就是中國近代哲學確立主客二分式的長期性與階段性。換句話說,主客二分式是建立在社會生產關系的基礎之上的,脫離了現實的社會生產關系就有異化為抽象主觀意志的可能。因此,中國近代哲學主客二分式的確立經歷了在漸進中實現突破的過程,絕不是一蹴而就的。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涌現出一大批向西方學習的先進思想家,從譚嗣同主張對“我”與“非我”進行區分,到梁啟超大力推崇笛卡兒和康德的主客關系學說和主體性哲學,再到孫中山通過“精神物質兩元論”宣揚主客二分思想,都無不體現了西方近代哲學主客二分式在社會生產關系變革中由淺而深地融入中國近代哲學的客觀過程。從根本上來說,在小農經濟走向解體并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的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不充分也是客觀事實。因此,中國近代哲學史上先進思想家通過引進西方近代哲學中的主客二分式以及與之相聯系的主體性哲學重建本體論的速度,并沒有也不可能超越社會生產關系的根本制約,而是與社會生產關系內部結構的矛盾變化速度保持總體一致。
二、中國近代哲學將本體論與認識論相結合,通過對主客二分式認識論的吸納與轉化實現人的主體性回歸
本體論的變革必然會催生認識論的變革,中國近代哲學變革不僅借鑒西方近代哲學重建本體論,同時也包含著對本體的批判,而對本體的批判是以認識論的變革為前提的。中國哲學在明清之前追求本體的絕對化,并將其作為世界萬物生成和發展的根本依據,哲學的主體性被掩蓋因而變成脫離主體的形而上學。本體作為人與世界關系的終極依據是絕對性的存在,但本體作為主體認識活動的現實依據卻具有相對性。作為一種既有絕對性又有相對性的辯證存在,本體及其內在矛盾運動需要主體進行揭示。中國哲學在明清之際以前因不重視認識論而壓制了哲學的本體論批判本性。沒有將本體論和認識論聯系起來,故中國哲學一直缺乏主體性。在明清之際以后,中國哲學在重“氣”的基礎上,在吸納主客二分式的過程中,開始關注哲學的主體性問題,這才使得認識論與本體論在中國哲學中實現了結合。
在明清之際,中國哲學認知論與本體論的結合主要走的是以“氣”否“理”的哲學變革之路。王船山是提出主客二分式認識論的第一人,他明確反對有脫離“氣”而存在的“天理”。在這一過程中,作為主體的人被呈現出來,中國哲學發展正式開啟了向認識論偏重的歷史。王船山指出,“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謂之道之器也”[1]。據此,王船山把“天理”劃入人欲之中,否定脫離人欲之外的抽象“天理”。雖然王船山基本是從存在論上講天人合一的思想,“天與人異形離質,而所繼者惟道也”[2],但他卻明確提出“能所”的認識論觀點,破天荒地在中國哲學史上明確提出了較為明確的主客二分思想。他指出,“有即事以窮理,無立理以限事”[3]。他構建了較為系統的認識論,開始挑戰中國哲學在明清之際以前的輕主體偏向,拯救出認識論并使其成為人類生產生活方式的認識論,而且通過強調認識論,使中國近代哲學本體開始具有了呈現出客觀規律的實踐形態。與王船山一脈相承,顏元也試圖將朱熹“理在氣先”的形而上學拉回人之現實生存的感性世界,強調“理氣融為一片”[4]86、“理氣俱是天道”[5],向宋明理學“主靜空談”發起了猛烈攻擊,提倡通過“事物之學”獲取具體知識。到了戴震這里,中國哲學已經有了系統的認識論。戴震從“氣”的條理變化出發,猛烈抨擊以形而上的“天理”滅現實的“人欲”的儒家傳統。戴震認為,“味與聲色不在我,接于我之血氣,能辨之而悅之,……理義在事情之條分縷析,接于我之心知,能辨之而悅之”[6]。這就可以看出,戴震對物與我進行了明確的區分,將認識論建立在主客二分思想的基礎之上。總之,明清之際中國哲學認知論與本體論的結合順勢起步,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體現了對人的主體性的尊重,標志著人的主體性的回歸,開啟了吸納與轉化主客二分式認識論的良好開端,具有極為鮮明的開創性意義。
鴉片戰爭后,受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壓迫,中國近代哲學的主體性思想進一步發展。從龔自珍認為“我”或“心”是世界萬物動力,到魏源強調“事必本夫心”“善言心者,必有驗于事矣”“善言我者,必有乘于物矣”[4]171,都集中體現了鴉片戰爭前夕中國近代哲學“事”與“心”的主客二分思想。在太平天國運動時期,洪秀全舉著基督教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旗幟,發起了打倒封建神權、封建皇權、傳統孔孟之道的農民運動,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動了西方近代主體性哲學在中國的發展。在維新變法時期,康有為在維新變法失敗之前,把“元”作為“氣”的本源,將“仁”作為“元”在人身上的現實體現和人創造一切的憑借,認為宋明理學的“天理”是“絕欲反人”的理論,為中國近代哲學的主體性思維開展提供了容納空間。譚嗣同認為,“至于原質之原,則一以太而已矣”[4]245。譚嗣同據此提出“仁”的學說,把“仁”作為“以太”膠粘世界萬物的性能,并以“仁”為依據傳播西方的自由及和平等思想,對儒家傳統特別是宋明理學中形而上的“天理”“天命”及其在地上的代言人“天子”進行了直接反對,在實際上體現出鮮明的主體性思想。嚴復認為,“質、力相推”演化而成世界萬物,強調“與天爭勝”,注重發揮人的主體性。梁啟超不僅推崇西方近代哲學家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強調人貴“能有自我”,也認同康德認識論中的主體性思想,提倡“非我隨物,乃物隨我”[7]。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孫中山強調“心”的主體性作用,將“心”作為“萬事之本源”[8],打破了中國哲學主要從道德意義上講知行的舊傳統,對“知難行易”學說進行了認識與實踐相結合的論述。在五四運動期間提出的民主與科學這兩大口號,對明清之際以后中國近代哲學家反對儒家的“天理”、天人合一,重視主客二分,總結與概括主體性,標志著中國近代哲學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可以說,鴉片戰爭后中國近代哲學的發展環境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性變化。中國近代哲學發展環境的歷史性變化,不僅給中國近代哲學發展帶來了一定的挑戰,更為中國哲學的發展帶了難得的歷史機遇。也正是趕上了這樣的歷史發展機遇,中國近代哲學的本體論革命真正突破了原有的歷史局限。在這個歷史時期,中國近代哲學在對主客二分式認識論的吸納與轉化的基礎上進一步生成了主體性,深入實現了本體論與認識論的有機結合。
三、中國近代哲學批判繼承“天人合一”思想,開辟出吸納并超越西方近代主客二分式的哲學變革之路
從五四運動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以宣揚民主和科學為起點,中國哲學伸張人之主體性的哲學變革在曲折中前進。在五四運動后,中國哲學雖面臨實現主體性發展的歷史機遇,但北洋軍閥和國民黨政府卻阻礙了中國哲學的主體性發展道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五四運動的歷史推動力,有力地推動了解放人的主體性的哲學變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哲學的主體性發展也受到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以及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這三次“左”傾錯誤的干擾。可以說,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哲學的主體性發展道路雖沿著符合發展大勢的方向向前突破,但也面臨一定程度的阻礙。這些阻礙雖然對中國哲學的主體性發展產生相應的消極影響,卻沒有根本阻斷中國哲學的主體性發展道路。在我國實行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哲學的主體性發展實現了歷史新跨越。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哲學界雖對主體性的概念還有一些誤解,卻已明確提出以主體性問題為標志,中國哲學界召喚西方主體性這場哲學變革的廣度和深度以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持續向前推進。可以預見的是,辯證繼承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思想,批判借鑒西方主客二分式,在伸張主體性哲學的基礎上超越主體性哲學,是中國哲學變革發展的現實必然。那種盲目推崇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思想的想法,不僅阻礙科學進步,使人成為自然的“奴隸”,更會淡化人們的民主意識,使人停滯于封建社會時期的思維模式。我們必須深刻認識到,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思想固然有其先進性,盲目推崇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思想,片面排斥西方近代的主客二分式,絕不是堅持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思想的正確做法,而且會在相當程度上阻礙中國傳統“天人合一”思想的創新性發展。
西方近代的主客關系式和主體性也有其局限性。在現代社會發展中,西方近代的主客關系式和主體性也造成了人被物統治的現象,使人在獲得一定的物質自由的同時,失去了原本的精神自由。而且,西方主客關系式和主體性精神也在哲學演進中呈現出階段性特征。在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強調人的尊嚴和基本權利的人文主義推動了民主和科學在歐洲大陸的輝煌發展。但民主和科學在歐洲大陸輝煌發展之后,人文主義也走向了極端,使人異化為極端自負而又全職全能的神物。其中,黑格爾從感性世界中抽象出的“絕對精神”就是一例。走向極端的人文主義主觀地將人絕對完善化,無情踐踏自然的尊嚴,成為自然的人類中心主義,導致自然對人類的懲罰和報復。可以說,西方從封建主義和神權編織的“牢籠”中掙脫出來獲得自由后,又在駕馭自然的過程中走進了“物”所編織的“牢籠”當中,從而使自身陷入不自由的狀態。這就要求克服極端的人文主義的弊端,防止出現人與自然絕對對立的惡劣局面。否則,不僅會對人類社會發展產生影響,也會損害自然界的協調發展。為此,以海德格爾等為代表的哲學家就對走向極端的人文主義進行批判,并對與之相聯系的主客關系式和主體性哲學進行了反思。海德格爾批評在人類中心主義下以君臨之勢對待自然的現代人,指明了“現代人的無家可歸”[9]。人與萬物的融合是第一位的,主客關系是第二位的,西方的問題就在于把人作為主體來認識和改造客體放到了第一位,卻對人與萬物的融合缺乏應有的重視。可以說,人與萬物的融合是將人與主客二分的前提。只有將人與萬物的融合放在第一位,才能科學地將人與萬物進行主客二分。對于這一點,我們應該具有超越感性的理性認識。
由于在明清之際以前中國哲學存在長期缺乏主客關系思維方式和主體性哲學的“落后”問題,又面臨規避現時西方哲學在國際市場和國際思潮沖擊下出現的將主客關系放在第一位的問題,中國哲學面臨著雙重任務。一方面,我們要直面中國的“文藝復興”較之于西方晚發生幾百年的歷史現實,強化科學思維和民主意識,推動人的主體性發展,趕超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如果我們不能直面中國的“文藝復興”較之于西方晚發生幾百年的歷史現實,就不能正確認識到為什么要實現人的主體性發展以及如何實現人的主體性發展等問題,就難以成功地推進中國近代哲學的本體論革命。更進一步講,中國近代哲學的發展必須符合世界哲學發展潮流,而不能絕對獨立于世界哲學發展潮流之外。如果不能成功地實現主體性發展,中國近代哲學就沒法沿著符合世界哲學發展潮流的方向正確發展。中國近代哲學如果沒有與世界哲學發展潮流有機融合,不僅會直接損害中國哲學的健康發展,更會間接地對中華民族的發展產生相應的消極影響。另一方面,我們不能主觀局限于西方的歷史腳印,用幾百年的時間走完西方主客思維方式和主體性哲學之路,等它出現弊端后,再接著補上西方現當代“后主體性的”哲學之課。西方主客思維方式和主體性哲學變革的道路固然值得借鑒,但盲目照搬西方主客思維方式和主體性哲學變革的道路也不可取。如果盲目照搬西方主客思維方式和主體性哲學變革的道路,不僅有沒法成功重現西方主客思維方式和主體性哲學變革的道路的可能,也有使中國哲學發展道路失去中國特色的危險。因此,我們應當立足中國傳統“天人合一”思想之萬物一體的高遠境界,將中國傳統的“天人相分”思想和西方主客關系思維方式補充到中國哲學框架之中,使中國哲學跨越西方哲學發展的“卡夫丁峽谷”。總而言之,將中國“天人合一”思想與西方主客關系思維方式辯證聯結,是中國哲學變革的必由之路。試看未來中國哲學變革之路,必將是融會古今、貫穿東西的超越式發展,從而在積極進取的精神占統治地位的哲學形態與自由豪邁的精神占統治地位的哲學形態的辯證融合中呈現出鮮明的中國特色。
總而言之,中國近代哲學重建本體論,是中國哲學史上的一場深刻革命,開辟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哲學變革道路,值得給予應有的關注。當前,學界對中國近代哲學重建本體論所實現的哲學變革研究雖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為我們開展相關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借鑒,但目前學界對該問題的研究也存在一些較為薄弱的地方,仍需結合時代發展的具體條件進一步推進。如中國近代哲學為什么會發生哲學變革、中國近代哲學是如何發生哲學變革的,以及中國近代哲學變革會產生什么樣的現實影響等問題,都需要結合具體實際進行深入探討。這就要求我們結合中國哲學發展的最新實際,對中國近代哲學重建本體論所實現的哲學變革進行進一步的歷史回顧與現實反思,對其進行深化理解,不斷深化對哲學變革歷史發展的規律性認識,拓寬推動中國哲學實現革命性變革的現實道路,從而引領中國哲學變革在繼承和超越的辯證統一中開辟哲學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