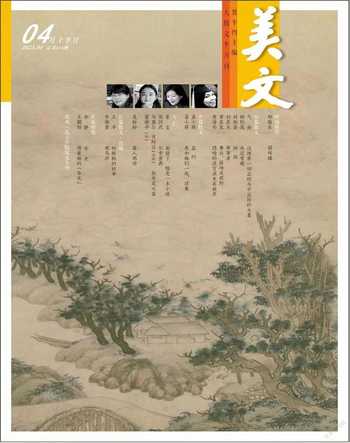這埋葬一切正經與不正經的大墓
弋舟
盛夏黃昏,那館遠遠望去竟略有秋意。這館,因著一個人的大墓而建。此刻,公元2022年的夏天,我從長安而來,防疫管控部門的電話,正如影隨形地追著我跑。而這大墓的主人,在公元前74年的初夏,從山東起身奔赴長安,去做西漢在位時間最短的一任帝王。時隔2096年的這一來一往,被我在心里面數算出確鑿的時距,當然不是出自妄比帝王的狂悖,僅僅是,大疫當前,作為一個卑微的生命,我不由得要在浩渺的時空面前恍兮惚兮。
彼時,大漢的這位繼任天子18歲。他是那位彪炳千古的漢武帝之孫,四五歲時,就做了西漢的第二位昌邑王,幼童嗣位,在世俗的價值體系中,是榮光與尊崇,是老天爺的褒賞,而在最為樸素的人倫世界里,卻是不折不扣的倒霉事兒,簡單地說,就是“打小沒了爹”。伏筆就此埋了下來——他在18歲的那一年,既要榮光尊崇地打馬入朝,承襲皇帝的尊號,又將倒霉地在短短的27天里,被權臣例數出萬般罪惡,僅征索物品一條,就多達1127起。27天,1127起,同樣是數字所記載下的歷史,真相卻全然失去了意義,所表征著的,只是人類抽象而虛妄的本質。
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這人,這18歲時做了27天皇帝的人,無端地總令我想起那位含玉而生的公子哥兒。不錯,他與賈寶玉,堪可在太虛幻境里彼此映照。甚而,他們那一派天然的頑劣,都各自在虛空中發出令人似曾相識的哂笑。相對于那煌煌歷史的“正經”,他們的價值與意義,卻全然在于“不正經”,他們反向而行,渾沌地躲避著日鑿一竅的巨錘。屬下日復一日地向他諫言,讓他還是正經點兒吧,正經點兒吧,終有一日,他掩耳走掉,撂下一句:“郎中令真會使人羞愧。”你瞧,他沒有發飆,沒有巨錘回過去砸爛聒噪者的狗頭,而是逃遁一般地捂著耳朵跑開,用一種“不聽不聽我不聽”的態度,遠離那“正經”的勒索。他知道“羞愧”了,但他拒絕這種感受,拒絕一切以“正經”之名讓人惶惶不安的壓迫。
他全無階級觀念,沒完沒了地賞賜仆役,和下人們吃喝玩樂,正正經經地盤剝,不正正經經地揮霍。“正經人”又來勸諫,雙膝跪地,低聲哭泣,周圍侍候的人都被感動得直落淚。于是,王與臣的一番對話,盡顯正經與不正經之真諦。
他道:“郎中令為什么哭?”——不,他不是裝傻,他是真的不曉得。
正經人回答:“我傷心國家危險啊!希望您抽出一點空閑時間,讓我把自己愚昧的意見說完。”——多正經,大事要小說,要私下里說,要避諱著說,要自認愚昧地說。
這樣啊,好吧,他叫周圍的人避開。
正經人問:“大王知道膠西王不干好事因而滅亡的事情嗎?”——明知故問,欲擒故縱,這才是正經的套路。
他說:“不知道。”——或者,他是知道的,但在套路里,人也難免跟著套路起來。
于是,正經人便開始口若懸河,所舉之例,從“正經史”中任意截取一段,都大差不差。最后,正經人推薦一批正經人與大王一起生活,坐時就一道讀讀《詩》《書》,立時就共同演習演習禮儀。他同意了,跟一群正經人呆上幾天,再把他們統統趕走。就是這樣,他能夠流暢地穿行于正經與不正經之間,間或給正經一些面子,然后,重新回到不正經里。
這樣的一個人,創下大漢皇帝最短的在位記錄,還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六月癸巳日,他混了27天,搞出成千上萬條罪過,在史書上以“漢廢帝”之名,被廢為庶人,重新打馬回了故地。
公元前74年7月18日—8月14日,這27天,在整部“正經史”中實為絕唱。那是一個不正經的人不給正經面子的27天,是全部的正經以數算不正經來自詡何為正經的27天,是歷史難得的、渾沌的27天,是人如何與龐然大物周旋而生發出可能性的27天。竊以為,那也是賈寶玉在大觀園中于夢里翻云覆雨的一天。
這個不正經的人遭到了廢黜,被從正經的世界驅逐了出去,依然還是要蒙受忌憚。新帝即位,派人密查他的行止,密使分條稟奏,說明他的廢亡之狀:奴婢一百八十三人,關閉大門,開小門,只有一個廉潔的差役領取錢物到街上采買,每天早上送一趟食物進去,此外不得出入。一名督盜另管巡查,注意往來行人,用故王府的錢雇人為兵,防備盜賊以保宮中安全……
后來,他二十六七歲了,在密使的眼里臉色很黑,小眼睛,鼻子尖而低,胡須很少,身材高大,患風濕病,行走不便,穿短衣大褲,戴著惠文冠,佩玉環,插筆在頭……
沒辦法,他還得和正經人一次次對話。
正經的密使又來了,兩人坐在庭中,正經人想用話觸動他,觀察他的心意,話術從鳥兒開始:“昌邑有很多梟啊,呵呵。”他答:“是啊是啊,以前我西行到長安,根本沒有貓頭鷹。回來時,東行到濟陽,就聽到貓頭鷹的叫聲了。”繼而,他跪著稟報了家屬的情況,盡管他還有著十六個妻子,二十二個兒女,但在正經人看來,已然“白癡呆傻”,幾近正經了。
在這一次次看似正經的對話中,盡管,他唯唯諾諾,但是可能還會在一些時刻,不正經地想起自己封國為王的那些日子:那時候,他常常見到不正經的玩意兒。他曾看見白色的狗,身高三尺,沒有頭,脖子往下長得像人,還戴著方山冠;他看到熊,可是他的左右隨從卻誰也沒看到;有成群的大鳥飛集于宮中,他問這是怎么回事,被正經人教導說:“這是天帝的告誡。”他仰天說:“不祥之物為什么總是來啊!”內心卻發出了對正經世界里正經的勸喻方式的嘆息。
他貌似正經了,便避開了兇險,公元前63年,他受封海昏侯,食邑四千戶,四月壬子日,前往其封地海昏就國。幾年之后,他口不擇言,又一次輕度不正經,食邑被削為三千戶。公元前59年,封侯四年之后,他死在了自己的33歲。
海昏,漢代設置的縣,為漢豫章郡十八縣之一。現在我立于此地,不由得再次感嘆漢語的奇妙。那個死在了33歲的不正經的人,你難以想象,除了成為一個海昏侯、除了葬于此地,神州茫茫,還有哪塊土地是合適他的?海,昏,這兩個漢字,就是你想象這個人一切的能指與所指,多加闡釋,既無必要,亦無可能。它在大地上具體的位置處于江西省北部,范圍大致包括南昌市新建區北部、永修縣、安義縣、武寧縣、靖安縣、奉新縣。
2016年3月2日,歷經數載考古發掘,位于此地的一座漢代大墓的墓主,得以確認。內棺被打開的那一刻,歷經2000多年,墓中人只剩下了依稀可辨的些許遺骸殘跡,專家在其腰部位置,發現了一枚凸起的小物件,方形,似玉。謹慎地提取出這枚小物件,專家最終確認這是一枚玉印。玉印上,清晰地篆刻著“劉賀”兩字。
沒錯,是他。劉賀,大漢帝國在任最短的皇帝,第一代海昏侯,那個2000多年前的不正經的人。
他在死后還不正經地和這個世界周旋著。“大凡漢墓,十室九空。”但是,他成功地繞開了2000多年來世道人心對他的覬覦和偷竊,躲過了大水,躲過了地震,躲過了大湖入江、滄海桑田,躲過了歷朝歷代盜墓者打下的孔洞,讓自己的埋葬之地,成為了中國迄今發現的保存最好、結構最完整、功能布局最清晰、擁有最完備祭祀體系的西漢列侯墓園。
大墓如今已是考古博物館的規制。“甲”字形大墓中,大型實用真車馬陪葬坑中清理出了大量的青銅器和車馬器,還有20匹馬的遺骸殘跡;主槨室,回廊,衣笥庫,隨葬品按照不同的功能被放置在了外回廊藏閣的各個區間,每個藏閣中的物品都堆積如山:編鐘、銅鼎、寶劍、伎樂俑、竹木器、漆器、廚具、錢幣、陶器……凡此種種,既是塵世之富貴,亦是人間之疾苦,是一切的正經與不正經,也是一切的實在與虛無,有如魯迅先生將一部史書統歸為了“吃人”二字,這一切,也只寫下了“荒涼”——荒唐,荒誕,凄涼,悲涼。
此刻,立于博物館的階前,我舉目四望,在這疫情肆虐的盛夏黃昏,倏忽記起,95年前,就是在這塊土地上,終于有一群人,打響了那埋葬一切“吃人”與“荒涼”、一切正經與不正經的第一槍。
(責任編輯:馬倩)

弋 舟 當代小說家。曾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獎,第三屆、第四屆郁達夫小說獎,首屆中華文學基金會茅盾文學新人獎,第二屆魯彥周文學獎,第六、七、八、九屆敦煌文藝獎,第二、三、四、五屆黃河文學獎一等獎,首屆“漓江年選”文學獎,2012 年《小說選刊》年度大獎,第十六、十七屆《小說月報》百花獎,第四屆《作家》金短篇小說獎,2015 年《當代》長篇小說年度五佳,第十一屆《十月》文學獎,以及《青年文學》《西部》《飛天》等刊物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