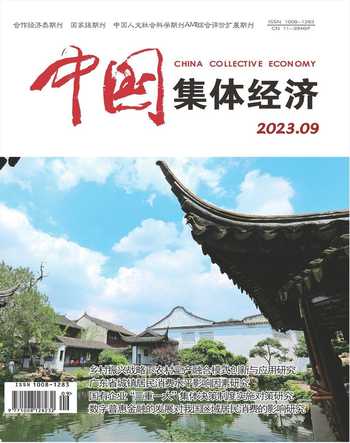消費者困惑對品牌至愛的影響研究
季星成 覃慶莉




摘要:企業會通過各平臺向消費者傳遞自己的產品信息,在這一過程中,消費者可能會由于產品信息的模糊等問題而導致困惑,進而影響消費者對品牌的感受。為此,文章研究將購買意愿作為中介變量,消費者涉入度作為調節變量,構建消費者困惑對品牌至愛影響的研究模型,并通過PLS-SEM對模型進行檢驗。結果顯示,消費者涉入度正向調節了購買意愿在消費者困惑和品牌至愛之間的中介關系,并依據這一研究結果提出了相應的品牌策略。
關鍵詞:消費者困惑;品牌至愛;購買意愿;消費者涉入度
近年來,由于通信技術的不斷成熟,企業可以通過更多渠道為消費者傳遞更多的品牌以及產品信息,然而信息本身不可避免地存在相似、過載和模糊等問題,這些問題阻礙了消費者作出購買決策,消費者困惑的出現情況也愈發增加。國外也以此作為切入點,研究成果也愈發豐富,但是當前國內關于消費者困惑的研究視角相對比較單一,成果數量較少,本文也從這一視角出發去進行后續研究與分析。
一、文獻綜述
(一)消費者困惑
消費者困惑是指消費者“在信息搜索過程中未能正確解釋產品或服務的各個方面”,這意味著一概念會讓消費者對市場產生誤解(Turnbull,2000)。依據Mitchell(2005)提出的概念框架,消費者困惑大致分為三類:相似性、過載性和模糊性困惑,可以理解為過相似、過多或不明確的信息。
相似性困惑是指“消費者由于感知到產品或服務的物理相似性,進而做出錯誤的品牌評估”(Mitchell,2005),這種困惑可能來自營銷者或消費者的領域(Walsh,2007)。過載混困惑被定義為“當消費者接觸到超過自身處理能力的產品信息時,為了評估替代品并做出決策過程中所遭遇的困難”(Walshl,2007),消費者在評估過程中接觸的產品屬性越多,決策就越困難(Cheng,2018),最終對自己的決策失去信心(Allan,2015)。模糊性困惑被定義為“消費者對于信息的理解不夠充分,迫使其重新評估和修改對產品或當前購買環境的一系列假設”(Mitchell,2005)。這類型困惑是由于不清楚、不一致或誤導性的信息所導致(Wang,2013),同時此前有學者發現,當消費者掌握的知識難以處理這些過量信息時,過載性困惑也會隨之加重(Gursoy,2003)。
(二)品牌至愛
品牌至愛是Carroll(2006)創造的一個術語,用于描述“滿意的消費者對品牌的熱情情感依戀程度”。通過對此前文獻的整理,雖然品牌至愛的概念仍然處在發展階段(Hegner,2017),但已有研究將積極的品牌情緒、評價、激情和情感確定為品牌至愛的心理維度(Batra,2012)。Ahuvia(2008)將品牌至愛的概念化為三個方面:第一,認知性品牌至愛,即與品牌相關的信念;第二,情感性品牌至愛,即與品牌相關的情感總和;第三,期望性品牌至愛,即愿意在品牌上花費資源和使用品牌的期望。此后,Rauschnabel(2014)又進一步將品牌至愛歸類為一種高階結構,這一結構有助于在消費者與品牌之間建立積極且牢固的關系,本研究也將從其他角度對品牌至愛進行衡量。
近年來,消費者困惑及其各維度與品牌的研究在國內逐漸增多,也被證實兩者之間存在相互影響關系,如林炳坤(2022)通過實證方法探究了消費者困惑對品牌轉換的影響機理,并發現決策延遲和轉換成本在這一過程中分別起到中介與調節作用;李英(2020)將顧客感知價值作為中介變量,研究了相似性困惑與過載性困惑對購買意愿的影響。由于品牌至愛被認為是消費者關于某一品牌的情感體驗,本研究也將消費者困惑對品牌至愛的影響機理作為切入點,在此之上構建模型,展開進一步的研究。
雖然當前國內外關于消費者困惑取得了豐富成果,但是關于消費者困惑對于品牌至愛的影響機理相對較少,缺乏對其中中介和調節效應的進一步研究。品牌至愛被認為消費者與品牌之間存在的一種積極情感關系,這種情感與人際交往相類似,當消費者產生困惑時,可能會對品牌本身產生負面情緒,這將導致其購買意愿的下降,并最終對品牌至愛產生負面影響。同時在這一過程中,消費者可能會因為涉入購買過程的程度不同,導致消費者困惑對購買意愿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并最終對品牌至愛造成影響。基于此,本文選擇消費者困惑、品牌至愛、購買意愿和消費者涉入度作為研究變量,進一步探究其中的影響關系,發掘消費者困惑對品牌至愛的影響機理,并以此為依據提出具有針對性的建議,旨在幫助企業減少因消費者困惑而遭受的損失,最終全方位構建企業品牌,以期填補這一研究領域的空白。
二、理論假設
(一)消費者困惑對品牌至愛的影響
消費者困惑可以從相似性、過載性和模糊性的角度進行衡量與分析。其中,相似性困惑是指消費者由于不同產品之間存在相似性,導致了消費者無法正確地處理信息,對品牌的選擇產生遲疑,消費者可能最終放棄選擇原本使用的品牌;過載性困惑是指消費者由于接觸到通過各種渠道傳遞過來的某品牌營銷信息過多,而自身的信息處理能力有限,導致處理信息的負擔過大,因此產生的負面情緒;模糊性困惑是指消費者難以接觸到充分且準確的產品信息,導致對品牌產品的最終評價出現偏差,在這一過程中消費者會由于接觸到關于品牌產品的過度復雜信息,進而產生出厭惡情緒。不論是哪一維度,消費者都可能對因此對品牌產生負面情緒,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H1:消費者困惑對品牌至愛產生負面影響。
(二)消費者困惑對購買意愿的影響
購買意愿一般被認為是消費者伴隨外界環境要素刺激下,對某一品牌產品的主觀看法與感受。購買意愿存在于消費者任意一次挑選品牌產品的過程中,直接決定了消費者購買品牌產品的可能性。不論是相似性困惑、過載性困惑還是模糊性困惑,都可能讓消費者在實際挑選品牌產品的過程中產生負面情緒,消費者也會因為難以獲取足夠數量的有效信息,而對品牌的選擇產生遲疑,改變其對品牌的選擇情況。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H2:消費者困惑對購買意愿產生負面影響。
(三)購買意愿對品牌至愛的影響
Carroll(2006)認為當一個客戶對產品的滿意度處于較高水平時,更有可能重復他們的購買行為,從而表現出更高的品牌忠誠度。Mody(2019)也得出過類似的結論,認為當某一品牌產品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時,消費者會對該品牌產生一定程度的依戀、情感聯系和忠誠,這種忠誠和積極內涵體現了品牌至愛。因此本研究認為,擁有良好購買意愿的消費者將對該品牌產生更強烈的情感依戀,即更高水平的品牌至愛。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H3:購買意愿對品牌至愛產生積極影響。
(四)購買意愿的中介作用
S-O-R(刺激-機體-反應)模型為消費者困惑、購買意愿和品牌至愛三者之間關系提供較好的切入視角。依據S-O-R模型,在最初的刺激(S)階段,消費者由于受到包括信息復雜和過載在內的外界因素刺激,因而產生消費者困惑這種主觀情緒,使得消費者的心理環境發生改變。而在最終的反映(R)階段,消費者關于品牌態度和行為的最終反應便是“消費者對于品牌的依賴程度”,即品牌至愛。購買意愿作為一種消費者感知和心理活動,可以體現出消費者在購買品牌產品過程中的情緒和認知,其本身可以被認為是處于機體(O)階段,因而可以在消費者困惑對品牌至愛的影響過程中起到中介作用,促成研究模型整個過程的實現。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H4:購買意愿在消費者困惑對品牌至愛的影響中起中介作用。
(五)消費者涉入度的調節作用
從本質上講,消費者涉入度是消費者基于個人喜好、偏好、興趣和需求對產品或服務的感知重要性(Kayeser,2013),增加消費者涉入度可以提高消費者對于品牌的信任程度,消費者使用認知能力評估服務的程度也同樣取決于其參與程度(Zhao,2018),當消費者具有高水平的涉入度時,消費者更愿意花費時間收集產品的購買信息,這將會減輕信息質量低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H5:消費者涉入度調節了購買意愿在消費者困惑和品牌至愛之間的中介關系。
結合上述理論假設,本研究構建研究模型,如圖1所示。
三、研究設計
(一)問卷設計與收集
為確保問卷的有效性,本研究收集一系列經過實踐檢驗的成熟量表,并依據研究內容對其進行改良,最終形成調查問卷。其中消費者困惑量表的設計主要參照Walsh(2007)、Schweizer(2005)、Mitchell(2004)和Anninou(2018)的研究成果,包含相似性困惑、過載性困惑和模糊性困惑三個部分,其中各部分均包含3個題項;購買意愿量表參照Gefen(2004)和Ba(2002)的研究成果,包含4個題項;品牌至愛量表參照Barbara(2006)的研究成果,包含3個題項;消費者涉入度量表主要參照Zaichkowsky(1985)和Mittal(1995),包含3個題項。為減少調查對象的認知負擔,提高問卷收集的有效性,問卷部分決定采用李克特五級量表法,分別為“非常不認同”、“不認同”、“一般”、“認同”和“非常認同”逐級遞增,最終形成問卷。本研究主要通過線上問卷發放進行正式研究數據的收集,并于2022年7月~8月之間完成對應數據收集,最終回收問卷358份,再剔除答卷時間過短、選項過于單一和反向題項沒有答對的問卷后,剩余有效問卷262份,有效率73.18%。
(二)信度與效度分析
本文通過對品牌消費者進行問卷調查,最終獲取到足夠的研究數據,但其中部分數據難以滿足嚴格的分布。同時,代言人可信度這一概念屬于形成性二階變量的測量模型,因此本研究決定采用PLS-SEM進行分析,旨在驗證模型假設中探索性預測的因果關系。通過SmartPLS 3.0軟件對研究數據進行分析,最終得到各構面的Cronbachs Alpha(CA)均保持在0.70以上,因此認為量表的內部一致性處于較高水平,同時Composite Reliability(CR)均保持在0.83以上,因此認為各量表間的內部一致性處于較高水平。各題項的因子載荷均保持在0.75以上,其中顯著性水平達到0.001,同時AVE的數值均保持在0.59以上,因此認為各變量之間的聚合效度良好。依據Henseler(2015)的觀點,PLS會高估因素負荷量和低估構面間的關系,因此本研究通過異質—單質比率(HTMT)來檢驗區別效度,由于該模型中各變量的HTMT均小于0.9,表明各變量間的區別效度良好,最后,各變量的因子載荷均保持在區間(0.75,0.91)之間,符合統計學的模型基本擬合標準。以上結果也表明,將購買意愿變量作為模型的中介變量具有合理性。本研究的多重共線性檢驗通過方差膨脹因子(VIF)進行,結果表明,各構面之間的VIF最大為2.532,小于5,表明各變量之間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同時通過Bootstrapping重復抽樣5000次,得到的外部權重均在0.00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綜合上述方法的計算結果,本研究認為各變量間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因此保留所有的題項。最后,Hair(2014)的研究結論,PLS-SEM無須檢驗模型的擬合優度。
(三)模型的解釋力評價
本文通過Bootstrapping進行5000次抽樣,結果如圖2所示。其中,消費者困惑的各維度,即相似性困惑、過載性困惑和模糊性困惑的路徑系數依次為0.407、0.401和0.342,均達到α=0.001顯著性水平;消費者困惑對購買意愿和品牌至愛的路徑系數分別為-0.419和-0.446,均達到α=0.001顯著性水平;購買意愿對品牌至愛的路徑系數為0.426,達到α=0.001顯著性水平,假設H1-H3成立。
(四)購買意愿的中介效應檢驗
為了檢驗H4,本研究使用Goodman、Aroian和Sobel檢驗的方式計算出z值,以此檢驗購買意愿在消費者困惑與品牌至愛之間的中介效應,具體結果如表1所示。同時計算模型內間接效應與總體效應的比率(VAF),最終計算結果等于0.285,依據Hair(2014)的研究結論,VAF在區間(0.2,0.8)之間被認為存在部分中介效果顯著。依據檢驗結果,購買意愿對消費者困惑與品牌至愛的影響關系中起到中介作用,假設H4成立。
(五)消費者涉入度的調節效應檢驗
本研究通過Bootstrapping進行調節效應的雙尾檢驗,在進行5000次抽樣后,最終得到調節效應的檢驗結果,結果均在α=0.01的水平上保持顯著,具體結果如表2所示。消費者涉入度不僅可以直接影響購買意愿,還可以在消費者困惑對品牌至愛的影響過程中起到正向調節作用,假設H5成立。
(六)研究結論
通過實證方法研究了消費者困惑如何影響品牌至愛,結果顯示,消費者困惑的三個維度,即相似性、過載性和模糊性會分別對購買意愿與品牌至愛產生負向影響,意味著信息相似、過載和模糊均可能讓消費者對該品牌的購買意愿降低,并且對品牌的好感下降。同時購買意愿變量的中介檢驗結果呈現良好,這也肯定了購買意愿在消費者困惑和品牌至愛影響關系中所發揮的中介作用,而消費者涉入度則是正向調節了這一中介作用,這也要求企業根據消費者涉入程度的不同分別采取針對性對策。
四、營銷啟示與建議
為了減少消費者困惑所造成的負面影響,發揮消費者涉入度對于品牌至愛的積極作用,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議。
第一,品牌對自身商品的信息發布需要嚴加篩選,確保消費者接觸到的信息是精練和準確,保持一定的市場調研頻率,及時了解品牌消費者對包括廣告和產品說明書在內的相關信息看法,并依據反饋調整相關信息,確保消費者可以高效獲取自身需要的目標信息。品牌在發布產品信息之前,營銷人員應該使信息內容獨特、精練和清晰,考慮到目標群體的認知負擔,讓消費者接觸到有效信息,以此來提升消費者購買意愿,提升對品牌的喜愛程度。此外品牌還應該考慮增加信息的趣味性,避免信息同質化程度過高,減少消費者的抵觸情緒,以便增加品牌與消費者之間情感上的關聯性。
第二,通過研究結果發現,購買意愿可以提升消費者對于品牌的喜愛程度,品牌的營銷人員可以通過這種關聯來與消費者進一步互動,以此影響消費者的決策過程。品牌應該為消費者提供準確且精簡的信息與個性化服務,并且及時依據消費者反饋為這些服務提供優化,以此賦予產品更多信息上的附加價值,幫助消費者更好識別本品牌的產品,優化購物體驗,進而提升購買意愿。通過這類溝通與反饋,可以強化消費者與品牌之間的聯系,從而幫助消費者產生對本品牌的喜愛情緒。企業也可以積極采取具有成本效益的廣告策略,通過多渠道向消費者傳遞品牌內涵,影響用戶的購買意圖和在線評論數量。
第三,品牌應該重視消費者涉入度的管理,以正確方式發揮出消費者涉入度在品牌至愛形成過程中的調節作用。品牌應該定期進行消費者涉入度的市場調研,通過可視化等技術手段進行分析,依據消費者涉入度的高低采取不同營銷策略。如果自身消費者呈現出高水平的消費者涉入度,企業可以將重點放在優化購買體驗上,為其提供更加個性化的服務。相反,如果消費者呈現出低水平的消費者涉入度,品牌應該對自身發布的產品信息進一步優化,確保消費者正確了解到產品情況,挑選到合適的產品,以幫助消費者更好地做出購買決策,減少因為信息原因而造成的購買意愿降低,建立起品牌與消費者之間長期穩定的情感紐帶。
參考文獻:
[1]林炳坤,呂慶華.消費者困惑對品牌轉換的影響——決策延遲的中介效應和轉換成本的調節效應[J].中國流通經濟,2022,36(05):65-76.
[2]張蓓,招楚堯,賴恒堅,馬如秋.綜合質量、消費情境與臨期食品購買意愿——價格敏感度的中介與食品安全素養的調節[J].貴州財經大學學報,2022(01):36-45.
[3]齊永智,張夢霞.新零售企業多渠道整合服務質量對重購意愿的影響——顧客涉入度的調節作用[J].中國流通經濟,2021,35(04):58-69.
[4]Hair J.F.,Sarstedt M.,Hopkins L.,Kuppelwieser V.G.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PLS-SEM): An Emerging Tool for Business Research[J].European Business Review,2014(26):106-121.
[5]Henseler J.,Ringle C.M.,Sarstedt M.A new criterion for assessing discriminant validity in variance-base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J].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2015(43):115-135.
*基金項目:廣西教育科學“十四五”規劃2021年度高校創新創業教育專項課題“中庸思想對廣西高校創新創業文化構建影響及對策研究”(2021ZJY1459);廣西教育科學“十四五”規劃2021年度高等教育國際化專項課題“廣西高等教育國際化運行機制優化與高質量協同路徑研究”(2021ZJY1646)。
(作者單位:季星成,桂林理工大學商學院;覃慶莉,廣西桂寧建設工程有限公司。覃慶莉為通信作者)